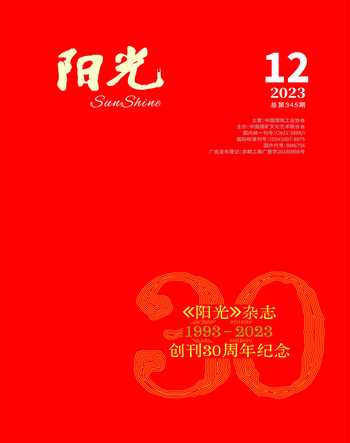文学流星雨
一
关注天体和宇宙,已经是这一代作家的必修课。这并非是说,作家都要像刘慈欣那样去写《流浪地球》,而是说,即便你写一个小小的村庄,作家本人有没有宏大视野,有没有人类意识,有没有宇宙概念,有没有星空与大地的互照,有没有对人类过往的理解和對未来社会的把握,其所呈现出来的文本和其所达到的高度,肯定是不一样的。而且,只有有了对人类过往的理解和对未来社会的把握,对当下生活的观察才更有立足之地,深邃的思考才更有安身之所。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不仅未能颠覆古老的哲学思考,反倒重新擦亮了伏羲、老子一代圣者先贤们的光辉,看天、看地、看人、看物,天体是个大宇宙,人体是个小宇宙,天人合一,这是必然。宇宙很大,人脑很小,但谁的心灵能与宇宙兼容,谁就能在这天地间通透。有时候,承认这世界很玄妙,可以很好地掩饰我们对这世界的无知。
二
不盯着地球,我们就失去了脚下的土地,无法生存。只盯着地球,我们就失去了仰望天空的能力,难获自由。当把地球放置到宇宙大背景下时,我们会莫名其妙地相信神秘的力量,人类是另一文明虚拟的游戏之说,人类因不同于地球上其他任何一种动物而极大可能并非地球上的原住民之说,正在掀翻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沉埋多年的站桩。在这样一个抉择的时代,仰望天体已不仅仅是天文学家、数理学家、物理学家的专属,不研究天体的哲学家、作家注定都不会有太高的成就。视野一旦被打开,边界便无从设置。
三
解决一个人的内心问题,文学要比科学管用得多。按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对未来的展望,参考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其创造能力,未来社会生活的面貌会急遽变化,几乎所有社会职业都将面临冲击,数十种传统职业将会消失,能够延续下来的职业和新生职业或只需少数人从事即足以胜任和饱和,机器智能的崛起和泛滥,会让人类中的绝大多数人成为“无用之人”。“人多势众”将让位于各行业精英,社会从宏观到细微的不平等不会缩小,而只会持续扩大。自然意义上的人,都将难逃激流漩涡的洗礼。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很可能需要重新寻找方向。
四
可以断言,自有文学以来,真正走到生活前边的文学并不多,最常见的景况大多是作家提着裤子,跟在生活的屁股后面疲于追赶。可以想见,但凡优秀的作家,无不时刻处于一种焦虑之中。因为衡量一个作家和一部作品的标准,始终很严苛,就看你能否用作品去兜住社会的震荡,能否用文字去咬住多变的生活,能否用思想去穿透尘世的迷雾,能否用形象去挑破人心的不古,能否用气蕴去传递性灵的美好。但纵观当下,与百年大变局相比,文学的绵软和无力,仍然欠缺在时代额头上猛击一掌的能力。众多作家只能驾着文字的一叶小舟,自鸣得意,祭出无关痛痒和浮光掠影。无论什么时候,现实都会呼吁,人类需要凌空翱翔的大作品。
五
智能机器人已经打败了最高明的棋手,相信这个不乐观应该仅仅是一个开始,接下来一定还会打败更多其他方面的专业人士。不过,即便ChatGPT已经诞生,但写作与其他行业还会有所不同,作家们仍然可以无忧。原因在于,文学是写人的,写人的命运,写人的意识,写人的心灵。痛苦和爱情的体验都是无法数字化的,所有的意识和感觉也都是难以用数字化去捕捉和转化的。数字化科技的到来,可以长驱直入,拱破固有的经济形态,但对人文形态的重塑可能仍然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在未来社会有可能成为一个巨大金属体,所有人情世故和曾经的温馨纷纷剥离的时候,也许只有作家仍有办法把一缕缕情怀,一丝丝悸动,一段段故事,像笨手笨脚的泥瓦匠一样重新糊上墙面,堵住缝隙。只是,当智能芯片可以植入人体或脑机接口,完成技术升级之后,陌生相遇的双方能够很清楚对方在想什么、要什么、干什么的时候,作家们或许会陷入前所未有的窘迫之中。写什么、怎么写、写给谁看、作品意义何在,这一系列老生常谈的问题,很可能会再次浮出水面。
六
人类文明进程的一个最大副产品,就是把人的欲望一步步从牢笼里释放出来,不仅正名化,而且不断给予其越来越高的礼遇和尊重,即使迄今为止,也仍然是人类的认知共识和普世价值。人类的欲望不可否认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本能力量,但也很可能成为最终埋葬人类的罪魁祸首。面对千疮百孔的地球和不断袭来的气候灾害,乃至生态灾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呼吁,绝不单单是一句漂亮和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人类实实在在的自救措施。放眼全球,看看那些仍然热心于地缘政治、醉心于利益博弈、故意挑拨地区纷争、不断加剧流血冲突、从而以求自己能够火中取栗的政治人物,其目光之短、气度之低、胸襟之小以及对人类危害之大便可显而易见。古人所推崇的世界大同,尽管在纷扰的现实面前,显得幼稚和脆弱,但很可能恰是正途。在能够看得见的未来,一定是命运与共,谁也别想独善其身。
七
我很愿意与学生交流,走进校园,感受青春气息。但又很怕过于强调文学,而把孩子们引入歧途。因此在合肥理工,当一千多人的学术报告厅坐得满满当当的时候,我却告诉同学们,文学并非唯一,并非生活的全部,并非我们成功的必选项。你们未来的路还很长,你们将来的故事会很精彩,相信你们未来的成就也一定会在多个领域斐然。只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热爱阅读,热爱写作,热爱文学,一定是你遇见最好自己的开始。因为我不认为文学有多么巨大的教育功能,我认为文学首要的是审美,它足以锻炼和校正你看人看事、看内看外、看远看近的眼光,让你比别人多出一副沉思悲悯的古道热肠,多出一块飘逸洒脱的心灵道场。其次,它也会让你慢慢揣摩到母语迷人的香味,体会到对母语折叠、开放、颠倒、破解、重构、变异等创造性使用的快感。
八
学科之间没有壁垒,如果有的话,聪明者就会将其打通。比如,早年的文学青年、后来成为收藏家的马未都先生举过这样一个例子:收藏学上的白釉,文学会把它描述为“甜白”;收藏学上的黄釉,文学会把它描述为“娇黄”。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学修养,断不能找到这种描述,更无法真正体会到其中的精准和意趣。这说明,具备一定的文学修养对一个收藏家来说其实十分重要。这也让我想起,某次跟一个县区的签约作家交流时,我专门为此有感而发。我说,哲学我们是学过的,历史我们是学过的,物理我们是学过的,化学我们是学过的,生物我们是学过的,生理我们是学过的,逻辑我们是学过的,可当我们去写小说时,我们却好像忘记了自己曾学过这些,并没有把这些该全部调动起来的东西调动起来。我们把小说只当成了小说,我们把文学只当成了文学。如果这点改不了,那么我们从事文学创作的苦还在后头,我们的小说作品所呈现出来的单薄和平庸注定不会改变。
九
时代,始终是一个大词,一个热词,一个永不过时的词,一个常说常新的词。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品相,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味蕾。作家可以不碰触政治敏锐话题,但其思想认知一定脱不开时代的框定。有的作家刻意不写当下,其实只是他们对当下还没有完成梳理的借口。因为要写好当下,更需要短兵相接的勇气,更需要闲庭信步的智慧,更需要准确表达的能力,更需要昭示未来的见解。当然,紧跟现实的作品,也有一时轰动,转瞬寂然的现象存在。
十
某次改稿会,有一作者写了个儿子送老人去养老院的故事。故事的起因是已经不年轻的儿子得了绝症,为的是安顿好母亲,自己去住院。因为大家庭已经四世同堂,所以安排的出场人物众多,主题却并没讲清。我以为,不如设计儿子查出绝症后,以各种理由动员老太太去养老院,并且自己主动去陪伴。进去后,老人不知道儿子的难处,养老院也不知道儿子是个重病之人。故事就此展开,不仅少了枝蔓,而且铺陈起来可能也会更深刻。小说的题目叫《尾声》,应该不算太理想,因为本来就是一个老年题材,事关临终关怀,再这么直白地用“尾声”,太过残酷,也太过悲凉。这种题材从题目到内容,一定要写出暖色來才是,否则就失去了意义。比方叫《陪伴》,可能也比叫《尾声》好。明面上,是儿子陪伴母亲,行文至后,也暗含了母亲陪伴儿子。
十一
我很早就注意到了“意公子”的视频号,并数次沟通和邀约。注意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在当下泥沙俱下的视频号中,“意公子”可谓一股清流。艺术本是小众,做这种内容从流量上说,是一种冒险。但她去掉概念,从寻常生活入手,短发,绿衫,盘腿之上压一棉软小垫,自然放松,娓娓道来,在貌似一番家长里短中挥洒出艺术浸润。这种自带烟火气的线上雅集,竟俘获了一众浮躁之心。她的文案有趣,有味,有品,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二是视频号取名“意外艺术”,很巧妙,挺好,因为越是意外才越有可能成为艺术!看新闻,知道她去年新晋全国政协委员,我觉得她配。
十二
很多人都在读苏轼,苏轼的确也值得读。作为北宋的一个“杠子头”官员,生生被逼成了千古文人。无论神宗,无论哲宗,无论徽宗,都是万变不离其“宗”。因为江山并不是他的,他只能选择乘风归去,把酒明月,起舞清影。一蓑烟雨,竹杖芒鞋,大江东去。年纪轻轻就冒充老夫,左牵黄,右擎苍,向西北挽弓,迎山头斜照。作为一身尘埃的倦客,他只任残菊傲霜,橙黄橘绿,山远云阔。他以洒脱把宋朝的山河往白头里去熬,顺带着熬出了自己不一样的人生。他制造出了很大的坡度,北宋从上面滑下来了。既然连北宋都滑下来了,那南宋也就别想再爬上去。
十三
每每翻阅历史长卷,都让我感慨古人的好奇与博宏之心,他们面对天空,面对大海,面对高山大川,思考的不单单是家国故园,而是宇宙的前世今生,甚或无尽的未来。他们的思考成果,一部分进入了哲学,一部分进入了宗教,一部分转化成了文学和艺术。即使剩下来的边边角角,也一直在民间口口相传。这也正应了大家一定耳熟能详的黑格尔的那句话:“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注定没有未来。”
十四
舆论一般习惯于批评官方的文山会海、繁文缛节、话语系统,但很少会把这种批评聚焦到文学领域。实际上,当下文学场的文字铺张和用语奢侈,几成大病。就小说文体而言,对短篇小说的地位,大家从理论上是有基本共识的,但在实践中,或骨子里,却往往又反了个个儿。近年来,我国长篇小说的创作量由过去每年的2000至3000部,迅速发展到每年七八千部之多,但真正能拿上台面,值得说道说道的,乐观估计也不会超过30部,真正能被读者广泛认可的,10部是一个大坎儿。在我看来,如果这七八千部中的大多数作品,能压缩提炼成精致的中篇,那么当下中国文学的面貌,可能不会因为长篇数量的骤减而显露凋敝之意,反而可能因质的巨大提升更呈繁荣之姿。文学的身姿,首先是清秀的,不应当虚胖,更不能浮肿,身材好的女人穿什么衣服都好看。有人说,曹雪芹没写过短篇,可他写出了《红楼梦》。但就是这部并不算太长的书,他前前后后写了十年,再看看现在的作者,有几个能有这样的耐心,这还只是说写作时间,还没论到作家的才情。
十五
读王蒙的《明天我将老去》,王蒙的确喜欢甚或说他迷恋上了“半隐蔽地告诉读者太多的事件,太多的感觉,同时它更愿意给你从感觉上猜测事件与乐趣的空间”,他让“小说解放着人,解放着时代,解放着生命”,然后让自己从故事中挣脱出来,把连接故事的筋骨打碎重揉,而且大幅度地削减来龙与去脉,独剩下一些意象,闪躲腾挪,漫笼一团诗意。王蒙自己说:“你如果高兴,你也许更愿意说它是散文、散文诗、甚至是长诗。”它的确具有小说的质地,有虚构也有梦幻,但读者却不得不牵着一根这儿断那儿连的线头,如果想还原他心中的故事大概是徒劳,因为他让你“猜”,所以最后得到的可能只是一种感觉。我想王蒙的作品是会排斥一些肤浅的读者的。但“感觉”本身不就是文学吗?所以我们只能说,王蒙是大师,他要的是大境界。看王蒙的作品,不是看不懂,只是不便于叙述,这和读残雪还不是一个概念。
十六
王妹英在她的《一千个夜晚》中,完全铺展开来,认认真真地给我们讲述主人公秀秀三年多来一千个夜晚的苦难和坚韧。在生活与生命的沉重中,引发我们的感喟和思考。杨仕芳的《谁遗忘了我们》,故事性很强,对现实的批判性更强,是个不错的中篇。但过多的巧合,对作品造成了一定损伤。这也是一个常规话题,故事性强,难免巧合的桥段就多,人为的痕迹就重,此非大作家所为。第代着冬的《魔术师》,“小小魔术团”来到沉寂的小镇,让小镇变活了,“小姨”的生活和命运随之变魔术一样地发生着变化,这就很有味道。实际上,很多时候生活就跟魔术一样,而小说本身也有着魔术的特质,作家用一块布一遮,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十七
对作家来说,必须终生致力于打造一块完全属于自己的肥沃土地,这很关键。只要有了这块土地,至于要种什么样的庄稼,都已经不重要,因为不管种什么,长势都不会太差。作家可以通过对自己一亩三分地的不断打理,借助于土地的日益肥沃和作品的不断叠加,一个专属的文学地理就会慢慢成形。
十八
真正的大家,在思想层面一定会默默向上兼容,在生活层面一般会虔虔向下兼容。大家很少说别人,尤其是说别人的不好,他们更多的是自嘲,喜欢将糗事示人,专门拿自己开涮。不太好打交道的往往是不上不下这一层级中的部分人,他们吃过苦,受过挤怼,也小有一些可以看不起人的资本,话风就很容易冒出些生硬。极个别的,甚至会给人以小人得志之感。恰恰是这部分人,是最容易顶到自己天花板的,终究只能在大家的门槛之外焦虑。《易经》的第十五卦,很值得关注,并让人引发思考。第十五卦是《谦卦》,其所组成的六爻无所不吉,且把天道地道鬼道人道皆梳理了一遍。这在《易经》中是少见的。《彖传》是这样说的:“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六十四卦中的六十三卦,皆好坏互含,唯有“谦”,无敌。莫言的父亲在莫言获诺奖后,专门嘱他一句话,说:没获奖的时候,你跟人家平起平坐,不比別人差,但获奖了,见人就要主动矮一截。可谓深得此法。
十九
一般来说,从生理上,人肯定都是在从小到大地成长,但达到一个临界点之后,心理上就会出现变化,会感觉自己在从大往小地矮缩。如果出现后面一种感觉,不必悲伤,恰恰说明你是个聪明人,已经活出了明白。作家和创作的关系也有类同,如果年轻气盛,会以为自己什么都能写,一切都不在话下。当写得多了时,即使当下正在写着的很可能是一部伟大作品,内心的忐忑也始终萦绕不去。兴奋和焦虑是作家写作时的两种常规状态,安静,孤独,沉默,则是作家阅读和思考时的惯常表现。
二十
读历史不是为了凑热闹、看故事、单纯围观、做看客、吃闲瓜,而是要把自己摆进去,让身心在重塑和还原的历史风雨中穿行,不断换位思考,推己及人,感同身受,举一反三。历史不能假设,但阅读可多做推演。事情既然这样了,就不会那样了,这是西方的一句名言,读历史书时一定用得上。说来,历史既是过往,也是当下,也是未来,这没什么区别。你不是历史主义者,同样做不好现实主义者,也莫谈未来主义。历史不会旅行,它只做前行,无论过去多少年,它都是热汤热水,新鲜如初。一如文物,每一件都不陈旧,它都在生动地讲述着属于自己的故事,所有的过往,都不过是它包浆的一部分。我们当然不会只盯着过去,那样两只眼睛会变成一只眼睛,但漠视历史,可能会很容易造成双目失明。
二十一
如何写对话,是看作家作品的一个重要指标。基础写作者往往拿对话不当回事,随手一写,让人物张口就来,然后加上引号了事。对话语是属于作品人物的,叙述语才是作家的。如果对话是白开水,不含信息量,缺少承载力,不具推动力,对勾画人物形象无帮助,最好能不写则不写,能少写则少写。有全篇没有一句对话的,也有全篇全是由对话组成的,这两种情况都少见,但值得研究。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如果小说用电视剧的对话语去写,就挺麻烦。好莱坞电影的台词倒是值得很好地借鉴。有则故事,说启功曾大病,出院后朋友们前去看望,问及身体,答曰:鸟呼了。鸟呼了啥意思?显然是:差一点就乌呼了。看到自媒体上有一则视频,妈妈问儿子,这次考试有没有不会做的题?儿子答:有,三乘七不会。妈妈问:那你怎么答的?儿子说:管它三七二十一,我答了二十八!网上有人让动物开口说话,袋鼠说:唉,兜里没钱,口袋再大也还是鼠;老鼠说:唉,成天为了点吃喝担惊受怕,能不老吗?鱼说:得了吧,打死我也不上网;乌贼说:妈的,满肚子墨水居然还是贼;刺猬说:真想感受一下与别人拥抱的滋味;奶牛说:这么多人喝我的乳汁,却没有一个人叫我妈。上面一则是真事,一则是文案,一则像寓言,文学写作至少得琢磨出这样的对话才行。
二十二
《追忆似水年华》的翻译团队很庞大,有十五个人,书名曾一度想用《寻找失去的时间》,多次争论后才最终确定下来。经典影片《魂断蓝桥》的片名,如果直译的话就是“魂断铁桥”,一字之差,可谓两重天地。可见题目的重要性。且不说小说标题,但看顾城的名诗《一代人》就知道,没有这个题目,全文只有“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两句的诗,一下就缺少了着落。作为一名编辑和主编,我给很多作者的稿件改过篇名,比如我把写成渝铁路题材的《过年》改为《大巴山的军礼》,把写男女爱情的《伟大的爱情,渺小的爱人》改为《体重秤》,把写一个姓何的女人一个姓马的女人与一个男人故事的《没出息的人》改为《何马史诗》,把河北作家的《成功史》改为《冀声冀韵》,等等不一而足。因为好的题目一定是好的作品的一部分。如果内容已经写得够好,只是题目弱了,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二十三
有个圈外朋友,不承认当下文学的繁荣,更对其质量提出疑问,放下狠话说,如果有个勤快又不识趣的人,肯拿起扫帚,到文坛上扫一扫,一定会扫出成吨的垃圾。问我怎么看,我说我会选择第一时间把他的扫帚夺下,原因很简单,我怕我的作品全部被扫掉。
二十四
萨特说,如果你独处时感到寂寞,说明你没有和自己成为好朋友。空谈容易误国,但也许空想可以养心,尤其对作家来说。但凡优秀作家,大多有着独处的习惯,胡思乱想的毛病,异想天开的灵感。想用作品愉悦人,就必得先用思考折磨自己。只有沉沉的黑夜,才最有资格作白天的前奏。作家是对夜晚浪费最少的人,也是从黑暗中攫取光明最多的人。
二十五
用汉语写作是幸福的,因为汉语能“烤”出香味。用汉语写作又是不幸的,因为在转换成外文时,香味基本会被去除。作品品质越高,语言容载量越大,歧义性越多,多义性越广,其转化的难度也就越大。对外国作家,读者较一致的观点是,看哪本书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看哪本书的哪个译本。很难想象《红楼梦》的外译本是个什么样子,单是那《芙蓉女儿诔》,谁能译好我就服谁。
二十六
早年,牛群和冯巩曾有过一个相声作品,叫《坐下说》,关键道具是一把椅子,站着说时便会冠冕堂皇,一旦坐下,就会吐露心声,内心的阴暗瞬间引爆。曲艺相比文学,好处就是可以更加直接、更加直观、更加直白,也更加轻松和俏皮,不需要“面上一套,背后一套”,直接夸张着来就行。文学讲究“绕”,越是“弯弯绕”,貌似闲话一堆,闲话不闲,草蛇灰线,水面之上三分,水面之下七分,那才有可能被叫好。
二十七
有的作品成功,但成功得很笨拙。有的作品失败,但失败得很精彩。有些成功,值得喝彩。有些失败,值得尊重。有些探索,值得鼓励。有些冒险,值得支持。所谓的突围,并非专指突破别人的重围,更在于突破自我的设障。
二十八
诗意主要是指对事物进行着色和重新赋形的能力,它意味着情感通道的另一种打开,以及由物化向精神的再一次升华。诗意会像开光一样,照亮你所要描述的物体或事件,让其聚结的情绪在语言的幽谷中难以自拔,只能缱绻氤氲,形成一种独特气场。
二十九
近年,生态文学这一概念持续走强。对此,评论家、文化学者肖云儒先生提出了“三位一体生态观”: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心灵生态。他实际是想说明,不是单纯写写山水,写写自然,就是生态文学,或说就是生态文学的全部。而人类社会,人的心灵,同样存在生态这个问题。这倒跟我的观点有点一致,因为我一直强调,一定要注意人的心灵雾霾,因为它可能远远大于自然界的雾霾。
三十
最后,跟作家们共勉:一定要超越这平凡的生活,不惧心灵漂泊。决不阻止内心的狂热,要保持对生活始终热爱,对文学始终求索,对未来始终执着。正如足球评论员贺炜的经典解说词所说,请不要相信胜利像山坡上的蒲公英一样唾手可得,但请相信世上总有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哪怕粉身碎骨。斗转星移,岁月轮转,一切自带命数。年轻的会老去,老去的会年轻,如此循环往复,造就生生不息,从而不断翻开新的篇章。没有人能阻止得了社会前进的脚步,更没人能拒绝得了思想和文化的遠航。
张世勤: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文学期刊社社长、总编辑、《时代文学》主编。作品被《收获》《人民文学》《十月》《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报刊刊载。著有长篇小说《爱若微火》、散文集《落叶飞花》、诗集《情到深处》等多部。获泰山文学奖、刘勰散文奖、团中央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