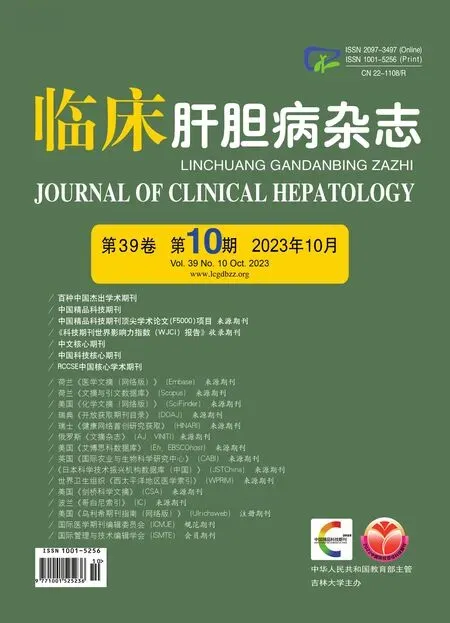血液代谢标志物在原发性肝癌治疗反应及预后预测中的应用
刘志英, 周智航, 何松
1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消化内科, 重庆 400010; 2 西安市中心医院消化内科, 西安 710000
原发性肝癌是2020年全球第六大最常诊断的癌症。预计2020年至2040年间,全球每年新发肝癌病例数将增加55%,2040年可能诊断出140万例肝癌患者[1]。据文献[2]报道,肝癌是我国第二大癌症死亡原因,因此我国肝癌负担依然沉重。75%~85%的原发性肝癌为肝细胞癌(HCC),早期肝癌患者有可能治愈,而大多数中晚期患者只能接受姑息性治疗[3]。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用于晚期肝癌的靶向及免疫疗法取得了重大进步。但即使在根治性切除或全身系统治疗后,很大一部分患者仍存在治疗应答欠佳、复发、转移等风险,导致预后相对较差。寻找可以评估肝癌治疗反应、预测复发风险或生存的预后标志物,对患者进行分层管理以增加获益和提高总体存活率,一直是肝癌预后研究的重点。本文旨在对关于原发性肝癌治疗反应或预后预测的血液代谢物研究作一综述。
1 预测肝癌预后及治疗反应的传统血液标志物
目前,甲胎蛋白(AFP)是临床最为广泛应用的预后生物标志物,AFP水平升高与HCC分期降低至满足米兰标准的患者的较低生存率、较高复发率及肝移植治疗后的较低治疗应答率有关[4]。甲胎蛋白异质体(AFP-L3)、异常凝血酶原复合物和骨桥蛋白也被报道与肝癌的较大癌结节、血管浸润、低分化等侵袭性特征有关,对总生存期、无病生存率等有很好的预测作用[5-6]。但目前它们作为生存或复发的界值设定存在争议,且异常凝血酶原复合物和骨桥蛋白并未被确定为预后预测和治疗反应评估的标志物[7]。近年来,不同形式的液体活检是肝癌预后和治疗反应预测研究的新重点,包括循环肿瘤细胞、循环游离肿瘤脱氧核苷酸和microRNA等。但面临着检测到的物质数量较少、不是肿瘤组织来源的细胞、非肝癌特有等挑战[8-9]。
2 肝癌代谢重编程和代谢组学技术
癌症代谢重编程是肿瘤细胞为适应恶劣的微环境生长所作出的改变,贯穿于肿瘤发生发展的每一阶段[10]。微环境变化也是促成癌症的关键因素,参与肿瘤恶性进展的所有过程[11]。
代谢组学用于定量检测两种不同疾病状态之间或疾病与健康状态之间的代谢物丰度差异具有强大优势,已被广泛应用于寻找肝癌监测和诊断生物标志物。苯丙氨酸、色氨酸、瓜氨酸、甘胆酸以及部分溶血磷脂酰胆碱(lysophosphatidylcholine,LysoPC)和胆汁酸在多项研究中被认为是有前景的肝癌诊断标志物[10,12-13]。早期一项关于肝癌切除术后复发的代谢组学研究[14]确定了肝癌复发的尿液代谢特征,包括增加的乳酸排泄,琥珀酸生成,嘌呤和嘧啶核苷周转,甘氨酸、丝氨酸和苏氨酸代谢,芳香族氨基酸代谢。这些特征反映出复发患者的代谢重编程表现为肿瘤细胞增殖增加、线粒体氧化磷酸化减少和氧化应激增加。近年来,代谢组学技术取得了巨大进步。质谱(mass spectrometry,MS)技术联合液相色谱(liquid chromatography,LC)或气相色谱(gaschromatography,GC)是代谢组学研究的主流技术[11]。核磁共振技术(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NMR)在近几年也被广泛应用[15-16]。
3 预测肝癌治疗反应或预后的新型血液代谢物
早期肝癌患者可以通过肝切除术、局部消融(乙醇、射频、微波)或肝移植获得治愈可能,而大多数中晚期患者只能接受经肝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放射、靶向、免疫等治疗方式[3]。治疗后的高复发率是肝癌患者预后较差的重要因素,准确的预后预测有助于临床医师制订科学合理的干预方案,改善患者生存状况以及优化社会卫生资源配置。早期有研究[14]确定了区分术后早期复发和非复发患者的5种组合尿液代谢标志物(乙醇胺、乳酸、乌克酸、苯丙氨酸和核糖)。关于预测肝癌预后或进展的血液(血浆/血清)代谢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肝切除术、射频消融、局部放射等局部治疗方面,针对中晚期肝癌的全身系统性靶向或免疫治疗相关的研究甚少。现有研究总结详见表1。
3.1 局部治疗 肝切除术是Child-Pugh A级患者的一线治愈性治疗方式,尤其用于治疗早期单个肿瘤结节[3]。近年来关于肝部分切除的预后代谢组学研究发现了一些对术后OS、DFS和复发有提示意义的血液代谢物,这些代谢物间组合或代谢物与临床特征组合的预测性能优于单个代谢物。鉴定出的血液代谢标志物大多为芳香族氨基酸、溶血磷脂、甘油磷脂、胆汁酸等,部分具有作为预后评估的代谢标志物的潜力。Wang等[17]使用非靶向LC-MS方法检测了78例HCC患者术前的血清样本,发现苯丙氨酸和胆碱是患者术后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提出了GPI评分模型(结合这些代谢物和卫星结节特征),此模型预测术后1年、3年和5年生存期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874、0.842和0.836,优于临床分期系统。该团队应用另一种方法——伪靶向GC-MS分析了相同的样本,发现苯丙氨酸、半乳糖与OS呈显著负相关(P<0.05),半乳糖、酪氨酸与DFS具有显著负相关性(P<0.05)[18]。此外,这些代谢标志物与临床指标的结合明显提高了OS和DFS的预测能力。Han等[19]分析了HCC肿瘤组织和血清的代谢状况,发现并验证视黄醇是HCC诊断和预后的有用生物标志物。随后的Kaplan-Meier生存分析显示视黄醇或视黄醛血清水平较低的HCC患者预后差于血清水平高者(P<0.001)。以上研究都是在中国人群中开展,样本量相对可观,慢性HBV感染为肝病人群的主要基础病因。此外,罗马尼亚一项对接受了治愈性治疗(手术或消融)的受试者随访3年的研究[20]发现,治疗前外周血清1,25-二羟基胆固醇、肉豆蔻棕榈酸、12-酮基去氧胆酸、LysoPC(21∶4)和LysoPE(22∶2)的水平与OS呈正相关。但这项研究样本量较少,大多数入组患者的主要病因为慢性HCV感染和酗酒。
肝移植是唯一能够真正治愈肝癌和潜在肝硬化的治疗方法[23],为了减少肝癌复发,米兰标准已成为选择目标患者的金标准。目前关于肝移植预后的代谢组学研究多集中在我国,但总体数量较少。基于血浆代谢组学的肝移植预后指纹图谱研究[21]分析显示,PC(16∶0/P-18∶1)、PC(18∶2/OH-16∶0)、胆酸和AFP是肿瘤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P值均<0.01)。据此建立的术前血浆列线图可有效预测复发风险,有助于肝移植候选人的选择。Liu等[12]应用LC-MS法对接受肝移植或肝切除术患者的肿瘤组织和门静脉/中心静脉血清进行代谢组学研究发现,门静脉血清和HCC组织中的致病代谢物包括DL-3-苯基乳酸、甘胆酸、L-色氨酸和1-甲基烟酰胺。当把单个代谢物的中位值作为队列分类的界值时,这4种致病代谢物对应的总死亡率风险比分别为3.975(95%CI:0.825~19.162)、3.975(95%CI:0.825~19.162)、3.662(95%CI:0.760~17.645)、3.487(95%CI:0.724~16.806),高于中位值的个体的OS显著短于低于中位值的个体。
射频消融是针对Child-Pugh A/B级、单个肿瘤直径≤3 cm、肿瘤个数≤3个患者的首选方案[3]。目前关于局部消融预后的代谢组学研究较少。欧洲的多中心、随机、前瞻性Ⅱ期SORAMIC试验(EudraCT 2009-012576-27、NCT01126645)的子研究[15],基于NMR方法检测了30例接受射频消融治疗(无论是否联合索拉非尼)的早期肝癌患者外周血清,发现高浓度肌醇、二甲胺患者的OS高于低浓度肌醇、二甲胺患者;高浓度的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颗粒与OS降低有关。一项意大利研究[16]对接受射频消融治疗前的28例早期肝癌患者的外周血清进行了NMR分析,生存分析显示血清酪氨酸水平是OS的预测因子。
SBRT和质子束(也称为碳离子束)是其他局部治疗失败时的一种合理选择,一般不作为单一治疗方式[3]。Ng等[22]评估了38例早期肝癌患者和9例进展期患者在SBRT后的治疗反应和代表肝脏毒副作用的Child-Pugh评分,发现包括血浆脂肪酸、甘油磷脂和酰基肉碱在内的20种代谢物在SBRT早期较基线水平有差异性上调,并能在SBRT后3个月区分完全/部分反应与无反应患者。丝氨酸、丙氨酸、牛磺酸和脂质代谢物基线水平升高的HCC患者治疗后3个月Child-Pugh评分增加最多,这可能预示临床肝脏毒性增加。
3.2 全身系统治疗 索拉非尼是一种Raf、VEGF受体、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受体、c-kit、Flt-3和RET的多激酶抑制剂[24]。过去几十年里,索拉非尼用于治疗不适合局部治疗且Child-Pugh A级的肝癌晚期患者(大血管浸润或肝外转移)[3]。但关于其治疗反应和预后生物标志物的研究甚少。欧洲SORAMIC试验的子研究[15]也对30例肝癌患者在索拉非尼(无论是否联合放射)治疗前的血清进行了代谢组学检测和随访,研究结果与早期经射频消融治疗患者一致,即高浓度的肌醇或二甲胺与OS的提高相关,而高浓度的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颗粒与OS下降相关。目前尚无关于其他靶向药物(仑法替尼、瑞戈非尼、贝伐珠单抗等)预后或治疗反应的代谢组学研究报道。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和新的系统性治疗方案已成为延长肝癌患者生存时间的有效治疗方案[25],特别是PD-L1抑制剂阿替利珠单抗联合抗血管生成剂贝伐珠单抗被批准作为晚期HCC的一线治疗[26]。TACE是无血管侵犯或肝外扩散的不可切除、直径较大/多灶性HCC患者的一线治疗方法。然而,目前基本没有关于这些方案治疗反应和预后的代谢组学预测研究报道。
3.3 重要血液代谢标志物 多项研究提及芳香族氨基酸(苯丙氨酸、酪氨酸、色氨酸)被作为预测肝癌预后的代谢标志物。酪氨酸主要在肝脏中通过苯丙氨酸羟化酶从苯丙氨酸合成,肝癌患者外周血液和尿液中的苯丙氨酸水平升高被发现与预后不良有关[27]。在肝硬化、酒精性肝炎和其他肝病的活组织检查中,发现苯丙氨酸羟化酶的活性降低。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在肝病末期,苯丙氨酸羟化酶催化反应才可能受损[27]。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循环水平升高的苯丙氨酸和降低的酪氨酸与肝癌预后的关系。但有研究[18]在肝癌患者中检测到相反趋势的代谢变化,这可能与苯丙氨酸-酪氨酸分解代谢中的谷胱甘肽转移酶在HCC中表达下调有关,而谷胱甘肽转移酶的低表达被证实与HCC患者的不良预后有关。
研究[28]发现早期肝癌与肝硬化组织中PC的增加有关,在肝癌发展的早期阶段甘油磷脂代谢可能已经失调,且磷脂量与肿瘤负荷呈正相关。胆碱激酶α是将游离胆碱转化为磷酸胆碱的关键酶,HCC组织中的胆碱激酶α水平较邻近非肿瘤组织表达增加,与肿瘤侵袭性和患者不良预后相关。溶血磷脂LysoPC(21∶4)和LysoPE(22∶2)表现出与甘油磷脂相反的趋势,这些溶血磷脂在癌症生物学中可能发挥双重作用[27]。肌醇是细胞膜磷脂的一种成分,在体内外均显示出化学预防和抑癌作用[29],OS较长的早期和晚期肝癌患者其肌醇血液水平均升高。肝癌患者体内循环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水平升高,这可能与癌细胞破坏大量肝细胞导致胆固醇分子释放增加和肝占位引起连续胆汁淤积有关[15]。
鉴于对肠道菌群在肝癌发病机理中的代谢活性认识加深,近几年不同地区的多项研究[13,30]发现初级胆汁酸与肝癌风险增加正性相关,次级胆汁酸与肝癌风险降低显著相关。牛磺鹅脱氧胆酸盐是影响肝脏脂质积累和炎症的关键代谢物[12],结合胆汁酸可能引起核受体失调,导致肝脏中胆汁酸的产生升高、NF-κB通路激活、肝脏炎症和致癌作用[31]。这些初级结合胆汁酸对于肝癌进展可能具有一致的作用。
视黄醇类代谢物参与细胞分化、细胞凋亡促进和炎症反应减少等多种生物过程。有报道称视黄醇与其他类型的癌症(如乳腺癌、前列腺癌、胃癌和结直肠癌)的风险发生率相关。例如,Formelli等[32]研究显示,高血清视黄醇与乳腺癌风险减小显著相关,低血清视黄醇患者的乳腺癌存活率低于高视黄醇者。而Mondul等[33]报道高血清视黄醇与前列腺癌的风险增加相关。大多数视黄醇储存于肝脏中,肝癌的发展可能较其他类型的癌症对视黄醇水平的影响更大,但具体影响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4 存在的问题及展望
目前,血液代谢标志物在肝癌预后预测及治疗反应评估方面的研究存在诸多问题。(1)代谢组学技术限制:筛选出的代谢物种类繁多,化学多样性和浓度范围差异较大,很难通过单一检测方法测得生物系统中所有代谢物的真实情况,还有很多未被检测到的代谢物。另外,虽然国际上有代谢组学技术样本预处理方法的相关指南推荐,但已发表的代谢组学研究中只有一小部分完全遵循这些标准,导致各研究技术方面异质性较大[34]。(2)对于同一代谢物,不同研究检测到的变化趋势可能不同,不同来源样本中(组织、血液、粪便及尿液等)的特征变化趋势亦可能不同,代谢物之间关联性不强。这可能是纳入研究的HCC病因分布特点和分期、人群特征(BMI、性别、年龄、人种、基础疾病、生活方式等)、采集血液样本的部位和时间、检测方法以及采血时患者的代谢状况等有差异。靶向代谢组学方法、NMR技术的同位素标记和多组学技术联合可能是研究代谢物变化特征、代谢途径的有用方法。(3)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代谢综合征(包括胰岛素抵抗、血脂异常、高血压和中心性肥胖)是肝癌的重要危险因素[35-36],包括吸烟、饮酒、饮食、锻炼等在内的生活方式也被证明与肝癌风险相关[37],目前的预后研究可能忽视这些因素对肝癌的代谢扰动影响,在未来研究中需要予以重视。(4)现有研究大多集中在早期接受治愈性治疗的肝癌患者,对接受免疫、靶向及TACE治疗患者的研究基本为空白状态;研究队列较小,大多缺乏内部及外部验证;且多集中在我国,慢性乙型肝炎为肝病群体的主要病因,关于丙型肝炎、酒精性肝病等重要病因的研究较少,需要更多大型、多中心的前瞻性研究来发掘并验证血液代谢物的价值。
肝癌是一种异质性较大的恶性肿瘤,血液代谢标志物可以反映肝癌发展的综合情况,对肝癌预后及治疗反应具有预测能力,部分代谢物被提出作为预测肝癌预后及治疗反应的标志物。此外,随着精准医学、综合诊断和多学科诊疗时代的到来,代谢组学技术在预测肝癌患者预后和选择个性化治疗方案方面具有较大的应用前景。
利益冲突声明:本文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
作者贡献声明:刘志英对文章的思路及撰写有关键贡献;周智航和何松参与修改文章关键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