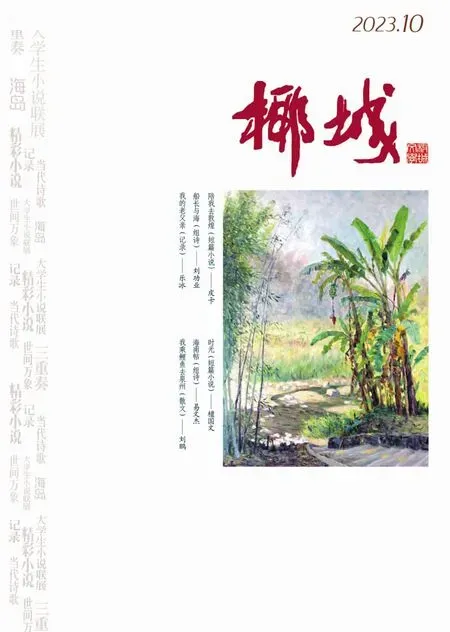生病(短篇小说)
◎方乐明
祁广签到后,就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这几天没有材料写,他漫不经心地浏览着报纸。忽然,手机铃响了,一看显示屏,号码是妹妹祁荣的。
“大哥,妈住院了。”妹妹祁荣的嗓音透着疲惫,“在市立医院西医内科。”
祁广似乎没有感到意外,去年母亲就因心脏病发作,住了一次医院,但此刻,祁广仍吃了一惊,急促地追问:“小荣,是不是妈的心脏病又发作了?”
“不是,”祁荣答。“可能是胆囊炎,她的胸腹痛疼得厉害,连背部都痛。”
祁广想了想,道:“我马上就去。”祁广的妻儿都在北京。妻子打工,儿子读大学。祁广在北京呆了半年,没找着合适的工作,只好独自回到家乡。
此刻,他草草地收拾了一下办公桌,便向上司的办公室走去。上司姓凌,是一位二十岁出头的俏姑娘。
祁广的脚步声惊动了正在上网的上司。
上司扭过头,一张粉脸写着疑惑。祁广除了去交材料,平日从不到上司的办公室串门。长期以来,祁广与年轻貌美的女孩,存在着沟通的困难。再则,上司的办公室与老总办公室相邻,且有一扇门相通,这使他格外地感到不便。
“凌主任,我母亲生病住院了。”祁广急速地说。
年轻的上司倒是很善解人意,说:“那你快去医院看看老人家吧!”
祁广请了假,小跑着出了公司,挤上一辆公交车。……他心急火燎地来到内科病房,在四五位病人中间,一眼发现白发苍苍的老母。
“妈,你咋了?”祁广问。
大概因为疼痛的原故,母亲脸上的皱纹又密又深,脸色也显得腊黄、枯干,像一枚放大的核桃壳。母亲一会儿躺倒,一会儿却又要坐起。剧烈的疼痛,使她坐卧不宁。
“大夫说是阑尾炎发作了。”母亲吃力地告诉祁广,“先打止痛针、吃药,看能否缓过来。”
“止痛针管用吗?我看你痛成这副模样。”祁广担忧地看着母亲。
妹妹祁荣在一旁说:“管用一会儿。”
祁广站起:“我去找大夫。”
一位中年女大夫坐在值班医师办公室里,祁广走过去,自我介绍道:“大夫,我是第六病室的家属。”
“唔,病人是一位老太太吧。”中年女大夫扶了扶眼镜。她有一张白纸般洁白的脸,不过,这张白纸上出现了几道纤细的皱褶。
“是呀,是呀。”祁广连忙应道,暗暗钦佩中年女大夫的记性。
“这位病人患的是胆囊炎。”中年女大夫又扶了扶眼镜,清柔的目光透过镜片撒在祁广的脸上,“这位病人年龄太大。唔,七十九岁了,是吧?”
母亲年老体衰,即使用药消炎或动手术,都使祁广感到担忧。
这时,大夫又问:“你是老太太的啥人?”
“儿子。”祁广答。
“你来了正好。”大夫将一支笔放在祁广面前,“这是‘危重病情通知书’,你在这上面签字吧。”
祁广的手颤起来。
祁广6岁丧父,母亲含辛茹苦将他兄妹三人拉扯大,他多么希望母亲多活几年!
“我母亲痛得受不住了。”祁广用恳乞的眼神望着大夫。
大夫便说:“我让护士再给老太太打一针止痛。”说完就走出去了。
祁广也回到母亲所在的病室。
母亲的脸色显得更加腊黄,嘴巴歪了、脸孔扭曲着。祁广心疼地安慰道:“妈,护士待会儿要来给你打止痛针。”
“针打了没用,还痛。”母亲吸着气说。
护士来了,给母亲打针。又有一位护士推来一只氧气瓶,给母亲的鼻孔插管输氧。
“针打了没用,还痛。”母亲仍然呜呜咽咽地说。
护士不吭声。忙完后,护士就走了。
挨到傍晚,水米未进的母亲,显得更加衰弱。正当祁广心焦如焚时,来了四五位大夫,说是会诊。大夫们诊视了一会就出去了。
一位女护士将祁广兄妹喊到值班医师办公室,那位中年女大夫神色严峻地告诉祁广:“经过一天的药物消炎,你母亲的病况没有好转,看来只有手术了,但风险还是较大,你们全家人商量一下,作个决定。”
祁广与妹妹面面相觑,他发现妹妹脸色苍白,脸色似乎瘦了一圈。
“不动手术行么?”祁广嗫嚅地问。
女大夫指着母亲的拍片,为难地看着兄妹俩:“老太太的胆结石体积大,可能将胆囊涨破,一旦发生这种情景,就没救了。”
祁广吓了一跳,就说:“那就动手术吧。”
女大夫又问:“家中还有别人吗?都喊来。”
祁广就打电话将母亲的病情告诉妹夫和弟弟祁安,催促他俩赶快来医院。弟弟祁安做生意老是赔本,但他仍然吃喝玩乐,开销惊人。几个月前,他连家中唯一的住房都卖了,一家人在外租房栖身。
这一整天,母亲自知此番病得不轻,想要见小儿子祁安一面。祁广便多次打祁安的手机,祁安每每答应得挺爽快,却总不见人影。
此时,祁广的弟弟祁安和妹夫小李听说要让他们来决定老太太是否动手术,方知老太太确实病势危急,不敢怠慢,相继赶到医院。
祁广见他俩来了,便一起去找大夫。在值班医师办公室,中年女大夫当着这一家人的面,郑重地将刚才对祁广兄妹说的话又复述一遍。
“你们商量一下,如果同意让老太太动手术,就签个字。”中年女大夫说。
大家脸色凝重,仿佛看见了死神正狰狞地向母亲走近。瞬间,谁也没有说话,空气令人窒息。女大夫用目光催促大家,重复地说:“你们商量一下吧。”
“我尊重大夫的意见,动手术!”祁广征询地看了看大家,“你们意见如何?”
祁安、祁荣和李西仁都同意让老太太动手术。于是,祁广便代表大家在“家属意见书”上签了字。
老太太当即被转到外科重症病房。
外科主治大夫姓汪,是一位不到40岁的年轻人,温文尔雅。汪大夫再次召集祁广一家人开会,挨个儿征询这一家人的意见。然后,汪大夫告知老太太此番手术费起码在一万五千元以上,见大家没有异议,便和护士、祁荣去重症病房,让老太太捺了手印。于是,不堪疼痛的老太太,终于被推进了手术室。
祁广一家人在休息室等候,祁荣说:“上午交的两千元,大夫已说用完了,要续交四千元,可是,这钱……”祁荣为难地看了看大家。祁荣与祁安合伙开了一家电器公司,法人代表是小李。公司开张两年多来,只做了几笔小生意,赔进去不少钱。祁广去年在单位买断工龄,拿了十万元,全放进了弟妹的电器公司里。
此刻,大家面面相觑。
祁广急了,觉得自己是大哥,有责任拢住家人拯救母亲。于是,他用凝重的嗓音说:“我看这样吧,这钱暂时由小荣垫付,以后再分摊下去。”
祁荣顿时拉长了脸,祁广见此情景,知道祁荣对他的表态不甚满意,想了想,便又说:“我是大哥,老太太的医药费我应该多摊点儿,这样吧,我摊三分之一,二弟没钱,就不摊了吧。”
大家仍然不吭声,但脸色显见缓和多了。祁安没能掩饰心中的喜悦和对大家的感激,立即站起,递了一支烟给祁广,又递了一支烟给小李。
祁荣忙乎了一天一夜,困乏极了,便先回去休息。小李坐了一会,抽了两只烟,借口出去买水,也走了,休息室里只剩下兄弟俩。祁广看了看暗淡灯光下显得消瘦的弟弟,有些心疼,就问:“你最近糖尿病好些了吗?”
“还行。”祁安说,“每天都在服药。”
“要注意身体!”祁广叮嘱道,“你可看不起病哟,你没有办医保!”
“不要紧!我不是在挣钱吗。”祁安说。
“你挣到钱了吗?”祁广的目光中略含讥讽。
祁安的脸色涨成酱色,分辩道:“现在没挣到钱,不等于以后也挣不到嘛!”
祁广以大哥的口吻道:“你可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寅吃卯粮,要抠着用,否则,老了谁养你啊!”
大哥的潜台词祁安当然明白。二十年前,受不住单位束缚的祁安自动离职作生意,那时生意好做,撞大运挣了一些钱,但都让他挥霍殆尽,如今落得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且身无分文,货真价实的一个穷光蛋!
“不要紧!我不是在挣钱吗!”祁安重复地说了一句,口吻透着一股自信。
不了解祁安的人,很轻易地为他的自信所感染,甚至钦佩他!但作为兄长,祁广知道弟弟是位糊涂人,他从不想着明天,当然也就没有丝毫的忧患意识了。
兄弟俩沉默起来,显得话不投机半句多。这时,祁安站起,说:“口渴啊,我去买水。”
祁安走后,偌大的休息室只坐着祁广一人。灯光显得明亮些了,却更加凸显出周围的寂静。一天的劳累和紧张像一场噩梦渐行渐远,祁广这才感到一些轻松。休息室里没有长椅,这颇使他有点遗憾。这时候能够躺下去,放松身体各个部位,该是一件何等舒心的事啊!近两年,祁广觉得身体越来越虚弱,双腿像灌铅似地沉重,还莫明其妙地厌恶油腻的食物。祁广担心自己患了肝病,因为他以前患过乙肝,虽然痊愈了,但现在是否复发,也未可知。其实,只需上医院体检一下就行了,祁广却懒得上医院,嫌麻烦。再说,若真的检查出肝炎肝癌啥的,那要花一大笔钱去诊治!现在他的当务之急是赚钱糊口。是的,糊口才是硬道理!
约莫半个钟头,祁安从购物袋里拿出两瓶矿泉水和两包云烟。那位管理休息室的中年勤杂工,不早不迟恰在此时走进来,似乎他是瞅准了祁安的购物袋而来的。
祁安抓起一包云烟,扔到中年勤杂工面前。
“烟不好,凑和着抽吧。”祁安说。
“哎!”中年勤杂工夸张地叫了一声,眼睛发亮:“谢谢!噢,喝水不?我去拿水。”
“不用,我已买了水。”祁安指了指那两瓶矿泉水。
三人闲聊了一阵,中年勤杂工揣起香烟离去。祁广迫不急待地抱怨起了祁安:“你送一包烟给勤杂工干吗?那包烟值二十多块吧。”
“客气一下嘛。”祁安含混不清地说。他自己也弄不清干吗要送一包恁好的烟给中年勤杂工,他“甩惯”了!毫不吝惜地将财物甩给别人,只需对方道声谢,或投以惊喜的目光,他便获得心理上的极大满足。
祁广不忘大哥的责任,此时仍喋喋不休地教导这位不争气的弟弟:“你若真要客气,花五六元钱买一包中档香烟送给他就行了。你现在要抠着用钱,能省则省,不可再像以前那样乱花钱了!”祁安无精打采地听着,不停地打着呵欠。
老太太的手术很成功,在监护病房住了一周,就移至普通病房,又住了一周,就拆线出院了。期间,祁安从祁荣手里拿了一千元钱做红包,准备伺机送给主持老太太手术的汪大夫,但遭到汪大夫的拒绝。祁安便将这一千元钱中饱私囊了。祁荣板着脸催要了几次,见毫无归还的希望,只好愤懑地骂了一句:“无聊!”自认倒霉算了。
祁荣没敢将这事儿告诉老太太,怕老太太听了怄气。
老太太出院后,仍回到祁荣家住。尽管小儿媳妇张梅花三番五次恳请老太太去她家住,但老太太对祁安卖掉住房仍耿耿于怀,不肯去小儿子的租屋去住。而大儿子虽有住房,但大儿媳妇和孙子都在京城打工,仅祁广一人在家,祁广又朝出暮归,家中无人照料。
张梅花听说不让她一家承担老太太的医药费,忒高兴,隔三岔五地煨了鸽子汤或鸡汤送来。其实,老太太每月都从退休工资中拿出两百元给了女儿祁荣,算作营养费,祁荣拿这钱每天都煲一些肉汤给老太太喝。
老太太和祁荣都不要张梅花送汤,但张梅花执意要送,弄得祁荣连老太太的每月两百元营养费也不好意思收了。
老太太此番花掉一万四千六百元医药费,却没要子女分担。前几年祁荣曾将老太太一万元存款拿去炒股,并承担了炒股的风险,如果老太太的股跌了,她负责自掏腰包填充亏空。现在,老太太提出要祁荣取出全部股金,加上她近年的几千元存款,医药费差不多够了。但祁荣背地里却对祁广说老太太在股市的钱已跌得所剩无几,为此,自己只好往里面填五六千元的亏空。祁广拿不准祁荣说的话是否有水分,只是在她面前装糊涂。
其实,祁广也给祁安填了三万元钱的生意上的亏空!祁安、祁广当初合伙成立电器公司时,兄妹俩约定各拿出三万元做本金,但祁安没钱,恰好祁广从单位买断工龄,拿了十万元,出于帮弟妹一把的仁义之心,他将十万元钱悉数交给了祁荣,但他声明钱是借给电器公司的,不是借给个人的,尤其不是借给祁安的,他深知祁安是个无赖,钱一旦到了这家伙的手里,便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星期天下午,祁广在家看书,忽然,祁安登门造访,他一进门,就左瞥瞥,右看看,像一条警觉的狗。自从祁广从京城打工回来,祁安还从未来过大哥的家。
祁安坐下后,祁广便问:“近来生意咋样?”
“接了几个大单,可就是本金不够。”祁安皱起眉头,唉声叹气。
电器公司成立几个月后,祁安、祁荣因生意上的分歧,各自分开单干,祁安另赁门面房经营业务,但帐务仍由祁荣代理。
此刻,祁安谈起钱,祁广只好闭嘴,因他无法替祁安筹钱。
祁安忽然愤懑不平地说:“大哥,你那七万元都让小荣独自拿去了,我想用一下她都不给,真气人!”
祁广听出了什么,立即警觉地问:“是十万元啊!咋变成了七万元?”
“哎,当初成立公司时,你代我垫付了三万元入股资金嘛。”祁安不假思索地回答。
祁广一下子跳起来,嚷:“我啥时候为你垫付三万元了?我的钱都是借给你们电器公司的,不是借给你和小荣的!”
祁安悻悻地回答:“我还你就是了!”
兄弟俩没法谈拢了,祁安一声不吭地离去。
祁广打电话给祁荣,询问三万元一事,祁荣道:“二哥说你当初答应过的。”
“我啥时答应过的?这钱……”
“你就只知道钱!钱!那三万元就算是帮了二哥一把,又怎样呢?!”
“我的天,三万元呢!”
“不就是三万元嘛,我还你!我还你!”电话那头传来祁荣因愤怒而走调的嗓音。
祁广无奈,默默地挂了电话。三万元呐,他要打一年工才能够挣够这个数!祁安就那么轻轻巧巧地拿去挥霍了!唉,当初与祁荣说好了他不能代祁安垫付,而现在祁荣咋变卦了呢?难道就是因为没有信守承诺分摊母亲的医药费吗?更要命的是,这笔不明不白烂掉的三万元钱,该如何向妻子交待呢?
这些天,祁广厌食,浑身疲乏,连去公司上班的那一段路也走不动了,只好请了假,去医院看大夫,查了血清和肝功能。
大夫用严厉的口吻说:“病情这般严重,咋到现在才来医院?”大夫狠狠地看他一眼,又道,“你家属呢?让她们来!”
祁广想了想,“我——没有家属。”
大夫睁大眼睛看着他,眼神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