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标准”和“老观念”
蒋子龙
一位交往多年的编辑,再一再二地约我,谈谈年轻时的“婚姻观念”和“择偶标准”。我不忍拂她的诚意,却也不敢贸然答应。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当初结婚时,真有什么“观念”吗?
那个时代的年轻人,简单而有理想,差不多都想干一番事业,先立业后成家。至于想干什么事、立什么业,说白了,就是干好本职工作,当好“螺丝钉”。是工人就要学好技术,一级级地往上升,成为“八级工”是连做梦都不敢想的。当时,我所在的工厂一万多人,“八级工”也就有数的几个。那时,能升到四五级工,就相当不错了。
那年,我晃晃荡荡,已经二十七八岁了。带我到天津读书的三哥发话道:你已经无业可立,连正经事都没的可干了,还是成家过日子吧。对了,过日子就是当时最流行也是最重要的婚姻观念。只有结了婚,才叫有了自己的日子。两口子打架,叫“日子没法过了”;离婚或配偶去世,周围同情的人都会感叹:“往后,他(她)的日子可怎么过呀?”三哥是想让我在这时候成个家,好躲开那些并不乐见的平常日子。
观念有了,我的家该怎么成呢?也就是说,想找个什么样的人组成自己的家庭呢?认真想了几天,将自己认识的姑娘,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还真找不出自认为能跟我过日子的人来。既然没有择人标准,就只好向哥嫂提出,什么样的人是我不能找的,共有三条:
第一,不找颜值太高的。我在工作中虽然有机会接触一些漂亮姑娘,却深知以我的条件,并不合适。这一条是给自己敲警钟,找对象别光盯着漂亮的。同时,也让哥嫂放心,你兄弟知道自己的斤两,不会好高骛远。
第二,不找本厂的。厂里即便有不嫌弃的愿意嫁给我,一不高兴了难免会抱怨、后悔,岂不等于开我的“家庭批斗会”吗?两人搭伙过日子,最好找肩膀一般齐的。
第三,也不想找城里的。至今,已在大城市里生活了多年,自觉仍不能真正融入城市。长篇小说《农民帝国》出版时,我在《后记》里说了一句话:“总觉得自己在骨子里,还是个农民。”
嫂子听完这三条,笑了:正好,我有个合适的人,就像专给你留的一样,完全符合你的条件。人家模样长得不错,比你小三岁,本分、牢靠,我绝对知根知底,论起来是我的叔伯妹子。
听完嫂子的话,我很后悔没有在“择偶标准”里再加上一条:不找拐弯抹角沾亲带故的。我干的是锻工(打铁),属于“特重型体力劳动”,又是三班倒,很快就把成家的事丢到脑后了。
有一天,嫂子交给我一个布包,让我给她的叔伯妹妹送去,并嘱咐道:你们俩怎么也得见个面儿,看看没有大问题,就趁早把事办了,她一个人过日子不容易,你也老大不小的了。嫂子动了真格的,这是叫我去相亲呀!反正早晚也得去一趟,否则,无法向嫂子交代,等回绝了那位叔伯妹子后,再向嫂子解释吧。
选了个我下早班、她歇班的日子,就“送货上门”了。在天津市最繁华的中心地段,找到了她家。一座老院里有一幢老楼,进院碰到一位大姐,拦住我像审贼一样,把我审了个底儿掉,然后,才领我敲开了她的屋门。屋子里空空荡荡,四壁光光,靠最里边的角上,有张旧床,屋子中间有个凳子,凳子上放着一盆水,显然,她刚洗完头,头发还是湿的,一时间愣在原地,有些手足无措,却越显得眉眼温顺。她是细高个儿,肤色白净,软弱无助地站在這样一间像刚被洗劫过的老屋子里,身上竟散发出一种东西,格外让人心动。
虽然我也浑身不自在,却在那一刻就拿定了主意:就是她了!这是个能跟我相依为命的女人。我赶紧把嫂子的布包递过去,说了句:“你有事找我。”随后,就慌忙退出来,走了。
很长时间以后,两个人聊天,她提起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尴尬,一直非常关心她的同院大姐,那天等我走了以后,就逼问她:刚才那个“大老黑”是谁?是不是你叔伯二姐的小叔子?不行,一朵鲜花哪能插在牛粪上。准备结婚的时候,我特意自制了一张请柬,让她交给同院的大姐,落款就是:鲜花、牛粪。
结婚前,工厂一位对我非常好的老大哥,也给了我受益终生的忠告:马上要成家了,好歹我是过来人,给你立三条规矩。怪哉,怎么都是“三条”?
第一,不管生多大气,都不能打老婆。只要动了一次手,下次一不高兴了手就痒痒,巴掌拳头是打不出感情的,也打不出好日子。
第二,永远不要骂老婆。有理说理,有事说事,只要骂顺了口,后边就收不住,一不高兴就张口骂街。
第三,能成两口子,多少都有点儿“天意”,不到万不得已、俩人实在走到尽头了,不能从你嘴里吐出“离婚”两个字。离婚不是儿戏,不要成天挂在嘴边儿上。
这就是我的“老标准”和“老观念”,让现代的年轻人见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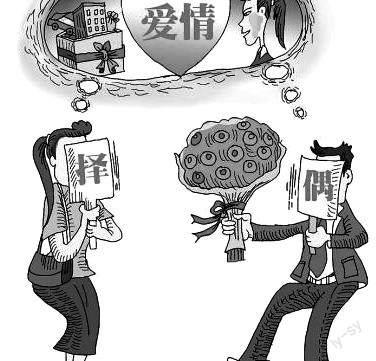
【原载《辽沈晚报》】
插图 / 婚姻观 / 佚 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