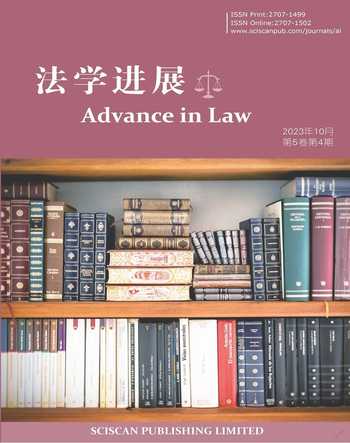风险社会视野下的行政训诫适用边界
孟哲
摘 要|行政训诫作为非行政处罚的措施之一,在实践中经常被行政机关用以规制行政相对人的行为。虽然法律上对训诫有明文规定,但其适用的法律效果及空间并不明确,这导致行政训诫在行政管理中被滥用。目前理论界的研究成果大多侧重于对训诫行为性质的分析讨论,较少对该行为适用空间进行分析。以对法律规定和实践案例的分析为切入点,从实质意义上区分警告、责令改正等与行政训诫类似的行为,构建行政训诫适用的法律效果及适用空间。
关键词|训诫;法律效果;适用情形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训诫作为执法实践中国家机关实施管理的手段之一,其作用就是化解危机,预防风险。随着社会进步与人自身行为的不断发展,风险社会理论逐渐成为国家安全职能扩张、变迁的社会背景,“‘风险社会并非纯粹自然意义上的,而是人类行为和决策意义上的,是它们的副产品,它是人类活动的反映。”a国家的根本任务就是保障公民的生命、健康和财产的安全,在自然风险与人为风险不断被认知的当下,国家有必要采取各种措施来防范危险、预防风险。与传统危险不同的是,现代风险时时存在又无法准确预估,很多时候行政机关要在经验与知识储备不完全充分的情况下做出决定,这就体现了“风险社会”与“法治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
非型式化行政行为因为具有弹性、可变性与创造性等特征填补了行政在应对复杂现实时的手段不足,为行政机关的执法方式提供了更高效、更便捷、更柔性化的选择可能,也给了行政机关更大的裁量空间。训诫拥有非型式化行为的优点,当然也具备非制度化的弊端。非型式化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行政的确定性与可预测性,存在更多的对相对人权利产生不利影响的可能。因此,必须对训诫适用的条件及边界予以明确,控制“双重”风险,即以训诫为工具控制现实生活中所产生的各种风险,同时控制因适用该行为而产生的风险。对训诫这个行政机关作出的非正式行政行为进行研究,明确何种行政机关有权进行训诫,其训诫的权限范围如何,训诫的法律效果如何,训诫与其他类似行为措施的区别何在,进而提升训诫的法治化水平。
一、训诫的实证分析
不同的法律领域规定了不同的规范内容,相同法律领域的规范也存在不同的要件与规制措施,“训诫”这一措施在不同的法律中的适用情形与构成要件也不完全相同。同时,在行政执法实践中出现了一些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侵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但司法判例却往往并不支持行政相对人的诉求,将训诫排除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这也导致行政相对人無法通过诉讼的途径救济其受损的权利。
(一)规范现状
根据笔者的检索与整理,目前有十一部法律和三个行政法规对训诫作出规定。如,在《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三大诉讼法中,训诫作为一种保障诉讼顺利进行的诉讼强制手段适用,属于程序法的自我保障措施。在实体法中,《刑法》第三十七条、《反有组织犯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了对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根据案情予以训诫或采取其他措施,作为一种非刑罚处置措施由司法机关适用。《保安服务管理条例》规定了对实施特定行为的保安员的训诫,《信访条例》规定了对违法信访人员的训诫,这都是将训诫作为一种非行政处罚的替代性处置措施适用。根据训诫做出主体的不同,可将训诫分为“司法训诫”与“行政训诫”,前者是由法院、检察院等做出,后者则是由行政机关做出。
不同的法律规定了训诫不同的适用情形,训诫可以针对相对人的作为或不作为,训诫决定作出的缘由都是相对人轻微违反相关法律所建立或维护的秩序,具体表现为:第一,训诫决定的作出以行政相对人实施的违法行为为前提,其不仅针对相对人的违法作为,还可以针对相对人的违法不作为。如《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1款中规定公安机关对保安员殴打他人、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等行为予以训诫;《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2款中规定了对不作为的训诫,法院可以对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出庭后拒绝作证的证人予以训诫。第二,在被训诫的对象方面,主要是违法行为人,但在某些特定情形下,也可能是行为人的法定监护人。如,在《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了对被申请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但不构成犯罪的,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在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中,除了对实施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训诫外,还会出现对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训诫的情形。《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公安机关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予以训诫,《家庭教育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了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可以在案件中存有未成年人有严重不良行为或实施犯罪行为时,对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予以训诫。第三,虽然不同领域的法律规定中对训诫的适用条件不同,但其共同前提是行为人的行为轻微违反该法律所要建立或维护的秩序。如,《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对其免于刑事处罚,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予以训诫或采取其他措施。《看守所条例》第三十六条中明确规定对于违反监规的人犯,看守所可以予以警告或训诫,情节严重,经教育不改的可以责令其具结悔过或对其予以禁闭。
从前述立法来看,仅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四十一条将训诫称为“矫治教育措施”,而其他规定了“训诫”的法律法规中,不仅未对训诫行为进行定位,也从未出现过“本法所称训诫”类的含义解释条文,导致本应严谨的法律术语“训诫”在行政执法实务中被一再扩张适用。
(二)执法现状
行政训诫并非《行政处罚法》中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之一,不属于《行政强制法》中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行为,也不属于目前已经型式化的其他行政行为。在执法实践中,行政机关选择训诫作为管理措施的频次较高。卫生行政部门对违规发布医疗广告的医疗机构予以训诫,市场监管部门对故意隐瞒商品真实信息的经销商予以训诫。存在安全隐患的企业被安监部门约谈训诫,有自制新闻采访证件者被网信新闻出版社行政部门约谈训诫。
目前,训诫在疫情防控领域适用得较为频繁。2020年1月31日,李文亮医生在自己的微博中公开了中南路街派出所作出的训诫书,其中认定李文亮医生发表不属实言论,以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规定为由,要求李文亮医生终止违法行为。而后,武汉市公安局以“处置不当、适用法律错误、执法程序不规范”为由,撤销了该训诫书。2022年8月31日山东省菏泽市郓城县公安机关对拒不参与核酸检测的7人予以训诫教育,2022年8月18日厦门公安机关对拒不参加核酸检测的四人依法训诫。除此之外,实践中行政训诫还被行政机关频繁适用于行为人的非法上访行为及发布不实言论的情形。涡阳县公安机关在2021年7月21日对王某某进行训诫并出具了训诫书,该训诫书中认定王某某与他人的集体上访行为影响了正常信访秩序,涡阳县公安机关根据《信访条例》(已失效)第20条第5项、第47条第2款的规定对其予以训诫。2020年1月31日,山东省东营市公安局东营港经济开发区分局对扈某进行训诫,认定扈某在微信群发表不实言论并造成传播。
根据笔者对上述训诫书及其他从各网络平台搜集的训诫书的研究,训诫书中的内容大致相同:首先写明训诫机关与被训诫人信息等必要的程序性信息,其次写明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再次告知当事人违反了何种法律规定(行政机关或将法条全文列出,或仅写明某法某条),最后告知当事人“你现在已经违法,希望你中止或改正违法行为,如果继续进行违法活动将对你进行处罚。”
(三)判例现状
目前涉及行政训诫的诉讼数量较多,被训诫的相对人对司法救济的需求旺盛。但通过对案例的分析来看,被训诫人希望通过司法途径得到法院救济的努力大多以失败告终。在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的观点较为一致: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作出的训诫行为是非强制性的教育措施,但各法院说理的进路并不完全相同。
第一种审理思路认为,行政训诫并未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这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在此类案件中的说理进路。在李际锋诉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公安复议纠纷再审案中,再審申请人李际锋向北京市西城区政府提起行政复议事项涉及公安部门依据《信访条例》作出的训诫处理行为,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该训诫行为对李际峰并不具有强制力,亦未对其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行政复议的范围,也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进而驳回了其再审申请。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赵春玲与徐州市公安局云龙分局二审行政裁定书中认可了一审法院关于训诫性质的判断:训诫书的内容为信访相关法律法规及对违法信访行为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的释明,本身并不直接设定原告的法定权利义务以外的权利义务。
第二种审理思路认为,行政训诫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之一。在鲁东慧与西安市公安局等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纠纷上诉案中,对于上诉人
(即一审原告,鲁东慧)所提出的其已经被北京市某派出所训诫,不应再由被上诉人进行处罚的问题,西安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条与《行政处罚法》第九条的规定,训诫并非一种行政处罚或治安管理处罚,本质上是一种批评教育,故对已经作出训诫的违法行为再作出行政处罚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在熊仁贵与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政府一审行政判决书中法院所查明的案件事实部分,被告区政府向原告熊仁贵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中认定,在随州市公安局曾都区公安分局对熊仁贵作出的曾公训字(2020)第0056号《曾都区公安分局训诫书》中,含有对原告予以行政警告处罚内容,与训诫内容不符,且有明显涂改痕迹,以行政法律文书存在重大瑕疵,程序违法为由撤销了该训诫书。原告认为复议决定没有按照其要求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诉至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法院认为被告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结果正确,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即本案中法院认可了训诫并非行政处罚的观点。
二、依法训诫的现实困境
行政训诫作为行政机关预防风险,化解危机的手段之一,常被用来解决社会问题,但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风险。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机关所实施的训诫行为侵害了其合法权益,继而产生了权利救济的问题。通过对执法过程及行政相对人所处困境进行梳理分析,更深入理解训诫行为,明确问题所在,才能有效地对行政训诫予以规范。
(一)“法外训诫”频发
在实践中,“法外训诫”的现象频发,即行政机关对当事人进行训诫时没有法律依据或法律依据错误。这一现象常见于治安管理领域,如上文所提到的被公众广泛讨论的李文亮案件,在公安机关对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中写道:“现在依法对你在互联网上发表不属实的言论的违法问题提出警示和训诫。你的行为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你的行为已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并未对“训诫”作出规定,公安机关对李文良医生的训诫以《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为依据显然是错误的。在黟县公安局宏村派出所作出的一份训诫书中写道:“××的行为妨害了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并扰乱了防控疫情期间的社会秩序,现依法对××的违法行为提出警示和训诫。”以及吴川市公安局作出的训诫书:“现因你微信随意发布信息的行为,扰乱公共秩序,违反相关规定,先对你进行训诫。”
从前述训诫书中可以看出,即使没有法律规定(《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并未明确规定“训诫”属于公安机关治安管理的措施之一),公安机关也会将行政训诫作为其实现管理目的的手段之一在实践中频繁使用,甚至将其作为行政处罚的一种替代措施,而这样的训诫无论内容多么合理,都应当被禁止。
(二)裁量空间较大
为了给行政权保留若干弹性及裁断余地,给予行政一定的权宜性和自由性,来保证法律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执行,法律屡屡对行政机关进行概括性授权,将具体的行动委诸行政机关政策性、行政性的判断。
目前关于行政训诫的法律法规规定得较为宽松,在具体案件中是否需要对行政相对人实施训诫属于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范围。如对实施了《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1款中所禁止的行为,且情节不严重的保安员予以训诫。在符合了法律规定的要件(保安员实施了法律禁止的行为)后,就到了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的环节,根据行为的严重程度并结合案件事实,认定保安员所实施的行为是属于应当被训诫,还是属于情节严重或违反治安管理。这一环节又被称为选择裁量,行政机关拥有选择行为方式的选择权,在自由裁量空间内更多地要依靠行政机关的工作经验、惯例等因素,参考法律规范的意旨,在合目的性与合理性的基础上作出决定。裁量空间过大也是训诫在执法实践中被滥用的原因之一,行政机关拥有更宽泛的自主权,为了更快完成行政管理的目标,会出现行政机关随意使用训诫来规制相对人的情形。
(三)缺少救济途径
行政训诫并不像行政约谈、行政指导等其他非型式化行为一样,具有较强的协商性,实现目的的方式也较为柔和,更易于行政相对人接受。在执法中,实施训诫的行政机关是管理者,处于强势地位,而被训诫的行政相对人基于自身的违法行为与公权力机关的职权,往往在训诫中处于力量和伦理上的弱势。而在实务中凡“训诫”行为不可诉,被训诫人提起复议或诉讼通常会被驳回,如在最高法院的判例中明确“训诫书属公安机关告知其相关法律规定及信访途径的告知行为,该行为未对其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亦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故而驳回了姜某的再审申请。这意味着被训诫人处于更为弱势的地位,当事人没有救济途径,无法请求对该训诫进行审查,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训诫却又规避了因做出训诫适用错误而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有权利必有救济,无论是合法的还是违法的训诫,都有侵害被训诫人权益的可能性,因此应当为其提供救济途径。
三、行政训诫的适用空间
(一)行政训诫的构成要素
1.主体
行政行为是由行政主体作出的,因此主体要件应当被首先明确。行政主体必须具有行政权能,而行政权能可以由法律赋予行政主体,也可以由行政主体分解、确定给行政机构和公务员。所谓行政权能,是指法律所赋予的享有某种行政权力的资格或能力。即只有法律规定的行政机关才有训诫权,能对行为人实施训诫。
2.权限
“无法律即无行政”,行政权的特性决定了必须以法律设定行政权的行使界限,即行政权限。行政主体只有在法定的权限范围内行使其行政职权才是合法的。第一,并非所有的行政主体都有训诫权;第二,有训诫权的主体对当事人实施训诫也应当在法定框架内。例如,公安机关可以依据《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对侮辱他人的保安员予以训诫,但是公安机关却不能以当事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为由对当事人进行训诫,因为《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并未规定公安机关有权对当事人进行训诫。
3.内容
行政训诫的内容要件应当揭示其法律效果为何,当训诫具有法律效果,才能达到行政机关实施该行为所要实现的行政管理目标。如果训诫决定的作出不能产生某种法律效果,那么该行为存在的必要性将大大减弱,因此法律效果的存在可以视为训诫的内容要件。
目前法律与行政法规中并未明确规定训诫的法律效果。根据新华字典与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训诫”一词应当被理解为:依据某个准则对当事人进行教导,同时告诫其应当警惕,不得再做先前的行为。这表明训诫在含义上有两层意思,教导当事人与告诫当事人不得再为先前行为。在执法过程中,行政机关对当事人违法行为及其后果进行分析后认为,如果不制止违法行为,有可能会对社会秩序或他人的权益造成损害,这是一种无法明确的潜在的危险,即通过训诫这种预防措施“所要遏止的不是已经知悉的危险,而是要去发现可能爆发的危机”。无论是训诫一词本身的含义,还是实践中行政机关作出的训诫书的内容,同样都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这两方面的内容也即行政机关实施训诫所要实现的法律效果:释明相对人行为违法,对相对人进行法治教育,然后告知相对人若再实施违法行为,将对其进行处罚,即下不为例。
4.形式
法律效果必须表示于外部,才构成一种法律行为。所谓表示行为,是指行为的主体将其旨在产生一定法律效果的内在意思表示以一定方式表现于外部,并足以为外界所客观理解的行为。训诫是行政机关的一种意思表示,其应当也满足一定的形式向当事人表示,但是法律中并未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训诫时应当满足何种形式要件,实践中行政主体依据不同的情况作出口头训诫或书面训诫。
(二)行政训诫的适用空间
目前已经有诸多行政行为被类型化,行政行为理论也愈发精致与成熟,但是在实现国家安全保障任务、完成风险预防目标方面,在提倡建设服务国家、福利社会的当下,以高权手段实现行政目标并非“最优解”。训诫作为一种非类型化行政行为,其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在遵照依法行政原则之上,追求“正确性”目标,提升行政效能。此部分将训诫与其类似的措施进行对比,在对比中明确训诫的适用空间。
1.口头警告
口頭警告作为法律明确规定的一种措施,在实践中也经常被行政机关适用。有学者认为口头警告并非行政处罚的原因在于:当事人被口头警告的情形并不会在其档案记录中留有信息,不形成违法前科,与要形成当事人行政违法前科信息的行政处罚完全不同。
在中央法律法规层面,《道路交通安全法(2021修正)》第八十七条、第九十三条第1款,《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2020修正)》第四十二条都规定“对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情节轻微,未影响道路通行的,指出违法行为,给予口头警告后放行”。地方法规、规章对何为“违法行为情节轻微”作出了更为细致的规定,《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2016修订)》第七十五条规定了对“违法临时停车”的行为人口头警告,《海南省无障碍环境建设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了对“占用公共停车场无障碍停车位,影响肢体残疾人使用”的行为人口头警告。
通过对上述立法的分析,行政机关对当事人适用口头警告的情形都是当事人违法情节轻微,重要的是未造成损害后果,如未对道路通行造成影响,对当事人以口头警告促使相对人及时改正自己的违法行为,最大程度减轻对公共秩序或交通秩序的影响。
2.警告
警告作为一种行政处罚行为,无论是其理论上的发展还是实践中的运用都已经较为成熟,法律上规定有权机关可以对相对人作出警告的法律超百部,可以说警告适用的领域非常广泛,它是日常生活中支撑社会整体稳定的基本秩序或主干性社会秩序行政行为之一。
3.通报批评
通报批评是在《行政处罚法》新修订后纳入处罚种类的行政行为,目前有20部法律和48件行政法规规定了“通报批评”的行政处罚。如《动物防疫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对瞒报、谎报、迟报动物疫情的部门通报批评;《审计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对拒绝提供或提供不真实完整资料的被审计单位通报批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对不履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或者虐待未成年人的学校进行通报批评;《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对无正当理由不采纳监察建议的机关或单位通报批评。
不同法律在规定对行政相对人进行通报批评时所要维护的法律秩序并不完全相同,但是通过对上述法律条款的总结,可以提取一些共性:第一,对通报批评的适用前提多数属于程序性义务,如验证义务、程序报告义务等;第二,通报批评的适用对象大多为单位而非个人,如审计单位、学校、网络服务提供者等。无论是否有实质上属于通报批评但形式上是其他名称的行为,仅从直接规定了“通报批评”的法律条文来看,与警告相比,通报批评保障的法律秩序较为狭窄,其局限于特定范围,警告更一般化与日常化。a
4.责令改正
责令改正也是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常用的措施之一,《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1款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黄锫学者认为该行为针对的是行政违法者的第一性法律义务,通过对法律所设定的第一性法律义务进行具体化,使抽象意义上社会主体的非自由状态转化为具体形态上社会主体的非自由状态,要求行政相对人实际履行法律所规定的义务,将已被破坏的法秩序恢复至理想状态。
有学者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责令改正的决定增加了相对人的法律义务,属于行政处罚,但通说认为,责令改正包括停止违法行为与恢复原状两个部分(若针对的行政违法行为是不作为,“停止违法行为”就应当理解为履行作为义务)。虽然责令改正不具有惩戒性,也不属于《行政处罚法》(2021)第九条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但是在实践案例中,若行政机关做出的责令改正决定产生了“溢出效应”,即责令改正决定所要达成的法律后果除了恢复至违法行为作出前的法秩序外,还对相对人产生了额外的制裁,使得相对人付出了比恢复原状更大的“代价”,此时的责令改正就可能构成行政处罚。
5.行政训诫
根据上文的分析,训诫的法律效果应当认定为告诫当事人行为违法,提示当事人应当履行法定义务或依法行事,并且告知其下不为例,但这是法律效果而非其适用空间,对适用空间的判断与划分还应当依据法律规定。如《社区矫正法》第二十八条中规定“视情节依法给予训诫、警告、提请公安机关予以治安管理处罚”,《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中规定“保安员有违法行为的由公安机关训诫,情节严重的吊销保安员证,违反治安管理的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当行为人实施某种违法行为,该行为隐含了某种危险或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但严重程度并未达到应当被处以行政处罚,行政机关基于实现公共管理与化解危机的目的,及时纠正行为人的违法行为,并且提示其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这也是给了行为人一次改正的机会,在其行为进一步恶化,损害结果进一步扩大之前采取补救措施,教育相对人依法行事,便于行政机关行政任务的实现。
6.小结
对训诫及类似行为的法律规定与适用空间的分析,目的在于将五类行为进行对比,进一步厘清训诫的适用边界。与口头警告相比,二者不属于行政处罚,都提示相对人纠正或改正违法行为,但训诫还强调不得再实施违法行为。口头警告针对的行为未产生危害后果,训诫所针对的行为产生了一定的危害后果。与警告相比,警告属于行政处罚,而训诫不属于行政处罚。训诫针对的违法行为的危害后果与警告相比更轻微,尚未达到应当被行政处罚的程度。与通报批评相比,通报批评属于行政处罚。通报批评多针对程序性义务,其适用对象大多为单位而非个人。训诫仅针对个人适用。与责令改正相比,二者都不属于行政处罚。训诫决定与责令改正决定都包含两层含义,都包括应当停止违法行为,但训诫强调下不为例,不得再实施违法行为,而责令改正强调恢复原状,且责令改正也可适用于单位。
四、结语
本文通过梳理相关法律规定,对行政训诫的构成要件进行分析,提炼训诫的法律效果和适用空间。训诫适用于违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或产生的危险尚未达到应当被行政处罚的当事人,作为行政机关对当事人作出一种提示与告诫,不仅是提示当事人其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告知其下不为例,防止更大的危险产生,也是给当事人一定的自我改正空間,在违法行为及所造成的后果并不严重或尚可挽回时给予当事人一定的指引与帮助。从此种意义上说,训诫是符合行政法比例原则的一种制度,对当事人所采取的训诫能够实现行政机关想要纠正当事人违法行为的目的,同时该行为无需公开,仅限于被训诫人和训诫机关之间,对当事人权利的侵害最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最小,因此作为一种非类型化行为,无论是实践层面还是理论层面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要化解行政训诫在实践中所面临的困境,最根本的方式是应当从立法层面对其进行规定或予以解释,对实施该行为的前提、程序、法律责任等构成要件予以明确规定。在立法层面的改变无法即刻实现的情况下,可以先完善相关程序制度。关保英教授认为,行政程序“关涉一国行政法治的质量”,在制度操作层面对训诫先一步予以规范,消除可能产生训诫滥用的因素。因此,需要建立一种公平的程序作为外在保障——保障相对人的权利,保障行政执法目的的实现。陈述申辩权作为程序正义原则的体现,是通过保障相对人参与程序的权利与机会来实现程序正义。对于被训诫人而言,针对行政机关所指出的违法事实与违法理由,能够充分且详细地表明自己的观点与看法,并得到行政机关的回复,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强训诫决定的可接受性。相较于仅告知行政相对人被训诫理由,允许被训诫人陈述申辩则更能达到教育目的。行政机关也可以根据被训诫人所提供的信息,认真还原事实真相,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行政机关错误实施训诫的可能性。
在司法层面,目前理论与实践都不支持相对人以对训诫决定不服为由提起复议或诉讼。而对于名为训诫实为行政处罚,或者没有法律依据的训诫决定,应当为被训诫人打开救济之门。即对于被训诫人提出的对训诫书的审查,不能仅以形式上训诫并非法定行政复议范围或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为由拒绝当事人的申请或起诉,应当从实质化路径判断该训诫书对当事人权益的影响,复议机关或人民法院应当判断训诫行为是否违法或实质上损害了当事人的权益,并对权益受损的当事人提供相应的救济。
嚴格执法作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中的一环,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环节和重点任务,是维护法律权威的重要手段,也是预防社会安全风险的重要措施。行政训诫作为行政机关执法手段之一,也应当贯彻严格执法的理念,严格依据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实施行为。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够为训诫的适用提供指引,规范行政机关的行为,减少违法违规训诫事件,推动行政训诫法治化建设。
The Boundary of Administrative Discipline Applic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Risk Society
Meng Zh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easures of non-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administrative admonishment is often used by administrative organs to regulate the behavior of administrative counterparts in practice. Although there are explicit provisions on admonishment in law, the legal effect and space of its application are not clear, which leads to the abuse of administrative admonishment in administration. Most of the current theoretical research results focus on the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f the nature of the admonishment behavior, and les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space of the behavior. This paper takes the analysis of legal regulations and practical cases as the entry point, distinguishes the behaviors similar to administrative admonishment such as warning and ordering correction in the substantive sense, and constructs the legal effect and application space of administrative admonishment application.
Key words: Correction; Effect; Circumstances
——对训诫法律属性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