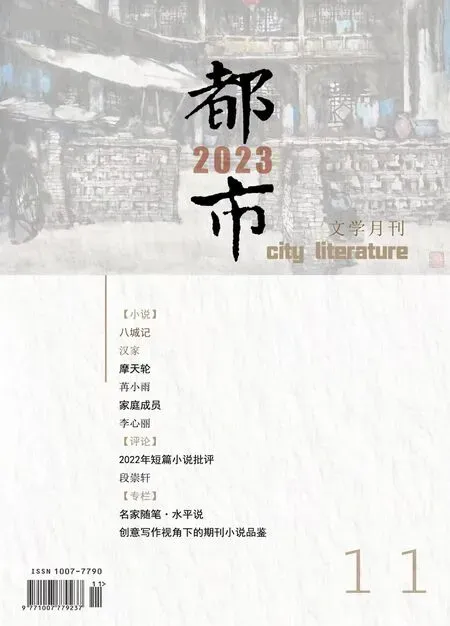月光下的凤尾竹
文 贺虎林
1
认识小山是在半年前,我们老两口从上海回来那天。外孙刚满月,老婆就拽上我赶快逃离。坐在飞机上,她一路捶胳膊,好在手机把时空捏巴得只有巴掌大,俩小时航程,提前下载的仨帖子没扒拉完就到了。
我们手拉肩背爬上楼,刚要掏钥匙,突然发现我家门头顶上吊了一只乌幽幽的圆疙瘩,老婆的快意霎时蒸发掉一半,瞪起眼睛问,那啥玩意儿?
我仰脸瞅瞅,像个摄像头。
摄像头?谁安的?
估计是对门吧。
他家……住人了?老婆说着,回身就嘭嘭拍响了那扇棕色防盗门。连拍了三遍,没回应,待要再拍,嘎巴一声响,一股浓烈的骚臭味扑出来,熏得她连退好几步,差点被皮箱绊倒了。
一颗光头从门缝擩出来,嘿嘿,你找谁?
找你!老婆从指缝里崩出两颗“爆米花”。
那光头两粒绿豆小眼动了动,嘿嘿,有甚事?
这是你家安的吗?
是,嘿嘿。
谁叫你安的?
嘿嘿,不知道。
那光头说一句,嘿嘿一下,惹得我老婆动了怒,跟你正经说话呢,嬉皮笑脸嘿嘿啥?
嘿……阿没嬉皮笑脸,阿真的不知道。
你家安的你能不知道?
不知道,阿是他家的保姆。
老婆一听泄了气,瞅着他手里捏着的卫生纸,问道,保姆你来啰唆啥?叫主家出来说话。
主家……出不来,嘿嘿。
那晚,老婆把床单都快轧破了,一向矜持的她,仿佛受到天大的侮辱。女儿在视频里说她,叫你们别回别回,你就是不听。
老婆说,这关回不回啥事?不回来他们就不安了?走了才俩月,就糟害成这样子。
随他糟害呗,那老破楼了,干脆卖了跟我们住得了。
你说得轻巧,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不知道住进去一家什么人,跟保姆说了半天话,都不露个脸。
打电话问问安伯伯,看他把房租给谁了,让他跟他们说。
安厂长早跟儿子出国了。
那就问物业。
准不是什么好人家,雇个保姆,还是个男的。个儿没板凳高,脑袋长得像土豆,眼睛还没芽眼大。连句话都说不清,张口嘿嘿,闭口嘿嘿,跟个傻瓜差不多。
我在一旁说,别这么说人家好不好,你教导了别人一辈子,老也老了,还……
老婆说,还什么?谁叫他们侵犯我的隐私权?
我说,关那保姆什么事?找不到阎王你骂小鬼。
2
第二天一早,我就跟着老婆去了物业办,物业老张说只知道住了俩老人,其他情况不清楚。
老婆说,要你们物业干什么吃的?小区住进啥人都不知道?楼道里安了什么设备都不过问?
老张说,好我的冷处长,咱厂的家属楼卖给个人多少年了,物业哪里管得住?
老婆说,那这事归谁管?
老张说只能找主家,要么找公安。
老婆悻悻朝回走,一路跟谁也不搭腔。进得单元门,她连着咳了几声,紧走几步,抬头见三楼扶栏上仰着个迷彩服,就立即大声喝道,谁在楼道里抽烟?
迷彩服哧溜转过身,不叫抽?嘿嘿,不叫抽阿就不抽了。说着就把烟蒂朝栏杆上摁。
我老婆已经到了跟前,指着栏杆威严地说,擦掉!
那保姆愣了愣,阿擦、阿擦,说着捏住袖口擦起来,边擦边赔着笑脸问,大妈早早去锻炼了?
大妈?我有那么老吗?我老婆的表情更难看了。
哦,不老不老,嘿嘿,那保姆赶紧又恭维,你们城里人,眉眼看不出老不老。
我赶快上来解围,你就叫她冷姨吧,大家都这么叫。
冷……嘿嘿,世上还有姓冷的?保姆在屁股上边擦手边自语,一抬头,见我老婆眉头上那俩“苍耳”快要崩开了,赶紧说,冷姨好、冷姨好,阿姓苟,叫小山,阿家这姓也稀少。
老婆竟扑哧笑了,不过语气依然很凌厉,你的名字倒是不稀少。
我进一步为他解围,对他说,我老婆得过气管炎,以后你要抽烟,要么到院儿里,要么去阳台上,安厂长家的阳台不是没封吗?
他说,阳台上不能抽,人家有监控。
我就问,为什么到处安监控?你家主人是干啥的?
他说,阿也说不清,合同是家政公司签的,阿才来十几天,前几个都干不下去,才派阿来了,阿是男的,有力气。说着握起拳,比了个秀肌肉的动作。
我问,你哪里人?
他说垒梁的,晓得吗?垒梁,山西最有钱地方,到处是煤矿。
我乐了,是吕梁吧?
他嘿嘿笑,说对对,垒梁,垒梁,阿的普通话没你们说得好。
逗得我老婆又笑了,说,你的“阿”比我说得都标准。
小山的脸马上红成了猴屁股,说阿改,阿改,以后不说“我”了。
弄得我老婆越发哭笑不得。
下午去买菜,跟他又撞见,见我买得多,就说老哥我帮你拿上些。我说,你的“阿”果然改得快。不过,你叫我老婆冷姨,咋能叫我老哥?
他说,我看见冷姨的头发都花白了,你的还黑黢黢。
我哈哈笑,说我这是伪装的,我老婆爱本色,她要听见,你又得挨剋。
他小绿豆眼眨巴两下,说你老婆真厉害,眼睛、嘴,比山里长的刺芥还扎人。
我说有那么厉害吗?
他说有,还压低声音问,你是不是也怕她?
我笑,说可不是,要不大家怎么不叫我老张,叫冷伯?
他惊讶地睁大眼,原来你不姓冷啊?
我说,是呀,奇怪吗?
他嘿嘿说不奇怪、不奇怪,转而问,冷姨原来干啥的?
我说搞政工的。
他小绿豆眼又骨碌两下,那你呢?
我?搞技术的。
他咧长了猴下巴,我一看你就是个大知识分子。
我嘟起五官说,我老婆的文凭比我高多啦。
他笑得眼睛都没了,说看你也是个怕老婆鬼。说得我脸颊还真红了。
3
那晚看完《新闻联播》,老婆迫不及待拿起她的葫芦丝练习起来。
我呢,带着任务敲开对面301 的门。开门的是位中年女士,卷发,戴围裙,听了我的介绍,客气地将我延至客厅。
沙发上坐着位白发老先生,女士说来人了,他仿佛没听见,我主动过去跟他握手问好,他瞅都不瞅我一眼,继续盯着电视屏幕。那女的笑笑,说你坐吧,然后走进厨房去。
我待在那儿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搞不清这位老同志为何这般不友好,更厘不清这两位是父女关系,还是“梨花海棠”。忽然听见阳面卧室里有人说话,我便朝那面踱过去。
里头说话的是小山,他正给一位卧床者收拾屎尿,边擦拭边絮叨,臭死了、臭死了,你老人家总是拉下了才呼叫。
我鼻孔即刻灌满浓烈的气味,搞得又是进退维谷。好在小山抬头看见了我,嘿嘿说,冷伯你来啦?快离远些离远些,不然会呛死你。我才趁机赶快退回客厅里。
那位女士从厨房出来,见我还站着,又说你请坐,然后解下腰里的花围裙,再去衣架上取外套。
我忙问,晚上不跟父母住?
她说,我是钟点工,只负责一日三餐和打扫房间,看护老人的事儿,由男保姆负责。
我问,那老人的子女呢?
她说,在国外。
几个子女?
两儿一女。
我惊讶起来,三个儿女都在国外吗?
她说,可能是,反正一个也没见过。
那你们怎么联系?
她抬手指指天花板,上头也安了个黑黑圆圆的东西。说完她过去跟小山打了声招呼,便朝门外走。
小山在里间喊,黄姐你注意安全!
我趁隙到其他房间看了看,见每间都有一个摄像头,忽然感到很不安,甚至有一点慌乱,仿佛头顶悬着个千斤闸,随时都要掉下来,又仿佛自己是个偷窥者,随时都会被发现,于是赶紧又退回客厅。正寻思要不要离开,老先生突然站起来,竖起右手大拇指高声冲我说,我的孩子们,个个是这个!说着展开双臂,做了个雄鹰展翅的动作。又说,我从小教育他们,要放飞理想,放飞理想。
我吓了一跳,为不失礼节,只好也竖起大拇指,同时用异样的目光打量他。他个子比我高出半个头,至少一米八,人又瘦削,越显得颀长,简直像根旗杆子。我笑问,老先生高寿?
他叉开虎口比画个“八”,又朝背后房间指一指,拇指食指中指捏一起,然后勾了个“九”。哦,我明白了,他八十,屋里的老伴儿七十九。我说老先生好福气,他呵呵点点头,上牙床露出一排空洞的豁口。
小山拎个鼓鼓囊囊的塑料袋出来,说,冷伯你先坐,我下楼扔了这些擦屁股纸,顺便抽根烟,不然嘴里、鼻子里都是屎尿味。
我说你快去吧,我也回去了。
刚走到门口,突然又听到丁冬一声响,接着是一个机器少女语音的呼叫,“我要解手,快来帮我。”
我还没反应过来,小山已撒腿跑回卧室,边跑边说,阿老天爷,刚收拾干净,你又拉下了。
看来还是远程监控啊。听完我的汇报,老婆把葫芦丝朝茶几上一丢,眉头又蹙起来。
我说要不就算了,他安就安着吧,反正咱俩“退伍兵”,有啥怕见人的?
老婆说不行,每天进出被盯着,像坐了监狱,算怎么一回事?
我说,估计是为了观察父母。
老婆说,观察父母他们安屋里,干吗安在走廊里?顿一顿又说,一家什么人,老太太卧床,雇个男保姆,也不嫌寒碜。
我说准是不得已。再说了,妇科病人难道不用男医生?
老婆说,去你的,哪儿跟哪儿?说着捉起葫芦丝,继续吹她的《凤尾竹》,刚吹了一句又停下来,把葫芦丝朝茶几上啪嗒又一丢。
4
老婆的血压又偏低了,我下楼去给她买药。小山提着两袋蔬菜回来,我问为啥不叫黄姐顺道买。
他说,主家规定的,她做饭,我买菜;我花钱,她管账。
我买完药回来,见他叼支烟蹲在垃圾筒旁边,便又问他老太太得的什么病。他说脑出血,半拉身子不能动,话也不会说了,但是知道大小便,一会儿要拉,一会儿要尿,不停地收拾。
我说为什么不穿尿不湿。他说人家儿女不叫穿,怕把老太太屁股腌烂了,还叫定时翻身,白天半小时一翻,晚上一小时一翻。
我说那你还睡觉不?他说没办法,前面几个熬不行都走了。
我说你能熬行吗?
他说熬不行也得熬,钱难挣,屎难吃,不过我睡觉还可以,脑袋挨着枕头就睡着了。
我说你睡着醒不了咋办?
他揉揉一圈乌青的眼,老太太会摁呼叫器,人家的孩儿们也在监控里常提醒。人家子女们孝顺,时刻盯着呢。
我老婆听了撇撇嘴,这也太孝顺了。
女儿在微信视频里说她,还是留在国内好吧?当年还嫌我不努力,抱怨我考不过雅思、托福,现在看到了吧?要是我出了国,你们也是这下场。这回,老婆没有怼女儿。
“七一”快到了,省老年大学葫芦丝班加紧了排练,庆“七一”文艺会演,给他们安排了俩节目,一个红歌联唱,一个葫芦丝经典曲目《月光下的凤尾竹》。老婆每天忙着练曲,家里、公园、老年大学三点一线屁颠屁颠跑,暂时忘却了监控器那档子烦心事。
演出那天,早早吃过晚饭,老婆就拽上我直奔文化宫。演出进行得很顺利,他们的表演获得了阵阵掌声,党的生日嘛,再没有比“妈妈呀妈妈……亲爱的党啊”更贴切,更叫人激情澎湃、热血沸腾了,而《月光下的凤尾竹》又那么柔美。坐在回家的大巴上,大家还沉浸在激动和兴奋中,我老婆也是神采飞扬,仿佛又回到了工作岗位。
回到小区,刚跨进单元门,她欻地又跳出来,情绪顿时从夏变成冬,捂住嘴闷声喝问,怎么楼道里这么臭?
我抓着门把手把头伸进去,的确有一股大粪味,猜道,可能是地下室排污管道漏了吧?
老婆说,那快去叫物业来修理。
我说,这么晚了找谁去?回家给他们打个电话吧。
老婆趑趄不前。她爱干净,干净得甚至有洁癖,连小外孙拉下了,都是戴着口罩、手套去收拾,顺带还要批评两句。这些年,因为卫生问题,我们父女俩没少挨她的剋。
我拉着她快步朝楼上走,说嫌臭还不快点进家?但是越往上走,臭气越浓烈,等上到三楼门前时,我一下愣住了。不等我开口,老婆已经嚷嚷起来,怎么把这么多臭垃圾丢在门外?说着推开我,冲上去就要拍对家的门。
我赶紧一把拽住她,别别别,可能小山刚睡着,不要把他吵醒了。
她两眼倒竖,大声吼道,他怎么能把手纸丢在这儿?里头有多少细菌啊!
我推着她说,先进屋先进屋,回头我叫他来处理。
她进了屋咣当一声就把门磕上了,我犹豫几秒,迅速捏起那两大包污物捂着鼻子跑下楼。
回到家,老婆坐在沙发上继续怒不可遏,见我进卫生间去洗手,马上问,是你替他扔了?
我说怎么可能!
老婆说,那咋没听见他家门响?
我说,小山正好出来了。
老婆上下打量我几眼,像对着小山一样厉声说,明天告诉那“土豆”,以后“三不准”:一不准楼道里抽烟;二不准门前堆垃圾;三不准帮你拿东西,特别是蔬菜、食品。手上不是屎就是尿,拿回来还叫人怎么吃?
我说,行啦行啦,人家帮你还嫌人家。老婆说,我不需要他帮。
我说,干吗和个打工的过不去?
老婆说,是我和他过不去,还是他们太欺负人?
我说,这怎么是欺负咱呢,你知道他有多辛苦?
老婆说,再辛苦也不能把擦屁股纸堆在别人家门口吧?
我说,老婆啊,先前在台上你的表演多温情,怎么到了台下,就变得这么冷漠啊?我看舞台上镰刀锤头两边那八个字,你连瞅都没瞅一眼,还表演呢!
老婆说,那还用瞅,早都化到心里了。再说,瞅不瞅关表演啥事儿?
我说睡吧睡吧,越说越讽刺。
老婆说讽刺什么?
我说你我的党龄,比小山的年龄都大,你说讽刺什么?
她一怔,但马上说,你不是说家里是讲感情的吗?怎么今天也给我讲开大道理了?
我说,这不都是你长期培养的结果?总不能手电筒永远捏在你手里。
她嗖地抓起葫芦丝盒,又嗵地扔下。
5
从此,我老婆的神经绷得比弓弦都紧了,一听见对门铁门响,立刻支使我或者她亲自到猫眼上瞅,有时躺在床上听见了,也要爬起来去观察。有几回,果然看见小山站在楼道里,马上打开门检查,吓得小山赶紧朝楼下跑或钻进家。
立冬那天,老婆的表姐打来电话,说自己右乳房里摸着个杏核大的疙瘩,老婆一听马上说,那赶快去检查呀。她表姐说到县医院查了,怀疑是肿块,建议去省城或北京进一步检查。老婆说那就赶紧来,我们葫芦丝队里就有一位乳腺癌专家。
她表姐第三天就来了,却碰巧火车晚点,下午四点发车延迟到五点,我们也只好顺延到晚上十点才出发去接站。一开门,小山正好站在楼道里,我俩出来得突然,他来不及躲,只好蜷着身体趴在栏杆上。我老婆先睁圆了眼扫视一圈楼道,又用鼻子四处闻了闻,突然问他,你半夜三更经常站在楼道里做什么?是不是等着我们睡了抽烟或者丢垃圾?
小山说,不是不是,我早就不在楼道里抽烟、撂擦屁股纸了,不信你问冷伯伯。
我说是是是,再没见他抽过、扔过。
老婆狠狠瞪我一眼,又瞪住小山,那你每天晚上站在门外干什么?
小山说,不干什么,楼外冷。停一停又嗫嚅道,我听见你在家里吹那个响响,嘀嘀嘀,哒哒哒,很好听。
我老婆歪他一眼,那叫葫芦丝,什么响响。
小山说,葫芦也能吹响响?阿家院里每年都种几棵葫芦,长成了一劈两半搲米舀面当水瓢,你要要了,我过年给你捎俩来。
小山脸颊红红的,带着一种讨好的神色。我老婆却像没看见,头也不回地说我不要!跨出单元门她又对我说,以后再给他加一条:半夜里不许站门外,怪吓人的。
老婆的表姐查出来是乳腺癌,很快做了切除手术,从住院到出院,我俩轮流着陪侍了六个星期。出院前一天,老婆又去帮着办手续,离开医院时感到有些头晕。她低血压,一辈子经不住累,禁不住饿,一不小心就会出现低血糖。女儿生完孩子刚满月,她说要回家,撇下就回来了。这回她表姐来省城住院,我知道她是强撑着,我说有我去就行了,她不依,说她表姐小时候对她怎么怎么好,又说她外甥白天晚上一个人熬,她不忍心。最后那几天,我俩都累得像霜打过的秋菠菜。终于可以出院了,她在电话里长舒了一口气。
我在家炖上排骨,烧上洗澡水,然后站在阳台上守望她。楼下的解放路车流滚滚,过街天桥上人头攒动,上下公交车的乘客像蚂蚁,菜市场打烊杀价的叫卖声浊浪排空。我眼睛不停地在公交站、过街天桥及小区大门间逡巡,眼见最后一抹夕阳余晖从金融大厦的尖顶上逝去,迎泽公园内的摩天轮也停止了转动,还是不见她人影。给她打手机,提示关机了;又给她外甥打,回说她姨临走时手机快没电了。
我悬着的心放下来,坐到沙发上打开电视,正看到梅西发点球,一阵踢门声咚咚响起。我嘟哝,你自己没有带钥匙?
打开门却是一个压弯的身躯,背上扛个人。我惊叫,老婆你这是怎么啦?
却听见小山在她身底吃力地说,冷伯快些快些,看往哪里搁?
我赶忙扶住他俩走进卧室,慢慢将她放到床上,老婆缓缓睁开眼,有气无力地说,快……糖、糖。
我跑着拿块方糖塞进她嘴里,又为她沏了杯红糖水,回身问小山,你在哪里碰到她的?
他说,一楼台阶上。阿下去倒垃圾,差点绊倒了,还以为是谁家的狗卧在那儿,拍着感应灯,看清是冷姨。阿要问,又不敢,手里提溜着腌臜东西。跑出去把垃圾扔了返回来,见她还塌靠在栏杆上,脸上冒着汗。阿喊冷姨冷姨,她不应,也不睁眼,阿觉着不对劲,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拦腰把她扛上来了。
我说谢谢啦,太谢谢你啦。
他说,谢甚谢,别说是人,就是个猫猫狗狗,看着伤了病了,也不能不管。阿只是怕冷姨嫌我……嘿嘿阿赶紧回呀,该给老两口喂饭了。
老婆在床上躺了半个月,再没提“约法四章”的事。我戏谑,要不要写张告示贴楼道里?
她抓起枕巾砸向我。
我说,还是远亲不如近邻吧?想想那天多危险,要不是小山碰上……咱可得好好酬谢一下小山。
老婆说,别小山、小山的了好不好?听着真别扭。
我说,那叫啥?总不能叫他老山吧?
老婆说,叫……小苟子吧。
我说,嚯,一下子变成宠物了?
老婆睨起眼,咋?吃醋了?
我哈哈大笑,我用吃他的醋?我巴不得你能像待你外甥一样体谅他,你外甥白天还能睡个囫囵觉,他每天,连俩钟头的完整时间都没有。
老婆说他为啥不叫老婆来帮他?或者干脆把黄姐那份活也揽下,多合适。我说这话我早问过,他说主家不肯,他老婆也来不了,家里还有爹妈和俩孩子。
老婆说主家为啥不肯?总比小苟子给老太太收拾好。
我说主家叫黄姐做饭他买菜,黄姐记账,他花钱,意图不是明摆着吗?
老婆说,这么说来,那摄像头是监控俩保姆的?
我说至少兼而有之吧。
老婆说,要这么着,门口那个更得叫他们拆掉。
6
冬日的阳光像金子,洒在长长的阳台上,我和老婆仰躺在藤椅里,享受着上天的恩宠。我家的阳台也没封,全厂大部分人家的阳台都没封。“军转民”之前,我们的车间都在山洞里,于是大家对太阳,便有了份特殊的情愫,谁也不舍得把她恩赐的紫外线隔在玻璃的外头。
对门老先生也来到阳台上,手里抱颗大篮球。我瞧见了站起来,隔着水泥栏跟他打招呼,他却仿佛不记得我,自顾自玩起篮球来。左手拍几下,右手拍几下,动作很娴熟,还不时做个跳起投篮的动作。
我惊讶,冲他大声问,老先生以前是运动健将吧?他抱起球拍拍自己的胸脯,我,当年是省教工队前锋。
我说,一看您就身手不凡,原来哪个学校的?
十七中。
你老伴呢?
也是十七中。
为什么搬到这里来?
学校教工宿舍拆迁了。
老先生继续拍篮球,拍着拍着转过身问我,你是哪个学校的?
我不明白他所指,便说我是北航的。
老先生说,北航的?我二小子也是北航的,老大清华的,女儿交大的。
我说,您培养的孩子都很优秀。
他说是的是的,我从小教育他们,要放飞理想。说着把篮球搁阳台上,又比画起那晚的动作。一阵小风吹过来,把篮球旋下了阳台。
楼下传来呵斥声,谁往马路上扔篮球?
老先生扒在阳台女儿墙沿上,像个孩子朝下喊,把篮球给我,把篮球给我,说着撩起长腿就要朝墙上趴。吓得我急忙伸出手去抓,小山从屋里冲出来,拦腰将老头抱下去。
老先生很生气,你干吗拦我?
小山说,不要命啦?你要摔下去,阿可赔不起。
我问小山刚才在干吗。他说坐着睡着了。
我老婆说,看来你得把阳台门锁死。
小山说,人家子女不叫,要他爸在这儿锻炼、晒太阳。
我老婆说,他们想得真简单,不考虑安全,也无端给你增加责任和负担。
小山说,咱挣了人家的钱,就得听人家的。
我老婆问他每月挣多少。
小山说,扣了管理费不到点四千。
我老婆说,这么少?还不及月嫂的一半。
小山说比种地强多了。
小山拉着老先生朝回走,我老婆突然叫了一声,小苟子,你等等。
小山扭回头,表情疑惑地问,冷姨是叫我吗?
我老婆脸上泛起红晕,说没事,没事,你忙去吧。又瞅着小山的背影说,还没咱辰辰个子高。她坐回藤椅上,又怅望着蓝天喃喃道,看来把孩子培养得太优秀了,也不一定都是好事。
我讶异她今天的言行举止怎么有些怪,又不好问,就附和说,所以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心里却在想,上帝为什么不能像太阳一样公平呢?
7
老婆没有明确表态是否请小山吃饭,也没再提摄像头的事,却拽了我,要去逛商场。我问是给小外孙准备周岁礼物吗?她不答,只管催我走。到了商场,先直奔波司登专柜。我说不到一岁的孩子,能穿羽绒服?她仍不搭腔。服务员小姐迎出来,说欢迎光临,大姐是给自己选还是给大哥选?
老婆说男士的,但是比他矮。
服务生瞄瞄我,问比大哥矮多少?
老婆用手比在我耳根,大概……到这儿吧。
服务生说有一米六,胸围呢?
老婆说比他瘦。
服务生问多大年龄?
老婆说四十上下。
我乐了,瞅瞅她。
服务生说那您看看这两款,一长,一短,颜色什么的都有,那个年龄段,建议您选这两种颜色。说着取下一款明黄一款大红的。
老婆问我哪个好。
我审视几眼摇摇头,说还是买个蓝的吧,或黑的,这两款,不耐脏。
老婆说,我看这个红的好,每天守着俩老人,太暮气,穿个红的,添点喜。
服务生就顺着她怂恿,对对对红的好,说着贴到我胸前,大哥您穿也没问题,您去镜子前照照,至少年轻二十岁。
买完羽绒服,又来到运动服专柜。我说,嚯,老婆今儿个是“大动干戈”了。
她说要买就买好一点儿。
我说小山不会在乎名牌不名牌。
她说实诚人更不可糊弄。
我说,不是那意思,我们可以用这钱,给他多买几套。
那天,我俩买了一件羽绒服,两身品牌运动服。又去超市买了俩最大号的塑料密封盖收纳箱,拎得我出了一身汗。
小山红着脸坐在箱盖上,试了这身试那身,嘴里一个劲嘿嘿说,这得多少票票啊,我可不敢要。
我老婆假装沉下脸,像训斥孩子似的说,别啰唆,叫你穿你就穿,给老太太收拾时,外面套上你的迷彩服,出去买菜,就穿这几件。
小山指着羽绒服说,这么红,叫别人笑话死。
老婆说,谁笑话?穿得脏才有人笑话,自古笑贫……你就听我的,以后不许再穿着迷彩服出去。
小山嘿嘿瞅着我,冷伯你说阿能穿出去?
我说,咋不能?我都能穿,你去镜子前瞧瞧,多精神。
小山说,不照了不照了,你们送给阿穿,阿还挑剔甚?
试过了衣服,小山忽然嗫嚅着问,冷伯我能不能留你个电话?
我说能呀,电话、微信都可以。说着报出手机号。他一边按键一边说,其实阿留你的手机也没啥用,阿不会随便给你打。就是想你们的孩子也不在身边,一旦有个啥需要,你们可以给阿打电话。
我说,是,远亲不如近邻,不过你也可以给我打,谁没个需要帮助的时候?他输完号码给我打过来,我正要回拨试一试,客厅里响起“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歌声,他接起来,是黄姐,说饭熟了,快回来喂老太太。
他搂起衣服朝外走,我老婆喊住他,把这俩收纳箱也拿去。
他说拿去做甚用?
我老婆说,天冷了,晚上不要再一趟一趟朝楼下跑,把这俩箱子放阳台或门口,每次擦下的手纸包起来扔里头,天亮了再去倒。
小山这回没推辞,眨巴着红红的眼睛离开了。
8
我微信里多了个新朋友,他的昵称是“吕梁山药蛋”。我老婆笑,他也把自己当土豆。
我说这是自谦,就像我叫“冷饮店小二”。
老婆把我的手机拍到了被子上。
我俩聊得很欢实,打字速度不分伯仲,只是他错别字比我多,“冷伯”常打成“冷白”。
老婆说,叮嘱他晚上锁好家门阳台门,防止老头犯痴跑出去。又说,告诉他可以适当给老太太穿个拉拉裤,每四小时换一换,既腌不烂皮肤,他也能睡个安稳觉。
小山回,那不行,人家儿女有规定,咱不能瞒人家,拿了人家的钱,就得替人家尽孝心。
我老婆说,这实疙瘩,一切从实际出发嘛,只要保证不生褥疮,干吗这么死搬教条?我把她的话有选择地给小山发过去。
小山回复说,尿不湿不透气,捂得老太太不舒服,四个钟头不翻身,会压得身上疼,阿不忍心,咱也有老人。大爷大妈有孩儿跟没孩儿一样,躺在床上孤零零的,看着真恓惶。
我老婆听了长叹一声。
偶尔我也跟小山逗,问他想家不。
他说想孩儿们。
我说不想老婆?
他嘿嘿。
我说你说实话,他说想也白搭。
我问那想得不行了怎么办?
他说不行了就找人放一炮嘿嘿。
我呵呵笑起来,老婆问傻笑啥。
我念给她。她呼地坐起来,他真做那种恶心事?若果真有,从此滚得远远的!
我说,好,我把冷处的指示传达给那小子,叫他如实交代。
老婆抓过我的手机扔床上。
小山又发过来,唉,我哪有钱光要子(逛窑子),就是有,也没时间。我家里有老婆,将心比心,人家要跟别人睡了,咱是啥滋味?
我老婆拿起看了说,这还差不多。随手把手机撂给我,又说,以后不许跟他聊这些。
我说那聊啥?
老婆说,他不是爱听我吹葫芦丝吗?以后想听,就进家来听,或者……你跟他视频,我吹给他听。
我原话发给了小山。他马上回过来,我可不敢叫冷姨给我吹,我是收拾了屎尿屋里臭得不行,在门道里透透气,又不敢抽烟。不过,听着冷姨吹的葫芦丝,也跟抽烟差不多,听着听着,鼻子、嘴里就不臭了。
我一字不落地念给老婆听,她捂住嘴把脸扭到一边去。
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小山像个红绒球在院里院外跑,老婆瞭见他总呵手,又送他一副毛手套,还给他手机上下载了《月光下的凤尾竹》。
女儿在视频里问我们过年去不去上海。老婆说不想去,潮渍渍的被窝比当年钻山洞还阴冷。
女儿说我们有空调。老婆说有空调也不去。
小山发来条微信,问手机上火车票怎么买。
我说你要回老家?
他说寒假孩们想来看看他。
我说叫你老婆也来。
他说老婆走不开。
我说,你少扯,把仨人的身份证号发给我,我叫我女儿帮你买。
9
一场大雪跟着腊八的脚步降下来,把整座城市拉进了童话里。迎泽公园的几株蜡梅迎雪绽放了,睡梦中似乎都能闻到幽微淳朴的香。我把单反相机准备好,跟老婆披挂整齐出了门。

孩子们在晶莹的雪地上打滚,红男绿女把几株橙黄层层围住,我俩只好站在远处,闭了眼与香魂神交。
女儿的微信发过来,火车票买好了,到站时间明天中午十二点。
我随即转发给小山。
赏梅的人终于稀疏了,我俩款款来到梅树前。老婆年年都要与梅雪同框,说喜欢这些严寒中仍给大地增香添彩的草木。
天光近午了,我们朝回返,步出公园门,穿过人行道,拾级爬上过街天桥,老婆突然心血来潮,要拍一张以自家阳台为背景的迎风吻雪照。我端起相机慢慢调焦距,正要按快门,突然发现镜头里有个人趴在我家阳台上,不,不是我家,是对门安厂长家。
我的天!我惊叫起来,对门那老先生爬到阳台墙上了。老婆快、快给小山打电话!
老婆说,我哪有他电话,你快打!
我慌忙掏出手机,颤巍巍找见小山的号,喂喂小山吗?老先生爬到阳台墙上了,你赶快把他抱下去。
啊呀冷伯,阿不在家,阿从菜市场刚出来。
我说那咋办、那咋办?
老婆在桥上大声喊,快救人呀,老人家要从阳台上摔下去了!
桥上的人顺着老婆手指的方向望过去,也一起声嘶力竭地喊,可都被桥下蜗行的汽车喇叭声吞没了。有人说快打119,我老婆捶着栏杆说,来不及了,来不及了,赶快另外想办法!
一个年轻人突然指着楼下喊,消防员来啦!
我定睛一看,果见一个鲜红的身影,像头猎豹朝楼下扑过去,十米、五米、两米……
啊——
所有的人同时爆发出一声惊天裂地的呼喊,老先生像根水泥电杆栽了下去……
入夜,女儿发来条抖音热搜,急切地询问,那楼房咋跟咱家的一模一样呢?爸妈你俩没事吧?
老婆回“没”,后面贴了一串流泪的表情图。那条视频的点击量已经过十万。
第二天中午,我和老婆守在火车站出站口,手里举块纸牌子:接吕梁护工苟小山妻子和孩子。
我俩一再互相告诫对方不许哭,可她胸前的黑围巾和我的大衣翻领上,早已结满白花花的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