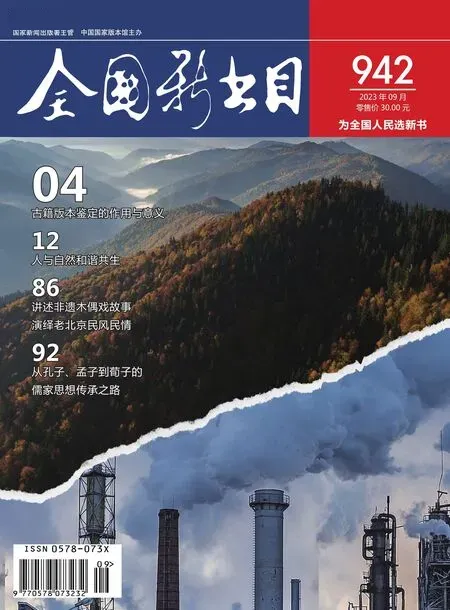一棵松,塞罕坝最老的松树
张秀超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等一等日子》《飘荡的乡音》《骨笛》等著作,散文作品发表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艺术报》等报刊。曾获冰心散文奖、孙犁散文奖、全国梁斌小说奖、《北京文学》重点优秀作品奖等奖项,散文《来看你,塞罕坝》被收入《新中国散文典藏》。
隋明照
新闻与传播硕士,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作品发表于《中国青年报》《四川文学》《西安晚报》等报刊。曾获2015 年度“濠江杯”“逐梦中国·我的读书故事”全民阅读征文二等奖;小说作品获第五届全国高校文学作品征文优秀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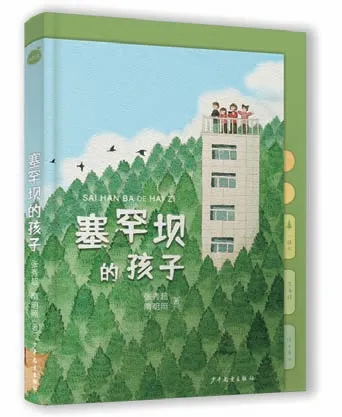
《塞罕坝的孩子》张秀超 隋明照 著/少年儿童出版社2023.1/48.00元
星期天,大头开着越野车载着花儿、小丫和我,去看我们的树。我们决定先去看望老松树,那是塞罕坝最老的一棵松树。
那棵松树立在一个高高的风岗子上,远远就能够望见它巍巍屹立在山巅之上,远看,它好似是一个人站在那里,手搭凉棚,向远方张望着。
小的时候我们就常来看它。我们上坝给栽树的亲人们送东西时,总喜欢在老树下歇阴凉。我们上坝挖药、采菜、捡蘑菇时,总把大白口袋、木头篓子放在树下,让老松树给我们“看”着。我们拿着小木条筐儿采山货,采满了一筐子就跑回到大树下放进口袋或者木篓子里,再拿着筐子去采。等跑饿了,我们就坐在老树下吃干粮;有时累极了,我们就靠着老树打个盹。每次离开老松树的时候,我们总喜欢抱一抱它,就像与亲人告别一样。
老松树有青苍苍的躯干,黑黝黝的老树皮,干巴巴的,一层一层,又硬又厚,一碰就落下来一片,就像鱼鳞一样。每次抱老松树,它总送我们几片黑苍苍的树皮,我们舍不得扔掉,就放进衣服兜儿里,回家放在铅笔盒中,它散发着隐隐的香气,那是松香。
荣军爷爷带我们上山栽树、采野菜的时候,来回总喜欢在老树下歇歇脚。荣军爷爷每次来到老树下,总要拿出烟口袋,点上一袋烟,抽着烟,仰头对着老树仔细地看。我们问他看什么,他说,我看看它又被伤着没有。
我们问荣军爷爷这树有多少岁了,荣军爷爷捋着胡子,说他小的时候也问过他的爷爷,他爷爷也回答不上来,只说很早的时候老松树就在这大山上站着了。人们都说,这棵老松树有二百多岁了。

荣军爷爷抽完烟,总要站起来围着老松树走几圈,他抚摸着老树对我们说:“你们要是看到酷夏严冬里老松树都经历了什么,你们就知道它能活着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荣军爷爷告诉我们,老松树立在塞罕坝高原,在这样一个八面来风的山岗之上,海拔有一千多米,山高风烈,冬天大风卷着白雪,呜溜呜溜吼叫着,像一群群怪兽一样扑向老树,总想要把它连根拔起,它的头曾被大风拦腰刮断,夏日里“咔嚓咔嚓”的闪电总围着它炸响。一年夏天,一个大霹雳打下来一个大火球落在它的身上,烧焦了它的半边身子……年年岁岁,它被大风打,被冰雪冻,遭雷电烧,它伤痕累累,满目疮痍,可它总也不倒,一直威风凛凛地挺立在山岗之上,就像一位战场上坚守阵地的老英雄。
老松树不是参天的大树,树干又不那么光滑,爱上树的大头总想爬到树顶上去看看。荣军爷爷不许大头上树,并告诉他:“永远都不许爬这棵老松树,它是塞罕坝人的老功臣!”
荣军爷爷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塞罕坝早已沦为白茫茫的大沙漠,哪儿都见不到树木。后来,国家决定治理这片大沙漠,要在这里建林场种树,可这荒漠上能不能长成树,在人们的心里打着大大的问号。几个考察的人骑着大马在塞罕坝跑了好几天,终于在荒原上看到了这棵老松树,望着它沧桑的模样,人们激动得热泪盈眶,茫茫的荒原只有这么一棵老松树独独地屹立着,人们称它“一棵松”。一棵松就像一面旗帜,它告诉人们,塞罕坝的荒漠能够栽活松树。于是,人们在塞罕坝搭起了草窝棚,开始开荒种树。
可是栽了两年都没能栽活几棵树,人们愁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寒冷的塞罕坝到底能不能够栽活松树?这样的怀疑又在人们的心头盘旋,每当情绪低落的时候,只要看看一棵松,看到这棵巍然挺立在荒原上的老松树,人们就又有了信心:塞罕坝荒原能够活这一棵松树,就能够栽活千百万棵松树。
有了这样的信念,种树人又打起精神,一定要在塞罕坝栽活松树。后来人们发现,从外地运来的松树苗儿不服塞罕坝的水土,所以栽下的小松树苗儿都没有成活。再后来,种树人把松树籽儿放在雪里冷冻,用接受塞罕坝冰雪洗礼的松树籽儿育出了自己的小松树苗儿。
那年早春,在料峭的春寒中,一帮年轻的种树人把一棵棵自己亲手养育的小松树苗儿栽种在塞罕坝大地上。一场春雨过后,小松树苗儿吐出了小绿芽芽——小树苗,活了!
旷野的风似乎也欢笑着,在大荒漠上奔跑着呼喊:活了——松树苗——活了——
一群年轻的种树人跑到老松树下,围着老松树又唱又笑,他们高兴地告诉老松树:“我们栽的小松树活了!”
从此,塞罕坝种树人开始围着一棵松在荒漠上栽松树。一棵松给了人们信心,种树人坚定地栽下一山山、一岭岭的松树,使塞罕坝由荒漠变成了绿洲。没有一棵松,就没有塞罕坝的今天,所以人们又送它一个名字:功勋树。
我们像儿时一样围着老松树转圈,老松树没有漂亮的树冠,也没有婆娑的枝条,它说不上有多么美丽,可天南海北来塞罕坝看风景的人都要来看看这一棵松。为了保护这棵老松树,人们会用大红布一层层地包裹住它下边的主干,还围着树根垒了一圈石头。
塞罕坝山高雾重,跑山人常常迷路,如果迷路人远远看到一抹红红的亮光,就奔着那里走,找到一棵松就是找到了家。就这样,一棵松成了山里人的指路航标。
当地人感念一棵松,谁家里有好事都会在树的身上挂个红布条,报个喜讯。如今,塞罕坝人家的喜事多,一棵松苍翠的枝杈上总飘挂着一些红布条,装扮得喜气洋洋的。
我们看着老松树就想起了荣军爷爷。荣军爷爷喜欢这棵老松树,临终前他还让我们陪伴他来到这里,最后看一眼这棵老树。他告诉我们,想他的时候就到这里来看看。他走后,与心爱的人在这里长眠。
我们四个人在一棵松下放了一把鲜花,而后向着老松树鞠躬,也向那些长眠于此的种树人致以最真挚的问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