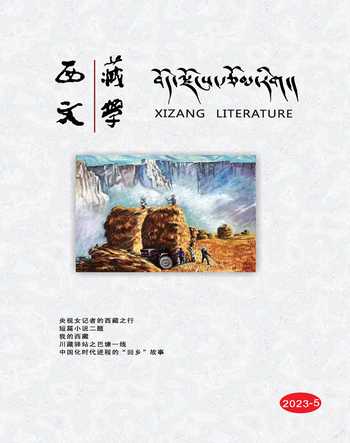缝纫机营生(外一篇)
永中久美
穿过萨迦颇章的巷子,顺着傍晚的建筑阴影在石板路上形成的笔直线条,再往左侧拐进,便是一个古旧的大杂院。
门口走廊一侧,有一排人坐在陈旧的木凳上,腿上放着一袋袋东西。这情景让人想起在医院科室门口等待就诊的人们。队伍前面是一位正在飞速操作缝纫机的短发妇女,明显不是本地人。后来经过一番询问,才得知她姓李,四川绵阳人,五十出头的样子。穿着厚厚的棉服,戴着褪色的粉红袖套。我不由得关注起她劳作的双手,那手不是干体力活的人粗壮笨拙的手,也不是居家太太细软肥嫩的手,而是一双长期冻红后肿胀的手,上面一块块鱼鳞似的干皮翘起来,让我想起西伯利亚那些忧伤的白桦树。但不得不说,这是一双异常灵活的手,以致双手与缝纫机的互动中产生一种前工业时代的劳动韵律美感。
李阿姨飞快地踩踏着缝纫机,长期磨损的不锈钢转轮在阴暗的角落发出明亮刺眼的光。缝纫机颜色是一种充满怀旧气息的淡绿色。有几次,我专注想看清上面是不是写着品牌字号,但是徒劳一场,毫无所获。机身的木质部分褪色严重,大面积露出惨淡的白木颜色,像极了在病床上奄奄一息老人的苍白肌肤。
“阿姨,这个缝纫机有年头了吧?”我试探着问道。
“对,很老了。”她边缝纫,边答。
“不知道什么時候买的,现在很少看到这种缝纫机了。”
“是的,现在很少呢!不过这台啊,是别人扔下的。”
李阿姨向着对面院子看了看,继续说道:“前些年,那个院子里的一户藏族人家清理出来的。当时他们要扔掉,我觉得可惜,就用五十块钱买下来了。从那之后,就在这个门口缝东西,日子也这么过下来了。”李阿姨语调平稳,从始至终没有停下手上的活。但我却异常激动,一下子有一些词汇窜到脑海里,最能对应的便是“生计”。像李阿姨这种人,无论走到地球哪个角落都能生存下来,不吃政策,不拿俸禄,靠自己的劳动生存,我不由得心生敬佩,也再一次思考起生命的分量来。
我后来去过几次李阿姨那儿缝东西,其实我也是恋旧的人,把舒服的衣服要穿到磨破为止。今天,我仍然保存着大学时候的衣服,偶尔还拿出来穿。所以,少不了光顾李阿姨那儿,缝个边角,上个拉链,钉个纽扣什么的。渐渐地开始喜欢观察八廓街周边这种在院落门口营生的人,发现有各色人,基本是从各地来拉萨讨生活的人,散落在各个角落,有缝补的,有修鞋的,有钉腰带的……
出于好奇,我不禁想去打听李阿姨对面的那户卖掉缝纫机的人家。
我开始在这个院子附近找房子,终于在朋友的帮助下顺利租下了一个小单间。正好在一个拥挤的大杂院内,洗漱打水要下楼,上卫生间也要下楼穿过一个堆满杂物的回廊。不过,这样遂了我一直想入住八廓老城区的心愿,可以安心观察这儿的生活,也可以在老城各类酒吧里踏实地喝酒了,不用烦心深夜长途回家。
一天晚上,街上刮着大雨之前的狂风。我加紧步伐,钻到那家名为大山之夜的酒吧。里面跟往常一样,坐满了三分之二位置,环顾一周,发现今天多了几个陌生的面孔。几个女孩穿着白色T恤,画着浓妆,也在观察着进来的人。我生性腼腆,微笑着进去,找了一个角落位置,点了一杯威士忌。过了一会,乌鸦也来了,带着在八廓街长大的人特有的满不在乎劲儿。乌鸦是他的外号,因为总喜欢穿一身黑。另外还有一位女士,也是一身黑,外号叫黑珍珠。乌鸦刚把上衣搭在椅子上,就开起玩笑来。
“老哥,又变帅了啊!”
“嘿嘿,就从来没丑过。”我也调侃着。
“不得了,人不要脸也可以到这种程度!”
“今晚,有没有出现央吉美女?”
“没有,估计她这阵子在张罗结婚的事。”
“哈哈,一个个结婚了,一个个又该离婚了。”
我们的聊天内容总是这样,这女的怎么怎么样,那女的怎么怎么了。曾经有一阵,我们其实是喜欢谈历史和宗教的,可后来发现这些不重要,也不会产生任何价值,只是纠结得让人难受,现在我们压根不讨论那些严肃的事了,只有酒色与生活。
我抿了一口真假难辨的威士忌,附到格桑耳边,问八廓街南侧是否有个老院子叫札萨?
“当然知道,我小时候就在那一带长大的。”他不假思索地说。
“哦呀呀,那知不知道以前那个院子有位老人叫强桑,是个裁缝,大约七八年前去世了,据说缝的一手好藏装,整天在家门口操作一台缝纫机。”这些是我后来收集到的信息。强桑老人是李阿姨那台缝纫机的前主。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有时候我会像个正在破案的侦探似的,喜欢跟踪一个线索,像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剥开,享受其间的乐趣。当然,我本来也对这些带有岁月味道的故事感兴趣,会带来很多思绪和灵感。
酒吧氛围变得嘈杂,人也差不多满了。格桑要了一杯啤酒,喝着听完我的话。似乎想起来了什么,惊叹到:“你这么一说就想起来了,强桑老人的裁缝活远近闻名,不过他们这些上一代的老人一个个走了。记得他跟我爷爷特别要好,经常一起玩骰子。”格桑顺势猛喝了一口啤酒,擦了擦嘴角,直直看着我,眼里既是怀旧又是一种无法理解。突然脸上露出一股笑眯眯的表情,拍着我的后背说道:“你怎么问起这个啊?是不是看上了他们家的女儿?嘿嘿。”格桑有着八廓街一带男孩的俏皮和喜欢戏谑的性格。但他是个非常善良的人,没有什么城府,对一切都看得很开。而像我这样的人,性格多半严肃又内敛,对什么事都认真不苟。格桑称我是“丢了三千块钱的人”——总是沉着脸。也因为这种性格的反差和共同的爱好,我们成为了朋友。
我一心只想多知道强桑老人的故事,笑着点头道:“是的,我看上了人家的女儿,这不想了解她的家人嘛!”格桑哈哈笑了起来:“够意思,冲你这个癖好,就得好好讲讲。强桑老爷一生缝过的东西,可以缠绕林郭大道几圈,我父母他们现在还这么说。虽然夸张了一些,但是我记得小时候穿的藏装都是他缝的。他手巧,心也好,是一个化身为裁缝的菩提萨埵。他老婆以前死在乱年。”我们的谈话到这儿时,酒也喝得差不多了。格桑说这些是他知道的全部信息。后来他还补充道:“哦,对了,强桑老人去世后,据说他们家搬到北郊了。”
这时候,丹增来了,带着两个女孩。
我们的话题戛然而止,格桑马上变得兴奋起来。忙着给女孩们摆椅子,点酒,开始讲起他擅长的段子,逗得女孩们前俯后仰大笑。他这个人在这方面确实有一手。
过了会儿,酒吧歌手说了几句开场白后,唱起了那首传播甚广的《街道》,我们也吼着嗓子跟着唱起来:“地球某个角落,有一条亘古不变的街道,街道的右侧有一座寺庙,虔诚的人们在那儿磕头;街道的左侧有一间酒吧,孤独的人们在那儿失语。”
后来我忙于在大杂院破旧的房屋内阅读写作,偶尔通过狭窄的藏式木窗看到李阿姨和那台忙碌的淡绿色缝纫机。她除了低头工作,得空也会在门口晒太阳,双手在太阳底下越发通红。有时候在路边蹲着跟隔壁川菜馆老板聊天,似乎蹲多久都不会累。我尝试过,在卫生间蹲一会都觉得腿脚发麻。
冬日的八廓街又归于平静,热情的日光再怎么努力照射,温度也会被高原清冷的空气消解。新年将至,李阿姨似乎也回家了。不过缝纫机在走廊边上包裹得严严实实。
普桑的两次失败婚姻
一
冬季刺骨的寒风掠过后藏东部的Z山沟,仿佛要带走一切可以吹动的自然物质和那些尚在酝酿中的隐秘故事。不过,仍然挡不住Z山沟儿女们煞有其事地讨论着关于瓦塘村普桑家刚刚才入门的媳妇。
天逐渐黑下来,普桑家人围坐在铁炉前享受着暖烘烘的牛粪烟火,观看电视上正在播放的藏语爱情剧。
热旦老人清了清嗓子,希望引起家人的注意,随后带着以往开村委会议的腔调,说到:“我们家目前各方面进展顺利,在瓦塘也算是首屈一指,跟隔壁几个村子比起来,咱们也是能在众人面前挺起胸膛来的,但是普桑你现在年纪也不小了,咱们该考虑给你物色一个媳妇了。”
说完,热旦老人呷了一口青稞酒,顺手拿起床边的历算小册翻看起来,希望余下几个月内能找出一个合适的日子。
普桑是个能干的小伙,平时勤劳肯干,又对父亲的话言听计从,加上自幼随父闯南走北,积累了一定的经商经验,商业上的天赋也逐渐显露出来,最近做了几件不错的生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热旦对普桑喜爱有加,对家族的日后发展也抱有很大的期待。
但是近来,热旦在村里的言行举止显然有些微妙的变化,这是村里人看在眼里的,确切地说热旦变得傲慢起来,经常在各种场合止不住夸耀自己儿子。
有一次竟然说到:“在瓦塘就数我家普桑才算好男儿。”
跟多数农区村落一样,瓦塘几户人家向来暗中攀比与较劲。老一辈经常喜欢把一句话挂在嘴边——“人无攀比,家无兴盛。”
普桑家的邻居是尼玛一家。他俩自幼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然而,纯真的年少友谊随着近来两家的竞争氛围,逐渐变得冷淡起来。
前几年,尼玛凭借玲珑人缘,承包到了几个河坝工程项目,赚了不少。他不仅给家里添置了全新的家具,又里里外外修葺了一番,家宅看上去气派了不少。加之,父亲又物色了个儿媳,前年藏历年时正式娶进门。媳妇虽然长相一般,但是为人踏实,干活也努力,而且会织一手漂亮的藏毯。
二
热旦老人心里早在盘算着,要给普桑娶Z山沟最漂亮的女孩,要全面压住邻居的势头。
Z山沟里大家都知道扎西岗村里有一个大美人。前几年有几家提亲,但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嫁人。
女孩叫玉珍。说起来还跟普桑和尼玛等人是小学同学。玉珍有惹人疼爱的瓜子脸和修长身材,再加上不俗的衣著品味,使玉珍每年望果节和藏历年时的藏装搭配,迅速成为Z山沟全部女孩效仿的对象。
近来西藏农区女孩越来越憧憬着自由恋爱,都希望跟一个有恋爱基础的人组建家庭,过小日子,不再愿意嫁入传统的所谓大户人家。大户人家意味着繁重的农活和干不完的家务,而且要时刻注意言行举止,防止随时会掀起的传统舆论。
玉珍早已听到普桑一家在打自己的主意,虽然对普桑没有格外的好感,但也不排斥,因为近来普桑确实是Z山沟里的创业明星,家家户户都会谈论他的生意。不过,想到这些,玉珍的情绪很是复杂。
她小时候其实偷偷喜欢尼玛。尼玛风趣幽默,乐观体贴。但他早已为人丈夫,玉珍的朦胧恋火也早已掐灭。可是,如今这样嫁给普桑家,就跟尼玛成为了邻居,其中感受复杂难言。
三
热旦老人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和近来被逐渐认可的家庭实力,终于说服了玉珍的父母。
玉珍父亲举着银质酒杯,留了一句话:“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这事还得要问一下女儿的意思,她默认的话就成了,要不然还是不行,我们不想委屈了这个宝贝女儿。”
那是在一个冬季的吉日,普桑全家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张灯结彩,门窗前的香布帘焕然一新,家门前用白石灰画着“吉祥八宝”和象征永恒的“雍仲”符号。热旦老人严格按照传统习俗,举行了整整一周的婚庆仪式,将玉珍正式娶进门了。
如今,普桑一家真是美满,经济蒸蒸日上,又添了一个气质不俗的媳妇,热旦老人睡梦里都笑出声来。
不过,世间之事的奇妙在于你永远无法完全掌控它,许多事情不会按照你的设想走。自从玉珍入门后,普桑的妈妈开始闷闷不乐,她嫉妒这位夺走宝贝儿子的美人胚子。越来越不满玉珍的种种行为,甚至觉得她挤牛奶的姿势都是不对的。
藏戏《朗萨雯波》里面有这样一句话——“美貌成敌”,形容朗萨因为其美貌而招嫉,命运也发生急剧变化。
玉珍也免不了相似的命运,成为瓦塘人们茶余饭后的消谈对象。村里几个不老实的男人对玉珍垂涎不已,他们脑海里总是计划着,趁普桑不在的时候摸过去。但没有一个人敢真正付诸实践。
自从玉珍成为隔壁邻居后,尼玛似乎也多了个心事。两家只隔着一道墙,一吵一闹互相都能知道。而且只要一出门,都能碰到。刚开始两人拘谨地微笑致意着,后来逐渐交谈起来,有时候甚至开上几句玩笑。
对于玉珍来说,尼玛成了每日期待见面的暖心大哥,有时候出门赶牛也想方设法追上尼玛。如此一来,虽然没发生过什么出格的事情,闲话是免不了的。热旦看在眼里,心里干着急。
玉珍渐渐对自己的丈夫普桑变得不满意起来。普桑人倒算端庄,但是一口豁牙使他形象气质大打折扣。
有一次,玉珍竟然在外公开称他为“我们那位豁牙子”。
普桑妈妈知道这个事后,自然对玉珍更加变本加厉,除了经常少添饭,还冷嘲热讽,说她是不顶用的“狐狸精”,这个家迟早要败在她手上,说不定还会把自己儿子赶走,家业拱手让给一个野男人。
普桑和玉珍本来就没有多深厚的感情,也自然每况愈下。普桑虽然是个有本事的小伙,但是在玉珍面前总感觉抬不起头来。有一天,终于发生了一场大战,两人歇斯底里谩骂起来,把家里闹了个底朝天。
热旦老人那天一直吸着鼻烟直呼:“人啊,人啊,不知道人究竟要什么!”
玉珍最终还是离开了普桑家,回娘家呆了一段后,在乡政府里谋上了一份厨师岗位。她脱下了象征传统女性的藏装,但又不知道怎么搭配现代服装,而且头上盘着一个不合时宜的大彩辫。
村里人现在嘲讽她是个“卖菜女的模样”。
四
自从儿子普桑的婚姻失败后,热旦老人变得沉默寡言。他一直在感慨:“人到底要什么?”这个问题使他苦恼不堪。
但热旦是个不甘失败的人,闷闷不乐半年后终于理出了一点头绪,自己为了儿子的人生和家庭的圆满,娶了一个美貌如花的儿媳,可是弄到如此下场,究其原因是“美貌”不能当饭吃,不顶用。女人不能看外表,要老实朴素,吃苦耐劳才是关键。还是牧区的女人实在,心眼少,人也老实。
那年夏天,热旦带了个帮手,前往Z山沟上部牧区一带物色儿媳妇。村里有种种说法,不知道热旦这牌打的是哪一出,不过许多人还是看好牧区女孩,也好奇热旦老人会带什么样的牧女媳妇进门。
在普桑不知道的情况下,热旦老人把婚事日期敲定了。
紧接着,普桑的第二次婚姻又张罗起来。这次入门的竟是一个身材矮小、皮肤黝黑的牧区女孩。全村人傻了眼,但是给普桑家的随份贺礼还是样样不少。热旦家仍然办了七天的婚宴。
这个媳妇叫曲珍,虽其貌不扬,但是人老实,干活也格外卖力。村里人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做“弥吾童”,是指侏儒。
曾经有个瑜伽士惊呼:“世人手上有金子,嘴上却带毒。”“手上有金”是因为老百姓生产一切,也会在危难时刻马上帮你;“嘴上带毒”是因为世人言语恶毒,习惯随意嘴上攻击。
普桑妈妈对这位媳妇真是五味杂陈,毕竟是热旦亲自挑选的,而且也是第一个媳妇的失败中吸取的某种经验与教训。但又真心喜欢不起这位矮小的媳妇。经常对着她的背影暗自感慨:“我的儿子究竟做错了什么?”
普桑自然也对曲珍没什么好感,不仅没拿她当回事,甚至不愿意正眼瞧一眼。
但好歹也是过了门的,父母之命难违。一年后,曲珍生了个胖娃。这或多或少对热旦是个安慰。
五
如果,一个侮辱性绰号被外人称呼还能接受,那么被自家人称呼,那内心别提多凄凉。村里人都知道,普桑妈妈在外面称呼曲珍时略显尴尬地用一句——“我们那位弥吾童。”
每每想到这些,曲珍内心是针刺般的痛。再加上丈夫的冷落与不闻不问,曲珍终于决定离开这个带来无限痛苦的家。
那晚,又是一次全家烤火炉的冬季。曲珍鼓足勇气诉说了所有遭受的委屈,带着颤巍的哭腔,坚决表示要离开这个伪善的家。
一年后,曲珍在Z山沟上部的塔林寺落发为尼,随着一撮撮发丝的飘落,曲珍彻底告别了这个尘世。
如今,曾经称她为“弥吾童”的那些人尊敬地称她为“阿尼曲珍啦”……
熱旦现在看上去衰老了许多,脸上经常浮现一种灰暗又戏剧化的表情。他似乎看开了一切,彻底不管家里事了,只是带着流着鼻涕的孙子出入在各种打骰子的场合。
责任编辑:子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