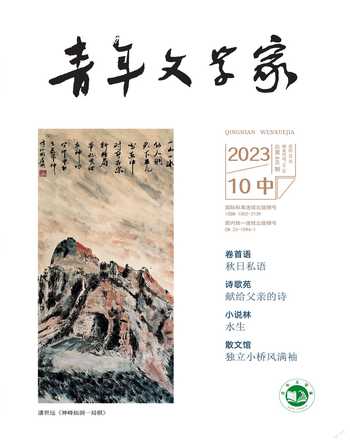在语象叙事视角下再议《厄舍屋的倒塌》
沈一然

“语象叙事”追根溯源,是一种来自古希腊的古典修辞手法,后来演变为书写西方艺术史的方法,也成为一种用语词来呈现与转述视觉艺术或造型艺术的文学形式或体裁。根据王安、程锡麟的《语象叙事》一文所述,当今学界广泛接受的语象叙事定义多为赫弗兰提出的“视觉再现的文字再现”。更确切地说,是文字表述出来的视觉艺术效果,也是文学与作为他者的视觉艺术之间的交融和博弈。可以说,这种叙事方式对文学作品中场景的描绘、人物形象的塑造、艺术作品的展现,以至于特定的文学艺术效果的体现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而以“效果论”为创作原则的爱伦·坡,在他的短篇小说中便大量运用了“语象叙事”这一手法。他善于驾驭和利用语言文字,通过对自然或人造场景、人物外貌、人物动作,甚至是一件艺术作品的文字再现,以达到他预先构思的效果。本文以《厄舍屋的倒塌》为例,就语象叙事在场景描写、人物刻画和绘画作品再现三方面的运用及作用进行探讨。
一、场景描写
在《厄舍屋的倒塌》中,愛伦·坡通过对故事发生的场所、环境的视觉化再现,烘托出阴郁恐怖的气氛,使其对读者产生强烈的心理暗示和感官刺激。
小说中对厄舍屋周边环境的描写具体如下:“那年秋天,一个阴沉、昏暗、岑寂的日子,乌云低垂,厚重地笼罩着大地”,宅邸边的小湖“黑黢黢,阴森森,倒映出变形的灰色芦苇、惨白树干、空洞眼睛一样的窗子”。而小说对厄舍古屋的描写是这样的:“它的主要特征,在于年代极为古远,时光的痕迹使它褪尽了鲜亮的颜色”,沿着“黑洞洞”的迷宫般的走廊往里走,可以看到天花板上的雕刻、四壁“黑色的帷幔”和“乌黑的地板”,宅子里的房间高而空阔,窗子狭长且远离地面。窗玻璃是“深红色”的,从窗口透进的微光被滤成了深红色,仅映照出了附近的一些物件,而屋内其他的东西则都隐没在模模糊糊的暗影中。墙上挂着“暗色的墙帷”,屋里的东西散乱破旧。这一切关于厄舍古屋景物的详细描写使得整体环境都显得阴沉、悲郁,弥漫着恐怖的气氛,仿佛预示着故事的悲剧走向。爱伦·坡“犹如一位画家,给故事打上了灰暗的底色,把一幅阴冷凄凉的画面展现在读者的面前”(任苗苗《恐怖与浪漫的融合—从〈厄舍屋的倒塌〉看爱伦·坡对哥特式小说的继承和发展》)。
另外,爱伦·坡对小说中最后那个暴风雨夜的描写尤其令人震颤:“虽说有暴风雨,但那个夜晚绝对美丽,是个恐怖和美丽纠结的奇特夜晚。旋风显然就在附近大施淫威,因为风向时时剧烈变动。乌云密布,且越积越厚,低垂着,仿佛要压向府邸的塔楼。乌云虽浓密,但还看得出云层活灵活现地飞速奔突,从四面八方驰来,彼此冲撞,却没有飘向远方。我是说,浓密的乌云没有遮蔽住我们的眼睛。不过我们没看到月亮和星星,也没看见一道闪电划破夜空。可厄榭府邸却雾气缭绕,被遮蔽了面目。那雾气亮光微弱,却又清晰可见。那奇异的雾光闪闪烁烁,使得大团大团翻腾着的乌云下面,还有周遭地面上的一切,都闪烁着这种光亮了。”爱伦·坡用生动具体的文字描绘出了一幅恐怖和美丽相结合的景象,让读者不由屏息凝神,去体会文中那奇异的感受。
二、人物刻画
爱伦·坡对小说中人物的描写同样有着强烈的视觉冲击。
在对罗德里克的外貌进行描述时,爱伦·坡写道:“他面如死灰;眼睛大而清澈,明亮得无与伦比;嘴唇有点薄,颜色暗淡,但轮廓绝顶漂亮;鼻子是精致的希伯来式样,鼻孔却大得离谱;下巴造型很好,但鲜有活力,并不引人注目;头发又软又薄,蛛网一样稀稀拉拉……眼前这苍白得可怕的肤色,明亮得出奇的眼睛,尤其让我惊愕,它们甚至吓到了我。那丝绸般柔滑的头发,也在不知不觉中,变长了,蛛丝一样纷乱,与其说是披拂在脸上,倒不如说飘飘扬扬来得贴切。”这些文字仿佛画笔一般描绘出一位苍白虚弱却又不乏“美丽”的男子形象,而“蛛网”这一具象的描写更增加了恐怖的效果,让人不寒而栗。
相较于罗德里克,爱伦·坡对其妹妹玛德琳小姐的直接描写着墨不多,读者与叙述者都是从罗德里克那里了解到这个可怜女人的。玛德琳自始至终一句话都没讲,只给读者留下了一个神秘、难以捉摸的背影。直到她“死”后,小说才对她的容貌进行了第一次描写:“我第一次注意到,他们兄妹二人的容貌惊人的相似……正当她青春的好时光,疾病却夺去了她的生命,像所有患有严重硬化症的人一样,胸口和脸上还似是而非地泛着薄薄一层红晕,唇上停泊着一抹可疑的微笑,那笑容逗留在死者的脸上,格外怕人。”而这些文字的刻画足以让读者眼前浮现出一位年轻、孱弱、苍白病态、毫无生气的美丽的女子形象,此外,那抹“可疑的微笑”更让人感到脊背发寒。
小说结尾处,爱伦·坡写道:“就在那两扇门外,果真站着厄舍屋玛德琳小姐那体型高大、裹着尸衣的身影,那白色的袍子上,溅满血迹;瘦弱不堪的身体上到处是苦苦挣扎的痕迹。”她从坟墓中走出,又拉着哥哥一同走向死亡。白衣,血迹,挣扎的痕迹……可以说,这些视觉化再现的文字都是爱伦·坡为追求恐怖效果而精心设计的。
三、绘画作品再现
在这个故事中,爱伦·坡还提到了不少艺术作品,并巧妙地运用了这些绘画、诗歌、音乐和小说等艺术形式来刺激读者的感官,以此来烘托主题,达成恐怖的效果。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爱伦·坡对绘画作品的文字再现。
(一)文本内绘画作品的再现
其一是对小说中的人物罗德里克画作的描述:“这画尺寸不大,画的是内景,要么是地窖,要么是隧道,呈矩形无限延伸。雪白的墙壁低矮,光滑,没有花纹,也没有剥落的痕迹。画面上的某些陪衬表明,这洞穴深深潜在地下,虽无比宽广,却看不到出口,也看不到火把或别的人工光源,可强烈的光线却浪浪淘淘、四下翻滚,使整个画面沐浴在一片不合时宜的可怖光辉里。”这幅画作画的是“洞穴”,爱伦·坡通过语言,再现了画面的内容:洞穴无比宽广,却看不到出口,并沐浴在不合时宜的可怖光辉里。这样的文字使人看见的同时,也能感受到罗德里克内心的绝境和小说叙事者内心的恐惧。
(二)文本外绘画作品的再现
爱伦·坡在观察罗德里克画作时提到了一位畫家—亨利·富塞利。笔者认为《厄舍屋的倒塌》一文正是爱伦·坡对亨利·富塞利的名作《梦魇》绘画艺术和绘画风格的语言再现。
亨利·富塞利是18世纪至19世纪著名的英国画家,他擅长隐晦主题的绘画,画作大多具有独创性和色情味道及怪诞倾向,“犹如具有独特恐怖美学的哥特小说”(曲海波《捕梦者与幻想家—亨利·富塞利》)。《梦魇》是富塞利极富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这是一幅混合了传说和梦境的绘画:在以大片的暗色为基调的背景中,一个白衣女人仰躺在床上,向下弯曲着身子,一只手垂落在床边,而一只可怕的魔鬼正蹲坐在女人的身上,左方红色布帘中探出了一个可怖的黑色马头。这幅画描绘的是一个噩梦的场景,在英国的传说里,恶魔总是骑着母马,在黑夜里张狂地呼啸奔驰,这个马头暗示噩梦以魔鬼的形象出现;而白衣女人向下弯曲的弧线,仿佛是被噩梦捕获,呈现一种无力挣扎的形象。画面明暗对比强烈,线条柔美而有诗意,构图富有幻想的色彩。作品充满寓意和暧昧不明的隐喻,仿佛是还原了梦境,以便和心灵深处直接对话一样。
自1781年《梦魇》诞生并于伦敦皇家艺术学会展出后,其印刷版本迅速在欧洲以及美国流传开来,知名程度可见一斑。而从《厄舍屋的倒塌》中直接出现了富塞利的名字这一点,可以推断爱伦·坡熟知富塞利和《梦魇》这幅画作。
1.色彩基调的再现
首先,小说中的环境仿佛再现了《梦魇》的背景基调,两者皆以“暗色”为主。油画中的背景呈大片的黑棕色,画面正中的女子与背景的暗色对比强烈,使得人物被黑暗包围,表明了画面描绘的是深夜场景,也体现了噩梦侵袭令人恐怖的感觉。而小说中的环境描写犹如油画中的底色,黑暗而又神秘,为整个小说定下了一个梦魇般的基调,影响着整部小说的阅读效果。
2.人物形象的再现
小说与画作中都有着一位可怜的“白衣女人”。她们一个被梦魇恶魔所折磨,一个被疾病和命运所摧残。油画中那个占了将近一半画面的,被暗夜笼罩,被噩梦压住胸口,无力挣扎,闭眼仰面躺在床上的白衣女人,无疑是个美丽而可怜的形象。而小说中唯一的女性—玛德琳小姐,毋庸置疑是作品中相当重要的一个人物,她的身上同样笼罩着神秘、悲剧的色彩,她是故事中的受害者,同时也是罗德里克悲哀和恐惧的来源。
值得一提的是,在故事结尾,也是高潮部分,从棺材中爬出来的玛德琳小姐身上穿的正是一件“白色”的衣服,就如同《梦魇》中身穿白裙的女人。
3.绘画主题的再现
(1)噩梦
综观全文,小说中的“我”所经历目睹的一切,正是一场噩梦般的经历。而事实上,小说除了通过叙事重现油画画面,还出现过一次与画作类似的静态场景,这一次比较直观的视觉化语言再现是一场关于“噩梦”的描写。
小说的叙述者在玛德琳小姐的遗体停放在地窖后的某个深夜,辗转难眠,竟被“梦魇”捕获,“当时,一场即将到来的暴风雨撩得黑幔不时在墙壁上瑟瑟飘摆,窸窸窣窣拍打着床上的装饰物。怎么排解都无济于事。抑制不住的颤抖渐渐传遍周身,最终,一个莫名恐怖的梦魇压上了心头。我喘息着,挣扎着,才算甩掉它……”这段描写中的“黑幔”“梦魇”“压”“恐惧感”与富塞利画作上的元素不谋而合。
(2)“恐怖”与“美丽”
“恐怖”与“美丽”的融合,是《梦魇》和《厄舍屋的倒塌》所蕴含的另一个相同主题。
先说《梦魇》。上文提到的白衣女子正是美丽的代表,富塞利所用的笔触细腻,线条柔和而富有诗意:雪白的肌肤,金色的头发,丰满的体型,如果除掉她身上的魔鬼和布帘后的马怪,这就是一幅美人图。然而,《梦魇》的主题即“噩梦”,这个概念本身就令人惧怕,画家通过画笔描绘出的景象更让人不寒而栗:黑色的背景,红色的窗帘和被单,梦中的白衣女子后仰着躺在床上,毫无知觉的样子,而压在她胸口的魔鬼十分可怖,怒目圆瞪,表情凶狠;而红色布幔后伸出的黑色马头好似从地狱而来,煞白的双目没有瞳仁,幽幽地从布帘后探头望着床上的女人。另有一说法,在西方传说中有男梦魔和女梦魔,男梦魔吸取女人精气,女梦魔吸取男人精气,而画中的就是男梦魔在吸取女性精气。这马形怪物其实就是所谓“梦魇”,西方的梦魇就是马形的怪物。美女与恶魔结合在同一画布上,明暗对比强烈,恐怖的同时又暗含着色情的意味,更是爆发出一种奇异的美感。这里可以提到富塞利另一幅与《梦魇》类似的油画《达特穆尔的恶魔》,此画中的恶魔形象更为贴切吸取精气这一说。总之,无论是《梦魇》还是它的姊妹篇,画布上的场景充满了恐怖与美丽融合的元素。
《厄舍屋的倒塌》中的恐怖无须多言,除了通过场景、人物的描绘和心理的刻画来烘托恐怖效果外,小说结尾玛德琳小姐的“死亡”将恐怖气氛推至高潮,那一刻即恐怖与美丽融合一处。爱伦·坡曾经在他的著作《创作的哲学》中明确地提出了“美女之死”这一主题。他在文中指出:“美是诗的唯一正统的领域”,同时“忧郁是所有诗的情调中最正宗的”,而“死亡”则是所有忧郁的题材中“最为忧郁的”,因此,“当死亡与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最具诗意。犹如富塞利柔美而有诗意的油画描绘的内容却是一场噩梦一般,小说中那个“恐怖和美丽纠结的奇特夜晚”,死亡伴随着美丽降临了。
4.绘画风格的再现
(1)浪漫主义
从艺术风格的角度来看,《梦魇》与《厄舍屋的倒塌》都是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同时又在各自领域有着独树一帜的风格,而令人惊讶的是,两者极为相似的艺术风格。
《梦魇》的作者亨利·富塞利是一位浪漫主义画家。浪漫主义画派以肯定、颂扬人的精神价值,争取个性解放和人权为思想原则;在绘画上主张有个性、有特征的描绘和情感的表达;在构图上变化丰富,色彩对比强烈,笔触奔放流畅,使画面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和激动人心的艺术魅力。简而言之,浪漫主义的精神意义是存在于感受上。随着浪漫主义的登场,各式各样的个性美代替唯一绝对的理想美。他们认为,一般人所谓的丑、恐怖,如果能够诉诸自己的感受性,这种艺术就是美。因此,理想美所不被允许的怪异性、奇怪幻想、死亡现象等在浪漫派世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作为浪漫主义画派的代表作品,《梦魇》通过融合了神秘、传说、鬼怪与美色的画面,表达了富塞利独特的个性,以及他独一无二的美学理想,使观者的心灵受到了震撼。
《厄舍屋的倒塌》一文當属哥特式文学,哥特小说属于浪漫主义运动中的一个特殊流派,有些理论家称之为“黑色浪漫主义”。哥特小说的故事情节恐怖刺激,甚至常有鬼怪精灵或其他超自然现象出现,小说气氛阴森、神秘、恐怖、充满悬念。因此,与《梦魇》传达出的美学效果相同,在《厄舍屋的倒塌》里那个怪诞、诡异、恐怖的哥特世界中,读者同样可以感受到浪漫主义“个性美”的体现以及作品渲染出令人战栗的独特艺术效果,这一点迥异于同时代的其他浪漫主义作家。可见两者的艺术风格存在着其他浪漫主义画家和作家难以达到的共性。换句话说,《厄舍屋的倒塌》也许就是爱伦·坡对浪漫主义绘画,尤其是对富塞利的绘画作品艺术风格的文字再现。我们欣赏爱伦·坡的小说犹如欣赏富塞利的画作,富塞利以图案和色彩带给观者直观的感受,爱伦·坡以文字营造的画面感及其渲染出的气氛给读者内心的冲击。
(2)潜意识
此外,《梦魇》与《厄舍屋的倒塌》在创作理念和思维方式上也存在着共性—它们同时关注到了“潜意识”这一领域,同时也是作者自身潜意识的反映。18世纪至19世纪这一阶段心理学正处于迅速发展中,人们逐渐了解了潜意识的存在。潜意识,是指人类心理活动中,不能认知或没有认知到的部分,人们的每一个选择、每一个行为背后实际上有一股未知的力量在影响着他们。对潜意识的越发关注,意味着人类对自身的认识更进了一步。随着心理学的发展,人们对梦境的解读渐渐与潜意识密不可分。
18世纪的人们开始将梦境的影像变成饱含特殊意念的领域。富塞利的《梦魇》便是通过画笔将梦境还原—面目狰狞的恶魔和弯曲着身体的女人,以及没有瞳仁的可怖的马头,同时还原的还有人们对噩梦的恐惧以及内心的不可遏制的压迫感,该作品着重刻画了思想的非理性方面的力量,将人的深层意识具体地描绘在画布之上。
富塞利的作品其实更是他本人思想状态或者说是他潜意识的表现。富塞利出生于艺术世家,但他一开始觉得自己没艺术天分,放弃艺术改习神学,决定成为一个牧师。后来,富塞利因为揭露当时政治上的腐败,被迫离开苏黎世,先后辗转柏林、伦敦、意大利。他虽然极富才华,但缺乏自信又悲观的态度加之生活中的种种不顺,始终令他郁郁寡欢。这一系列的原因,使他在作品中逐渐表现出营造恐怖阴郁气氛的怪诞倾向。关于《梦魇》的诞生,有一说法为:富塞利爱慕的女人刚刚在家长干预下另嫁他人,作品同时展示了他未实现的色情梦境,以及一个女人做噩梦的场景。
而生于19世纪的爱伦·坡对人类潜意识更是抱有极大的兴趣。在现代心理学对人类的潜意识、无意识等领域进行科学、系统的阐释归类以前,爱伦·坡就已经在他的作品中对此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述与分析。D.H.劳伦斯在《美国古典文学研究》中提出,爱伦·坡是一位深入人类灵魂的洞窟、地窖和阴森可怕的地道的冒险家。常耀信教授也在《美国文学简史》中指出:爱伦·坡的最伟大之处在于他是第一个开掘人类意识最深处幽暗领域的人。
在《厄舍屋的倒塌》中,爱伦·坡通过探索人大脑最隐秘处无意识和潜意识的精神活动,展示了人物从心理变态到精神崩溃的全过程。小说中的罗德里克由于身处环境的阴暗,加上其性格的扭曲和对妹妹畸形的情感,使他的精神饱受摧残,他的一系列古怪举动其实就是潜意识的展现,比如他“一想到要出什么事儿,哪怕这事儿再微乎其微,也会使我心神不安,难以承受,免不了就会瑟瑟发抖”。自小说问世以来,对主人公罗德里克或者叙述者进行深层次的心理分析一直是人们的焦点。虽然有些说法可能与作者本人的意图毫无联系,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爱伦·坡对一些反映人类欲望和本质的人的内心活动有着无穷的热情。
从富塞利和爱伦·坡对潜意识的共同关注,以及作者潜意识于作品中的呈现来看,两者在创作思维上也存在着共性,爱伦·坡的文字除了能够重现绘画形象性的感染力,还在更深层次的创作心理层面达到了语图合一。
在《厄舍屋的倒塌》中,爱伦·坡无论是对文本内事物—场景、人物、艺术品等的语言再现,还是对文本之外—富塞利绘画作品的文字再现,都体现出了一种极具魅力的叙事语言,即语象叙事。这种叙事手法仿佛为他的“效果统一论”量身定制,正如他说过的:他那么相信语言的征服魅力,于是就能利用语言描绘出那些转瞬即逝的美好,并且使之具体化,从而为读者所欣赏和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