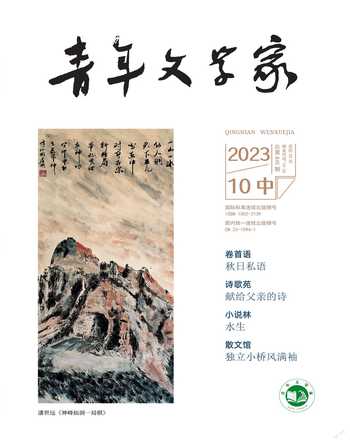约翰·福尔斯小说的叙事艺术研究
吴强
约翰·福尔斯的小说具有显在的现代主义特征,因其叙事上超前的先锋性而被称为“动态的艺术家”。约翰·福尔斯对传统现实主义技法的革新使其文学创作既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又具备畅销的市场价值。约翰·福尔斯以叙事形式的变形和转化为文本的叙事内容找寻到了恰切的形式,使小说的外部结构与内在肌理形成圆融的美学状态,以自由的叙事状态实现了对现实的观照和对时空的哲性反思。
一、自由变换的叙事视角
卢伯克的叙事学理论揭示了视角在文本中的重要叙事功能,叙事视角的择取,表征着隐含作者的内在情感立场,决定着读者以怎样的眼光和道德标准审视作品中的人物,如何获取以及获得怎样的文本信息,因而叙事视角的择取对文本的叙事效果具有巨大的影响作用。约翰·福尔斯小说中的叙事视角呈现出自由变换的特质,根据叙事内容的展示需要灵活地变换视角,使不同视角下的讲述形成复调式的叙述,从而使文本产生多义性的特征。
约翰·福尔斯擅长以视角的切换揭示同个事物的不同面目,视角的转化如同棱镜般折射出不同的光线,揭示着真实本身所具有的丰富性。例如,在《收藏家》中,约翰·福尔斯的视角择取就别有意味,小说共分为四个区间由交织穿插的双重视角进行讲述,不同叙事者的视角交替出现并操持着各自的叙事立场,使线性发展的故事情節衍生出多变的面貌和质地。小说先是以克雷戈的内聚焦第一人称叙述讲述了其对米兰达的炽热感情,这份熊熊燃烧的情感使他不自觉地向米兰达的所在之处靠拢,并期望能将其永远留在身边。而第二部分的叙事则采取了米兰达的内聚焦第一人称叙事,以日记为载体向读者毫无保留地敞开了人物的主观心理空间,让读者了解到同克雷戈视角下的讲述迥然不同的事实:克雷戈热切的迷恋并未打动米兰达的心,反而使她感到身陷囹圄。双重视角下的讲述呈现出各异甚至矛盾的面目,从而在文本中形成了富有张力的复调,多重视角下的叙事声音在文本中回荡,相互补充、相互质询并形成互照,使读者不得不依靠自己的道德判断与信息分析来判断事情的真相。而后,叙事视角又重归克雷戈的掌控之下,他以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痛诉米兰达染上肺病后凄美死去的经过,将自己渲染成为失去爱人后“痛不欲生的失落者”,失掉所爱的苦楚甚至令他丧失了生存的意志。正当读者为他的深情所打动,并将两人的爱情悲剧视为命运的阴错阳差时,结尾部分中的克雷戈却重新发现了可供他投射深情的对象—美丽活泼的商品销售员玛丽安。至此,读者才在复调的矛盾叙事中发现事情的真相,克雷戈所谓的“爱情”不过是为了遮蔽自己收藏癖的托词,他对玛丽安的执着仅是物化他者以实现自我满足的外在表现。约翰·福尔斯有意地以多重视角完成故事的讲述,同时在文本中悬置道德评判或价值标准,使小说具有开放性的广场特征,使读者能切身地参与进文本意义建构的审美过程。
而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约翰·福尔斯对视角切换的使用则更为纯熟和圆润,叙事者“我”在全知视角和限知视角之间不断切换,有选择地向读者敞开或遮蔽信息,从而使小说中萨拉的形象变得扑朔迷离。在文本的叙述中,第三人称的叙事者“我”以全知视角出现并统摄着文本,从各形各色人物的家世出身、人际往来到他们隐秘的情感关系、性格特征,似乎是无所不知的全能叙述者。在叙述故事的同时,“我”还大段地插入自己的议论与评说,在文本中表现出巨大的话语权力。然而,当涉及萨拉时,“我”的全知视角却瞬间转变为限制性的叙事视角,变得吞吞吐吐、语焉不详,使读者和主人公查尔斯一样被浓重的谜团所吸引。全知视角与限知视角的互照使萨拉毫无疑问地成了小说中最独特的存在,使萨拉不需要经过任何词语的渲染即成为文本叙事聚焦的所在。叙事视角的转换构成了奇特的迷宫,使读者同主人公查尔斯般着迷地追寻着萨拉,试图了解她复杂的身世、揭开她身份的谜底,在虚构与真实之间不断地涉渡,只为了在文本的细枝末节中拼凑出完整的真相,从而在审美接受的过程中保持着高度的集中状态。
叙事视角的自由变换使约翰·福尔斯的小说呈现出现代主义小说的多义性特征,不同视角下的讲述形成了别有意义的互文,使文本本身具有敞开性与开放性,使文本意义的最终实现成为创作主体与接受客体在互动中完成的动态过程。视角的变换凸显了约翰·福尔斯对叙事形式的驾驭能力,以其具有先锋意义的叙事形式表现了作家出众的创作才赋。
二、形式复杂的叙事结构
约翰·福尔斯的小说通常具有复杂的结构形式,作者善于通过编织复杂的叙事结构为小说制造出人意料的反转,从而产生戏剧化的审美效果。约翰·福尔斯的小说因对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线性叙事结构的颠覆而充满现代主义的先锋性,由结构的繁复变形而制造的叙事迷宫,使读者在对小说进行审美接受的过程中,不得不通过对结构形式的拆解来实现对文本的解读,从而使他们的接受过程产生了有意味的延宕,造成了其审美接受过程的时延。
约翰·福尔斯擅于在小说中织构层层嵌套的套盒结构,不同的叙事层级相互叠加并套合,使小说形成了层次丰富的“剧中剧”式的结构形态。例如,《巫术师》所采取的是“故事套故事”的结构方式,表层叙事讲述了出身于中产阶级的青年尼古拉斯困惑于身份所带来的安逸生活,及其随之而来的巨大空虚感,在双亲因意外而离世之后前往希腊寻找内心真正的自我的经历。约翰·福尔斯在尼古拉斯的自我寻找之旅中,嵌套了神秘富豪康奇斯的自叙传式的讲述,分段性地敷陈了其如何从逃离战火的普通士兵摇身变为德康伯爵的承袭人,再到北极进行鸟类考察的传奇经历。此时,表层叙事中的主人公尼古拉斯隐秘地实现了聚焦的转移,从叙事聚焦的客体变为了聚焦他者的主体,成为读者实现视角代入的被动聆听者。而后,文本实现了从表层叙事到深层故事的过渡,康奇斯以排演戏剧的形式帮助尼古拉斯实现对“自我”的确证,全景式的沉浸戏剧渐渐使尼古拉斯失去了对现实和虚幻的辨别能力,他爱上了戏剧中的演员霍尔慕斯小姐,却无法辨别她的爱来源于自身真实的情感,还是角色在服从剧本情节的发展理路。康奇斯所排演的戏剧作为文本的深层故事,同表层叙事之间构成了奇异的“剧中剧”的关系,他的本意并非扰乱尼古拉斯对真实的感知,而是为了使其理解“存在所具有的可靠性”,从而实现对真正自我的清晰认知。尼古拉斯从戏剧所制造的迷宫中的觉醒表征着其自我认知的明晰,人物对于“存在”合理性的认同也标识其思想演化进程终于抵达了可以自洽的终点。嵌套式的叙事结构使尼古拉斯的自我寻找之旅充满了奇幻色彩,背离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叙事常规,从而使文本产生了强烈的存在主义哲学底色。
而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这种嵌套式的复合结构被运用得更为纯熟。文本的表层故事讲述了伦敦绅士查尔斯对萨拉的寻找过程,充满了传统骑士文学的理想主义气息,当读者将文本“误读”为现代骑士对沦落在莱姆镇的流言蜚语中的少女进行拯救时,约翰·福尔斯却又引入了小说的深层叙事,揭示了“被拯救”的萨拉实则并不需要被拯救的事实,她主动地选择了让自己成为法国中尉的女人并通过这个虚假身份获得了真正的自由,这种“消极优势”的获得使萨拉得以有意识地操纵并误导整个小镇的居民,以便让自己从维多利亚时期的传统道德秩序中脱身,成为真正意义的现代自由女性。深层叙事对表层故事的颠覆令读者的审美惊异得到了放大,戏剧化的情节陡转使小说取得了波澜起伏的叙事效果。同时,约翰·福尔斯有意在嵌套式的结构中增加结构形式的变体。在小说的结尾处,故事的外部结构衍生出了新的“枝节”,多元开放结局的呈现使小说在收束阶段形成了橘瓣式的并置结构。与萨拉短暂地交契,随后又与之分离的查尔斯,同欧内斯蒂娜成婚,并获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随后即被隐含作者指出,这只不过是查尔斯的一段空中楼阁般的想象。接着,隐含作者讲述了属于两人的另一重结局,萨拉离去后查尔斯也因毁坏婚约而离开英国谋生,在美国同萨拉重逢后,才得知他们已经育有一个可爱的女儿。然而,当故事的画面定格在幸福的时刻后,原本重新隐没在文本中的隐含作者却再次登场,并“将手表倒拨了15分钟”,主人公们幸福的场景随即破裂,萨拉依然不愿重蹈维多利亚时期传统女性的既定命运轨迹,查尔斯在失望中颓然离去,却感受到自己已经焕然一新,重获新生。多元结局的同时敞开予以文本以开放式的结构特征,不同的可能性被统摄在同个主题下相互并列,使时空的复杂性得以具象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使文本因叙事结构的复杂而形成了无穷的魅力。
叙事结构的复杂形式使约翰·福尔斯的文学创作具有现代性的先锋特征,它所指向的是与传统现实主义文学迥然不同的审美范式,成为把握繁杂的现实的有效方式。小说中叙事结构的多变形态与丰富的叙事层级在文本中形成了余韵悠长的复调,时刻拓展着读者想象力的边界。
三、寓意丰富的互文手法
互文是约翰·福尔斯小说中常见的叙事技法,通过吸收和转化其他文本并对其进行重述和再创作并由此形成新的文本,使两个故事之间生成丰富的指涉关系,向读者展示了文本建构的想象过程。不同文本之间的交汇产生了丰富的对话性,通过引用、戏拟、模仿,以及暗示等手法,在本无关联性的文本之间建立联结,使小说的阐释空间得到了充分的拓延。
戏拟是约翰·福尔斯小说中经典的互文手法,《收藏家》同莎士比亚的戏剧《暴风雨》之间具有鲜明的模仿和转换关系,两个文本的女主人公共享着“米兰达”的命名,她们同样美丽而顽强,以顽强的意志力守卫着自己的灵魂的纯洁。而《收藏家》中的米兰达自述的日记中始终以《暴风雨》中的人物“凯列班”作为克雷戈的代称,这个粗野而可怕的形象正隐喻着克雷戈真情流露的外衣下蛮横自私的灵魂。同时,克雷戈对米兰达非理性的爱情也在文本中构成了“暴風雨”式的情绪氛围,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使“暴风雨”成为《收藏家》中人物之间深沉而暴烈的情感涌动的外在表征,成为读者理解小说叙事的一条通幽曲径。故事结构模式与人物形象的高度相似使小说《收藏家》可以被视为剧作《暴风雨》的现代转化,两重文本之间相互指涉的关系使《收藏家》不再仅被理解为“爱而不得”的俗套故事,而是通过对古典戏剧的再创作和再演绎获得了浪漫的诗性,得以被置放在更严肃的语境中加以探讨,并从中发掘出文本对人性的深邃探问。
而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约翰·福尔斯则通过引用不同文体的作品的言语片段来为小说与其他文本建立互文关系。与情节无关的语段的插入和拼贴,既造成了读者审美阅读过程的延宕,也使他们在引用的文段中获得有关情节发展的暗示。例如,小说的首个章节便引入了哈代诗作中的名篇《谜》:“茕茕孤影,日驰天遥。”在海边远眺的神秘女人萨拉正是这样一个茕茕孑立的孤独者形象,而她谜一样的气质和神态不仅深深地吸引了主人公查尔斯关注的视线,也在读者心中投下了巨大的疑影。整部小说正是萦绕着萨拉这个美丽而神秘的“谜”团开始织构文本,对萨拉真实身份的找寻构成了文本的经纬和线索。诗歌同小说之间因相互指涉和隐喻形成了奇妙的互文关系。随着读者对文本的深入越深,对开篇这首“平平无奇的小诗”的叙事功能及其隐喻作用就会越感心惊。而第30章中,约翰·福尔斯则别有用意地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大段论述,以此来暗示波尔塔尼太太对待萨拉的方式。她虚伪的本性和温情背后的冷漠使萨拉感到鄙夷和恐怖,并最终以反抗的形式重新获取了自我的主导权,重获了自由。这些引文同小说的章节所具有的隐喻关系,使它们彼此之间形成了有意味的互文,使多重文本在小说中自由地交汇,形成了极为宽广的意义阐释空间。互文手法的应用使约翰·福尔斯的小说敞开了更宽广的阐释可能,令其可以通过对其他文本的调用实现自身的叙事目的,在文本空间的互通间实现叙述的自由。
约翰·福尔斯小说的叙事形式具有鲜明的实验特征,他打破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封闭的审美范式,使现代主义的美学原则逐渐崛起,揭示了文本形式所具有的独立的审美意义与叙事功能。约翰·福尔斯小说中自由变换的叙事视角、复杂多变的形式结构和具有丰富寓意的互文手法,从叙事的层面深刻地启迪了当代文学的创作,产生了难以忽视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