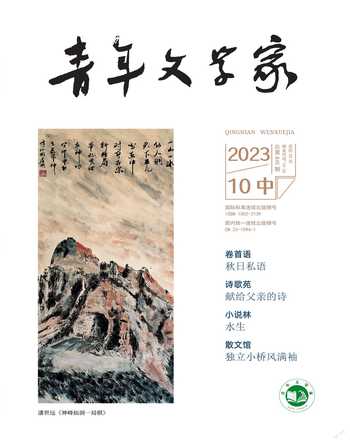“诗可以怨”命题的发展流变
王铖
“诗可以怨”是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重大命题,其对中国古代乃至当今的文学创作动机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它的影响之深远,甚至可以从我们当今的生活方式上窥见。从文学的角度上来看,了解“诗可以怨”这一观点的发展流变,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区分各时期作品的特征和主要的创作动机、创作风格;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我们可以通过其了解文艺创作、生活方式的底层原理。本文将阐述“诗可以怨”这一命题的产生、发展、含义的延伸与扩展,以及古代文坛上“诗可以怨”的典型代表。
“诗可以怨”出自《论语·阳货》,“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即通过诗歌表达情态,从而发挥社会作用。这里面还列举了诗的很多其他作用,如观习人品、参与社交。而本文将着重讲“怨”这一社会功能。“怨”在此处为动词,孔安国注为“怨刺上政”。孔安国如此注解,这与先秦及汉代对于诗歌的认识有关。先秦及汉代广泛认为“诗言志”,即赋诗、作赋是表达自己的志意和志向的,带有很强的功利性和实用性,作诗的主要目的是用于规劝统治阶级,或者表达自己的壮志与才学,使“伯乐”相中自己。孔安国作为汉代人,自然不免受其影响,他认为“诗可以怨”,即诗就是用来起讽谏作用的,只适用于写给君王,诗作者通过“诗”来表达自己的主张并加以劝谏,从现在来看,是一种较为狭隘的观点。黄宗羲在《汪扶晨诗序》中所说的“怨亦不必专指上政”,就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孔子曰:“择其可劳而劳之,又谁怨。”(《论语·尧曰》)这是对“怨”的原因加以阐述,就是如果不对民众施行仁政,对百姓强加徭役,违背农时,百姓就会心生怨念。而士大夫作为百姓的代表,自然要上书劝谏。然而,即便他们是因为“怨”而上书,但不能直书其事、言辞激烈,要用字委婉,所以作诗来劝谏君王成为很好的手段。对君王“勿欺也,而犯之”(《论语·宪问》),就是不要直言君主的过错,只需小小的“冒犯”,让君主知晓自己的过错。朱熹《论语集注》注为“怨而不怒”,指出“怨”是含蓄之怒,而非“怒发冲冠”。
荀子对这一观点的看法相同。在《佹诗》中,他描绘了大自然颠倒黑白、四时失序、令人可怖的情景,接着描写人类社会的贤才良士受诬受困、奸佞猖狂肆虐。而全诗的第一句便是“天下不治,请陈佹诗”,“佹诗”,即辞意诡异、语调激切的诗,是先秦和汉代对诗的作用及认识的最佳代表。荀子也认为诗的作用在于讽谏,一旦天怒人怨,君王必须作出改变时,就需要有壮士向君王陈诗,指明君王的过错。屈原的《离骚》就是广为熟知的“佹诗”,屈原以美人自比,讽刺君王“终不察夫民心”。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来看,《离骚》已经突破了孔安国对于“诗可以怨”的认识,因为在创作这首诗时,屈原已经多次对楚怀王劝谏无果。《离骚》的创作,更多地是抒发自己的苦闷与失意,实际上已经和后世的诗歌创作动机一致了。屈原在《九章·惜诵》中说:“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他认可诗的劝谏作用的同时,也指出诗的抒情作用。这是诗歌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
进入汉代,“诗可以怨”在继承讽谏的职能的同时,也有所发展。《诗大序》中所说的“下以风刺上”,是对先秦“诗可以怨”认识的继承,即“怨刺上政”。然而,《诗大序》也对“诗可以怨”这一观点有了新的突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即心中所想,可以以作诗的形式抒发出来。虽然加上了“止乎礼义”的制约,但也是理论上的重大突破,那就是诗的“去功能化”,诗不但可以起到劝谏的作用,同时也成了抒发自己个人情感的工具。而“怨”又何尝不是一种常见的、想要抒发的情感呢?封建社会体制下,只有士大夫阶层拥有识字的能力,吟诗作赋也是他们的专利,士大夫官场沉浮,失意之事也自然良多,满腔愁苦何处排遣?唯作诗一途。从此以后,“诗可以怨”的命题逐渐明朗起来,并向着抒发个人的怨愤之情而不断演进。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提出了“发愤著书”说,这是对屈原观点的进一步发展:“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将个人的怨愤之情诉诸笔端,通过创作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并指出自己之所以仍然在隐忍苟活,就是因为自己“私心有所不尽”。而令司马迁青史留名的《史记》,不就是司马迁一边受尽刑苦,一面发愤著书而来的吗?可以说,司马迁以自己的方式诠释了“发愤著书”的观点。
魏晋时期,随着陆机“诗缘情”观点的发展,“诗可以怨”这一命题已然完全转化为个人情感的抒发。诗人排遣诗句,除了少数专门用来拜谒的功利诗之外,我们如今看到的大多名诗都是心有所感,随后作诗以叙。钟嵘《诗品序》中的“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强调了诗能起到情感寄托的功用,能使人们在面对艰辛苦闷的生活时,获得心安;换句话说,一个人潦倒愁闷,全靠“诗可以怨”,获得了排遣、慰藉或补偿。诗人在人生得意时,喜爱作诗;悲凉失意时,也爱作诗。然而,欢乐的喜悦往往千篇一律,但苦难和悲痛有不同的样子,所以“怨诗”常常别有风味,引人共鸣,让人回味无穷。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云:“蚌病成珠。”失意的现实经历,往往让诗人写出悲绝的作品。成功的喜悦之情,往往填满诗人们的内心,使得他们无暇顾及其他的事情,他们品山鉴水,只觉得是大自然在为自己歌唱;登高望远,看到满目山河,只觉得心怀无数壮志。可人生的悲苦使人消沉,使人冷静,使人有時间注视自己的内心世界,可以深入思考并用心看待眼前的风景、斟酌自己的诗句,内心的曲结和婉转往往便可以化作同样凄婉的诗句。
唐宋时期,作为中国诗歌艺术的巅峰,诗歌理论自然也蓬勃发展。此时,“诗可以怨”已然成为诗人们的广泛共识,甚至诗人们为了写出更好的诗句,走入“为诗造情”的歧途。南宋辛弃疾的《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写道:“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这便是很好的例证。从笔者个人角度来看,将“诗可以怨”从情感层面上升到另一个高度的人,是南唐后主李煜。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评价他的词:“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词这一题材开始发展的时候,只是源自民间的唱词,相当于我们当今的流行歌曲。王国维认为,李煜将词这一诗歌题材的气度和格局放大了,使词在后世能和诗一起并列中华文苑。当然,在这里我们不谈李煜对于词历史地位的影响,只谈他千古奇绝的、影响深远的抒发愁绪的方式与词句。众所周知,李煜在被俘成为亡国之君后,被关押在一座小院中,只有一个仆从和一个老兵相伴。对于他们,李煜自然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更何谈互诉衷肠。于是,李煜只能独上高楼,而他举目所见,景色依旧,却非故国,无限愁绪自然应运而生。“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是如此凄婉;“无言独上西楼”(《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无言”“独上”二词,已然写尽心中的愁绪与无奈;“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以流水比作愁绪,从此流传后世。欧阳修亦写道“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踏莎行·候馆梅残》),是如此的缠绵;“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以梦中的乐景衬醒来的哀情。每次读到此处,笔者几乎可以想象那种难言的失落与悲伤。李煜也是如此,又如何不泪湿枕巾,提笔赋诗?可以说,李煜完美诠释了“国家不幸诗家幸”(赵翼《题遗山诗》),他的词句太过泣血苦痛,他的经历也同样如此,也造就了词坛一座永恒的高峰。人们在谈论词作时谈到李煜,将“凄婉”作为他的代名词。“诗可以怨”的主旨,在他手上达到了一个情感上的顶峰。
唐代杜甫在《天末怀李白》中提出的“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从反方向说明过于顺利的人生轨迹是无法造就奇绝的诗句的。韩愈作为古文运动的发起者,将“诗可以怨”这一理论的范围继续扩大化,主语从“诗”延展到了一切的文学创作中,他在《荆谭唱和诗序》中提到的“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好之,则不暇以为”,从正反两方面说明文学创作中苦难经历的必要性,他又在《送孟东野序》中进一步阐述出“大凡物不得其鸣则鸣”。可以说,到了这一步,“诗可以怨”观点已经完全发展成熟了,从“诗可以怨”到“不平则鸣”,它的命题含义已经被无限放大,且没有更多的发展空间了。后面的文学大家,只是在这一观点上作进一步的补充,如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梅圣俞诗集序》)。“诗可以怨”从一开始的“怨刺上政”,只有初级的劝谏作用,到发展出“抒情”的额外含义,再到诗人们发现“怨”在诗歌创作中的帮助,最后到韩愈“不平则鸣”的一锤定音,将“诗可以怨”的主语和宾语都扩展到了无限大。至此,这一套理论命题已经成了从古至今文学创作的基本原则。更有甚者,这一原理从文学层面被剥离,渐次演变为触及人们生活起居的人生哲学。
那么,谈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才子骚客们创造诗篇的永恒灵感了。心中的怨恨因何而起?无非是生活、官场的失意。心中的愁绪因何而发?积累的伤感何以抒怀?这就无法绕开诗词历史上的经典意象—“凭栏”。早在《诗经》的《国风·周南·卷耳》中,便有了以登高抒怀情感的诗作:“陟彼崔嵬,我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登高望远,看到满目山河,心中自然顿起人世沧桑之感,心中伤春悲秋的积郁之情,也自然而然地被引发出来。自唐五代之后,诗歌的题材、意象逐渐固定,诗歌的抒情方式也臻于成熟,于是凭栏而望,借景抒怀的作品开始井喷。独倚栏杆,只是引出愁绪的方式,而每位诗人的愁绪,却有千种万种。有深闺怨妇的“春日凝妆上翠楼”(王昌龄《闺怨》),“梳洗罢,独倚望江楼”(温庭筠《望江南·梳洗罢》)和“斗鸭阑干独倚,碧玉搔头斜坠”(冯延巳《谒金门·风乍起》)。美人凭栏,在中国诗歌的传统意象里,无非是思念爱人,他们也许是游子,也许是征夫,但总归不在自己身边。独上高楼注定是孤独的,否则也不会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千古名句了。也有爱国壮志难酬,如岳飞“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满江红·写怀》)何其悲壮!更多的时候,登高望远,往往引发人们对自己身世凄凉的感叹。于游子,是久未归乡,如柳永的“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于士大夫,是壮志难酬,如辛弃疾的“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于亡国之君,是国破家亡之恨,如李煜的“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种种凭栏,不同愁绪,岂不是“诗可以怨”的最好写照吗?
当然,“诗可以怨”虽然臻于成熟,后世对于它的补充仍在继续,如宋代苏轼的“秀语出寒饿,身穷诗乃亨”(《次韵仲殊雪中游西湖》);但整体而言,并没有什么创新之处。明清时代,“发愤”观点进入了更多的文学创作中,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评价《水浒传》是“怒书”,将这一观点引入了小说批评。可惜韓愈已然将“诗”的含义放大到了所有的文学创作中,所以这些观点只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把更多的文学体裁纳入了这些范围而已。清代赵翼在《题遗山诗》中写的“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拉高了这一观点的格局,以一个历史的视角去验证这一观点。近代,钱锺书先生著《诗可以怨》,系统地梳理了这一观点的来去走向,他对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为赋新词强说愁”的行为进行讨论,也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上的一些风气进行研究,原因在于“诗可以怨”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一些作者文人便认为,没有苦难与愁绪便写不出好的作品,从此便钻了牛角尖,开始无病呻吟。钱锺书先生肯定韩愈“不平则鸣”的观点,但同时也认为,不是只有悲剧才能写出好的作品,喜剧同样也能。可是,钱锺书先生也不得不承认,从数量上看,悲诗确实要比喜诗要多得多,他引用张煌言的言论说:“欢愉则其情散越,散越则思致不能深入;愁苦则其情沉着,沉着则舒籁发声。”“诗可以怨”观点的流变宣告完结。
可以说,“诗可以怨”是古人在文学创作领域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它的影响是巨大的,同时,也回答了很多世界范围的问题,比如莎士比亚的悲剧为何要比喜剧更加精彩动人,在电影、话剧、表演、歌唱领域,深刻而悲剧的思想内核也往往比爆米花式的喜剧更加让人回味无穷。“诗可以怨”已经成为中国人和世界艺术认同的一部分,作为艺术创作之林的土壤一直滋养着从古至今的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