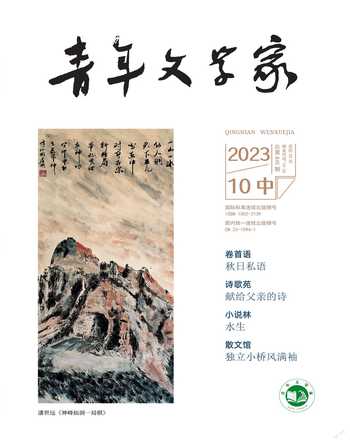父亲的“藏宝盒”
毛建忠
仰山止高,俯水止深。我生活在苍莽巍峨的祁连雪山脚下一片绿洲上,在记忆深处,父亲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身影就如眼前的祁连山一样伟岸,定格在我的心里。
打记事儿起,我就知道父亲有个“藏宝柜”,柜子里又有个“藏宝盒”。“藏宝柜”是20世纪70年代农村很普通的高低一体柜,低柜两层,里面有父亲舍不得喝的几瓶酒,还有酒具、几本历史演义书籍等。高柜上着锁,小时候,好奇的我趁着父亲外出,翻箱倒柜地找到了钥匙,打开柜子,里面只有一个盛放过茶叶的铁皮盒子,盒子里有一个存折,再就是大大小小的纸片,都是我不感兴趣的东西。我悻然地锁好柜门,此后的30年里我都没有再打开过那个柜门。
父亲去世后,我想留下一些父亲的东西,以便日后有个念想。于是,我再一次打开了柜门,把那个装着纸片子的盒子带回了城里的家,并认真地整理了那一沓沓的纸片资料,大致可以分为五类。
第一类是存取款凭证或历史凭证。上百张的流水账,一笔一笔都非常详细,存多取少,存多了就转成定期。还有一笔3万元的定期存款,显然是留给母亲的养老钱。历史凭证有粮油定购交售证、化肥供应证、社员股金证等,这些极具时代特征的凭证上的指头印,记录了社会发展历程,也记录了一个小家庭日子好起来的变化,还见证了父亲教会我娴熟地使用每一样生产农具和机械器具,教会我熟悉每一样春种夏收、秋耕冬藏的生产劳动技术。
第二类是土地承包合同。土地历来是农民的命根子,在1985年记录上,我家总承包面积是15.2亩,1997年变成了6.8亩,2004年又减少到4.7亩。有几份经营权流转协议书,转出方是父亲,转入方有二叔、小舅。爷爷奶奶在20世纪60年代初先后离世,当时叔叔8岁,姑姑5岁,父亲是家中老大,毅然扛起了这个家,抚养着弟弟妹妹。父母婚后不久,外祖父外祖母又身患重病先后去世,当时大舅被学校保送上了兰州医学院,二舅、三舅、小姨都尚未成人。建房、嫁娶、立户,青壮年时的父亲扛起了一座座山,为家人努力打拼。父亲确实留给了我一些微薄的财产,但更重要的是留给了我善良正直、真诚待人的美德。
第三类是一些购物票证。1975年3月,177元购一辆飞鸽牌自行车;1981年6月,370元购一台12寸春风电视机;1985年3月,156元购一台缝纫机;1989年,406元购双卡录音机;1995年,340元购一辆凤凰牌自行车。这些数字,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可能不以为然,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概念;但对我来说,很是不菲。我清楚地记得,1987年,我成为一名农村教师后,第一个月工资是76.2元,直到三年以后才涨到100多元。这些购置的“大件”财产是父母辛劳一年的所得,是勤俭持家的点滴积攒,是一个家庭生活积极向上的美好見证。
第四类是补助领取证和党费证。父亲当了13年的民办教师,干了16年的村干部。从2008年开始,他享受每月100元的离任村干部补助。父亲的党员党费证,每月0.2元,一直缴纳到去世前,还有一份30元的党员抗震救灾特殊党费。另外,还有一份酒泉市人大代表工作证,父亲是三届人大代表,这是一个老党员朴素的本色和情怀。
第五类是一些病历报告。三份病历报告结论分别是肺膜炎和肺结核,颈椎病,胃肠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检查时间都是父亲60岁前。看到这些病历,我很是羞愧,我只知道父亲于2005年患心肌梗死,之后一直吃药维持,最后也是因为心脏病去世。我知道,当我们站到父亲肩膀上享受人生乐趣和自由的时候,总是以为父亲的身躯高大坚强,总是忘了低下头看看父亲真实的样子,总是忘了他的身躯为了家人已经萎缩孱弱。
“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父亲“藏宝盒”里的岁月流水账,闪耀着岁月流光的深沉朴实,沉淀着岁月流金的温暖光辉。每一个父亲都有时代的烙印,都有性格赋予的正面或侧面,但总有一天,心头定格的一定是正面印记。因为我明白,父亲的意义不仅仅是哲学意义上生命的保存、延续、发展,更是生命传承的信念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