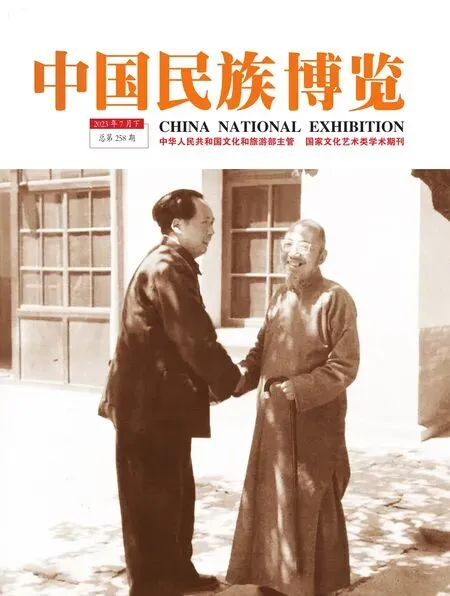《青春变形记》:精神分析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少女日记
陈志杰
(南京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2022 年3 月皮克斯首部采用女性为创作主体的动画电影《青春变形记》自上映后便引起广泛关注。这是主流动画电影史中首次由女性负责影片的主要流程;这部影片借助青春期的外衣透露出一个关乎女性意识觉醒的命题。这部充满女性导演半自传意味的动画影片体现着创作者自觉的女性自我书写的创作意识。在某种程度上《青春变形记》中导演所表述的女性话语具备埃莱娜·西苏所提出的“女性写作”的某些特质。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批评所关照的文本中的女性话语建构也成为解读影片《青春变形记》最恰当的理论武器。
一、“女性写作”:个体生命经验的影像表达
写作通过文字符号的组合完成作者的思想表达,是沟通交流的重要手段。“在西苏看来,写作也是女性可以抵抗和颠覆男性‘菲勒斯中心’的语言秩序的一个领域,她认为女人应该用自己的‘躯体’来写作,凸现女性力比多及其无意识。”[1]西苏所提倡的“女性写作”强调通过“躯体写作”的方式表达女性最隐秘的部分以图摧毁西方话语建立的以“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男性话语。但西苏的女性写作理论对身体和性体验的强调过于具有破坏性,而将其置于商业语境中,难免会被断章取义,成为取悦男性的噱头。女性写作的最主要目的是通过女性作者的自我言说,补齐缺失的女性话语,达到两性平等。导演石之予在《青春变形记》中将自己的生命经验融入故事中,进行自我言说,将动画影像作为媒介在银幕空间中构筑了一个女性主义表达的场域。
导演石之予在影片中以李美琳的身份将自己(或者说女性群体)青春期所萌发的那些少女心理通过影像告知观众。影片中李美琳的设定与导演石之予在身份上存在某种互文性。1989 年出生于中国重庆的石之予在两岁时随父母移民加拿大,与故事的主角——加拿大多伦多的13 岁少女李美琳具有相似的童年经历。从这一点来看,导演是将自己的经历写入故事,构成女性主义推崇的“女性写作”的意味,即“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本文”。
此外,导演所书写的内容还包括青春期时男女之间懵懂的好感,由于生理原因产生的、不被家长认可的情感。影片中李美琳多次重复她的年龄,在弗洛伊德的人格发展理论中人13 岁时开始进入“生殖期”——大约在这个阶段,男女两性的差异开始凸现,对异性的好感也由此产生。但青春期的情感通常迫于父母的压力而难以表露,影片中李美琳在偶然的书本涂鸦中绘出了男性超市店员戴文的形象,在不断画出两人暧昧的场面中而萌生出少女的情愫,而迫于母亲这一角色的干预,少男少女的故事无法继续。导演石之予个体生命经验所书写的内容并不仅限于对两性关系的懵懂,还包括青春期所遇到的尴尬事件,例如由于女性生理原因带来的青春期月经初潮。影片巧妙地将女性初潮的尴尬通过一个偶然事件传达出来——因为变身成红熊猫害怕父母知道反被误会,母亲惊慌失措地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物资,而母亲的关心行为却让女儿的私密事件在学校被广为人知。
石之予在《青春变形记》中所付诸的“女性写作”表达的是女性群体在青春期的共性特征,这些内容以个体生命经验形式表达出来,以一种真实、私密的表达方式告知观众。在这种情况下,女性观众能够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归属,因为她们有着相似的经历;而男性观众则通过这种心理活动的具象化呈现感知女性,将男性观众带入隐秘的女性世界。
二、“红熊猫”:青春期的抉择
《青春变形记》中“红熊猫”被赋予了特殊的意味,青春期的变身看似偶然,实则潜藏着双重疑问,为什么变身的时机是青春期?为什么只有家族中的女性才具有变身的能力?如果将这两个疑问放置于女性主义言说的场域中,“红熊猫”无疑是女性意识的象征,青春期诞生的女性主体意识是“红熊猫”出现的契机。
在弗洛伊德那里,青春期具有重要意义,“女孩必须经过青春期的潜抑作用,才能变成一个真正的女人。”[2]换言之,女性在男权社会被压抑的某些部分在这一阶段开始觉醒,而她们只有丢掉自己觉醒的部分才能成为女人,即成为“他者”。女孩进入青春期后心理开始发生变化,随着年龄的增长开始具有成人感,她们渴望自己能够被父母接纳、能够与父母平等交流。伴随着青春期少女主体意识的觉醒,她们开始寻求摆脱来自父母的束缚以图证明自己的成人身份。影片中李美琳同样面临着女性群体在青春期时所遇到的困境,她被要求无条件顺从父母,在此过程中她的独立的自我意识隐退。《青春变形记》中母亲向美美灌输的就是这种异化的孝道伦理,通过压抑美美的独立意识来达成所谓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
在影片的前半段中李美琳在生活中处处遵循传统的孝道准则,她尽力维持自己在母亲眼中乖乖女的形象,与之交换的是她极力地压抑自己作为女性的自我意识。影片中关于独立的、自我的女性意识觉醒的转机发生在母亲对面对质戴文的那一晚,青春期少女最私密的情感被公之于众,少女自尊心在一个公众环境中被践踏。影片通过将李美琳“变形”成红熊猫来具象化呈现少女的心理抗争,因为母亲的公开对质后的情绪失控,红熊猫才有了出现的契机。某种程度上来看,红熊猫的出现构成了少女女性意识觉醒的意象。当美美开始能变成红熊猫后同时也开始反抗母亲的控制,而深层所指的是对传统的孝道的反抗。影片中美美的乖乖女形象在变成红熊猫后开始解构,被压抑的欲望、对异性的好感、对偶像的崇拜开始显露,变成红熊猫的美美在演唱会时第一次表露出自己的内心:“我不再是你的小美美了!我说谎了,妈妈!……我喜欢男孩!我喜欢响亮的音乐!我喜欢扭动身体!我已经13 岁了!面对现实吧!”影片中的母女矛盾也是在压迫和反抗的二元对立中展开。
影片中红熊猫作为女性意识觉醒的意象,美美的长辈都有意将其变身红熊猫的能力去除,其中潜藏的所指意义便是女性自我意识的去除。她们对于自己变身成红熊猫(女性意识的觉醒)是极度抗拒的,并将其封印到自己的贴身物件中作为图腾。虽然影片中没有明确表达出除美美以外家族中其他女性角色从红熊猫的觉醒到去除的过程,但也不难推导出其中的共性:家族中的女性在青春期时的一个偶然中觉醒了红熊猫,但因为其破坏性而被迫封印 。这个封印的过程同样也是女性意识去除的过程。在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主体只有通过语言的介入完成“二次同化”才能进入象征界,在这个过程中人往往本能地接受、认同社会规范,成为社会“我”。这个过程从一开始就是掌控在男人手中的。结合拉康精神分析的相关理论,李美琳在经过男权话语同化后第一次面对自己的自我意识(进入青春期),同时这个自我意识中也包含着反对男权话语的女性意识。
影片中李美琳在青春期变成红熊猫后面对同性力量的去除并未陷入到与母亲一样的命运,她接受了自己“红熊猫”的一面并与母亲达成和解。而在李美琳之前,家族中的女性毫无例外都选择了“去除”,以此换取进入男权社会的入场券。李美琳的出现打破了这女性悲惨的宿命,她坦然接受自己的另一面,成为拥有独立意识的女性;也为其他女性开辟了另一种选项,象征着女性在男权社会有了平等表达的可能。
三、“少女日记”:女性主义的私人言说场域
从文学领域看,具有女性主义意识的言说方式大多采用“身体叙事”,即女性将自己的身体作为沟通交流的媒介不断诉说着有关女性独立性意识方面的话题,意图通过性意识的觉醒表达更深层次的女性意识的觉醒。我国20 世纪90 年代女性主义文学在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交汇中演化出带有个人私语特征的“躯体写作”,她们大多通过文字构筑展示女性独有生命体验的场域,意图夺回女性话语权。“一般来说在男性社会中女性躯体具有一种属他性,女性写作者首先要找回自己被扭曲被‘他者’化了的躯体,打破男性的价值标准和成规,才有可能作为言说主体的存在。”[3]例如我国女性主义作家陈染、林白在作品中那触及个人私人隐蔽空间的言说方式。私人化的言说在某种程度上使她们的作品也带有自传或半自传的意味。
《青春变形记》中导演石之予将自身成长的心路历程以影像方式呈现,在影像功能上具有与我国90 年代女性主义“躯体写作”类似的效用,即将自身生命体验、关乎女性主体的理解以一种自传或半自传的形式表述。相较于我国早期女性主义作家私人写作的特征,《青春变形记》更像是导演石之予在青春期特殊阶段书写的“少女日记”。或许是因为合家欢动画电影无法将自身更为私密的体验传达出来,亦或者导演青春期女性意识的初醒时获得了和解,影片虽然带有“女性写作”的自传意味但其表达方式则更偏向于温和。影片也在“日记”的私人言说与电影的公共叙事达成了微妙的平衡。“一方面,日记可视为一种‘最真实而细腻’的个体化书写形式,还往往带有丰富的个人经验感知、情感介入及意义解读,能够生动地刻画出书写者的日常生活百态和个体生命历程。另一方面,日记又呈现出超越私人言说、关联社会秩序或社会变迁等社会性问题的公共叙事取向,可以透过个体的经历及反思,去了解和分析其背后的社会文化系统、历史进程。”[4]日记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往往以个人书写的方式记录个人生命经验,这点与影片《青春变形记》传达的影像内容不谋而合;而在公共叙事层面,首先电影作为艺术本身就具备公共叙事的职能,其次影片传达的导演关乎女性意识的思考也具有公共传播的现实意义。
纵观美国动画电影的历史,以迪士尼为代表的动画帝国长期以来将女性角色置于“被凝视”的位置,充当影片中男性角色的行为动机。其间虽然涌现出一些带有女性意识的作品,如《花木兰》《美女与野兽》等,但绝大多数的女性意识表达都流于表面,或是将男女角色的叙事功能对调、或单纯歌颂女性的独立。从根源来看,这些关乎女性主义的影片仍然是出自男性之手,意图以这种方式达成现实社会女性抗争的“想象性解决”。这些影像也构成了一种“景观”,“这种景观最终成为了一种传播意识形态的工具。”[5]
女性话语自诞生起就处于一种“夹缝中求生存”的状态,“她借用他的口吻、承袭他的概念、站在他的立场,用他规定的符号系统所认可的方式发言,即作为男性的同性进入话语。”[5]《青春变形记》本身的独特性在于女性创作者的自我言说,是来自女性导演打破男权社会束缚的女性话语。这种来自女性生命经验的表述方式在另一层面与女性观众达成共鸣,达成了个人书写与电影公共叙事的平衡,也构成了与男性平等对话的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