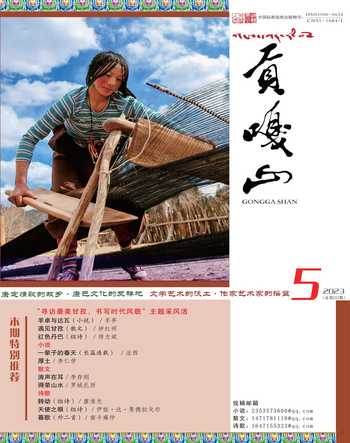又见合欢树(外一篇)
陈秀梅

在雅砻江大河边的山区,合欢树是常见的一种树。比较奇特的是,合欢树很少长在荒山野岭,它们更乐意长在有人出没的地方,如公路旁,庄稼地的土坎边。在我的印象里,合欢树都不是特意栽种的,它们好像天然就长在土里,纯属野生。
这种树与人走得特别近,也很容易被人视而不见。没有人去给合欢树锄草,施肥。它们亲近人却不依赖人。它们唯一依赖的是脚下的土地和头顶的阳光雨露。
合欢树叶纤细如羽毛,但它一样绿荫如伞;它的花丝粉红,清香袭人,花形如扇,毛茸茸的,每一朵都如女子耳朵上的吊坠,微风拂过,摇曳生姿。
这棵合欢树长在别人家的土地里,它的主人是我的发小。我每次从外县回乡,总要到这棵树下走走,渴望与发小偶遇,可是每次都带着失望而归。偶遇是一件多么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啊。
这棵合欢树已经长得很大,主干粗壮了许多,树冠呈圆形,在冬天也能遮住偏西的阳光,村里的妇女,喜欢三五成群地在树下盘膝而坐,做些诸如绣花,做鞋垫一类的手工活。只有我喜欢盯着合欢树出神。
那时,正值六月,合欢树开阔的树冠,枝叶纷披,粉花散如丝,团若云。我跟发小经常爬上树梢的枝杈间,惊奇于昼夜里小叶片的展开闭合,忍不住摘下好多枝,编成花环,戴在头上。
我跟她都不是调皮的孩子,所以我们基本上没有过什么壮举,放学路上一起聊得最多的就是电视节目,那时候我们晚上追剧,第二天放学路上,一边走一边講剧,我落下了哪集她给我讲,她落了哪段我给她讲。那时,我们听迟志强、邰正宵的歌,喜欢看《射雕英雄传》《少年张三丰》《新七侠五义》……不停地哼唱《千年等一回》,因为在放学路上讲剧、唱歌耽误了回家的时间,母亲常常是拿着又长又细的桑条到半路来“接我”。
不顾身上紫色的条痕,每个周末我们依然聚在合欢树下玩“跳房”或者踢毽子。“跳房”时,我们先在树下选块平地,找一根树棍或一块尖利的石块,在地上画上“房”。“房”以方格为主,总体呈长方形,共八个格子,长四宽二,相当于两列。
我们先找一块厚薄适中的石片,人站在两个格子的其中一边,先将石片丢在第一个格子内,跳的人全神贯注,单腿蹦跳,将石片轻轻踢进第二个格子内。这样依次一格一格跳下去,直至将石片踢过全部格子。中途累了,我们就在合欢树下促膝详谈,当作休息。
进入下一轮,我们再将石片丢在第二个格子内,再从第二个格子踢进第三个格子,依次跳下去,最先把格子跳完的就算取胜。跳完全部格子后,就取得了盖“房子”的资格。盖“房子”要求跳的人背向“房子”,将石片从头顶向“房子”抛过去,石片落在哪一格,哪一格即为胜者的“房子”。如果石片压线了,或者出线了,则算失败。不知不觉,太阳偏西,父母喊回家吃晚饭的声音,透过合欢树叶的缝隙传了过来,我们才依依不舍地作别。
回到家,我才发现胶鞋右脚大拇指的地方已经破裂,脚指头从胶鞋里钻了出来,鞋帮也破了洞。第二天,发小一见我这狼狈的样子,总是咧嘴笑开了,弯弯的眉眼,上翘的嘴角,带出右脸颊那个深深的酒窝。
又到周末,父母是不再允许我们“跳房”了。我们只有满世界寻着能做毽子的材料。最受我们青睐的是火麻,火麻树两三米高,树形像一把伞,树叶似爪,上面长着细细的绒毛。我们摘下它的叶子,用细绳从中间穿过,扎在一起变成了“毽子”。白杨树叶和废弃塑料袋都是我们做毽子的材料。那时明媚的阳光异常温柔,肆意地洒在合欢树的枝丫上,树下又成了我们斗“毽子功”的战场。
后来,因发小的家庭突遭变故,接着她便辍学了。我也去了外地读书,后来的假期,我去找过她几次。她总是在灶台边忙碌着,那是一个土灶台,用土砖垒砌,糊上黄泥石灰。她爱干净,灶台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拾掇得清清爽爽,锅碗瓢勺、油盐酱醋各归其位。接着她挑出两个大点的土豆切成细细的丝,轻车熟路地放到锅里翻炒,再做出一些洁白绵软的馒头,她说现在迷上了织毛衣,还经常去那棵合欢树下边织边打发时间。
再后来,等我假期回家去找发小,发现她的房子大门紧闭,锁孔隐隐透出斑驳的锈迹,台阶上长了一层绿色的青苔,庭院安静。村里人告诉我,发小早已远嫁。那天,我回到我们的合欢树下,闭眼能清晰地听到风过合欢树叶的沙沙声,一阵落寞袭来。
“春色不知人独自,庭前开遍合欢花。”时光如河,合欢犹在,穿过合欢牵缀的旧时光,我仿佛看到发小在自己的角落,长成了一株合欢树,那温暖的笑,那双勤劳的手,将生活过得有滋有味,美好合欢,生生不息。
我的外公
我的外公是一个瘦小却精神矍铄的老头,头上永远包着青布帕子,嘴里叼着旱烟袋,他一“吧嗒”,冒出一股轻烟,兰花烟的味道就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外公喜欢抽烟、喝酒,已经达到嗜烟嗜酒的程度。在那个过滤嘴香烟还没普及的年代,外公的烟都是自己种的。
那年春天,他在房子的旁边开辟出一小块地,四周用大大小小的石头垒起个小园来。锄头刨开土,拣出小石子,平整好肥土,就开始育烟苗了。我望着外公手心里比天须米还小的烟种子,问外公:“这么小的种子,能长大吗?能变成你嘴里的兰花烟吗?”外公不厌其烦地回答我的一通问题,现在想来,外公说的大概就是只要是种子,只要种下,只要努力发芽、生长、开花,总会成熟。以至于后来,我都相信,每一粒种子种下,都是一个希望,总有结果的时候。
兰花烟被外公在小园里种得一片片的,他每天坚持浇水,果不其然,在他的精心照料下,兰花烟发芽、长大。虽然兰花烟的个头不是很高,但是它椭圆细密的叶片吸引了我,忍不住伸手摸上去,墨绿色的叶子黏黏的。
阳光和雨露是植物最好的催化剂。叶子依然围着毛茸茸的兰花秆四散展开,叶柄与秆的结合处,开出状如小铃铛、指甲盖般大小的黄色小花来,一朵朵向着太阳。
外公一如既往地给它们浇水,施肥,发现根部的叶片黄了,便立即揪下,放在阴凉通风处晾干,揉碎后的烟沫被他迫不及待地装入烟袋,盘腿坐在一棵桑树下吸起来,一圈圈袅袅的烟雾和解了他弓身烟地的辛劳。等立秋过后,外公收下所有的兰花烟叶自制成了旱烟。他每次抽完一锅旱烟,便将烟灰随意磕在鞋帮上,开始给我讲起故事来。
外公还喜喝酒。酒是文化,喝酒可助兴,喝酒能解忧。但是,乐呵呵的外公喝酒,可能只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爱好。那时候的酒器没有现在齐全,一个葫芦就是外公的酒罐,无论上山放牛羊,还是下地干活,外公的腰間总带着它,让我想到游乎四海,自由快乐的济公。那时酒的种类没有现在丰富,外公的酒罐里装着散装白酒。放牛羊累了,找一块大青石坐下,拿出酒罐放在嘴边轻轻抿几口,酒液滑过外公的喉咙,他的一皱眉,一眨眼,都让我觉得喝酒是让他快乐的事情。所以外公每次酩酊,坐在二楼隔板上对着外婆和小姨发酒疯,她们偶尔会迁怒于我,在她们眼里.外公最疼爱的孙女都不劝外公少喝,真是白疼,只有我知道,喝酒才能让外公真正地快乐。
每逢村子里红白喜事,有酒仪式才能完成,正如《左传》里说的“酒以成礼”。在这种场合,外公也是必醉的。有一次,村里一户人家有喜事,小姨在家左等右等不见外公带着我回来,随即找到这户人家,只见外公早已喝得酩酊大醉,怀里还紧紧搂着熟睡的我。
还有一次,村里有户人家办丧事,外公照例醉得不省人事,一到家,他颤巍巍地从怀里掏出一个黄皮纸团递给我。打开纸团,虽然热腾腾的雾气早已散尽,但油光锃亮的两块肉正散发出诱人的香气。
根据村里传统,无论红白喜事,都会弄“三盘九碗”来招待宾客,答谢四邻,在那个生活艰难的年代也不例外。待到开席,每桌都会上一道“硬菜”——“墩子”(红烧大肉),那时物资匮乏,每份“墩子”都是算好的,一块不多,一块不少,每人两块,外公等其他人把自己的分子夹走,便找来一张黄皮纸,把剩下的两块夹起来包上,揣在怀里,给我带回来。
外公带我上山放牛,教我认识黄峰、黄芩、川芎、当归……那些草药,有的长着狭小的针叶,有的是阔大的叶片,有的开着五色漂亮的花朵。外公把草药挖回来,洗净放人瓶子泡酒。我最喜欢看他的药酒瓶,里面总有一些花瓣舒展,漂浮在酒面上。有时候走累了,外公让我在岩石底下休息,我便蒙上自己的耳朵,对着泡灰里的小窝大声吼起来,不一会儿,爬出一只不知名的小虫,这样一直可以玩到外公采药回来。以青山绿水为邻,以花草虫鱼为伴,便是那时我初识自然的写照了吧。
外公信奉“男带魁罡,女带文昌”的这一类男女,必有出息。他总说我命带“文昌”,坚信我是必有“出息”的。7岁那年,我上小学,外公用积攒下来的35块钱,为我交了第一学期的学费。外公寄予我的厚望,就是好好读书,将来“有出息”。现在想来,外公所说的“有出息”,可能就是摆脱父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吧!
后来外公生病,被大姨接到县城治病、休养。第二年春天,外公离世。就是这个慈祥的老头儿,在疾病中艰难地走完了60年的人生。
“那些死去的人/停留在夜空/为你点起了灯;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又熄灭/离人挥霍着眼泪。”不知道人死后,会不会幻化成星星,但是外公的灵魂一定是有光亮的,在那个叫作“天堂”的地方,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