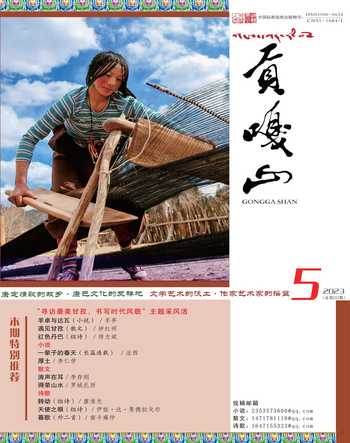涛声在耳
李存刚

降落
从天全方向走国道318线去泸定,须得翻越二郎山。这座海拔三千多米的高山,如果真走老川藏公路“翻越”而过,至少得半天、一天,甚至更长时间。好在新千年后从半山腰修通了公路隧道,只需几小时,就可从山这边的天全去到山那边的泸定。2016年,过境天全的雅叶高速雅康段还未建成通车。我去二郎山另一边的泸定走的旧公路隧道。
出发的时候下着细细密密的雨,雨水生出浓浓的雾气,满世界迷迷蒙蒙的,像被一张铺天盖地的帷幕罩着,空气里弥漫着丝丝初春的凉意。过境大货车依然很多,经过“4·20”地震灾后重建,大部分路段已是平坦的沥青路面,车行在路上,有一种无可比拟的快感。因为重建改造工程尚未完全收尾,少数路段依然是坑坑洼洼的,我们的车子跑一段路便不得不减速下来,倒也避免了我们总是高速行驶可能出现的麻痹。
穿过二郎山隧道,眼前的世界便是另外一番模样:天空湛蓝,阳光灿烂。山两边的植被依然是记忆中的样子:天全一面满眼透绿,山的另一侧,目力所及的山体险峻陡峭是自然的,山色焦黄得恍如山那边的深秋,仿佛刚刚被大火肆虐过,偶尔有一两株绿色植物呼啦一下撞入眼帘,让人惊喜得想要失声尖叫。我曾若干次到过泸定,及至往西更远的涉藏地区,并为此写过一篇《二郎山记》,说的就是多次翻越二郎山的感受,但我总觉得还没有写够,还想找机会再写写它。没想到这个料峭的春日里,我又一次踏上了这条路。
下午4点过34分,终于顺利抵达了此行的目的地泸定县城。我对时间一向缺乏必要的敏感,这个时间,是在手机通话记录里保存下来的。之前的4点28分,我接到一则发自泸定县人民医院办公室的短信,告诉我到达后找谁联系,并且发来了联系人的手机号。我翻看完短信,电话尚未拨通,便接到对方打来的电话。那时候,我们的车子已经穿过二郎山公路隧道,正沿着二郎山蜿蜒绵长的山间公路一点点盘旋而下。
通向医院的街道正在重修,县城高处与之相通的道路皆成了“断头路”,满街乱七八糟地堆着各种杂物,从县城高處去到医院,须得绕道城尾,从进出医院的绿色通道才能到达。我们不知道这个情况,我们的车子从高处的道路拐进一条斜坡,还没开到坡底,便不得不踩下刹车。这样的情景是我熟悉的,一山之隔的那边,我来的雅安(天全县)更靠近“4·20”地震震中芦山,灾害更甚,很长一段时间里,整个县城差不多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街边行人的表情也似曾相识,和我来的地方一样,人们打心底里知道不破不立的道理,未来可盼可期,若干时日以后,现在的脏、乱、差将会被净、齐、新取代。人们小心翼翼地躲避着街中心立着的围栏和街边的乱石水泥堆,在逼仄的小道上躲闪腾挪,以免和身边同样小心翼翼地走着的行人撞上。
倒是开车送我们来的师傅显出了些许不适,此前他曾在这里工作(与我们同样性质)过两年,他满以为两年的时间足够让他熟悉这个小城,因此主动当起了我们的司机兼向导,一路上不停地给我们讲述他在这里工作期间耳闻目睹的逸闻趣事,没想到刚一进城,这个小城便当头给了他一记棒喝。好在我们及时下了车,改由步行去到医院,否则还真不晓得他会窘成什么样子。
在泸定县人民医院办公室,不出意外地见到了吴勇。我之前就和吴勇有过一面之缘。2014年11月22日康定地震时,我所在的医疗队受命第一时间赶赴灾区,我们的救护车在夜间翻越二郎山时出了故障,走走停停,勉强行驶到泸定县城便彻底熄了火,我第一时间打电话回去向医院领导汇报了情况,医院领导又打电话到泸定,结果就联系到了吴勇。他二话没说,便连夜开着救护车,将我们送到了那次地震的震中——康定。那时候,吴勇是泸定县人民医院的副院长,分管日常业务,现在分管的是行政和后勤。在稍后举行的见面仪式上,我还知道了,吴勇是成都市青白江人,毕业后来到泸定工作,不久将与一位泸定姑娘结婚,彻彻底底地把自己变成一个泸定人。
见面仪式后搬行李去住处,住处就在医院办公楼旁边的另一栋楼里,与医院办公楼隔着一条水泥小路。那是医院的旧家属楼,建在靠近大渡河的斜坡底部。在吴勇的安排下,后勤处的高大姐带着我们从医院办公楼出来,走到街边与水泥小路的交叉口,高大姐指给我们看时,我以为楼房是三层的,等我们到了楼下才看清,楼房原来是五层的。因为地势更低,有两层楼房建在了街道平面以下。水泥小路刚刚被雨水浇过,湿滑得厉害,我们只能侧着身,像膝关节病患者那样横着双脚,一点一点地向前挪动,可终究没能控制住自己的身体,刚走出两步便不得不挥舞着双手,大鸟一般,一股脑儿冲到了小路尽头的空地上。
空地之外便是堤坝,堤坝之下便是滔滔不息的大渡河河水。我们提着行李进到楼里的房间,关上房门,耳边依然盈满了大渡河河水不息的涛声。对岸近乎壁立的山体上,贴着几张绿色的大网,大网紧贴着山体,仿佛破损的外衣上缝合严密的补丁。想必是为防止石块脱离山体飞滚而下,特地挂上去的。
站在房间里,我是彻底明白过来了。我们此刻的所在,其实就是大渡河岸边的一处斜坡的最低处。自打穿过二郎山公路隧道的那一刻起,我们就一直在沿着盘曲的公路不断地往下走,降落,再降落,目标就是大渡河,就是眼前这栋老旧因而很可能用不了多久就将消失的楼宇。现在,我们抵达了。
房间里悬着十五瓦的白炽灯,灯泡悬吊在屋子的正中央,电线贴在一整片白色涂料涂抹后的墙壁上,仿佛光滑的腿肚子上突显的静脉,白色的墙壁因此显出了些许生机,单调不再了。高大姐开门的同时摁下了开关,我猛地打了个激灵,不由得闭上了双眼,再睁开来时,才看清这突起的光亮是由一盏白炽灯发出的。
高大姐和同行的一位中年男子一起为我们装被子、铺床,两人配合十分默契,像是共事了多年。高大姐一边为我们铺床,一边叮嘱我们:这里风很大,夜里会冷,最好盖两床被子。生活上有啥需要,随时和她联系。在我们嗯嗯地应答着的时候,中年男人也开始附和高大姐的话,高大姐每说一句,他便附和一句,所谓附和,不过就是在高大姐每句话后重复两个肯定的词而已,像录音机的重复播放:是的是的,就是就是。后来高大姐似乎听得烦了,突然收起笑容,屏着气,抖手里的被套,眼见中年男人没跟上,高大姐便瞪了一眼中年男子,吼了一声:扯好!中年男子看着高大姐,不但不恼,反而嘿嘿一笑,嘴里和手里同时配合着高大姐:扯,再扯!
高大姐和中年男子都不是本地口音。从默契的配合可以看出,他们不是第一次接待我们这样的外来者,不是第一次一起干铺床铺的活儿。一问才知道,中年男子原来是高大姐的丈夫,他不是医院的职工,那天他来医院,纯粹是为了帮高大姐的忙的。他们的老家在四川靠近重庆的某个县份,但具体是哪个县份,我没问,所以就暂时不知道了。
晚上,枕着大渡河的涛声躺在温暖的被窝里,禁不住在微信朋友圈发送了一条消息,内容就是到泸定途中手机拍摄的几张照片:二郎山上的积雪和云雾、医院旧家属楼外的河堤、河堤之下蓝汪汪的大渡河河水、河西岸打了“大补丁”的山体。看到消息的朋友们纷纷点赞、留言,有朋友甚至打来电话,表示无论如何也要抽时间到泸定来看我,我笑着回答:来吧来吧,来了,我们一起听大渡河的涛声。
成武路111号
泸定县人民医院所在的街道叫成武路,蓝底白字的门牌号码就贴在医院大门旁的外墙上:成武路110号。我起初想当然地以为,旧家属楼也会是同一个号码。后来有一天,我站在水泥小路与街面交叉的路口,无意间瞥见靠近水泥小路的外墙高处也贴着门牌,编号却是另外一个:成武路111号。这是两个不同的序列,成武路是一个,111号里面是另一个,最靠近水泥小路的那栋是“1”,往里走是“2”,我们入住的是“3”,再往里走是“4”。算不上庞杂,却也足够井然。
人住“3”以后的第一天早上,不到6点就醒了。叼着烟,裸身去卫生间。一离开被窝,浑身便禁不住接连打了几个冷战,赶紧抓起床头的外套披上。
卫生间左侧的墙上高过人头的地方挂着电闸,电闸下半部分没装外壳,金属片外露,从天花板上掉下的电线通过闸刀弯弯曲曲地连着热水器。热水器是一口斑驳的铝质大桶,放在墙上支出的金属架子上,推开门便可看见朝向门口支着的喷头。进水管阀门就在右侧齐腰高的墙上,铝质水桶外面竖着一根塑料颜色的导管,打开进水管阀门,或者放水洗澡时,可以看见塑料色导管里的水位变化,以此判断铝桶里水量的多少。
住进来那天晚上,高大姐替我们铺好床,专门把我们叫到卫生间讲述热水器的使用方法。为了打消我们心头的疑虑,高大姐还很肯定地告诉我们:不要担心,以前这里很多人家都是用这个的,现在好些人家换电热水器了,医院也准备换,还没来得及。此刻再看,高大姐的安慰和鼓励似乎没起任何作用,心里嘀咕着,但愿真正使用起来时如高大姐所言,不会弄出什么岔子。
正走神间,耳边突然响起一阵嗡嗡声。心里一惊,定睛细看,一只蜜蜂正围着铝质水桶不停地翻飞。我对蜜蜂的了解仅限于外貌和声音,其余一切皆是空白。眼前的这一只,只一眼就觉出它与印象中的不同,它太大了,身体肥硕得有拇指尖那么大,却一点也没影响到它围着铝质水桶不停地翻飞,嗡嗡、嗡嗡、嗡嗡……我大气也不敢出,赶紧捂着嘴,生怕它循着我呼出的热气呼啸而来,停驻在我身上,蜇我一下。接着,我赶紧拔腿,飞也似的逃离了卫生间。
回到被窝赖到7点,这也是我多年习惯的起床时间。有了刚才的经历,披好衣服再站到卫生间门口时,便没敢即刻进入,而是站在半掩着的门前,侧着身体,一边轻手轻脚地将门尽可能地推开,一边侧耳细听,随时准备着撒腿逃跑。直到确认卫生间里没有大蜜蜂的身影,没再听到嗡嗡声,这才抬起腿,放心地跨进去。
时间稍稍长些之后,我注意到,111号旧家属楼里住的基本上是医院里退休的老职工和刚到医院工作的新人,少部分是像我这样的暂居者。楼下的空地里,但凡能够栽种的地方,都种上了花草和各种时令蔬菜。我好几次看到有老人弓着腰,专心致志地拔除菜地里、花草间的杂草,起自大渡河的风吹不着他们面朝黄土的脸,一个劲地吹拂他们的头发,像被一只看不见的大手揪着,一阵东倒西歪过后,整整齐齐的发丝便乱成了茅草样。阳光洒下来,他们的白发,便更加具有了深秋茅草的神韵。他们手里握着杂草,刚刚放上身旁的小草堆,便被整个地掀翻在地,好些草枝随风扬起又落下,也不知是否落回了它们被拔起的地方。
天气晴好的午后,有几位老人抬了麻将桌出来,摆在楼梯口边打牌。有时候是三个或者四个,有时候是五六个。五个或者六个人的时候,四个人上桌,另外的一两个人围着桌子,不时指指点点。桌子挡住了进出樓梯的路,我打楼梯口经过,他们便手扶着桌缘,慢慢悠悠地满脸羞赧地站起来,侧身让我过去。我有几次站在桌子旁,听他们在打牌的间隙,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些远远近近的事情,像老旧的收音机里发出的嗞嗞声。
不知是听人说起,还是从我的口音里听出了端倪,老人们后来都知道了我是外面来此短暂工作的医生,对我们就更加热情了。证据之一是在我经过或者站在桌边的时候,他们纷纷停下正在进行的牌局,询问我工作和生活的情况,不止一次指着菜地告诉我:需要就自己去扯。证据之二是更加耐心地解答我提出的各种疑问。楼梯口对着的空地里种了一棵重瓣粉红海棠,五六米高,我住进去不久,海棠树上便开满了红艳艳的花,似乎一直没见谢过。我起初不知道那是什么树,怎么会开出那么艳丽的花朵,问老人们,老人们便从它的植物学史、形态特征、物种分类,讲到它的病虫防治和主要价值。从老人们七嘴八舌地讲述里我第一次知道了,在古时,海棠花又被称作断肠花,常常被借以抒发男女离别的悲伤情感。我好奇:这花是谁种的?一位老太太笑呵呵地指着旁边刚才给我讲述的一位老者:他!只有他喜欢干这事嘛!我看到老者脸上明显地愣了一下,脸上的笑容骤然收紧,却没答话。我很想再问问老人:那么,你是不是也将这株海棠当成了断肠花?话到嘴边,却终究没说出口。这样的问题实在太过唐突,我不想冒犯了老人家。
后来有一天一大早,旧家属楼下的空地里突然搭起了灵棚。进出旧家属楼的路呈“L”形,灵棚因地制宜地搭在那一“折”上。最靠近河堤的一边被单独隔开,成了一个单间,朝街的一面敞开着,正对着水泥小路路口,从水泥小路进出旧家属楼的人,走到街面上的斜坡顶,一眼就能看见里面的长条凳,和凳子上白色被单下躺着的逝者。逝者旁边蹲着几个人,不断往燃着的火堆里添加纸钱,火堆摇晃而起的光亮映红了他们悲戚的面容,和他们脸上亮晶晶的泪珠。灵棚旁边是一溜更广阔的大棚,整整齐齐地摆满了桌子和凳子,随时等待着有人坐上去。
临近中午,大棚里便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人,他们嗑着瓜子,抽着烟,轻声交谈着。单间和大棚之间,一直摆满了花圈。灵棚下的人似乎更多了,他们依然围在一起,不停地往眼前燃着的火堆上添加纸钱,纸钱冒出的浓烟四下里缭绕着他们沉默的悲戚的臉,大约是烟雾太浓了,熏得他们一个个泪汪汪的,不得不隔一会儿便抬起手来擦拭一次,擦过之后,便又继续默默地将手里的纸钱丢向火堆。
听办公室里的同事们说,逝者是医院一位退休职工的家属,腰疼了多年,一直以为就是腰上的毛病。几天前老人去我工作的那个科室里找到医生,二话没说就要求理疗。接诊医生觉得不对劲,老人以前很精干的,突然瘦得很厉害,感觉也没了以前的精气神。接诊医生拒绝了为老人理疗,反而建议老人去检查一下内脏。这一检查可是吓坏了老人的家人:胆囊癌晚期。
我曾不止一次地看到过一组统计数据,那是以秒为单位,分门别类地统计出来的全球范围内各种因癌症去世的人数。数目算得上庞大,但条分缕析,一看便知,每看到一次,便惊心一次。个体的生命总是脆弱而渺小,正如科室里的同事所言,像一枚叶片,每个人都逃不过离枝的命运。我无从知道眼前的老人是否也将进入统计数据。枯燥的数据也总是让人感觉冰冷而恍惚,有一种无以言说的距离感,似乎很近又似乎遥远。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数据里的每一个组成背后,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可能正值壮年,可能老态龙钟。这是一种既可怕而又十分明晰的指向。这样的指向很像刀割,一刀一刀,刀刀都戳向我们脆弱而敏感的神经。因为我们都会设身处地,仿佛我们或者我们的亲人已然是统计数据里的组成部分。
老人去世之后,旧家属楼的楼梯口很久都不见麻将桌再摆出来。我从楼上下到楼梯口,抬眼便看到院子里的海棠花兀自灿烂地开着,树下落满了粉红的花瓣。胸中瞬间塞满了莫名的悲伤。
土豆晚餐
在高原,人们喜欢把聚在一起的人叫“伴儿”,有时候明明是彼此刚见面,可能非亲非故,只要认识继而彼此认同了,也被叫作伴儿。
我喜欢这个词,尤其喜欢它既亲切又涵盖无边的概括力。牟医生来自市里的一家三甲医院,从事西医骨科,我来自天全——个小县,从事的是中医骨科,我们一同来到泸定,进入不同的科室,入住同一套房子,入乡随俗,牟医生就是我的伴儿。
牟医生十多年前从川北医学院毕业,被分配到重庆的一家企业做厂医。因为离家太远,不方便照顾年迈的父母,牟医生于是收起了随时可能迈向重庆的脚步,转而在家乡另找了一份工作。他最先是去了汉源县的一家医院,医院接待者一听他辞掉工作的事情,便直摇头。那是20世纪末,在偏僻川地的很多地方,双向选择还是个新鲜事物,好些人还接受不了自由择业。
牟医生接着去了泥巴山另一边的荥经县。医院的领导很赞赏他的勇气,大约也有对家乡和父母的拳拳之心,同意接收他,唯一的前提是无酬试用三个月。牟医生当然地点了点头。牟医生本就是荥经人,能够回到家乡工作,离父母更近,是他求之不得的事情。但是,三个月没有经济收入,生活便没有着落,一日三餐便成了他每天冥思苦想,却不得要领,又不得不面对的大问题。有一天父亲去医院看他,顺道给他送去了一口袋大米、一大筐鸡蛋,外加一大口袋土豆。父亲说是去看他,其实是知道他刚刚参加工作,没多少钱可用来花销——他一直不敢对父亲说他暂时没有收入,他怕父亲担心,继而把担心传到母亲那里,继续把自己变成家里的负担。
那一口袋大米、一大筐鸡蛋,外加一大口袋土豆,便是牟医生三个月的口粮,不够是当然的。因为方便加工,最先吃完的是土豆。有一天下班回到住处,牟医生便发现土豆所剩无几了。他掂了掂口袋,索性把剩下的土豆一锅煮了,独自坐在仅有一张床、一口锅的宿舍里一个接一个地吃,一边吃一边记下了吃过的数目,等数到32的时候,装土豆的小锅便见了底。这时候,牟医生扶着肚皮站起身,一点点挪到床上,临产的孕妇般艰难地躺下,目不转睛地盯着斑驳的天花板,思考自己不长的人生,也思考接下来的日子该如何过活。有那么一瞬间,牟医生觉得自己已经到了世界末日……三个月后,牟医生顺利通过了医院的试用考察,成了一名正正经经的医生。不久前又调到市里的一家三甲医院。这也才有了这次,我们在成武路111号的相聚。
我受大蜜蜂惊吓后的一天,牟医生也经历了同样的遭遇。也是在大清早。只不过牟医生当时举着手机,查看回复朋友们夜间发来的信息,走进卫生间蹲下去时还在翻看、回复,等他发现刺耳的嗡嗡声时,那只大蜜蜂已经盘旋、降临到他头顶。牟医生腾一下起身准备跑开,当然地忽略了对手机的管控,握着的手机于是从手里滑落,直直地掉进了便坑里。
手机后来是捞起来了。牟医生很有经验地拿出电吹风,吹了好一会儿,试了两次,都没能顺利开机,便不敢再试了。怕短路,这是牟医生说给我听的理由。这个简单的物理常识,我倒是知道的,但牟医生接着十分肯定地说,如果及时将手里的水分清除干净,手机还能用,我就有些将信将疑了。
事实证明牟医生是对的。因为早上有个手术,修手机的事牟医生只能托付给我。我先后去了两家手机维修店,店主们都摇头,表示无能为力,但后来的一家店主指给我菜市场上—个小摊点,叫我去试试,言语间带着明显的“死马当活马医”的意思。我去了,老板听我说了情况,接过手机猛烈地甩了起来,然后揭开手机盖子,拉起电吹风,呼呼啦啦地吹个不停。其间,摊点前来了两个买手机保护壳的,—个贴膜的,看起来都是老主顾。老板叫他们等着,他们便都静立在那里。过了不下半小时,老板放下电吹风,问他们要什么。停当之后,老板拿起牟医生的手机,再次猛烈地甩了几下,然后合上盖子,摁下了开关键。我看到,牟医生的手机屏幕果真重新闪亮了起来。
牟医生很高兴。那天的晚饭,牟医生提议吃土豆。吃惯了馆子里的大鱼大肉,我们今天吃素,这是牟医生的理由。我没有反对。土豆和佐料是我们几天前去逛菜市场和超市买回的。一直放在那里,没机会做。牟医生一提议,我当然地同意了。牟医生还特地跑到楼下,给住在一楼的两位老人打过招呼,从楼下的菜地里扯了小葱,洗净切细,拌上辣椒和花椒末,香得让人直流口水。等土豆快煮熟的时候,我突然想喝啤酒。有些时日没喝了,莫名其妙地就想喝,想念喝过之后腹部的胀满感和不时打出的酒嗝。牟医生于是又一次跑下楼,买了四瓶啤酒回来。
餐桌是入住后找高大姐要来的方凳子,热腾腾的土豆和佐料碟就放在方凳上。我和牟医生一人拿了一瓶啤酒,对坐在方凳前,在方凳子上方很响亮地碰了一下,咕嘟咕嘟地大喝了一口,然后开始剥土豆。蘸上佐料吃了第一口,我便开始夸赞,从可口的土豆和香艳的作料,到牟医生调制作料的手艺。牟医生则微微笑着,既不赞许,也不反对。等我夸赞得差不多了,便见他呼啦一下举起瓶子,大吼一声“来”,然后举起酒瓶,和我在方凳子上方猛烈地相碰。如此反复了三五次,牟医生便有了些许醉意,再次拿起土豆时便陷入了与这个平凡之物有关的回忆里。
牟医生从医的经历,我就是那时候从他口中得知的。
但是,那天晚上的土豆和啤酒,我们都没有吃完、喝完。牟医生后来说,看来,我们都是过了用土豆充饥的年代的人了。这话,我打心底里赞同。
杵泥,岚安,以及任坤有
如果以天全和泸定为起始点,取一个二郎山的截面图,应该是一个放大了若干倍且略略倾斜的“N”字,酷似城垛,却又比城垛多了一个巨大的反折—那是泸定县城西面的延绵山脉。东西两面的山川之间,天空被切割成了逼仄而狭长的一缕,天花板一样罩着谷底的大渡河和沿河而立的泸定县城。
我知道杵泥是一个乡,但从没去过,不知道在那个巨大反折上的哪座山间。四月里的一天,同事们邀约去乡下吃樱桃,我问去哪里?同事们说杵泥。我于是很爽快地开上车,跟着同事们沿县城对岸的公路,拐上一条崎岖的小路,越过一个垭口,回肠似的道路绕着山体盘曲回转,弯弯拐拐之间,眼前突然豁然开朗。同事说:喏,那就是杵泥乡。古语说“别有洞天”,说的大约就是这样的地方。这也是泸定县城给我的印象:那些极不起眼的小街,拐弯抹角间,各种店铺因地制宜,见缝插针。不知道的人,走大街上经过时,以为那就是一条小道而已。一天晚上,我开着车,陪一位朋友去接他的女友。朋友下了车,拐进街边的一条石梯小路,我停了车在街边等,左等右等不见朋友出现,电话打过去却是“您所拨打的用户不在服务区”,我只好下了车,踏上朋友消失的石梯小路走进去,拐过一个小弯之后,我就不敢贸然前行了。因为前面摆着三条岔路,我无从知道哪一条才通往朋友此刻的所在。
樱桃树都种在田地的边角、土埂上。田地边静卧着几间老木屋,大门紧锁。那是一位同事的老家。同事从学校毕业后进到泸定县城工作,把父母也接到了城里,留下几栋孤苦伶仃的老屋,和田地间年年挂果的樱桃树。同事吆喝着:随便吃,随便摘。我们便呼啦一下冲到树下,伸手扯住低处沉甸甸的枝丫,有几个年轻同事即刻摇身变成了猴子,三两下爬上树梢。树下于是噼里啪啦地下起了樱桃雨。有些是因为熟透了,稍有风吹草动便会猝然落下,更多的原因是那些樱桃被虫子吃过了,只剩下空空的皮囊,即便没有外力的作用,坠落也是早晚的事情。我们选那些尚未被虫子光顾的吃,一边吃一边感叹:甜,太甜了!吃剩下的,同事们作为礼物,装好后要我带回了天全,我分给亲友们品尝了,感叹是一样的:甜!太甜了!现如今,我们的味觉是太熟悉这种味道了,甘甜、香甜、甜美、甜蜜,蜜一样甜……花样翻新,琳琅满目,却依然禁不住要啧啧称赞,我想我的同事和亲友们是被它纯正的味道给迷住了。记得有一回,我和作家们去到一个以樱桃闻名于世的地方采风,主办方盛情,每人分发了一小篮子樱桃给我们品尝。我没敢下口,因为那樱桃看上去太完美了,无论外观还是色泽,乃至包装,都那么无可挑剔,我抓了一把捧在手里,在水龙头下冲洗、翻看了半天,竟然没发现一颗樱桃有虫子光顾的印痕。
进出杵泥的路边竖着一块水泥石碑,但凡去到杵泥的人都会看到。水泥石碑显然已经竖起了不少岁月,好些部位已见皲裂,边角已风化脱落,几个大字上涂抹的红色油漆也已淡化,字迹却是清晰可辨的——“中国红樱桃之乡”。站在水泥石碑前,头顶着狭长而逼仄的天空,心里不得不对泸定人暗生佩服。一个川西崇山峻岭之间的小山村,却要建设“中国红樱桃之乡”,这是何等的视野与雄心!都说环境造人,这环境,其实不是禁锢和束缚,而是萌发和催生的动力之源,关键在于置身其间的人。
没去泸定之前,我就知道杵泥是泸定下属的一个乡,也知道泸定出产樱桃,却不知道泸定的樱桃大多出产于杵泥乡。到了泸定,吃过杵泥的樱桃之后,我必须说,那可能是我有生以来吃过的最美味的樱桃。
和杵泥一样,我很早就知道岚安,却也从没去过,不知道它是在东西南北哪个方向。自打得知要去泸定的时候起,我就计划着,一定要去岚安看看,我甚至想到要找一本《泸定县志》,以更多地了解岚安和泸定的其他地方。我好几次请泸定的同事们帮忙,说起的时候同事们都很爽快地答应,过后就都不了了之,始终没见把《泸定县志》送来。我想同事们是没有找到,或者是我作为医生却要找厚如砖头的县志来读,让他们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了。
尽管没有《泸定县志》可读,但我还是大体知道岚安的一些历史,最辉煌的要数1935年11月,红军长征曾经过这里,并在此驻扎了49天,600多名红军指战员在这里牺牲,缔造了康区第一个红色苏维埃政府。我最初听人说起岚安时,也犯了所有天全人都会犯的毛病,l和n不分,阴平、阳平不分,边音、鼻音难辨,把岚安听成了南岸。后来医治了好些个来自岚安的病人,从他们的身份信息里,我才明白自己一直“误读”着这个地方。
我医治过的岚安病人中,给我印象最为深的当属任坤有。
他是搭乘拖拉機去县城路上受的伤。他背对着驾驶员,坐在拖拉机货箱后挡板上,双腿悬吊着,像一个调皮的读书郎。他看不见前路,也就没法看见拖拉机车头驶离公路,否则,在拖拉机朝着悬崖飞速坠落之前,他完全有可能也有足够充足的时间从货箱上跳下,躲开那场车祸,从而避免货箱里掉落的重物和飞石砸中自己的双腿。
后来任坤有被送到县里,很快又转送到了省城,得到的都是一样的说法:想要保住双腿,悬!家里的人和任坤有都坚持着,不愿意截肢,他们抱着试一试的心理,转到了天全,成为我的患者。那时候,任坤有差不多已经彻底死了心,听我就他的双腿说出同样的话语时,他显得是那样淡然,有一种听天由命式的无所谓。
死马当作活马医——任坤有三个月后对我说。话语间,当然地充满了强烈的死而复生的庆幸。事实上,要不是三个月前他和家人选择了坚持,坚决要求先观察一下再看,这一切都是空谈。内心里,我和任坤有一样,对他当初的选择感到庆幸。三个月的治疗时间,别说保全的是一双腿,就是一根脚趾尖,也已足够我们庆幸。
这都是十多年前的旧事。后来有一天,我接到任坤有从岚安打来的电话,他刚卖了几头牛,新买了一部手机,还学会了玩微信,要我通过他的好友申请。随后,我就接到他发来的几张图片,图片拍摄的是岚安的山水和他放牛的地方,绿树成荫,百草丰茂,鲜花盛开。我正看着照片出神,电话又一次响了起来,电话里,任坤有邀请我有空去岚安玩。
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任坤有。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己真有机会去到泸定,而且一待就是三个月。
现在,三个月的时间已经成为过去。硬要说起来,遗憾也是有的。没能够待更长时间,从而更多地了解泸定,此为其一;想要一本《泸定县志》而不得,此为其二;其三便是一直想着却终究没能找到机会去岚安,没能够再次见到任坤有,这件事情已然变成了一个梦想,若有机会再去泸定,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个梦圆上。
过桥记
从泸定县城东岸到西岸,有三座桥相连。站在医院旧家属楼外的河堤边,抬眼便能看见城南大桥,往上是泸定桥,再往上出县城不远是彩虹桥。
源远流长的大渡河自北向南。但在我此刻的想象里,它就是流经泸定县城的那一节,更具体些说来,就是从城南大桥到泸定桥之间的一小段。但是,站在城南大桥上看大渡河与站在泸定桥上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在我的想象里,它活像一个人身体的躯干部分:城南大桥下的一段河床宽阔,水流平缓,两侧的河床上乱石堆砌,那是一副胀满的肚腹;而上游不远的泸定桥下,河床陡然收紧,河流湍急,乱石穿空,那是大肚腩上方连着的脖颈。
城南大桥和彩虹桥都是公路桥。彩虹桥地处县城之外,我只开车去西岸加油时路过过一次。城南大桥和泸定桥广场却是去过若干次的。天气晴好的午后或者黄昏,我和牟医生时常一起出门散步,有时候经过城南大桥到县城西岸去,有时候从医院旧家属楼出来,往左沿成武路走,去泸定桥广场。
泸定桥广场自然是以泸定桥为中心的广场。从此刻回溯,在并不漫长的时间史上,公元1705年便是泸定桥的最上游。那时候,大渡河还叫泸水。这一年,为了解决道路梗阻,康熙皇帝下令修建泸水上的第一座桥梁,仅仅一年之后,长103米,宽3米,13根铁链固定在两岸桥台落井里(9根做底链,4根分两侧做扶手)的桥梁建成,康熙皇帝遂御笔亲书“泸定桥”三个大字,并立御碑于桥头。“泸”即是泸水,“定”则是平定、安定之意,康熙皇帝是希望借助桥梁建成后的便利,平定西藏准噶尔叛乱。这次起于1690年(清康熙二十九年)的战争,迭经三朝,历时68年,最终于1757年(清乾隆二十二年)弭息,取得了完全胜利。这些都是题外话。事实是,自从泸水之上有了泸定桥,泸定县名随即确立,并且一直沿用至今。县名随桥名而生,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事情了。
从1705年出发,沿时间之河顺流而下,1935年是必定要停靠的一个站点。5月29日,泸定桥让全世界的目光又一次聚焦。这一天,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经大渡河,以22位勇士为先导的突击队,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在泸定桥上匍匐前进,一举消灭桥头守卫。从此,这座桥便成了新中国历史上一块举足轻重的纪念地,有历史学家甚至说,是泸定桥上的“十三根铁链托起了共和国”。一拨又一拨的人,千里迢迢地赶到大渡河边,为的就是一览泸定桥的风姿,听闻大渡河四海闻名的涛声。
康熙皇帝当年御赐的《御制泸定桥碑记》就立在泸定桥东岸,它记载了修桥的原因、桥的规模及维修办法,桥的东岸就是以桥头为中心、向东边山脚铺开的泸定桥广场。广场旁边静卧着一家书店。店名有些老旧了,叫新华书店。一个星期天的午后,我原本是要去看泸定桥的,在广场上闲逛时,忽地看见路边高挂的“新华书店”,便不由得跨步而去。门口收银处坐着两个长发披肩的女子,我是店里唯一的顾客。我从只开了一边的双扇玻璃门进去时,收银处的两个女子正说着话,看到我,她们不约而同地看了我一眼,又扭过头去,继续她们似乎永远说不完的话题。书店里打扫得其实很干净,从玻璃墙壁斜照进来,依稀照见我打地板上的面影,给我的感觉却是混乱的,具体乱在哪里,一时说不清。大约和记忆中新华书店里热气腾腾的情形有关,这与时下、这里的安静造成了某种错位,它们同一时刻呈现在我的记忆中和视线里,混乱由此而生。我进到店里后不久,又来了一个中年男子,好像是走错了路,在玻璃大门内停了一下,便又转身走了出去。在文学架上,我看到了卡勒德·胡塞尼,这位旅居美国的阿富汗人最新出版了一部长篇《群山回唱》,定价36元。我毫不犹豫地取下书,递给收银处的女子时,问打折不?对方诧异地抬起眼,面无表情地吐了个“不”字,就冲我伸出了手。这可能是我开始文学阅读以来买下的第一本不打折的书。也许是受了书名的感染和提醒,抱着书回去的路上,我突然想大吼,像儿时置身荒寂的山野时大吼着为自己壮胆,尽管此刻实在没有什么让我惊惧的。我只好紧闭了双唇。在熙来攘往的成武路,我的大吼是否能引起山间远远近近的回响是另一回事,让人们回头侧目倒是必然的。
终于还是去过了一次桥。时间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即将离开前三天。整整90个日夜即将过去,开始的时候我是以为日子还长,还有的是时间。那天往返书店、乃至之前和后来若干次打泸定桥广场经过时,这个念头便会涌上心头,但我老感觉自己还没准备好。直到此刻,我就要离开,才觉得是时候必须再去走走了。
我把手伸进衣兜。我知道外地游客过桥要买门票,10块钱一张,本地人免费。正准备掏钱,忽然听到旁边有人在叫:“李医生!”我一愣,扭过头去,原来是上午刚刚看过膝盖的一位病人的家属。听到有人叫我,站在眼前的管理员也愣了一下,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我从他脸上的笑容里猜测,我们大约觉得是在哪里见过,但一时忘记了,听到有人叫我医生,他一下明白了过来。管理员微笑着侧过身去,让开通向桥面的小铁门,并且摊开手掌,掌心向上,轻轻地指向了泸定桥和它通往的西岸。
波濤滚滚的大渡河在桥下咆哮着,一如记忆里第一次来时的样子。第一次来泸定桥是什么时候,已经不记得了,但可以肯定是在11月22日康定地震之前,因为那时我那篇至今仍有朋友提及的《二郎山记》已经完成,而且那时我的目的地是更西边的康定,根本无暇他顾。
站在桥头,出现在眼前的依然是记忆里第一次来时的情形:“风尘仆仆地赶来的人们站在河边,踏上铺着木板的桥面,铁索摇晃着,有人紧闭着眼睛默不作声,心里似乎想到了当年红军飞夺此地的情形,有人不免惊声尖叫了起来,尖叫声响在耳畔,算得上惊心动魄,但在河水巨大不息的咆哮声里,瞬间便被稀释成了蚊蝇一般的嘤嗡声。”
我忽地觉得这就是我一直期盼的时刻——种我想象中的仪式感。
我跟着人群,默默地,向着摇摇晃晃的桥面迈开了步子。
——根据课文《勇夺泸定桥》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