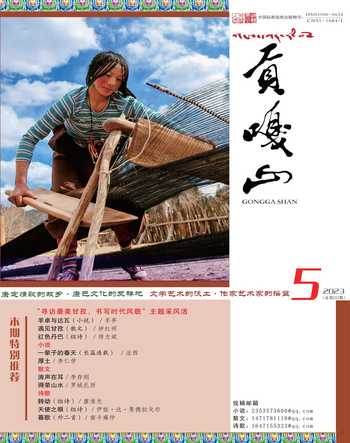小草低语(散文)
李育樵
甘孜回成都的车上,海拔的下降,气温的升高,我从浅梦中苏醒,才发现车窗外的天空已从湛蓝开始泛白,高速两旁的灌木开始变得参差不齐,杂乱无章,一切陌生如初。刚才的梦里,我看到自己漫步在90年代的康定,又看见那个小女孩在水井子玩水,她跟我素未谋面又无比熟悉,梦里我知道她的名字,知道她的前世今生,于是呼喊她,她没有回眸,捧起手中水抛向天空,腾起的水花让我一阵眩晕,她也转身消失在小巷里。
海拔下降导致的闷热让我烦躁不安,于是戴起耳机,听同行老师推荐的邓丽君的歌曲《微风细雨》:小草也在低声细语,诉说无尽秘密。
歌声让我想起龙灯草原上无边无垠的小草,它们和高山一起构建了神圣的高原布景,高原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命们都为这世间短暂的存在而博尽所有,草如此,牛如此,人亦如此。高原小草矮小而卑微,五月初见绿,八月底枯黄待来年,对于我们这群追随风景而来的人,草青草黄皆是风景,可阳光和草原背后还有寒风和暴雪。那些行走在这片土地的人们相信万物皆有神性,信奉高山和河湖,信奉大地和小草,他们彼此依赖,天人一体。我是红尘俗人,伫立在这里,也觉风烟俱净,生命卑微无常感扑面而来。神祗讓我们适应了无常,可我总想不出自己的神祗,如果有,故乡曾经算吧。
很多原生的事物越来越多地被岁月带走,少时从未想过它们会不知不觉离开。步人中年后,故乡和我越来越远,关于故乡所有念想逐渐消失殆尽,曾经魂牵梦绕的,终究形同陌路。
故乡的缺失,让生命无了来处。
二十来岁年纪,我离开故乡前夜,连日的暴雨让嘉陵江怒不可泄,淹没了我和朋友们的啤酒广场,淹没了我抓鸟蛋的河堤,我从小生活在江边,总觉得潮起潮落早已习惯。那晚,我陪父亲江边散步,跟青春期后很多年一样,父子俩一路无语,他忽然开口:我知道你喜欢这里,出去就出去吧,不要总惦记,把自己过好。我并未被父亲的话激起涟漪,老人啊,总爱闲言碎语。
此时想起,故乡对于少时的我,就是神祗。为人父后,我开始在乎孩子的喜怒哀乐,远远超过自己,于是想起父亲那夜的只言片语,他太了解我了。前些天,父亲嘱托我了解下成都的墓地,我一愣,心如刀绞。
去过很多地方短暂停留,一直幻想有一天能发现一个容身之地,弥补故乡缺失带来的无常感,而脚下的草地让我第一次有留下来的想法。我知道那是幻想,却依然相信,某一天,我会回来直视这里的阳光,会亲吻这里的草地,会朝拜这里的雪山。
龙灯草原上的金雕和秃鹫在低空盘旋,盯着地面可能出现的野兔和田鼠,或者动物尸体,这是它们的家,理所当然地应该俯视我们这些不可一世的众生。我仰望它们,也低头看大地,却全然没有书中那种旷古的孤独感,倒想成为它们的食物,化成这大地一物。
大部分时候,总是夜晚梦中醒来,却无法再清晰勾勒出梦的大概,今天车上的梦境却异常清晰,闯进我梦里的90年代的康定城和那位小女孩,现在已随时光荏苒不现旧日面貌,小女孩现在或许和我一般年纪,只是那时候,她在康定河,我在嘉陵江,她手中捧起水花再抛向天空的画面最终汇入岷江,或许某一天,和我门口的嘉陵江江水一起在长江口汇合。这是暗喻,或是杂乱无章的倒叙,未置可否,和故乡一样,一场梦罢了。
我离开龙灯草原合影的人群,再往深处走,甘孜的阳光一直陪伴着我,炙热而纯粹,我裸露在阳光下的皮肤开始微痛,这种微痛让人愉悦,我终于鼓起勇气抬起头去对视阳光,短暂的眩晕让脚步踉跄,我再次看见我自己,看见我的朋友亦或者故乡,看见手捧水花的小女孩,这一刻,我追随雪山和神祗,化身小草,终和这山河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