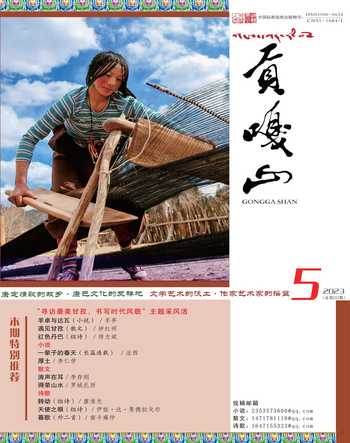三重奏(散文)
卓慧

土,石,木,三种物质,不同形态、不同质地、不同手感,大自然中,随处可见。它们来自哪里?什么时候来的?很大可能,这地球上没有人知道。知道的是,从我们开始爬、开始走、开始跑、开始跳时,它们就在那里。一不经意,它们就和自己的手脚遭逢:土的绵软,石的坚硬,木的粗涩,只需稍稍一触,大脑里的“百度”,就能感性地准确弹出它的“词条”。真去网上“百度”,会赫然发现,它们都来自远古:作为汉字,在最早的甲骨文里,它们均就已经存在,并且在几千年来最常用的汉字之列。作为物质,土和石早在寒武纪就有,可能从地球诞生那天起,它们就已存在;木稍晚一些,出现在泥盆纪,距今也是三四亿年。它们的历史之悠远、漫长,按现今学术猜测只有几万年的人类,与之完全没有可比性。但有时候,历史的悠久不代表就具有绝对优势、绝对的控制权。自从人类进化到会制造工具后,它们中一些成员的命运,不知不觉就被人攥在了手里,存在的方式、地点就因人所需被改写,或者被人切、被人削、被人捣、被人磨,或者被断臂、被折叠,甚至被粉碎、被重新组合,最终以它们自己都意想不到、都不认识的面目出现在大地上。我还是我吗?不知道它们会不会这样自问。无奈吗?欣喜吗?无从得知。或许,自在自为也好,被人类折腾也罢,不管以什么方式,只要在,存在,就是它们的终极追求。
前不久“寻访最美甘孜”,从泸定到丹巴,又从丹巴到道孚,不知是因了奇迹般目睹了贡嘎雪山神圣庄严、冰清玉洁的真颜,还是因了呼吸到龙灯草原夹杂有格萨尔王雄阔余绪的疏旷气息,我的灵魂竟仿佛经受了一次洗礼,格外开了窍,对进入眼底那些民居建筑,格外有感触——甘孜是藏族自治州,境内的民居,大体属藏式建筑范畴。不过,这里作为青藏高原向成都平原过渡地带,属多民族聚居地,即便是藏式建筑,也充分体现着过渡地带和民族走廊的特色:既有夯土式,又有石砌式、木构式;而且,既有单一型,又有两厢、三厢合奏。
土
用土壤做基本材料,夯土为墙,置以木窗,上覆稻草、青瓦或者别的什么,这样的建筑样式,似乎在亚洲和非洲比较多见,欧美相对少些。何以呢?经济的因素、地理环境的因素、审美的因素、文明形态的因素等等,说法各一,未见定论。我肤浅地认为,很多事情和现象都不是单一因素所致,而是多种因素合力叠加的结果。当然,它们也不会是平均用力,里面也分主次深浅。对其的考量,有时回到原初的意义上,可能更能让人洞悉到个中因由,比如土墙的“土”。
据甲骨文,“土”就是土堆的象形化表达,后来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为“地之吐生万物者也”,已是在阐释其引申义了。许慎的引申,当然不是凭空的,因为在《周易》阴阳五行中,“土”就是位居中央布四方,“百谷草木丽乎土”,是世间万物所依存变化的载体,万物之由来,万物之依靠,十分特殊,也十分重要。而《周易》的阴阳五行理念,不只在许慎所在的东汉时代,就是中华大地上盛行甚广的一种重要思想,在21世纪的今天,也仍有相当多信众。观念关乎意识,也决定人的行为。不管怎么说,一个显然的事实是,作为农业文明十分强盛且延续时间甚长的华夏子民,对土的认识、对土的感情,世界上其他族群可能没有谁比得上中国现代诗人艾青那句“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土地爱得深沉”,在一部分人那里,可能不只是诗,更是他们内心真实情感和认识的写照。不过,在已经进入后工业时代的当下,这部分人群已日渐稀少。乡村的减少,乡村功能的弱化,也许是人类文明发展中绕不过的一种宿命,但“土”作为永载万物的一种实体,我相信它永远也不会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永远都自会有一种生机。
记忆中最早对土墙建筑的认识,是小时候在乡间。大人说,那叫“干打垒”。还说,土墙好,冬暖夏凉。记得还看见过修筑的过程:两块木板,相对着放置在墙基上,两头各找块小板子一挡,就构成一个长方形箱子,然后就往箱里填土,边填边用棰夯实。做实一箱,拆下板子又顺着做另一箱。一箱一箱又一箱,夯完一圈,又往上夯第二圈。门框的位置,则先用木头搭好架子撑着。新夯的土墙,拔地而起,四棱四角,平平整整,颜色也是新鲜泥土的颜色,还带有光泽。小时的我觉得它非常漂亮。也见有老土墙房子,早已失去光泽,不仅苍黄发白,有的还有干裂的缝隙,一下雨,墙被雨洇湿,雨水沿着缝隙,窜进屋内,窄小的屋里就湿乎乎、黏嗒嗒的。小脑袋就想,它怎么这么丑?它新的时候也那样平整、那样漂亮?不可思议。就像怎么也不能把一个皮肤细嫩的年轻姑娘与一个满脸褶子的老太婆同框。看见那些住老土墙房子的人家在雨天里的困窘相,便问,他们怎么不修成砖瓦房?大人说,没钱呗。于是,再看见土墙房子,穷、困窘、不安全等标签下意识地就覆了上去。这标签一贴就贴了好些年,直到那年在福建漳州看到南靖的土楼,看到当地人用来自大地的土泥和木石,修的楼随随便便就是三四层不说,还很气派地围成几百上千平方米的圆或者方形四合院,一整个大家族都容纳在里面,不仅邻里之间相互照看或借个东西,十分方便,农耕时代宗法社会,族里有事,也好商量,而且还十分坚固,是抵御外敌或野兽进犯的有效堡垒。那些土楼,最久的已经屹立五百余年了,妥妥地颠覆了浅陋的我对土墙建筑的认知。
甘孜境内,以我短浅的目光和视野,发现夯土建筑似乎不多,也没有南靖那种土楼,但在泰宁镇,看见昔时商铺的一段土筑残垣断墙,与斜对面一栋外墙贴有瓷砖且带有一个小庭院的二层小洋楼,历史的遗迹与现实形成了强烈反差:土墙的土,虽苍老,却纯净,看上去就像是从黄土高原上移植来的;断垣的垣,名副其实,原本的四壁屋墙,既没有了屋顶,高也只不过一米左右了;门尚在,是道木门,歪斜着立在那里,脚边全是土,推不动,也倒不下去……颓败至此,屋早已不成其为屋,更非商铺,早已不可能住人,更不可能见到原主人。真的是时过境迁,物不是,人也非!
据说这个镇,地处北来南往要道,曾经是个热闹的贸易集散地。周边人们,或者陕西、甘肃的汉人、藏族人,有蘑菇、虫草、毛皮、茶叶等交易需求的,通通就往这里来。抬眼看一下几条街的布局,不规则“井”字形纵横交叉,每条街估摸都有上百米长。这规模,在总体上人烟稀少的高原,应该说不算小。可见它确实繁华过。但时移势易,谁也保证不了永世繁华。曾经的土夯商铺,虽称算不上“繁华”,但它当年能在这里有一席之地,能站稳脚跟,想来它的主人也不是慵懒无识之人,它现今颓败的身体里,当年一定承載了主人不少心血。风吹雨打去,换了人间,不乏的是后来者。它对面的新邻,夯土墙的进阶版——泥土烧制的砖混漂亮小洋楼,可算是对新时代风貌的一种注脚吧。
石
石者,坚也。
我们都知道,成语“坚如磐石”,借喻的就是“石”这种物质的坚硬品质。利用石这种品质,叠石为墙,垒石为室,建造石屋、石桥等建筑,古今中外皆不乏践行者。但迄今存留下来最多的石质老建筑,是在欧洲几百上千年的教堂、王宫、市政厅,几乎都是石墙,坚固高大,气势恢宏,每每令人震慑、赞叹。
我生长在蜀地汉区,自小目之所见,不是普通的青砖瓦房,就是简陋的土墙木屋,石头房子,貌似阙如,最多,也就是用石头做屋基、础石或者底座。第一次见识通体石墙建筑,是在汶川,看见羌族人用大大小小不规则的石块垒成的线条笔直的墙、房屋,甚为惊叹:之前在汉区所见之石头建筑,无论是两三圈高的屋基,还是几级几十级石板台阶,所用的石头,要么是规规整整的方形条石,要么是标准的圆石。这大小厚薄极不整齐,有的甚至十分尖利的石头,他们竟然垒得那样整齐,就像是垒好后经过刀劈一般,放倒的话,目测就是一个整齐的平面;立在那里,墙体的转折处,棱角还十分分明整齐的!我万分纳闷,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当地人告诉我,天生的。羌族人生来就会这样垒墙!听后,我除了叹服就是臣服,我们的羌族人何其聪明,何其有智慧!
去过几次涉藏地区以后,发现那里的民居,很多也是石头垒建的,有的是用规整的条石垒的,有的也同羌族人的一样,是用不规则的石块垒成。石墙木窗,大都两层(也有错落的三层),底层是牛、羊等牲畜的圈和贮藏室,楼上住人。屋顶则根据主人的需要,或者是可以晒粮食的平屋顶,或者是青、红瓦斜屋顶。最抢眼的是屋檐和窗框的装饰,沿边嵌的红白黄蓝线条图案,听说寄予着人们对白云、蓝天、星星、月亮的礼遇和热爱,对吉祥安康的祈祷和追求。
丹巴的甲居藏寨,风情万种,十分美丽。虽然早就闻听,但这次才有机会亲身走进。藏寨位于距丹巴县城不到10公里的卡帕玛山峰下,是在近千米的山坡上,沿起伏的山势建起的一幢幢藏式楼房。楼房多是石质,有的是规则的条石建的,也有的是羌族人那种不规则的石块垒的,平屋顶。屋顶四角各有一个几十公分高垂直向上的白色“翘檐”,非常醒目,就似在向天致敬,却也有几分可爱。时值晚春,天空是高原上那种明净的湛蓝,散在的朵朵白云疏软得让人直想把它拎过来一缕一缕撕开。站在半山腰,远远看去,那些灰灰褐褐、红红白白的藏房,稀稀疏疏地隐在山坡间,高低错落,青林环绕,脚底下,大渡河在缓缓流淌,不时有山间花香传来,又宁静,又安详,整个儿俨然一副世外桃源模样。
木
“木”,這个现今异常简单的象形字,细看它的甲骨文和篆体,很有意思:上是枝叶,下是根,中间一竖是主干。要啥有啥,简单又丰富,可不是吗?它的引申义,“质朴”和“呆笨”,表面上一褒一贬,两个走向,但其实,我们在说一个人“呆笨”的时候,是不是也暗含着一些亲昵,一些爱极生恨、恨铁不成钢,一些包容和宽宥呢?比如我们说一个人或者什么东西呆萌呆萌的,比如黄蓉骂郭靖“呆笨”,里面没有喜爱的成分吗?换言之,木,总体上还是让人亲近的。至少,在我心里,它是这样。
木质建筑,在我确也是熟稔无比的。除了一直以来的居住环境,木窗、木门、木柜、木床等木质东西随处可见外,还因小时候家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木楼。那原本是父亲单位的办公楼,当时因职工住宿房不够,办公室好像还比较宽松,于是,我们家和另外两家人就住在那办公楼上。楼是20世纪50年代修的苏式楼,四边外墙是砖石,内里全是木的,木楼梯、木楼板、木隔板,人一动就有声响。小孩子的我们,常忘了大人的叮嘱,一随性就撒开脚丫在上面跑,那时那声音就是轰鸣般热闹了。虽然屡屡因此被大人训斥,但一转过背,一开心就忘了。特别是把楼梯扶手当滑梯(那扶手是圆木的,大概有三四十公分宽,很光滑),骑上去或趴上面,一哧溜滑下去的爽感,现在想起都还觉开心。
愚生浅陋。木质建筑,之前已见最宏伟的,应该是故宫。皇家宫殿,当然有底气宏伟,不宏伟也不好意思叫皇家宫殿吧。但那毕竟是皇家的东西,隔着距离审美,没有可比性的东西,不说也罢。我们作为平民,最有感觉、最能亲近的,当然还是民居。话至此,不说说道孚民居,仿佛所有的话都是白说。
道孚民居十分漂亮!这话在我耳边萦绕了起码有二十年了。记得刚到杂志社不久,时任主编,一个在康定出生长大、甘孜州所有的县几乎都跑过的甘孜人,秉性忠厚、从不浮夸的意西老师,跟我聊天时,不知说到什么,就十分肯定、赞赏地吐出了这感慨。之后,一遇到相关话题,就又会说起。当然,他也说过找机会带我们去见识。谁知一直不凑巧,一直未能成行。但胃口已然吊上,就会心心念念着,那是不容置疑的。今次终于得遂所愿,亲眼得到验证。
怎么形容道孚民居的漂亮呢?一句话好像是不能涵盖的。浑朴、典雅、大方、奢华……看见没,有悖谬的词语?没法,感觉它确有一些那类气质。看来要仔细品,还是得回到它本身。
道孚民居,当然是一个大概念,道孚境内的民居,都可以叫道孚民居。道孚境内的民居,当然不是只有一种,如我们现在建的水泥砖混高楼或者仿古小镇,齐齐普普都一个样式。不是的,道孚境内的民居,有甲居藏寨那种石质藏式楼房,也有水泥砖混藏式楼房,还有纯木架构的藏式楼房。跟别的地方不同处在于,道孚境内这些藏楼,窗框、屋檐、楼顶的装饰,色彩更加明艳,也更加纯净,就仿佛天然彩石经过了水洗,既亮又净。
这还是一个整体感觉。让我特别震撼又特别难以阐释的概念,是“崩科”这个词,先从讲解者嘴中蹦出来时,我完全不知其意。又听他接连提到几次,我还是不明所以,甚至连是哪两个音都没听清。后来请教藏族作家尹向东,他一个字一个字告诉我,我才慢慢理解其意,原来这是藏语的音译,“崩”的意思是木头框架,“科”的意思是房子,“崩科”就是以木头为建筑材料的房子。这是一种纯木房子(窗玻璃除外),穿斗结构,两三层楼,通体采用我们传统的卯榫技术,整幢建筑可以不用一颗铁钉。这种建筑最大的好处是,地震时屋体廊柱和外檐之间的斗拱会像弹簧一样变形松动,房屋整体可能会发生位移,却不会垮塌。道孚正是处于青藏高原和四川三大断裂带之一的鲜水河断裂带上,历史上地震频发,故人们常采用这种建筑类型。建筑学家梁思成曾说:“中国建筑之个性乃即我民族之性格,即我艺术及思想特殊之一部,非但在其结构本身之材质方法而已。”看来还真是如此。当然,汉区原来一些老建筑,也是这种纯木结构,整体不用一颗铁钉,比如应县的木塔。问题是,那是老建筑,那是过去式,现在几乎绝迹,民居未见这样修造的。而道孚的很多民居,都是这种崩科。这还只是外表,只是房屋一眼看去的框架。更惊人的还在内里:作为框架的廊柱、斗拱和横梁,全是直径几十公分漆成红色的实木;四边木墙的表面,全是彩绘,或云纹,或花朵,或“回”字,围绕着一幅幅唐卡,五彩斑斓,华丽之至!
最惊奇的是,当地一个二三十岁的青年(现在是位老师),在十多岁的时候,就发愿要给自家修一幢美丽的崩科。这种愿,可能好多人都会发,但一般都当它是梦想,多在梦里眼热一番、抒抒情就罢了,梦醒之后便丢之脑后。但这个男孩没有。他真的把它作为生活的目标,一步步,从打工攒钱,到批地基、批木条(当时可以按批条计划伐木,现在不许了),再到上山去一根根选木、伐木,一根根弄回家,最后攒齐了所需的所有建筑材料,然后开工,动具,风里来,雨里去,就像燕子衔泥筑巢,硬是将一幢三层楼的崩科立了起来。那内里的瓤子,除了传统藏式民居的装饰,还有浴缸、席梦思等现代家居器具。此外,还特地辟了一间书屋、茶室,让书香、茶芳氤氲缭绕,这辈子除了喜欢读书没有别的嗜好的我,置身此氛围,焉能不心动,焉能不怡然生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