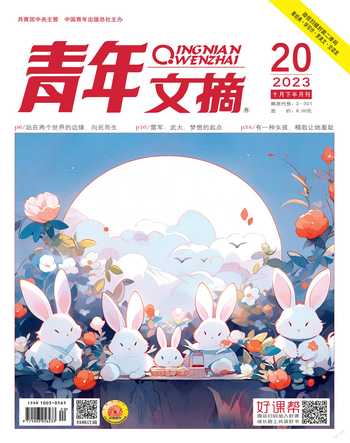守书人
王若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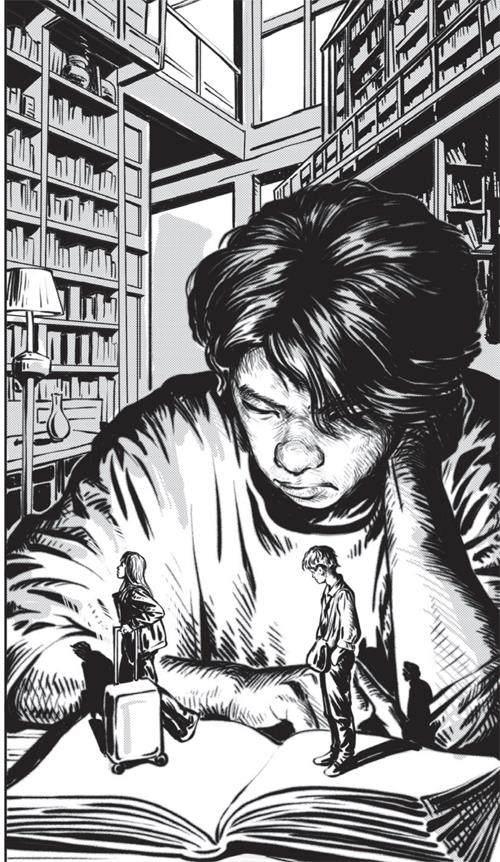
在墓地和图书馆,我们会怀着一种发自内心的敬畏和信仰而保持安静。而一座图书馆对于我的意义,就是书的坟墓。
一
我们学校的新式图书馆兴建于十年前,藏书的官方数据是四百六十七万册。我总是坐在图书馆三楼外借部的某张桌子边,右边是一排很大的窗户,阳光和煦。每天有两三个小时我就在这里度过——我坐在这里,却能知道整个世界,就像诸葛亮当年虽是个宅男,但他家一定能开个小型图书馆。
我不是普通的借书学生,我是个守书人。
守书人和守墓人听起来有点像,区别是前者热爱他所守护的东西。不过,我所守护的,可不是这四百多万册书籍,那是图书管理员的职责。
我只守护八十三本書——而在一年前的那个下午,他坐到我面前的时候,这个数字还只是七十八。
直到今天我也不确定他说他叫尚书是不是真的,但这无关紧要。关键是,他知道我偷了什么东西。
假如你去查阅一个大学生四年当中在学校图书馆的借书目录,就可以看出他是个怎样的人,甚至可以看出他学什么专业。不巧,我借的书很杂,觉得什么好看就看什么,并不带有学习或写论文的目的。
但不是每本书都和它们一样。
那天尚书坐在我的对面,什么都不说,只是推过来一张小字条。我疑惑地看了一眼,倒吸一口凉气,合上自己面前的书,定定地看了他一会儿,确定四周没有别人,轻声道:我们认识吗?
他摇摇头,说:但我们都认识同一本书,在电脑系统里它叫《晃晃悠悠》,在书架上它叫《柏拉图之恋》,但你和我都知道,这本书其实应该叫另一个名字。
说完他用手指敲敲那张小字条,上面写着四个字——“噢,是你呵”。
二
怎么从学校图书馆偷一本书?
任何一个现代化图书馆的常客都会告诉你,图书馆的书和普通书有两个地方不一样:一是书名页上有张条形码,用专门的机器扫描后可以确认借阅信息——书名、作者、价钱、类别、架位等;二是磁条,在书脊部位,任何没有消磁的书在进出外借部时,那道红外线探测门都会响声大作——这两项措施保护着图书馆里的书不被混淆和遗失。
然而,这里有个严重缺陷,那就是每张条码和磁条都是在书买来后用不干胶粘上去的,虽然很难把它们撕下来,但假如用锋利的刀片把它们从书上切割下来,然后粘在其他书上,那么就可以蒙混过关。因为在还书的时候,很少有工作人员去看电脑上显示的书目信息和手头那本书是否相符,尤其在每周一学生们挤在一起还书的高峰时刻。
一言以蔽之,狸猫换太子。
这个图书馆有几百万藏书,其中一百本被动了手脚根本不会被发现。而且就算发现了,每本书的借阅记录上几乎都不会少于五个人,有些甚至已经毕业,只要那些学生一口咬定,就很难追查是谁做的。
比如我。
但显然,眼前这个男生知道我是怎么做的。
我身子往后靠去,同时脑子在飞快地转动:《学生手册》里规定盗窃图书馆书籍是什么处分?三十倍罚款?开除?
忽然他笑了,轻声道:其实你不必担心,因为你并没有盗窃学校的任何财产——有些事,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尚书说,他不是追查孔乙己的福尔摩斯,他只是这所学校三万学生中很普通的一个,只不过正好他有个阿姨在图书馆工作,所以他可以进入图书管理系统,偶尔毫无恶意地查阅一下别人的借书清单。
他引着我来到一排书架前。我很熟悉这个书架,就是在这里我找到了那本《噢,是你呵》。我唯一奇怪的是,他是怎么发现我的。
尚书忽然问我:你平时喜欢写东西吗?
我点点头:以前写,现在几乎不写了,只是看。
他耸耸肩:每个喜欢写点文字的人,心里几乎都有一个梦想,无论他本身水平如何,那就是出一本书。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写一本书的,更不用提出版了。有的人最终会在现实中放弃那个梦想,只有极少数人成功了。这很残酷,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用另一种方法来让自己成功。
我抢着说:自费出版?
那是在浪费纸张和钱。他讥笑的表情转瞬消失了:让我告诉你,你换走的《噢,是你呵》,在这个世界上,只此一本。
三
尚书说,在这座图书馆中,有七十八本书,和《噢,是你呵》一样,都可以称为“绝版”。它们的作者名不见经传,但他们是真正的作家,写自己真实的感想,不受出版商的约束,不在乎读者,不在乎销量和市场,没有宣传和刻意的炒作。他们孜孜不倦地写作,投稿、枪毙、再写作、再投稿、再枪毙,直到有一天不再提笔。
然而,有一天,他们中的某个人忽然有了个想法,那就是把自己写过的东西编成一本书,找人排版、设计封面,请朋友写序,书上的刊号、出版序号、售价、媒体评语、条形码……一切都伪造得像真的一样,但仅此一本,不做任何商业用途,只为纪念。
当制作出这样一本书之后,也同时意味着他们写作生命的完结,所以你可以把这本书看作一个写作生命的尸体。
我们会把尸体放在哪里呢?答案是墓地。沙子的墓地是沙漠,树叶的墓地是树林——那么书的墓地呢?
自然是图书馆。
每个读书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作者,或者说,偶像。这也是激发他们从阅读转向写作的原动力之一。若能将自己唯一的著作和偶像的作品摆放在一起,是最大的荣幸。
而把书弄进图书馆很简单,因为他们认识一个叫尚书的人。
我不是第一个想到“狸猫换太子”的人,也许尚书也不是第一个。总之,他从图书馆里摆在那些名家作品旁边的书中借出来一本,将条形码移花接木到那些人唯一的作品上,然后还掉,工作人员都是根据书脊上的编号把书放回原位的,不会去看书名。于是那些世界上独此一本的书籍安然下葬了。
尚书除了帮书下葬之外,还是个守墓人。他有一份名单:名字、作者、顶替哪些书、分别放在哪里。每月他都会查看一次它们的情况,看看是否被人借走,没被借走的是不是还在原位。
一星期前的某天,他巡视到这排书架,发现那本《噢,是你呵》不见了,但查阅电脑发现已经被我“还”回来了,最后通过索书号发现,被调包过一次的书又一次被调包了。
其实当时我是欣喜多过愤怒的,尚书说。一个无名作者的作品,居然值得被人冒险偷走——假如当初多点像你这样赏识他的人,也许这本书真能出版呢?
事到如今,我只能承认了:明白了,我会把那本书还回来。
他急忙摆手:这不重要,关键是我找到了你,你喜欢书,就像我一样,并且你拥有一种强烈到几乎可以为之违反规定的偏执的热爱,你也能理解那七十八个作者的心情和境遇。我已经大四了,不可能继续在这里看守那些书,所以,我今天不是在找一个小偷,而是在找一个接班人。
尚书毕业后,我成为继任的守书人。他离校前,还给我带来了礼物。
那天我答应接替他之后,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我偷走的那本书《噢,是你呵》只有上册,下册我一直都没找到。
他说,守书人和作者之间有个约定:一个人只能放一本书进去,字数控制在十万之内。那本小说总字数十四万,分为上下册,只能放进去一本上册。
而他离校前带来的就是下册。只不过不是他亲手带进来,而是通过还书的程序。尚书走后,我在书架里找到那本下册,和上册一样的封面,印刷也一样略显粗糙。
我找了个位子,安安静静地一口气读完那个故事,在翻到最后几页时,发现作者还特别留了两张白页给读者写意见。只是那上面已被寫满了,仔细一看,是一封短信,开头赫然写着我的名字。
是尚书写给我的。
这本书的作者其实是两个人,尚书和一个女生。他们是在这座图书馆初遇的。两人都喜欢写作,一拍即合,一起写了这部小说。
后来她的文字之路越来越顺,很快出版了真正的作品,声名鹊起,还去了国外深造——说起她现在的笔名,的确是一个知名畅销作家——而每当她离成功越近一步,就离原来这个圈子和他越远一步,最终不再联系,仿佛不曾认识他,也没有再同他合著过一部小说。
书名“噢,是你呵”,源自初识时她对他说的第二句话。
第一句是“谢谢”,因为当时有本书放得很高,她够不到,他帮她取了下来——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在一排排书架间邂逅多次了,彼此熟悉,只是不曾交流。
信的末尾,尚书写道:这是她的处女作,只是她永远不会承认;就像这是我的初恋,而我也不愿承认一样。
从她离开那刻起,他心中的女主角便死去了,于是他放弃了写作,在这里守护着他们共同的作品。直到若干时光后,我这样一个盗墓贼偷走了他爱人的“尸体”。
我起身,走到书架边,把小说的下册——那第七十九本书,放到上册边上,紧紧挨着。
《噢,是你呵》(上)。
《噢,是你呵》(下)。
现在,他和她,都被安静地埋葬在这里了。
(摘自《守书人》,上海文艺出版社,本刊有删节,一刀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