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智社会”与21世纪社会主义文化领导力
高世名
从剥削到剥夺:21世纪的资本主义危机
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造成了21世纪人的危机。经过漫长的20世纪,在金融资本、信息科技的数度迭代中,资本主义不断呈现出新的升级版本和运作形态——从剥削发展到剥夺,从压迫变成置换,从占有转为支配。而人的本质、人民的命运,在21世纪资本主义的状况下,正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在全球范围内,当代人身上内在的能动性、人之为人的可能性,以及人民自我创生、自我更新、自我想象的能力正在被逐渐地剥离开来。这是一种对人之本质性的“剥夺”。
被剥夺的,首先是历史感。在当代媒体的“开放空间”中,一切事件都迅速变得过时而被抛诸脑后。实时媒体时代,集体在场的现场感取代了历史感。后真相时代,世界和事件随时被刷新、被颠覆,社交网络提供的“现场感”和“参与感”是如此轻易、廉价——今天我们欢呼“我们正在参与历史”,明日“历史”就成为旧闻与八卦。在关于当下的海量记录与智能书写中,我们失去了“现在”;在由无穷算力推动的“实时”与“同步”中,我们失去了历史。
人民在帝国与民族国家的双重结构中被重新切分,在殖民史和冷战史的纠缠交织中被分断与离散,在全球化的生产消费网络中被分配与整合,在网络媒体的情感操纵中被分化和极化。
被剥夺的,其次是共同性。这次全球范围内流行的新冠疫情,让我们深刻地感知到了国族间的分断和人民间的壁垒。其实,在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市场的供需关系中,19世纪开启的国际主义联结、人民的共同性早已被割裂了。原本应该联合起来的各国劳工阶级,被转化成跨国订单的竞争者和工作上的敌对者。我们眼睁睁看着,人民在帝国与民族国家的双重结构中被重新切分,在殖民史和冷战史的纠缠交织中被分断与离散,在全球化的生产消费网络中被分配与整合,在网络媒体的情感操纵中被分化和极化——我们看到,今天的“后真相时代”也是一个“后共识时代”。人民在这个“后真相-后共识”时代中重新部落化,在智能技术和科技金融的共谋中毫无知觉地走向一种“新种姓主义”。我以为,这是21世纪上半叶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与此同时,我们也在网络媒体的自我数据化中“被个性化”,在“朋友圈”与“众筹经济”的网络互动中“去社会化”,在越来越自动、越来越便利的服务系统中陷入一种“功能性愚蠢”。万物互联,众生孤独,人们在日益智能的技术迭代中日益低能,在“社交媒体的深渊”中陷入网络的隔绝与忧郁。
被剥夺的,还有能动性。数字智能技术的加速度和实时性,迅即的自动化与现成性,正在取消我们自主性的学习与生产。一方面,信息无限累积,算力无穷增长,渠道无比便捷;另一方面,我们却看到,消费主义使生活日渐套路化,自动技术导致人的感受力愈发贫乏,社交媒体/自媒体使人的自我越来越空洞,AIGC的各类产出让公众越来越浅薄。在学校里,我们教得越多,学得越少,学得越多,想得越少;在网络上,我们点击得越多,记住得越少,浏览越多,感动越少。现代文化工业的发展,通过一系列疏导装置和知觉复制,导致消费者感受力的贫困和感性的无产阶级化。大众正被变成普遍而单纯的文化消费者。人的社会性和社会能力(sociability),以及更重要的主体性、能动性被极大地削弱了。全球范围内新自由主义和假左翼合流的话语政治,资本主义官僚化的智能治理,以及由人工智能和社交网络所赋能的消费主义,共同构成了当代人生命政治的“莫比乌斯环”。这是一种“温水煮青蛙”式的新凝固状态——由网络所动员起来的亿万网民的全球链接,或许只是制造出了一个被冻结的公共领域,在这里时刻喧嚣着的,只是社交网络时代中“无用的多数”。
这一切都是因为,世界范围内统治与压迫的形式改变了,权力运作的结构改变了,变得更加隐密、更加透明。在最近三十年中,资本经由生产关系对人之劳动价值的“剥削”,已经转化为生命政治层面对人之能动性的“剥夺”。在这种情况下,生命政治的根本问题不再是压迫,而是置换。从压迫到置换,就是用假肢置换并废除我们的器官。资本主义的基本逻辑是生产先于需求——不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有所缺失才生产出假肢,相反,正是这预先生产的假肢废除了我们的官能,把我们变成了残废。

现代文化工业的发展,导致消费者感受力的贫困和感性的无产阶级化
在最近三十年中,资本经由生产关系对人之劳动价值的“剥削”,已经转化为生命政治层面对人之能动性的“剥夺”。
新世纪以来,消费主义的置换逻辑及其超高效能让我们震惊:你要社会革命,就给你置换为社会运动;你要社会主义,就给你置换为知识左派;你要生活发展的自由,却被置换为自由市场的自由;你要媒体自由,却得到自媒体;你要的真相,被置换成八卦;你呼唤社会团结,获得的是社交网络;你本应是文化的生产者,却变成了消费者;你想做个战士,却只成为演员……
前不久,OpenAI的CEO山姆·阿尔特曼(Sam Altman)在一篇文章中宣称,人工智能将创造一种“所有人的资本主义”。他认为,改善资本主义最好的方法,是让每个人都能够直接作为股权所有者受益。阿尔特曼承认这并不是一个新想法,但他相信,随着人工智能变得越来越强大,它将成为一种新的可行方法,因为据说未来将有更多的财富可供分配。这位“ChatGPT之父”所许诺的“所有人都从资本主义中获益的世界”还在云端,但是GPT本身却必须先行受到质询:众所周知,人们使用GPT的同时也是在训练它,我们都在用自己的问题、资讯、知识甚至隐私来喂养它。全世界数亿人都为此付了使用费,然而,却没有任何人收取培训费。GPT这个知识的吸收者和信息的盘剥者,俨然装扮成一位有求必应的超级教师、一个无所不能的超级艺术家。它掩盖了用户共创与使用者生产的本质,完全背离了Web3.0的基本伦理——用户即股东。
人们使用GPT的同时也是在训练它,我们都在用自己的问题、资讯、知识甚至隐私来喂养它。全世界数亿人都为此付了使用费,然而,却没有任何人收取培训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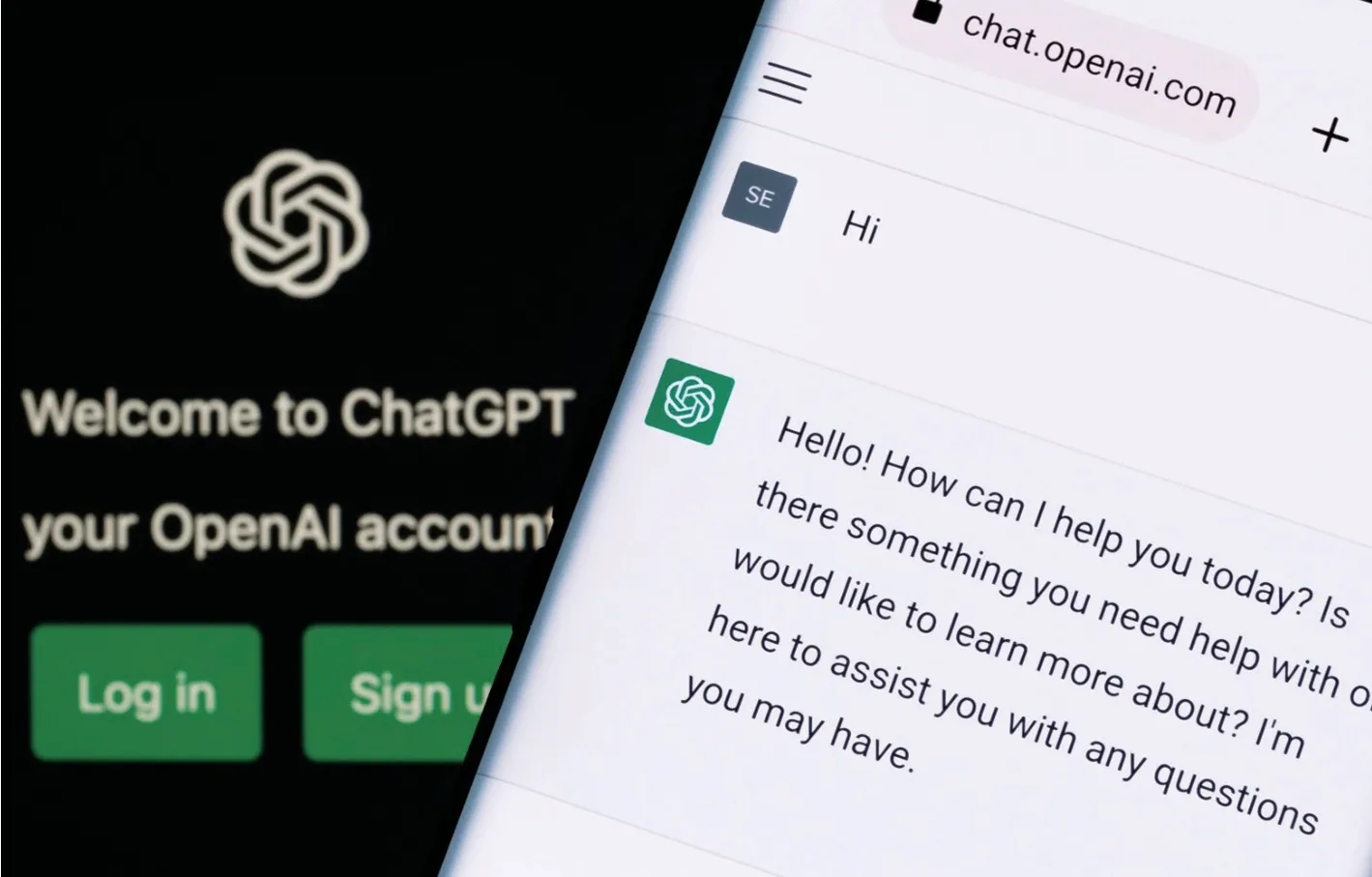
GPT掩盖了用户共创与使用者生产的本质
其实,何止是GPT,在自媒体时代,千百万所谓的“内容提供者”将他们生产的内容甚至隐私放在网上发表,而不在意任何报酬。其内容不只是出于每个人的智性和情感,而且来自操作键盘的身体劳作,而利润则归控制这种虚拟生产之物质手段的大公司所占有。平台化了的科技公司和社会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不清,它们无限地隐身于社会,或者说,公司已然成功地装扮成社会本身。由科技资本和金融资本支撑起的平台资本主义所构造出的全球治理装置没有外部,于是压迫和剥削就隐于我们自身,融入我们身处其中并且乐在其中的日常生活。对于我们这些互联网和智能工具的用户来说,这个异常便利的自动化的数字世界是如此现成,似乎就是日常甚至自然的一部分。我们完全忽略了这个虚拟的数字世界其实是有代价的,它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譬如根服务器和海底光缆,这些都是看不见的旷世工程。我们全然忘记了“数字孪生”“元宇宙”以及整个云端系统都需要耗费大量的能源,这种能耗是每时每刻的,而且数量越来越大。数字智能科技日益发达,数字虚拟世界一层层蔓生,这一切都在消耗着这个星球的现实资源;况且,这种熵增现象还伴随着人类自身性和存在感的巨大亏空。通过完全消除作者工作以及“非异化”的艺术和文化工作,互联网加上人工智能几乎已经完成了19世纪开始的人类的无产阶级化进程。Web3.0宣称的平等和解放被抢先置换为平台资本主义的话术和戏法,在社交媒体/自媒体之欲望机制的操作下,人们正心甘情愿地投资于对自己的剥削与剥夺。
当前,全球范围内的生命困境是:没有确凿的外在的敌人,所以人们在“政治正确”的泥沼中画地为牢、作茧自缚;没有可为之奋斗的未来愿景,所以大家在无公害的科幻中沉迷狂热。前一阵子,我重温了布莱希特的长诗《致后代》,情不自禁地写下这样一段话:
对全球艺术界来说,创造和辩证无从谈起,虚假与平庸铁证如山。艺术同时是解药、补药和泻药,大多数时间是镇痛剂和迷幻药,而作品一半是症候,一半是寓言。……平庸的恶是超越伦理的,其根本是无生产性劳作和消费主义轮回,如何突破这个莫比乌斯环,重新成为精神和价值的生产者,才是“逆天改命”的大事。否则,我们这一代所书写的《致后代》,恐怕只能是——“我们活在一个平庸的时代”。
“数智社会”与21世纪社会主义文化领导力
Web3.0宣称的平等和解放被抢先置换为平台资本主义的话术和戏法,在社交媒体/自媒体之欲望机制的操作下,人们正心甘情愿地投资于对自己的剥削与剥夺。
这些年,学界越来越关注过去一个世纪中被忽略了的马克思主义技术观,以及由此而生的伦理和解放原则——如何通过技术自动化将剩余劳动扬弃为自由时间。法国的隐形委员会(Comité Invisible)在2014年底出版的《致我们的朋友》中,有一章叫“Fuck off Google”,指出必须发展一种有伦理的技术,以回应这个算法和大数据作为治理术的时代。为此,我们需要在有伦理的技术(technique)和资本主义裹挟的科技(technology)之间做出区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科学技术都是高度敏感、高度关注的。他们关心技术,以及由技术发展所导致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我们知道,马克思的劳动观念和社会理论很大程度上筑基于他对技术的思考,《1861—1863年手稿》中就有“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一节,《资本论》第1卷第13章也专门讨论了“机器与大工业”;他甚至还创造性地提出了未来社会“新的技术人类生活共同体”的理想。在世界现代史的进程中,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始终是先锋性的,具有高度创新性。1970年,阿连德作为第一个民选社会主义总统上台,他开始推行一项被称为“智利社会主义之路”的规划,打造一个由电报机组成的网络系统——Cybersyn。这个计划的目的是,使用类似计算机网络的系统来统筹管理整个国民经济。在当时,“互联网”一词并未诞生。Cybersyn是一台超级“计划机器”,能够实时地把智利所有国有工厂、每一条生产线上的数据传输到位于圣地亚哥的数据中心,输入到一个模拟软件中,用来宏观预测、实时监督、合理调控全国的生产和资源。Cybersyn由此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大数据系统。很遗憾,1973年9月11日,在美国的支持下,皮诺切克发动政变,阿连德总统在战斗中牺牲,这场数字智能社会的革命因此推迟了三十年。
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根植于19世纪工业革命时代的经验,经过科技大发展的20世纪,到了21世纪,事情有了很大变化。最近这二十年以来,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化之大,让我们不禁猜测,人类的技术发展已经进入了又一次加速期,尤其是近年来人工智能的发展,使技术真正实现了日新月异,人类的生命经验也在不断地自我迭代。技术、资本和那些构造出“单一普遍性”(singular universality)或者“普遍独一性”(universal singularity)的跨国企业及其金融王国,正通过技术-信息-资本-权力的社会网络建立起一种总体性的全球治理,一种与地缘政治交错共构的新形态的全球阶级分化正在进行,一种数字智能时代的新种姓制度正在浮现。
面对上述的新局面、新命题和新挑战,我们如何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出发,发展出一种影响全世界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种先锋性的新文化又如何在国内外形成真正的领导力?我认为,确立21世纪社会主义文化领导力的关键,在于社会主义能否创造出一种科技的新思想、发展的新伦理、创新的新路径,能否发展出一种从“科技-信息-资本-权力”的网络中实现人之解放的新政治。
在现实层面,最近十几年来,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创新正在中国发生。伴随着数字经济、智能技术而形成的“数智社会”正在逐渐成形,我们身边出现了太多的试验和崭新的探索。随着未来社区、未来乡村、未来工厂的推进,许多未来生活场景正在迅速成为现实。随着数字智能社会的深入建设,一种新的发展格局正在全面展开,连带出现的是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混合现实时代的新生活经验、新社会意识、新感性和新伦理。
21世纪,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这或许是人类文明的一次新的开局。谁更能把握住新科技的演进和生产力的最新发展,谁能够克服信息科技、智能技术和金融资本所建立起的总体性治理,提出人类社会的新议程,谁就能在这场新的文明竞争中胜出。
确立21世纪社会主义文化领导力的关键,在于社会主义能否创造出一种科技的新思想、发展的新伦理、创新的新路径,能否发展出一种从“科技-信息-资本-权力”的网络中实现人之解放的新政治。
抛开西方世界形形色色的左翼理论不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和现实斗争中,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和社会治理学说正逐渐趋于成熟。这些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精神,对社会治理、政党政治、市场经济进行改造,其核心是伸张一种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社会发展模式;在“资本-社会-国家”的不对称结构中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动力机制和组织机制,从新的技术和生产力状况出发重新建构社会关系。十年来,新时代的中国实践总结出了许多原创性思想贡献,比如:(1)“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国际主义的最新发展,在格局和道义上蕴含着对西方中心主义、地缘政治和“新冷战”思维的超越;(2)“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实践,蕴含着对殖民式全球化/现代化的“资本空间再生产”的克服与超越;(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理念,蕴含着对西方新自由主义“大市场、小政府”话语和垄断资本主义、平台资本主义的超越;(4)“五位一体”发展理念、“共同富裕”发展目标,是社会主义社会理论和实践路径的创新,蕴含着对西方“资本-市场”二元驱动的发展逻辑的超越;(5)“生态文明”“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是对中国传统天人观、自然观的继承和发展,克服西方狭隘的“环保 vs. 发展”二元困境,蕴含着对西方现代性观念和“人类纪”(Anthropocene)话语的超越。

第一个民选社会主义总统阿连德试图打造一个由电报机组成的网络系统
以上五个方面都是21世纪社会主义的最新发展,其中所蕴含的“共同价值”,是对西方诸种“普世价值”的克服和超越,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这十年,党的理论建设全面开动,纲举目张,但要真正形成感召全世界、影响21世纪的政治文化和思想,形成文化领导力,依然道阻且长。在未来十年中,我们需要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观念和创新理论进行更为系统的研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理念,蕴含着对西方新自由主义“大市场、小政府”话语和垄断资本主义、平台资本主义的超越。
先说发展。西方主导的现代化只是让全世界8%的人得到发展,却让80%以上的民族经受了殖民之痛。而以中国为首的金砖国家,带领65%以上的人得到发展。近年来,中国的脱贫攻坚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这几年“金砖五国”被分而治之,其影响力逐渐衰退,而科技金融以及平台资本主义等新界面,使得后发国家的优势被迅速瓦解,南北差距越来越大。根据乐施会(Oxfam)2018~2019年的年度报告,在2018年,全球前26名富豪所拥有的财产,约等于全球一半(约38亿人)较贫困人口所拥有的财产的总和。随着科技金融资本的扩张,随着美国的“脱钩”与科技封锁,在三年疫情之后,这个数据会更加夸张。中国如何面对这样的世界问题?能否提供超越性的解决方案?
再说创新。长期以来,社会主义更强调集体协作、集成创新,对于熊彼特所谓的个人英雄主义式的企业家精神和垄断性超额利润并不鼓励,甚至还有所限制。当前,在“熔断”“脱钩”体制之下,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社会治理、政治运作的创新,都需要直面挑战,自主思考、自主实践。在近年来对全球知识经济、创意经济产生巨大影响的AI科技领域中,华人科学家的人数最多、贡献最大,但中国却依然在这个领域被“卡脖子”。这个令人痛心的现实背后,是国内科研和教育体制长期存在的系统性问题。在此背景下,社会主义如何超越个体主义、自由主义的创造性假设?如何培育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创新联合体,激发起“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能量?如何营造出体现社会维度和共同价值的创新生态?这些都成为21世纪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思考的重大命题。在当下这个数字智能时代,智能被重新定义,人被重新定义,创造性被重新定义。社会主义的人学和创新理论必须要在这个全人类的大困境、大命题上发力。
在当下这个数字智能时代,智能被重新定义,人被重新定义,创造性被重新定义。社会主义的人学和创新理论必须要在这个全人类的大困境、大命题上发力。

21世纪正在迎来史无前例的AI革命
在21世纪,我们经历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前所未有的两极分化,经历了数字经济与科技金融的大爆发,经历了从社交媒体到“元宇宙”的迭代,更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疫情,同时正在迎来史无前例的AI革命。这一切,不但改变了我们对国际政治、社会伦理以及公平正义的看法,改变了人们对生产和消费的理解,更改变了我们对日常生活的感觉、对社会进程的体认以及对未来的想象。这些改变,很可能是一场持久而深刻的变革的开始。不远的未来,似乎已初露端倪。如果说在文化创造的意义上,“19世纪”始自革命浪潮汹涌的19世纪40年代,“20世纪”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终结,那么“21世纪”的精神奠基,可能就始于过去这三年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以及此刻正在发生的AI革命。
21世纪已经过去了近四分之一,我们看到,现实加速迭代,历史激进前行,人的发展却瞠乎其后。在艺术领域,今日的蔚为大观或名存实亡,全球市场的巨大惯性和乏善可陈,创造与行动的“力比多”经济已是难以为继。在设计领域,曾经作为现代生活之发明者的设计,曾经建构宏大社会想象的设计,曾经作为革命和解放力量的设计,已经被窄化为全球制造业链条中的一个生产环节。甚至,它已经被异化为全球资本“空间再生产”和“创造性破坏”的力比多、催化剂,成为消费主义品牌战争的“白日焰火”。创造新生活的设计原动力,被置换为功能的优化、花样的翻新、品牌的包装推广,以及成本和利润的精明算计。艺术和设计越来越沦为一种服务业,越来越文创产业化,它所生产出的不再是新社会的愿景、新生活的方式,而是单纯的利润和算计,以及一个在AI面前瑟瑟发抖的“创意阶层”。
面对技术和资本主义的自我迭代,面对从占有到支配、从剥削到剥夺、从压迫到置换的治理与宰制新方式,我们对于文化、艺术和创造的理解已然改变。跳出艺术界和知识界的小圈子,重新回到马克思及其后继者们的敏锐感知、宽广视野和远大抱负,我们是否可以试着发展出一种文化斗争与精神生产的新方式?是否可以开辟出通往自由和创新的新路径?是否可以形成一种开放包容、以民为本、共同富裕的发展新模式?
我们身处一个大变革的时代,科技的迅疾发展、大国之间的博弈正将我们带向不确定的未来。让我们抛开一切狭隘和割裂,超越所有纷争与鸿沟,以我们的诚意和善意,拥抱最新的科技、最前沿的产业、最挑战的知识、最遥远的他者,汇聚社会思想、艺术设计、智能科技、数字经济的全球力量,打造一个多方协同、多元开放的“创新联合体”,一个思想、艺术、科技、产业共生共创共享的新文化的“反应堆”。因为我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只有创新才能让21世纪的社会主义生机勃勃,只有发展才能形成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化领导力。为此,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直面最新的科技、最激进的现实,进行不断的理论创新,必须对人的当代状况做新的解释,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描绘新的愿景。
艺术和设计越来越沦为一种服务业,越来越文创产业化,它所生产出的不再是新社会的愿景、新生活的方式,而是单纯的利润和算计,以及一个在AI面前瑟瑟发抖的“创意阶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