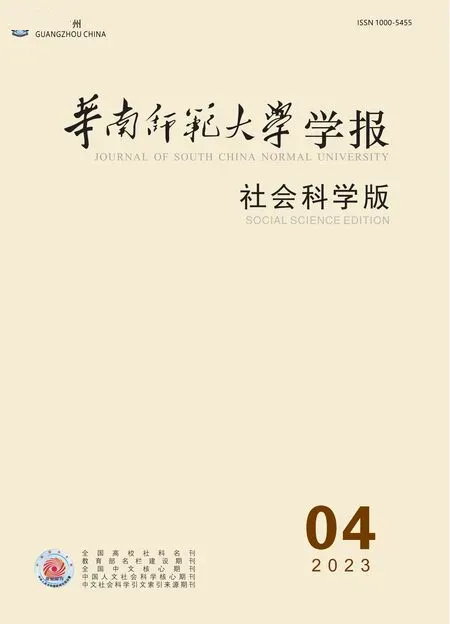杞柳与骈拇
——人性的真与善
赵金刚
(清华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084)
《孟子·告子上》诸章记述了孟子与告子的诸多辩论,透过这些“辩性善”的章节,可以深入理解孟子人性论的基本立场和倾向。(1)牟宗三在《圆善论》第一章《基本的义理》中就专门顺着这些章节的疏解,展开了他对孟子人性论的理解,讨论孟子人性论的研究者应该关注这些章节的义理空间。参见牟宗三:《圆善论》,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0。第一章《性犹杞柳也章》是这些论辩的发端。然而,古今孟学诠释者对此章的关注却不如其他几章——“湍水之喻”由于与宋明理学人性论说的复杂关联而被学者关注,《生之谓性章》有理学与辩论逻辑的双重加持,之后两章涉及“仁内义外”等哲学论证,第六章涉及对当时人性论的总结、孟子思想中的“情”“才”问题、“四心”问题,因之思想打开的空间均比较丰富。敞开第一章思想言说空间的,当属唐文治先生。《孟子大义》特有一“愚按”表达他对此章的总体理解:
杞柳不能自然为桮棬也,必戕贼而后成之。桮棬成而杞柳之本性失矣。以此而喻性,则人将曰:“吾欲适吾自然之性,宁拳曲臃肿而不中于绳墨也。”此即庄子以仁义易其性之说也。(见《骈拇》篇。)如是则人皆畏仁义,故孟子斥之曰“祸仁义”。(2)唐文治:《孟子大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第356页。
这里比较关键的有两点:一是“自然之性”与“绳墨”的关系,这是古今注家都会注意到的问题;二是将这一章讨论的人性问题与庄子(特别是《庄子·骈拇》)联系起来,将此章“祸仁义”的思想意涵打开,这是以往孟子人性论研究较少关注的。惜乎唐文治先生之论仅止于此,更进一步的比较有待今人申说。之后的学者,较为明确地提出此章与道家人性论关系的,则为徐复观先生。(3)当然,这还涉及告子思想流派的归属问题,赵岐以为告子“兼治儒墨之道,尝学于孟子”(焦循:《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第731页)。古今学者相关考证,可参黄俊杰:《孟学思想史论》,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1,第212、214页。当代学者中李景林先生承继钱穆先生,以为告子属于道家(李景林:《孟子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第50页),杨海文先生以为告子属于“以道为主,兼采儒墨者”(杨海文:《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的世界》,齐鲁书社,2017,第102页)。本文以为告子属于儒家学派的孟子前辈学者,如若不然,此章“祸仁义”的论证力度便会弱了很多。然而徐先生的论说也集中在对《孟子》此章的文义阐发上,哲理空间还有待展开。
孟子与庄子同时,然而《孟子》文本中没有提到庄子,《庄子》中似乎也没有孟子的身影,这不得不说是思想史的一个遗憾。《骈拇》虽属“外杂篇”,但也可以反映“庄学”或道家某一流派的思想气质。透过杞柳与骈拇的对照,或可在孟告之辩外再打开一个辩论的空间。
一、杞柳与桮棬:人性与“制作”
徐复观先生以为,“告子的人性论,是以‘生之谓性’为出发点”(4)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114页。。本章开始,告子以比喻的形式,说明了他对人性与仁义关系的理解:
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孟子·告子上》)
赵岐以为,“告子以为人性为才干,义为成器,犹以杞柳之木为桮棬也”(5)焦循:《孟子正义》,第732页。。“才干”即焦循所谓“枝干”(6)同上。,为待成就的“材料”;“成器”即完成品,是材料经由制作而成就的。人性与仁义为二,二者并非“内在性关系”,而需要外在的“为”,“必待矫揉而后成”(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第325页。。“制作”对于仁义的长成,是主导性的因素,而非辅助性的。牟宗三先生指出:
告子以杞柳喻性,是把性看作材料,是中性义的性,并无所谓善恶,其或善或恶是后天造成的,因而其中亦无所谓仁义,仁义亦是后天造成的,因而仁义是外于人性的。(8)牟宗三:《圆善论》,第3页。
告子认为人性是无规定性、无内容的“材料”,不认为仁义为人性所“固有”,不认为“仁义”可以以某种形式作为人性的“内容”。但这里依旧需要讨论告子能否接受仁义作为人性的“潜能”。徐复观先生认为:
由他这一譬喻,可以导向两种结论。一个是杞柳的本性无桮棬,以杞柳为桮棬,乃伤杞柳之性,因之以人性为仁义,也是伤了人之性,这是道家的结论。另一种结论是杞柳不是桮棬,而可以为桮棬,人性无仁义,也可以为仁义,以见主张性无分于善恶,并无伤于仁义之教。就告子的基本立场说,似以前一结论为合于他的原意。但就此段话的问答的情形说,则又似以后一结论为合于他的原意。孟子则是以后一结论作基点而加以诘责的。人性既无仁义,则各人自己亦无为仁义之意欲,则为仁义不能顺各人自然的要求,而只有靠外在的强制力量。顺人性之善以为仁义,这是顺人的自由意志以为仁义,这是人的自由的发挥。靠外在强制之力以为仁义,则只有以人类的自由意志作牺牲。(9)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第120页。
按照第一种结论,告子的人性不包含仁义作为潜能;按照第二种结论,则无所谓有何种可能,或者说是有一种开放性的可能。可以说,告子言说的重点在于外在的“强制力量”,即制作,即“非人力,则杞柳不可以为桮棬,非人力,则人性不可以为仁义”(10)焦循:《孟子正义》,第732页。。告子所讲的人性自然性,排除了倾向性(性能),排除了性本身的一切动态可能,是纯然静态的,相当于“朴”(11)李景林先生以为告子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人性“白板论”,参见《孟子通释》,第211页。。告子的性完全是被动的,不含有任何主动的“动能”。其从人性到仁义的过程,是制作的逻辑,而非生生的逻辑:制作以一外在于质料的形式来“规范”“材料”,生生则是形质合一的事物自身的变化发展。(12)参见吴飞:《论“生生”——兼与丁耘先生商榷》,《哲学研究》2018年第1期;丁耘:《〈易传〉与“生生”——回应吴飞先生》,《哲学研究》2018年第1期。
孟子思想中,人性与仁义是内在性关系,从四端到仁义是生生的逻辑,强调主体内在的道德动能,“仁义即人性之实,从人性而发的仁义是人性本然的表现。从人性而仁义呈顺成之势”(13)郭齐勇:《中国哲学通史·先秦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第324页。。故孟子自然不能接受告子的观点:
孟子曰:“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棬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桮棬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桮棬,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孟子·告子上》)
孟子并未明确言说自己的观点,而是指出了外在力量作用在材料上的两种模式:第一种是顺性而为,保持事物自身的存在方式;第二种是戕贼破坏本性,改变事物原有的存在方式。(14)传统技术多为第一种模式,而现代科学则倾向于第二种模式。第一种就必须承认仁义要么为人性之内容,要么为人性之潜能,这显然不是告子的立论基础。告子本人似只主张一“中性”的制作,但从制作与事物的存在方式之关系来看,这种“中性”是不可能的。只要不承认第一种模式,就必然要承认第二种模式,即此种制作彻底改变了“材料”;在制作完成后,桮棬就不再是杞柳,人们直接观察完成品,甚或无法知晓其来历。对于普通材料而言,这种制作站在有主体的制作者来说,可能是创造了一种新的“有用性”;而站在人性这种材料来讲,则是对人的本真状态(原初状态)的破坏。这其实就涉及了真与善的关系问题。真或本真意味着“因其自身之故而存在”,“不再为他者(他人与它物)所规定,而是仅仅自我规定着”。(15)陈勇:《生存、知识与本真性——论亚里士多德与海德格尔的实践哲学》,《哲学研究》2017年第4期。在中国哲学的语言中,此种真往往与自然有关;善则是道德、伦理的价值,包含着个体乃至共同体对美好生活的理解。同样地,在中国哲学的语言中,此种善往往与仁义有关。这就牵涉到真善是否合一的问题,以及如果真善不合一,那么在价值序列上,真与善谁更重要等一系列问题。
在孟子与告子的第一个论辩中,人性属真是双方都接受的。在告子的思想中,显然真与善是分离的,“杞柳是质料,而桮棬是由此质料制成的器具。告子这一比喻的要点在于指出,义不是人的自然,而是以人的自然为质料‘加工’而成的”(16)杨立华:《穿越告子的丛林》,《读书》2005年第12期。,善非真是告子立论的前提。并且,从他的描述中可以看到善要重于真——成器比材料更为有用。这就可能导致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在价值上重视真,将真视为优先的、值得呵护的,他会如何看待第二种制作模式下“对真的破坏才能成就善”这一问题?他是否会接受此种制作?他是否还愿意为善?在强调真的绝对优先性的人看来,这种制作所达到的善是一种“伪”。为了保持真,那就不能接受虚伪的外在善。“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究竟指怎样的行为,历代注家似讨论得并不显白。朱子以为,“言如此,则天下之人皆以仁义为害性而不肯为,是因子之言而为仁义之祸也”(1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25页。。显然朱子所讲的“不肯为”只有站在对真的优先性强调的基础上才可能发生。徐复观先生指出了两种情况:“一是为了保持自由而不谈仁义,这是许多道家的态度,也是西方文化20世纪的主要趋向。另一则是牺牲自由而戕贼人以为仁义。”(18)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第120页。第一种依旧是强调真胜过强调善;第二种是对强制之力的过分推崇,甚至有可能将强制力本身异化为目的,把仁义当成是强制力的手段。从孟子使用“戕贼”一词来看,“戕贼”不包含对强制力的推崇之义。孟子认为的可能因制作伤害本性而不为仁义的行为,主要还是指向第一种(19)陈冀博士指出,“以人学以成仁义视为对人性的戕贼,这一理解很可能是孟子出于对杨朱学派的焦虑以至对告子进行了过度的道家化解读,将其塑造成了类似于庄子的形象,这一形象为后世大部分重要诠释者所接受”。见陈冀:《从孟告之辩看告子思想》,《孔子研究》2018年第2期。,也就是徐复观先生所指出的道家的态度;而在文本上与之呼应的,则是唐文治先生指出的《骈拇》篇。
二、骈拇与仁义:以真黜善
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中以为“道家不承认仁义是人的本性”(20)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15,第314页。,特举《骈拇》篇为例进行说明,道家认为“仁义并非常然之性,奔命于仁义,亦是以物易性;认仁义为性的思想,乃是乱人之性。仁义是在性外的”(21)同上书,第315页。。此正是《孟子》担心的“祸仁义”者的言论。
关于《骈拇》篇,陈鼓应先生指出,“道家人性论议题始于《庄子》外篇。《骈拇》列外篇之首,有学者指出这是一篇道家的人性论。从《骈拇》《马蹄》到《在宥》,常被学界视为内容相连的一组文章,其主题在于阐扬任情率性与安情适性”(22)陈鼓应:《庄子人性论》,中华书局,2017,第76页。引文中“有学者指出……”,指曹础基的《庄子浅注》,中华书局,2022,第119页。。陈引驰并以为,“《骈拇》一篇,述《庄子》之自然人性论,主旨以为儒家所提倡的仁义之类非人性之固然,因而是必须加以反对的,正当的途径不过是尊重人性的本然,自适自得而任性命之情”(23)陈引驰:《庄子讲义》,中华书局,2021,第283页。。这些均可看出《骈拇》篇在儒道对话上的意义。
《骈拇》篇的立论出发点即“仁义是对人之存在的‘侈’——即多余之物”(24)赵帅锋、郭美华:《仁义对道德的阻碍与中断——论〈庄子·骈拇〉对仁义的批判》,载《诸子学刊》第19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第83页。,也就是认为仁义这种一般被认为是善的价值,相对于存在之真、存在之自然而言,是外在的,“仁义作为造作之物,是对于道—德之间自然畅然关联的阻碍和中断”(25)同上。。此即宣颖解释《骈拇》时所说:“圣门言仁义即是性,庄子却将仁义看作性外添出之物。”(26)宣颖:《南华经解》卷八,载《中华续道藏》初辑(影印本),新文丰出版社,1999。当然,这里的“圣门”当是以孟子为代表的性善论者,告子在此一辩论中何尝不将仁义当成“添出之物”呢?只是《庄子》所强调的“添出”的负面意义是告子不愿意接受的罢了,毕竟告子还要承认仁义的正面意义。
《骈拇》开篇就讲:
骈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于德;附赘县疣出乎形哉,而侈于性;多方乎仁义而用之者,列于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骈于足者,连无用之肉也;枝于手者,树无用之指也;多方骈枝于五藏之情者,淫僻于仁义之行,而多方于聪明之用也。(27)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第231页。
骈拇、枝指、附赘县疣是“天生”的,但相对于“德”“性”则是多余的,对人来讲是“无用”的。仁义与之类似,仁义并非“道德之正”。按照徐复观先生理解,“这里所说的‘道德’,即是德,即是性”(28)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第228页。郑开教授也以为:《老子》中尽管没有“性”字,但其常说的“德”与“命”“朴”与“素”“赤子”与“婴儿”,皆相当于后来的哲学概念“性”;同样,《庄子》里的“德”“真”“性命之情”等概念,也相当于“性”。郑开:《道家形而上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第325-326页。,也即仁义不是“人性之正”,不是按照人性之“自然”所当拥有的,“凡是后天滋多蕃衍出来的东西都不是性,或者是性发展的障碍”(29)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第228页。。相较于骈拇等的多余而无用,仁义的多余则是有害的,是更要避免的。“枝于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声,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30)同⑤书,第232页。曾史即曾参和史鰌,是主张仁义的儒家代表。在《骈拇》的作者看来,“曾参、史鰌作为五脏禀性侈于其性者,以一己肝之仁为普遍之德,标榜拔擢以为至道,阻塞人性以求声誉,让他人汲汲于竞逐他们天性所不及之物,荼毒他人生命、扭曲天下之大道”(31)同②书,第83-84页。。对照《孟子》的语境,曾参和史鰌就是“戕贼人以为仁义”,《骈拇》即是以仁义为祸。在《骈拇》的语境中,“道德之正”即“性命之真”,也即人性之自然;仁义则是以制作破坏真的行为,“是对自然真实之情的虚伪化”(32)同②书,第84页。。
多余之“德性”可以有两种方式。第一种类似骈拇、枝指,虽是多余,但还是天生,可以纳入自然,只要不以其为不善,在自己的性分中适性而行,那就不会有害。(33)参见赵帅锋、郭美华:《仁义对道德的阻碍与中断——论〈庄子·骈拇〉对仁义的批判》的相关诠释,载《诸子学刊》第19辑,第81-94页。孟子讲:“今有无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则不远秦楚之路,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则知恶之;心不若人,则不知恶,此之谓不知类也。”(34)《孟子·告子上》,载《四书章句集注》,第334页。以下所引《孟子》,皆同此出处,只注篇名。在孟子的逻辑中,人有“同类意识”,如果指不若人,就会有求若人之心,这是孟子对人情的理解。而如果回到《骈拇》的逻辑当中,“无名之指屈而不信”是“自然之真”;而要求伸,则是害真。第二种多余则类似仁义,完全是后天的制作,不但多余,反而有害。张岱年先生以为,“自然与人为的关系本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人为是对于自然的改变;另一方面,人为对于自然的改变也是自然而然的”(35)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中华书局,2017,第95页。。在《骈拇》的逻辑中,仁义显然不属于自然而然地对自然的改变,而是含有某种“刻意”的“造作”在其中。“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忧也。意仁义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忧也!”(36)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第235页。这里的“续”“断”都是以外在的善为标准,对自然进行破坏;回到人这里,则是以外在的仁义之善破坏人性之真。成玄英在解释《骈拇》时特别强调,“自然之理,亭毒众形,虽复修短不同,而形体各足称事,咸得逍遥。而惑者方欲截鹤之长续凫之短以为齐,深乖造化,违失本性,所以忧悲”(37)郭象注,成玄英疏:《南华真经注疏》,中华书局,1998,第184页。。对照《孟子》,可以说“欲截鹤之长续凫之短以为齐”,即变杞柳为桮棬的过程——杞柳不需要成为成器就有自己的价值;而这样的造作过程,是违背万物本真的行为。林希逸也讲:“以凫鹤二端言之,则仁义多端,非人情矣,故叹而言之。使仁义出于自然,则不如是其多忧矣,多忧者,言为仁义者,多忧劳也。”(38)林希逸:《庄子虞齐口义校注》,中华书局,1997,第140页。《骈拇》始终将仁义置于自然之外,将仁义看成是“失真”;而在价值序列上,始终将自然之真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屈折礼乐,呴俞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39)同上书,第141页。,认为“儒家吹嘘仁义来抚慰天下人的心,这也破坏了人的本然之性。所以要保持人的自然本性就应该弯者自弯、直者自直,自圆而不用规,自方而不用矩”(40)张岱年:《中华的智慧》,中华书局,2017,第102页。。“自然”本身就包含着最高价值——最高的“善好”,不需要破坏了这种“善好”再去追求外在的善。“物丧其真,人亡其本,既而弃本逐末。故失其真常自然之性者也。”(41)同⑤书,第186页。成玄英此疏中的本末之说,更是点出了真在价值序列中的位置。当然,这里的本末也不是生生的自然展开逻辑,而是一种价值上的对举。
《骈拇》篇的内容意旨虽不见得与《庄子》“内篇”相同,但却有能反映庄子乃至先秦道家思想的一般倾向之处,即对自然之真的高扬,对制作出的超越人性之真的善的贬黜。与《骈拇》呼应较为紧密的是《马蹄》篇。“《马蹄》《骈拇》皆从性命上发论。《骈拇》是尽己之性,而切指仁义之为害于身心;《马蹄》是尽物之性,而切指仁义之为害于天下。”(42)刘凤苞:《南华雪心编》,中华书局,2013,第220页。《马蹄》篇讲:“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馽,编之以皂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策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43)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第244页。这里“烧之”等一系列动词,即“矫揉”“为”的过程,就是对“材料”的制作,而这一切都是破坏性的,即“戕贼”。《马蹄》以为“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44)同上书,第247页。。此道德即“道德之正”,也就是自然之真。不独《马蹄》有此观点。早在《老子》那里就已经强调万物只要能保持自己的“朴”,不受外力干扰,就能实现自身的完满,达到彼此的和谐。《庄子·大宗师》意而子和许由的对话,也认为儒家的仁义是对人的“黥”“劓”,所谓“夫尧既已黥汝以仁义,而劓汝以是非矣”(45)同②书,第207页。。而这些,可以说是潜在于孟告杞柳之辩背后一个不容忽视的思想史背景。否则,就无法理解孟子为何会“敏感”地讲出“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这样的结论。
可见,告子并没有意识到,一旦把真和善分离,把自然与仁义看成是完全外在性的关系可能导致的哲学质疑。特别是,如果像道家一样强调真的圆满、自足,就不会有仁义的位置,而这也是孟告这一辩论中,告子最为致命的思想问题。孟子显然对此保持了高度的思想敏感。而孟子之所以能保持这样的思想领会,则与其对“人性善”的理解密切相关。即,孟子在讲善的时候,并非只看到了道德、价值的意涵与意义,而是“收真于善”。孟子讲的善是真善合一的,必须要看到其言说中真的面向,才能对孟子人性论有更深入的理解。
三、孟子人性论:真善合一
学者们已经指出,“十三经无‘真’字”,真字始见于《老子》《庄子》诸书,但这却不意味着真字要表达的思想意涵在儒家思想中有所缺失,儒家思想中会以贞、正等字代替真。(46)参见杨少涵:《十三经无“真”字——儒道分野的一个字源学证据》,《哲学动态》2021年第8期。更为重要的是,真字所表达的本真、源发、本始等意涵,在儒家则以其他概念指代、收摄。这些概念对真的收摄,反而体现出儒家思想的特色。
真的思想所指被儒学收摄进自身的概念之中,这一现象在诚这里体现得最为充分。《大学》讲“诚意”,直接对峙“自欺”等虚假的意识活动,而《中庸》的诚更是被视为形而上学的“诚体”。(47)同上。《中庸》之诚是“真实”与“善性”的合一,其真的面向重点体现在“为物不二,生物不测”(《中庸》第二十六章)。朱子以为“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4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1页。。如是,人的“诚之”就可以视作对自己本真的复归,成善的过程本身就是成真的过程。这就不存在《骈拇》所批评的破坏本真而成善的可能,也就不存在仁义对人的戕贼了。
随着对出土文献的释读,孟子承继子思这一观点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相较而言,诚在孟子思想中虽然没有在《中庸》中那么突出,但其真善合一的特性却在孟子言说“人性善”时继承了下来。
首先,孟子以心善言性善,其特重“本心”。此“本心”即人原本自足、自身规定自己的心,四端是“本心的乘机而作”。后天损害、玷污、放逐的心,即被外在环境影响作用的心,是“非本心”。这一“本心”可以说即是“真心”,只是相对于道家纯粹无内容的、虚的真心,孟子的本心具有先验的道德意识。但在其排除后天经验性这点来说,依旧可以强调其本真性。孟子讲“可欲之谓善”(《孟子·告子下》),可欲的就是以仁义礼智为内容的人性(49)《孟子通释》,第311页。,而此种可欲是发自本心的自我追求、自我实现的欲望,人对仁义的追求本身就是内在仁义,而非外在力量强制作用的结果。李景林先生指出,“‘可求’‘可欲’,构成了人性之先天内容”,这与孔子讲的“求仁得仁”“欲仁仁至”有一致之处。(50)同上书,第312页。
其次,孟子成就仁义的路径是“扩充”“求放心”,而不是“制作”。这也是对自然自然而然的改变,顺着人性的自然而成就自然。孟子讲要对四端之心“知皆扩而充之”(《孟子·公孙丑上》),知就是对自身性善的肯认。在此基础上,将善端扩大,此“扩充”是本真的自我实现,而非外力的强制作用。孟子的比喻类讲法,多能说明这一点,如他讲“火之始燃”“泉之始达”(《孟子·公孙丑上》),这里的“燃”和“达”都是内在力量的自我成就,而非外力的加入。因此孟子反对拔苗助长,认为此种外在的强制不是正确的工夫。而“求放心”(《孟子·告子上》)这样的讲法,更是蕴含了本真、本善的自我复归的意涵。成仁义是人“以自身为对象”(51)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第281页。,是人的内在转化,是自我转化,而非外在形式对自己的强制的制作。
可以看到,后世基于孟子展开论说的儒家思想流派在论述善的问题时,往往会强调善有真的面向。如王阳明的良知学说就特别强调“良知之诚爱恻怛处,便是仁,无诚爱恻怛之心,亦无良知可致矣”(52)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二六《寄正宪男手墨二卷》,中华书局,2015,第1141页。,这里的“诚爱恻怛”即是真与善合一的道德状态。阳明更是讲“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53)王阳明:《王文成公全书 传习录》,中华书局,2015,第104页。,良知是“扎根于仁体之中、带着鲜活的生命同体的体验的一种觉知”(54)陈立胜:《知情意:王阳明良知论的三个面向》,《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这种对道德本体真善合一的讲法,是对孟子思想的自然发挥。
当论者强调孟子的道德观是自律的形态时,就要意识到,如果真没有被收摄进善当中,自律是不可能成立的。根据孟子对人性的理解,仁义本身就是人性的内容;而这样以善为内容的性,本身已经摄真于善,其思想展开自然不存在告子那里的“制作”义,不包含工夫对本真的破坏。相反,成善本身就是成真。因此,在孟子这里也就不存在为成就仁义而对人性有所戕贼的问题了。当然,道家或可质疑孟子摄真于善的真还是一种不真;然而,孟子自有对性善的论证。站在孟子的角度也可透过“人禽之辩”去质疑道家所讲的真不是人的本真。这就涉及各自立场的根底问题了。
在《性犹杞柳也章》孟子与告子的论辩中,孟子已经注意到将真、善分离可能导致的对善的质疑,此种言说模式终将导致“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孟子当时的论辩对象既是告子,更是高扬真的道家。而孟子的思想对手,在今天则更为常见。徐复观先生以为,“为了保持自由而不谈仁义,这是许多道家的态度,也是西方文化20世纪的主要趋向”(55)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第120页。。把此处的“自由”理解为真毋宁更为恰当,今天多见“活出真我”的口号、多见以天性的名义对教化的质疑,即是明证。
真、善的分离,一种表现形式就是实然与应然的分离。如是,人类的一切道德就可能失去“自然之基”,而都成为后天的建构,成为某种形式的契约。这样,道德的相对特性就会愈发明显,甚至可能撕裂道德本身并使其碎片化,将一切相对化、虚无化。此外,如果将真、善彻底割裂开来,那么不同的对真的理解空间也将无限打开,会面临各种以真为旗号的对善的质疑。当善被理解为外在强制的“规训”,而非人的自我实现,还有可能理直气壮地要求善吗?当然,在现代语境下,面对着真对善的质疑,对善的强调者自身也要反省,对善的理解是否失去了真的维度,而仅仅是某种主张?对善的实行是不是成了强制?对善的主张有异化为“伪善”的可能,完全可能出现“人人都在‘行善’,而‘恶’却周流于天下的悖论”(56)格非:《雪隐鹭鸶》,译林出版社,2014,第114页。。
此外,对真的高扬者也需反思,高扬的真究竟是什么样的真?真是不是只能是“现实欲望的率性真机”(57)同上书,第125页。?在主张“真欲望”时,是否需要思考“真欲望”对“主体”一定好?纯粹的任情能否构成“善好”(此“善好”可以剥离儒家或任何道德主义的立场,而仅从自我保存的角度理解)?当真被主张到极致时,会不会出现某种形式的“妄”?“我”以为的真会不会也是被某种观点(比如“消费主义”)建构起来的,而“我”完全“无思”?
孟子以诸多形式对善进行论证,很难完全归于社会物质力量构成某种社会文化心理的过程,孟子的论证有其普遍性诉求,而此种普遍性是包含了真与善两重维度的。当孟子用“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去论证人性善时,他着力要排除的就有因为要誉等私欲导致的“伪善”,而格外强调“本心”自身的力量带来的善与真的合一。这种对于人性理解的方向,或许应成为今天重新思考善的重要维度。这,或许也是我们今天再去看待孟子人性论辩需要打开的思想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