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髦的身份:时尚体系中的他者议题研究评点
□熊亦冉
【导 读】 身份认同是时尚社会建构的核心。首先, 作为身体实践的时尚往往面临着苗条的暴政与身体的规训, 进而蕴含着对现代主体与虚拟他者的反思; 其次, 时尚对女性气质和男性气概的形塑生成了极为复杂的性别政治, 并在亚文化的语境中再现性别化的多重凝视; 最后, 本土时尚与全球视野的关系构成了现代时尚体系的重要议题之一, 跨东方主义成为了重申国族认同与异域他者的全新视角。由此, 伴随着他者研究的三重面向, 时尚始终处于身体、 性别、 国族相互交错的张力之中。
时尚与衣着不断讲述着诱人的时尚故事, 而作为 “社交皮肤”(social skin) 的身体则通常意味着一种赋权行为。无论时尚体系中的身体、 性别和亚文化如何变迁, 这些议题都旨在借助时尚实现自我认同以及他者的建构。正如文化历史学家伊丽莎白·威尔逊(Elizabeth Wilson) 所言, “作为行为艺术的时尚是这种矛盾心理的载体; 时尚大胆地表达了恐惧和欲望”[1]。社会身份及其心理机制的生成与传达构成了时尚的关键所在。在这一意义上,时尚既是个体的也是社会的; 既是潮流与服饰的物质对象, 又是文化共同体的社会行动; 既彰显了静态的符号学分析, 又展现了动态的社会学阐释。因此, 时尚充当了协商身份机制的视觉媒介, 从虚拟的他者到性别化的他者, 再到异域化的他者, 基于自我认同的时尚身份持续演绎着生动的着装辩证法。
一、 苗条的暴政与虚拟的他者
时尚在本质上是赋予服装以某种意义的交往实践, 并在特定的语境中通过“行为” 产生效果。换言之, 它是一种既基于着装互动又朝向他者预期的社会行为方式。在时尚中, 作为对象的服装始终与历史情境、 社会关系和身体本身密切相关, 着装因为这样的身体实践而具备了生命力。传统研究通常关注时尚与社会历史的关联, 进而将其视为对社会文化背景的特定表达或客观证据, 在这一意义上, 服装具备了惰性的物质特征。然而, 从乔安妮·恩特维斯特尔(Joanne Entwistle)的开创性工作开始, 时尚的身体研究就不再局限于服装的物质维度,而是将其置于社会情境的框架中予以阐释。[2]穿衣的身体时刻暴露于社会之中, 因此不能脱离身体行为而孤立地谈论着装功能。换言之,时尚问题就是身体问题, 社交互动就是着装互动。对此,FatFashion:TheThinIdealandtheSegregationof Plus-SizeBodies(《大码时尚: 苗条的理想与大码身材的分离》) (2021)考察了与身体密切相关的大码时尚现象, “大码时尚” 实际上充当了一种逆喻, 因为肥胖和时尚显然是一对极具矛盾的概念, 这也反向指认了时尚与苗条的关联性。只要大码服装孤立于常规时装周 (Full Figured Fashion Week/FFF Week) 之外, 它在时尚体系中的边缘地位就将得以持续固化。肥胖的身体并非因为天生丑陋而招致排斥, 而恰恰因为这种排斥本身才使其显得不够“时尚”。
事实上, 身体是社会互动的基本工具, “造型” (look) 的概念实则远远超出了消费者购买、 拥有和使用的服装之总和。除了服装, 造型还包括妆容、 发型、 身体操控 (节食与整容)、 身体装饰(文身) 和身体规训(姿势与体态) 等诸多方面。它是个体针对他者而予以 “呈现”的外表, 在本质上源于与他者的相遇及预期。这种预期不仅是审美的,更是存在性的和关系性的。造型的这种关系性还意味着“它不仅仅是一个图像, 它还是一个计算的对象,是一种不断加工、 塑造、 竞争、 表演的东西, 是一种……可以识别的东西, 但又不断以新的形式被消解和重新稳定”[3]。这正是外形如此重要的原因, 它以衣着—身体复合体(clothes-body complex) 的形式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中译本《美丽的标价: 模特行业的规则》 (2018)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考察了外形的民族志以及魅力的隐形标准, 并检视了“颜值” 在时尚模特群体中得以定义和筛选的复杂过程。
尽管造型是一个极富层次的概念, 但由于体型(size) 的直观可见性, 它几乎构成了外形的决定性因素。西方时尚体系将体型分为肥胖、苗条或正常三大类, 同时借助大规模服装生产的尺码分级技术建立了相应的阈值。但这种分类显然固化了描述性、 价值性和规范性的差别,普遍的价值判断将苗条置于积极、好看的属性中, 肥胖则与之对立。这由此构成了对肥胖或超重的污名化, 胖成为一种身体 “原罪”。因此, 体型构成了主体嵌入时尚文化及其价值体系的重要方式, 并以此锚定了主体与时尚的关系。穿衣的身体成为价值判断的媒介, 社会共同体通过共享时尚造型或穿衣行为而明确地分享或隐晦地展演。换言之, 个体将身体调整至理想化样态的过程, 实际上也就是内在地确认自我与他者、 理想与现实身体差距的过程。此外, 身体理想并不单纯意味着个体的完美标准, 而是预示着得以持续构建和培养的共同理想,即文化标准。因此, 经验的一致性形塑了文化的本质特征。文化不仅对行为方式施加影响, 而且迫使个体调整行为以适应规范。
既然身体的理想并非单一而是复数的, 那么美的理想则更为突出地体现为一种高度变动的价值观。女性主义理论一直试图表明, 美的价值观具有极大的暂时性。在内奥米·沃尔夫(Naomi Wolf) 看来, 这恰恰构成了“反对女性进步的政治武器”[4]。女性美的理想之所以变成了一个神话, 正是因为它构建了一种虚假叙事, 并充当了父权社会用以征服女性的工具。现代经济依赖于女性身材的神话, “苗条的暴政”(tyranny of slenderness) 与其说源于时尚需要, 不如说源自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将女性置于一种永远不完整、不完美和不满意的状态之中, 进而阻碍了她们挑战男性政治和经济霸权的意愿。FatFashion一书认为,女性在“苗条内化” 的趋势下越发陷入了“苗条的暴政” 和“纤瘦的崇拜”。着装的作用在于隐藏脂肪,因为外形在本质上充当了衣着—身体的复合体, 它总是掩盖并修饰着身体及体型的呈现。而“超重” 仍然意味着反脂肪, 这一概念的存在本身就暗示着某种合理体重的限制范围, 任何人都不能超过这一明确界限, 这种委婉的说法反而确认和强化了身体偏见。
与此同时, 我们对于身体、 他者和自我意识的认知已然步入了一个全新阶段。正如TheArtificialBody inFashionandArt:Marionettes,Models andMannequins(《时尚与艺术中的人造体: 提线木偶、 时装模特和人体模型》) (2016) 一书所表明的那样, 在人文主义时期, 匹诺曹(Pinocchio) 想成为人类; 而在所谓的后人文主义时代, 人类却渴望成为匹诺曹。在这种“真实” 和“建构”的转变过程中, 想象的他者经历了持续的内化, 人为的自我逐渐被折叠进自然的身体之中。从机器人到机械玩偶, 以人类形象构建的人造身体始终扮演着复杂而微妙的角色。在后现代语境中, 自然的身体开始被一系列虚拟的原型所取代, 玩偶充当了主体最为忠实的镜像伴侣。这一现象最初在戏剧中得以充分体现, 即主体是否只是一个复杂而残酷的幻象, 以及演员在多大程度上被视作剧本的外壳或傀儡。康德早在《实践理性批判》 中就曾探讨过类似的困境: “只要人类的本性维持它现在的所是, 那么人类的举止就会变成单纯的机械作用, 在那里就如在傀儡戏里一样, 一切表演得惟妙惟肖, 但是在人物形象里面不会遇见任何生命。”[5]就自在之物而言, 主体只是一种机制; 而在事件和现象世界中, 主体则是更大的原因流以及物种之内在性的一部分,主体的自由(判断力) 被困于两极之间并由此构成了无法逃脱的僵局。[6]
现代主义与玩偶的关联性还体现在它试图探索人类意志及自我意识的极限, 并聚焦于人类能动性的终极边界。对自由的现代主体而言,玩偶作为人造的他者并未被驱逐,而是代表了自由的最大可能性, 以此承载着主体面对后现代及其不确定性所产生的恐惧心理。在自我定位以及自由主体的形成过程中, 最经久不衰的神话就是皮格马利翁的故事, 他为自己的雕像带来了生命,但也同时预示着主体终将死去的诫喻。到了18 世纪, 主体与人造身体的现代演进逐渐呈现为两种极为重要的趋势: 其一是作为技术进步的自动机, 以及在生物和智力水平上模仿人类的挑战; 其二是对于情感智力 (affective intelligence) 问题的提出, 进而主张现代主体性更多的是一种负担而非优势。对时尚而言,其关键在于时装模特如何延续了玩偶与自我的关联。时尚模特的出现使得人造身体、 自然身体以及理想身体之间的界限越发模糊, 身心分离抑或身体类型化和风格化的趋势也日渐凸显。然而, 在此情境之下,人们反而希望自己装扮成日本漫画中的芭比娃娃, 抑或沉迷于后现代的cosplay 亚文化, 从而构成了一个奇妙的循环: 从玩偶模仿人类到人类想成为玩偶, 后者彰显了对技术身体最为反常的美学庆典。
作者在书中指出, 我们不应再把玩偶看作主体自身之外的东西,它与主体的差异仅存在于程度上而非性质上。[7]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包括医美和整容在内的生物医学强化了对最佳身体状态和容貌形象的质疑, 即究竟什么构成了一个自然的身体, 而并非人造的“完美” 身体, 这由此呼应了作为西方后人类身份隐喻的赛博格概念。唐娜·哈拉维曾在《赛博格宣言》 中指出, 赛博格作为有机体和控制论装置的混合状态, 对西方社会定义的人类本体论及其纯粹性构成了质疑。[8]但笼罩于这一选择之上的问题在于,它究竟是对人类境况的“改善”, 还是充当了对原始形式的压制。既然所有的自然都是一种建构, 那么借助暴露“人性” 的可塑性, 赛博格超越了西方现代性、 父权制和殖民主义所建立的二元框架, 且不再涉及人类、 技术和自然的等级, 以实现所有这些范畴的依存性和渗透性。因此, 该书旨在承认一种新的秩序,在这一秩序中, 人文主义的来源和目标都将得以重新配置。正是由于人类始终在调适自我的身体, 主体对于身体神话的拥趸才呼之欲出。尽管充斥着“后人类” 和“人类世”这样的新词, 但人造的身体与自我认知的关联实际上早在现代主义诞生伊始就已投下了阴影。
如果将时装模特及时尚玩偶视作某种时尚装置的话, 那么这种基于身体、 空间和表演的表现形式将极为生动地呈现出它与当代艺术的微妙关联。这也正是FashionInstallation:Body,Space,andPerformance(《时尚装置: 身体、 空间和表演》)(2019) 所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19世纪末, 随着时装设计师查尔斯·沃斯(Charles Worth) 开始起用真人模特, 人体模特的展示功能就沿用至今。在模特走秀的过程中, T 台相当于雕塑作品的底座抑或绘画的框架,它充当了具有分隔性能的中立空间,用以理解被展示之物。在这一意义上, 它与装置艺术是相通的。“装置” 一词通常用于当代艺术, 指的是某种使用或占据空间的形式。物的“底座” (plinth) 立场暗示了一种去语境化的理解方式。换言之,底座要求观者忽略所有物的外部阈值, 只关注物本身。与时尚诉求相似的是, 装置同样意味着空间的激活, 正如时尚将时装置于底座 (T台) 之上予以重新定位并赋予其特殊的抽象力量一样, 时装表演的关键恰恰在于实现场所及其相遇的可能性。此外, 装置还旨在呈现物对感性秩序及其稳定性的颠覆。20 世纪60 年代以来, 装置艺术与观念艺术共同达成了这样的诉求——将艺术从商品化的暴政中剥离, 并将其置入观念领域以激活观者体验。这同样重建了艺术之“物性” (objecthood), 正是这种物性真正拉近了艺术与时尚的距离。以此为基础, 该书详尽展现了身体与空间的张力关系, 并将装置视作理解现代时尚体系的重要方式, 以呈现时尚在符码、图像及意识形态叙事中的复杂面貌。
二、 凝视的目光与性别化的他者
数字文化变迁为重审女性身体和性别政治提供了新的动力。自1975 年以来, 关于劳拉·穆尔维凝视理论的学术研究逐渐得以涌现, 文集RevisitingtheGaze:TheFashioned BodyandthePoliticsofLooking(《重访凝视: 时髦的身体与观看的政治》) (2020) 就对与之相关的学术脉络展开了详尽回顾。它一方面描绘了穆尔维研究聚焦于电影媒介的特殊性, 另一方面又指出这种视觉愉悦和奇观政治同样适用于时尚领域。视觉与触觉的交织性使得时尚不仅呈现为一种美学或表征, 而且更为深切地表达为一种触觉体验。其中, 论文The Ambient Gaze: Sensory Atmosphere and the Dressed Body (《氛围凝视: 感官氛围与穿衣的身体》)借鉴了梅洛-庞蒂关于感官知觉的描述, 将穿衣的身体及其感官理论化,借助“氛围凝视” 这一概念为时尚的触觉研究提供了新的洞见。
这由此关系到电影理论中日渐兴起的“触觉” 屏幕研究。肇始于文艺复兴的视觉中心主义表明, 视觉通常被视作一种“距离” 而非触觉, 而后者恰恰预示着身体和感知对象的直接接触。视觉中心主义随后遭到了女性主义理论家的批评,如露西·伊利格瑞认为它倾向于控制被凝视的对象, 身体作为知识的对象由此招致观察、 掌控和侵占。[9]这种对感官和触觉的重新评价也导致了认识论上的转变。劳拉·马克斯(Laura U.Marks) 在其开创性的著作《电影皮肤》 中曾提出“触感影像”及“多感官知觉” 的概念, 并以艺术史家阿洛伊斯·里格尔的“触觉图式” 为基础, 指出触觉发生于“眼睛本身的功能宛如触觉器官发挥作用” 的地方, “触觉倾向于在物体表面移动, 而并非陷入幻觉深度, 与其说是区分形状, 不如说是识别纹理”, “它更倾向于轻触(graze) 而非凝视(gaze)”。[10]因此, 触感视觉(haptic visuality) 强调了视觉的具象性, 这在该书所收录的莫·索普(Mo Throp) 和玛丽亚·沃尔什(Maria Walsh) 关于视觉和触觉的对话中也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2016 年,i-D杂志发布了“The Female Gaze Issue” (《女性凝视问题》)(No.344), 并指出“在i-D杂志 36年的历史上, 我们第一次赞美女性镜头的力量, 并始终与女性摄影师保持合作。……以发现当今女性看待自身的多重方式”[11]。不过, 女性观众仍然可能陷入一种男性化的观看方式, 并非得以逃脱与摄影镜头相关的阳具中心主义。[12]对穆尔维来说, 男性凝视是父权社会心理沉迷 (psychical obsessions) 的一个隐喻: 我们可以在主体及其被塑造的社会形态中分解魅力模式。[13]但本书超越精神分析视角的一个重要动机在于, 需要在对观看者的描述中觉察到性别之外的其他权力轴。因为女性并非单一轴线的性别范畴,而是需要经由格奥尔格·齐美尔所定义的“交叉社交圈” 的复杂映射,这也是本书所强调的凝视理论及其交叉因素的重要影响所在。在视觉文化中, 自拍主题对凝视的性别政治进行了重要干预。对于女性自拍者而言, 自拍被理解为“一种激进的政治赋权行为: 一种反抗男性主导的媒介文化对女性生活和身体迷恋及压迫的手段”[14]。这也呼应了数字女性主义的特点, 即以数字媒介的形式强化自我表征与性别规训。在本书中, 学者道恩·伍利 (Dawn Woolley) 还揭示了一种基于自我关注的“解剖式凝视” (dissecting gaze),并指出图像共享的激增放大了恋物凝视或过度聚焦, 从而塑造、 利用并重新赋予了性别身份以价值。
女性气质的塑造无疑是女性主义理论的核心议题。1963 年, 贝蒂·弗里丹 (Betty Friedan) 曾表达出对“女性奥秘” (feminine mystique)的担忧, 进而指出女性的困境在于“女性奥秘中隐含的女性与人性之间的误判”, 因为二者显然是相互排斥的。[15]因此, 女性主义学者们认为,将女性塑造成孩子气的形象将会固化两性之间的不平等, 女性既然充当了所谓的孩子, 那么就自然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成年人, 也就更容易遭遇差别对待。与前文所提及的“第四次浪潮” 或“数字女性主义”相对应的是, 女性在时尚媒体中仍被持续地塑造为童真气质。Picturing theWoman-child:Fashion,Feminism andtheFemaleGaze(《图绘轻熟: 时尚、 女性主义与女性凝视》) (2021)试图揭示的正是媒介话语中的女性赋权与轻熟气质 (woman-child) 之间的悖论, 这尤为鲜明地体现于欧洲时尚杂志 (1990—2015) 对女性轻熟形象的类型化。该书首先对早期女性主义的“虚假普世主义” 展开了批判, 后者囿于性别二元对立而难以察觉不同女性群体的权力差异, 这也正是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屡受诟病的原因所在。
PicturingtheWoman-child进而指出, 尽管性别研究被赋予了分析的优先级, 但这仍然需要用复数形式指代轻熟的女性特质, 以此强调女性身份的交叉性。这也意味着女性主义将以多元化的形式阐释女性差异, 并重新关注性别与其他身份轴的交叉性。以朱迪斯·巴特勒对性别二元结构及其复杂性的分析为前提,该书进一步考察了权力机制与女性话语的概念化, 进而将其置于福柯意义上的权力关系网络之中予以阐释。女性主义的发展始终伴随着时尚行业对女性理想的形塑与规范,而这些理想反过来又被女性内化而实现了自我规训。概言之, 该书主要关注两个关键的研究议题: 其一涉及轻熟气质的意义及其演变历程;其二旨在探究轻熟对于英国当代女性可能产生的吸引力。“woman-child”(轻熟) 一词并不意味着女性在本质意义上更加接近童真, 相反, 它仅仅充当了一种概念的简称, 即轻熟的女性气质通常出现在对各阶段女性的重叠叙述中, 其关键在于阐释童真与女性内涵相结合的方式、 少女气质(girl-childhood) 与女性话语交叉重叠的方式, 以及这种气质得以复制和强化于成年女性身上的方式。
尽管此前已有学者关注到女性特质与童真气质的复杂关联, 如欧文·戈夫曼在《性别广告》 中对模特气质与姿势关联性的讨论, 但该书着重研究了21 世纪头20 年出现的新一波轻熟女性特质, 进而将其细化为四种分支类别: 浪漫的轻熟女性气质 (the Romantic woman-child)、蛇蝎美人(the femme-enfant-fatale)、萝莉风 (Lolita style) 以及纯欲风(Kinderwhore)。浪漫的轻熟气质呈现了孩童般女性特质的杂糅与转译,这与女性气质的话语内涵相一致。而蛇蝎美人则构成了对传统女性气质的颠覆, 作者借助穆尔维的“好奇” 概念详尽剖析了女性凝视的赋权潜力。而当代时尚摄影对于萝莉风的挪用实则刻意排斥了母性, 这由此表明了时尚行业对于划分少女(girlhood) 和熟女气质(womanhood)的执着, 轻熟气质的反叛和时尚逻辑永不满足的消费者幻梦达到了完美契合。最后, 对20 世纪90 年代兴起的纯欲风摄影而言, 明星科特妮·洛芙充当了最为典型的代表。这表明轻熟的女性气质将再次戏仿规范女性气质的固有矛盾, 比如处女/妓女的二分结构及其演化逻辑。但正如巴特勒所言, 模仿本身并不具有颠覆性, 语境和接受才是有意义的颠覆应具备的双重决定因素。[16]通过对不同轻熟风格的时尚案例分析,该书梳理了时尚形象、 性别理想以及轻熟女性气质之间的关联, 并尝试以接受研究和视觉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阐释时尚摄影的类型及其多样呈现。
在女性气质的研究之外, 对男性气概的探讨则显现出了极为特殊而微妙的性别展演, 这在运动潮鞋亚文化中体现得尤为明显。Sneakers:Fashion,Gender,andSubculture(《运动鞋: 时尚、 性别与亚文化》) (2016)将运动潮鞋视作性别差异及其复杂化的重要表征, 并以民族志的方式重现了潮鞋亚文化中的男性特质及其建构过程。运动鞋充当了炫耀性消费的一种潜在表现, 只有圈内人能够辨识并分享意义, 这正是亚文化群体的核心特征所在。该书重点论述了潮鞋爱好者如何在虚拟和物理空间中构建非正式的网络社群,以及潮鞋狂热如何通过圈层内的攀比而得以复制、 传播与提升等核心问题。与此同时, 作者还将潮鞋的收藏、 狩猎和交易视作极具特殊性的社会现象, 因为正是这些环节最终推动了潮鞋亚文化的成型及转化。而在早期的青年亚文化研究中, 越轨和反抗构成了一对关键概念。相较于传统以主流—抵抗为特征的亚文化, 尽管当代青年文化仍在表达反叛的政治取向, 但风格本身的抵抗潜力似乎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对亚文化“本质上” 的颠覆其实只是一种幻觉。[17]43对于潮鞋亚文化而言, 第一波潮鞋现象起源于有色人种, 是少数族裔青年反抗美国主流社会的结果。第二波浪潮始于1985年Nike Air Jordan (AJ1) 的发布, 这款鞋改变了亚文化仅限于地下流行的境况, 时尚把关人的功能从收藏者那里转移到了球鞋行业。第三波浪潮则更多地表现为以社交媒介为沟通工具的买家互动。
其中, 亚文化本身的性别偏见是显而易见的, 运动潮鞋爱好者收藏和穿搭的过程即创造和扮演男性角色的社会过程, 女性在运动潮鞋亚文化中往往处于边缘地位。运动鞋的品牌修辞是材质性能、 自我认同和美学关注的融合, 而运动鞋语言则主要由行动导向的符码(如Nike 广告语“Just do it”) 构成, 以此激励穿着者积极行动, 这些都强化并维持了男性对女性统治的结构性因素。此外, 运动潮鞋也更加符合男性“炫耀性低调” (conspicuous inconspicuouness) 的时尚心理, 始于19 世纪英国摄政时期花花公子的自我塑造模式仍在发挥作用。细节成为决定性的因素, 服装成为目的本身, 即“无须掩饰的本真性” (unapologetic authenticity) 才是真正的男性气概, 这也从另一层面强化并再现了男性霸权的观念。[17]89中译本《男装革命: 当代男性时尚的转变》(2020) 同样聚焦了男性气概及其现代生成这一议题。该书分析了媒介在塑造男性时尚中的作用, 以及男性气质的霸权叙事如何在流行话语中得以显现等文化议题。从20 世纪60 年代的“孔雀革命” 到80 年代的新浪潮美学, “理想” 的男性身体及其演变进程同样也是时尚设计师不断重塑性别观念的过程, 这些无疑为性别操演、 亚文化以及酷儿时尚的研究提供了更具洞见的视角。
三、 全球化的视野与异域化的他者
印度人类学家阿琼·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 曾在其著作《消散的现代性》 中论及时尚的概念,并指出“所有消费的社会组织形式好像不外乎以下三种模式的某种结合: 禁令、 禁奢令和流行时尚”[18]。在这一意义上, 时尚可被视为服装消费的模型, 并以此激活了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所谓的 “身体的技术”。FashionasCulturalTranslation:Signs,Images,Narratives(《作为文化翻译的时尚: 符号, 图像与叙事》)(2021) 以阿帕杜莱的“景观” 和维基·卡拉米娜 (Vicki Karaminas) 的“时尚景观” (fashionscapes) 概念为起点, 探讨了时尚现象的全球视野,以及它在不同社会场景和文化分析中彰显的多元性与复杂性。作者认为“翻译” 概念在本雅明意义上呈现为一种实践, 这种实践将语言的异质性转变为一种可延伸至更高、更纯粹语境的机会, 进而超越了对主题本身的传递。该术语在不断转译的过程中图绘了时尚的愿景, 而时尚又在成衣模式的基础之上强化了主体对身体的 “翻译” 和伪装,即视觉在本质上表现为社会意象投射及建构的复杂机制。从本雅明的时间概念出发, 时尚首先被视作从现在返归过去的“虎跃”, 它以体系的形式生成了一种特定叙事, 并依次建构了差异性的空间, 由此演变为基于文化和符号间性的转译。
作为文化、 生产和象征体系的时尚与全球视野的辩证关系始终构成了时尚理论的核心线索之一。按照萨义德的说法, 东方主义应被视为欧洲中心主义对非西方社会的文化刻板印象。对此, 亚当·盖奇(Adam Geczy)引入了 “跨东方主义” (transorientalism) 的概念, 以“摆脱东方和西方更为二元的逻辑, 以及 ‘东方’一词所暗含的谴责。它提供了身份的移动性, 并预测了不断变动的边界”[19]5。这一术语保留了更具意识形态波动性的“东方主义”, 但其内部蕴含的异域凝视并不会集中于某个特定方向, 而是呈现为一种复杂镜像, 主体通常会将这种凝视规训于自身并重新东方化 (re-Orientalized)。因此, 作为一个极度不连贯的概念, 东方更多地包含一种隐晦感觉, 而并非指称某个有形地点。异国情调的诱惑也由此表征为危险的未知, 这种未知在某种程度上极易被升华为一种现实隐喻, 这正是东方主义批评的关键所在。
作者指出, 东方主义实际上是对文化反复重申的指认, 这种动态在艺术、 时尚和电影中都体现得极为明显。正如周蕾的 “视觉主义”理论所暗示的那样, 文化差异性在视觉特征中具有压倒性的根基, 这表明种族更多是一种建立在图像分类基础之上的任意术语, 并以此影响了阐释与建构意义的方式[19]14。东方主义的空间保持着彼此不同的独特品质, 它构成了一种多维度、 跨文化的居间性 (in-betwenness), 这突出体现在本书第五章对于中国风的考察与剖析。此外, 该书还对后殖民主义中的“混杂性” 概念提出了质疑。尽管这一概念重新融入了身份的多样性, 但这种多样性仍然笼罩在 “已知的未知” (known unknowns) 这样的异域谜题中。因此,跨本土性(trans-indigeneity) 对很多艺术家来说仍然构成了协商、 指认抑或抵制其身份归属的手段之一,而跨东方主义的概念则以想象建构的方式再次介入了这种变革。
由此可见, 时尚与非时尚的二分法在本质上仍是一种身份认同的神秘化, 它迫切需要破除对传统与现代、 本地与全球、 西方与非西方的僵化二分。对此,ModernFashion Traditions:NegotiatingTraditionand ModernitythroughFashion(《现代时尚传统: 以时尚协商传统与现代性》) (2016) 重点关注了全球时尚体系中的诸多悖论, 从而质疑了欧洲时尚作为现代体系之起源的合法性, 抑或非西方时尚仅仅是全球化的最新结果这样的论断。作者认为19 世纪和20 世纪早期以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致使西方文化占据了等级制优势而对时尚下了定义, 进而使得欧洲资产阶级将潮流的话语权凌驾于非西方时尚之上, 后者往往只能沦为静态的异国情调, 充当了霸权叙事中被强行构建的文化他者。这由此构成了一个极为有趣的悖论:当非西方设计师利用其自身的文化遗产作为灵感来源时, 它通常被视为“传统”; 但当西方设计师融合其历史文化时, 它被自然地归为一种“时尚”。该书还援引了莱斯利·拉宾(Leslie Rabine) 的观点, 认为 “传统” 可能是从殖民话语中遗留下来的最具问题性的术语。[19]10与其说传统是对过去一成不变的隐喻, 不如说它是全球趋势和创新动态的最新融合。异域的影响越大, 就越需要对本土时尚进行创造、 定义和分类。正如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Eric Hobsbawm) 所强调的那样, “发明传统本质上是一种形式化和仪式化的过程, 其特点是与过去相关联, 即使只是通过不断重复。创造此种仪式和象征体系的确切过程尚未被史学家很好地加以研究”[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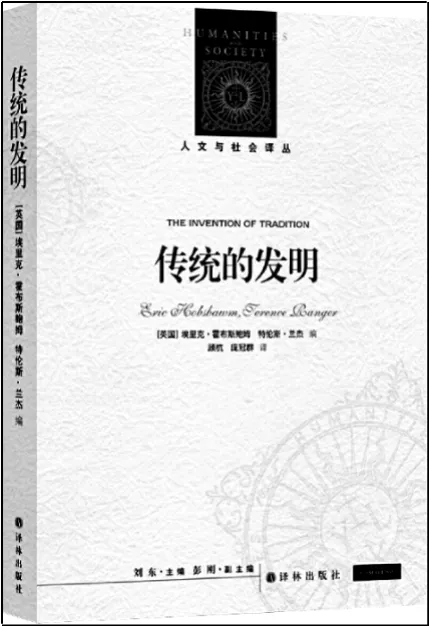
对于后现代而言, 匿名性与不确定性越明显, 对于本真体验及其文化归属的追求就越强烈。在这一意义上, 现代性是传统的催化剂,而现代性所持有的自反特征又导致了确定性的终结。对时尚来说, 无处不在的现代性持续地重塑过去以发明传统, 从而引发了全球与本土互为建构的悖论关系。对此, 中译本的《巴黎时尚界的日本浪潮》 提供了从反向考察东方主义的绝佳视角。尽管以时尚之都闻名的巴黎实现了对高级定制、 半定制和高级成衣的结构化分类, 并以此构建了层级森严的把关体系, 致使非西方设计师很难介入其中。然而, 一些极具影响力的日本设计师(如川久保玲和山本耀司) 仍然颠覆并反转了传统的法国时尚风潮, 并掀起了巴黎时尚界的日本革命。在日本设计师与法国时尚体系相互依存的同时,法国时尚的全球扩散机制仍然炮制并固化了新的身份认同, 并丰富和完善了前卫时尚的观念。
同样从全球视角出发,TheEnd ofFashion:ClothingandDressintheAgeofGlobalization(《时尚的终结:全球化时代的服饰》) (2018) 认为时尚体系的重要演变与新的发展模式密切相关, 这种体系性的根本变化甚至导致了“时尚的终结”。这一概念源自齐泽克的术语—— “末世”(End Times), 该词之所以是复数形式, 其原因在于“末世” 是在人口过剩、 资源紧张和生态威胁的背景之下、 在消费及传播的根本变化之中产生的。“末世” 时代也意味着神话和信仰的式微以及后民主时代的终结, 所谓的新秩序不过是一种更深层的脆弱秩序。时尚终结的另一个理论来源是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他在研究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时, 将其置于一种以历史进程论证其合理性的拓扑学之中。当精神发展到某种程度的自我意识而日臻成熟时, 艺术就需要转移至别处, 因为此时的艺术将沦为一个废弃的外壳。阿瑟·丹托在谈及这一终结论时指出, 由于流行艺术的介入, 艺术在20 世纪60 年代实现自我意识时就已经表明了它的终结。换言之, 艺术不再模仿生活, 而是表征了生活本身, 其内容和形式开始变得无关紧要。
19 世纪以来的“时尚终结” 轨迹同样复制了相似的线性进程: 传统时尚传播的涓滴模式逐渐被生产体系和媒介数字化趋势所打破, 就像不再模仿生活的艺术一样, 时尚也不再关涉阶级区分, 而是充当了表征本身。正如丹托所说, 艺术的终结并非艺术本身的终结, 而是叙事的终结, 这也正是时尚体系终结的原因。昭告这一终结的事件莫过于设计师迪奥的“新风貌” (New Look)系列(1947) 的推出, 时尚在此之后便“终结” 了, 因为它所预设的普遍标准以及支配身体的整体风格将不复存在。高级时装的质感与剪裁观念逐渐被打破, 时尚与阶级的关系也最终受到了后现代艺术的冲击。20 世纪60 年代末, 人们对时尚的态度发生了颠覆性的倒转, 因为嬉皮士宣称坚决反对时尚, 他们将自己定位为反从众、 反消费和反等级, 以拒斥时尚产业所推动的持续变幻的风格。书中援引了德国学者芭芭拉·温肯 (Barbara Vinken) 的观点, 认为“时尚的世纪已经结束:巴黎时尚的理念本身业已结束——即使是反时尚也无法拯救它”[21]。此后所出现的时尚已然是“时尚之后的时尚” (fashion after Fashion) 抑或“后时尚” (postfashion), 这种在“艺术的终结” 框架中探讨艺术与时尚的话语仍然呈现出了后现代意义上的理论批判视角。
而在时尚体系中, 最为核心的议题始终是趣味研究。再版后的The InventionofTaste:ACulturalAccountof Desire,DelightandDisgustinFashion,FoodandArt(《品味的发明: 对时尚、 美食和艺术中的欲望、 愉悦及嫌恶的文化阐释》), 从感官文化史的角度剖析了趣味的生成机制。作者在书中指出, 将恶习转化为美德是现代社会形成的关键因素: 虚荣被重塑为野心, 懒惰被形容为闲暇,对美食的饕餮之乐则被巧妙转化为对品味的精致洞察。鲍姆加登最初引入的“aesthetic” 一词源于希腊语“aisth-esis”, 指的是不依靠理性就能辨别多种感官品质及其统一性的能力。此后直到亚历山大·蒲柏和大卫·休谟的理论介入, 这种能力才最终演化为品味。这也由此解释了“趣味无争辩” 一直受思想家青睐的原因, 正是出于感觉被假定为自发的、 前理性的以及主观的特征, 这种结构才与个人主义的兴起、 感性的崇拜以及经验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此后对美的体验只能作为一种感知, 而并非某种客观品质。在品味被隐喻化的过程中, 它也逐渐与感官愉悦相分离, 恰如康德所阐释的审美无利害及趣味净化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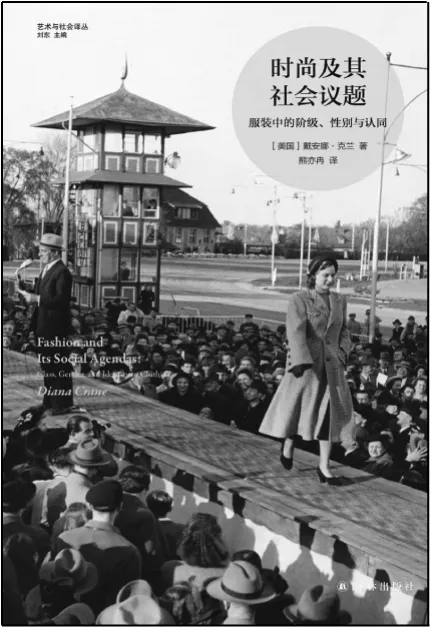
但该书的重心实则在于揭露康德判断力批判所蕴含的矛盾, 因此作者致力于考察各种“不纯粹” (impure)的品味, 认为这种“轻佻” 的趣味本身与后启蒙时代的自我塑造相关,进而充当了个人风格的载体。法国大革命时期最显著的成果与其说是追求平等的权利, 不如说是打造欲望的权利, “愉悦的艺术” 最终成为发现和完善个体情感的途径。19 世纪的拱廊街就已经见证了资本主义逐渐从基于自我规训和感官限制的生产方式转变为以自我放纵和感官愉悦为前提的展示—诱惑(如橱窗)模式。在这一意义上, 时尚的不可抗拒性正在于它能够以自我实现为名义, 煽动欲望并鼓励对奢侈的冲动, 尽管最终面对的是 “承诺尚未实现的空洞幻想”[22]。概言之, 品味的发明同时也是隐喻的发明, 在这一过程中, 品味的语义化对艺术感知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并最终促成了享乐在消费社会中的胜利。
总而言之, 正如中译本 《时尚及其社会议题: 服装中的阶级、 性别与认同》 (2022) 所阐明的那样,时尚与身体、 性别、 亚文化等社会议题始终处于持续互动的关系之中。19 世纪以来的现代时尚体系及其构建必须将其置于美学、 文化史和社会学的脉络中展开研究, 才能真正剖析时尚扩散模式的演变、 时尚性别霸权的生成以及全球化时尚转型等重要议题。此外, 与时尚相关的身体经验也最大限度地折射出了现代性的自反性特征, 并蕴含着对欧洲中心主义及其话语霸权的反思。因此, 时尚在经历了全球文化交错、重叠与杂糅的同时, 也更为凸显了审美建构的复杂性以及文化生产与身份认同的特殊性, 进而不断开启着更为丰富的探讨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