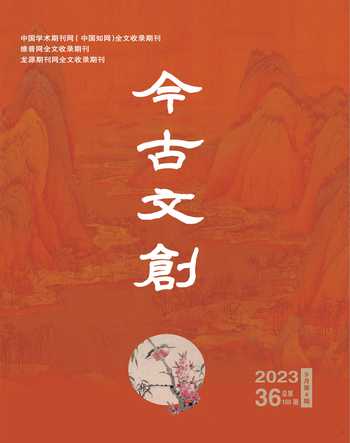河流叙事对国家民族形象建构之比较
谢欣然
【摘要】中国与美国都有大量与河流有关的优秀文学作品。作为“历史之镜”,这些文学作品也一定程度上记录了中美两国的民族历史发展脉络和国家民族形象建立的过程。本研究意在运用“河流叙事”这一独特的叙事视角,以中国作家徐则臣的长篇小说《北上》和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河流三部曲之一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为主要研究对象,因为其以河流为主要叙事空间这一共同点,对河流叙事如何建构国家民族形象这一问题进行平行研究。研究得出国家民族形象可从三方面进行塑造,分别是民族景观、民族人格与民族文化。又因河流地理空间对于两国社会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不同作用,中美国家形象存在着各自鲜明而迥异的特点。可以承认,文学作品中的河流叙事的确对民族形象构建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键词】河流叙事;民族形象;《北上》;《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河流空间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36-0035-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36.011
一、引言
自古以来,河流在孕育人类文明、国家区域形成和地域风俗生成等人类社会活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国家民族形象建构的过程中,河流地理空间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河流地理空间也为文学书写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来源和情感寄托。纵观中外文学发展历程,几乎每个孕育在大河之上的民族或文明都产生了大量的河流文学文本。本文对中美文学作品中典型的河流叙事文本——中国作家徐则臣的长篇小说《北上》与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做出比较,发现这两部作品创作通过描绘以河流为主体的特色乡土自然景观,塑造河流哺育下有民族代表性的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与命运,展现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认同,成功将所述河流打造为国家或民族形象的代言者。《北上》以中国古老的京杭大运河为背景讲述主人公“小波罗”沿河北上的旅途故事,通过连接运河人家的百年历史时空探寻运河与中华民族兴衰成败紧紧啮合的精神图谱。《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是马克·吐温以密西西比河为背景创作的“河流三部曲”之一,也是《汤姆·索亚历险记》的延续。这部作品被誉为“美国一切现代文学之源”,培养了马克·吐温丰富想象力的密西西比河奔流不息,连同美国共和党的初始岁月被一同写入小说中[1]。
本文侧重的“河流叙事”,是指河流文学作品中以河流为主要叙事空间和场景,跟随河流这一地理景观的空间构成与变化展开情节并提炼主旨,可纳入文学地理学范畴。中国学者颜红菲认为所谓“地理叙事”是指作家在叙事文本中使用一些艺术加工方式凸显地理空间,并由此展开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表达思想主题、勾勒出一幅社会百态的全景图[2]。本文即是延续这一观点,认为《北上》与《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两部作品都巧妙地完成小说叙事的“空间转向”,即叙事主角从人物故事转向地理空间。通过对比与分析,人们能对河流叙事方式得到充分了解,并区别由河流叙事体现出的中美国家形象差异,随着河流“溯源”,加深对中美历史文化发展脉络的认识,强化民族精神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
二、河流敘事与民族景观
《北上》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打破了寻常叙事空间的“静止性”,通过北上的河流与船只将沿岸的城镇与村落联系起来。因河流在地理空间的延伸,小说在情节的行进中向读者展示出随河流前进的文学地图画卷,每到一个新地理位置就有新的景色与世态风貌。这些景观又因其所在的社会历史背景不同,使得中美国家形象迥异而鲜明。《北上》中的京杭大运河沟通中国地域南北方各自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主人公沿河北上之旅也是中国民族景观的铺陈。《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则是沿河南下,两个孩子却没有想到他们逐渐深陷蓄奴区,其经历展示了当时美国南方的真实面貌。在这两部作品中,通过河流叙事展现的乡土风情从“自然景观”与“社会景观”的角度完成了民族国家形象的建构
(一)自然景观
在《北上》中,主人公“小波罗”从杭州出发,沿运河途经了一系列的城镇和村庄。作者根据叙事需要,对城市景观、乡村景观和运河景观进行了详细描述。对运河沿岸城市和乡村风景的详细描述突出了运河这一地理空间下的中国景观。小说以小波罗眼中的无锡景象开篇,空中俯瞰视角下的无锡风光尽收眼底:“房屋、河流、道路、野地和远处的山;炊烟从家家户户细碎的瓦片缝里飘摇而出……再远处,道路与河流纵横交错,规划出一片苍茫的大地。”[3]无锡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城市,长江、太湖与大运河生长成为城市流动的血脉,水路交错,人烟稠密,构成了中国现代城市的典型图景。作者又以谢平遥的视角写了氤氲着水汽的砖瓦与石板路、街巷里时而传来的吴侬软语、惠山清冽甘甜的泉水等,幽静清丽的江南特色自然风情一览无遗。
此外,小说还详细描述了小波罗一路过船闸的体验。船闸是河流体中体现中国智慧的独特景观,因自然地理特征不同,各路船闸处展现的河流景观亦有不同。无论是水情凶险、繁忙或宏伟壮观,无不展现大运河流动空间下独具特色的中国河流景观。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对密西西比河自然景观的描写大多来自作者在河边的生活经历。密西西比河清澈见底,宽广辽阔,充满生机。作品中多次提到主人公哈克躺在河边的所见所感。自由而自然的景色让哈克感到舒适和快乐。大自然的美让他着迷,他在岸上体验到了寻常世间难得的松弛与安定。马克·吐温融合自己的记忆,借哈克的眼睛再现了他心目中密西西比河的自由之美,也正是体现了美利坚民族将其对自由、民主和平等的理想寄托于对密西西比河的归属与赞慕中,密西西比河的纯粹天然之美更像是美利坚民族的精神桃源。
(二)社会景观
《北上》中从河岸景观转移到大运河本身,那些依托运河为生的底层人民的真实生活景象,更是是国家民族的缩影。《北上》写了运河上纤夫们的日常景象,因为常年辛苦的体力支出,拉纤的男人们黝黑而干瘦,却只能仰赖着承载全家生计的运河生意,甘于重复着悲苦的命运。纤夫的队伍里还有带着孩子来拉纤的女人,生活的操劳消磨了她们的女性特质,成为“纤夫娘”。纤夫与运河同在,纤夫就是行走在陆地上的另一条运河。这些劳苦民众与运河息息相关的生活延续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勤劳自强的传统美德,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历经磨难浴火重生的历史缩影。《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创作时的社会背景是西进运动完成,生产工业化带来效率的提升,进而日益演变为对财富的占有与追逐,许多人把获得金钱作为终极目标。可以说哈克在密西西比河上“出逃”的原因与河岸上日益污浊却无法摆脱的社会金钱关系息息相关。种族间的不平等也是他们南下蓄奴区后难以掩盖的社会事实。对黑人无意识的冷漠与歧视难以支撑其宣称的民主追求。马克·吐温通过哈克与吉姆在沿河南下的社会景观感触尖锐地展现那段历史的原本面貌,以暴露彼时美国社会存在的弊病与人性深处的险恶。
三、河流叙事与民族人格
通过阅读,本文发现两部小说中涉及大量与所述河流密切相关的人物形象对河流空间的感知与考察。民族国家的建立不是简单的区划与国家机器建设,而是更需要代表民族国家核心价值与精神的人物意识出现,故小说中的河流塑造的人物形象就是对宏观且有代表性的民族人格的象征性书写。同样基于不同的文明与历史发展进程,《北上》中的大运河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的密西西比河为我们呈现出鲜明的中美民族人格,一定程度上成为民族国家形象的代表。
(一)归属感与责任感并存的中华民族人格
徐则臣在末尾将小说中的各色人物稱为“运河之子”,可见运河对人物塑造功能之强大。总体来说这些“运河之子”分为两类,一是“异域参与者”,即从1901年开始的时间线索下以小波罗、马福德这对意大利兄弟为代表的人物群;二是“本土亲历者”,即从2014年开始的时间线索下以“谢望和、周海阔、胡念之”三位家族后代为代表的人物群。虽然他们在与大运河结缘的时间和原因大相径庭,但从他们身上能反映出中华民族人格的一些典型——归属感与责任感。
《北上》一书对运河书写的点睛之笔就在于“异域者”视角的引用。文中侧重写意大利人“小波罗”兄弟在运河北上之旅中的中国风俗体验和中国文化感受,生动形象地展现了“异域参与者”对运河和中国文化与精神的归属感,虽不是本土居民却因运河产生了与当时的本土中国人同样的中华民族人格。例如,小波罗在北上之旅的前半程以观光猎奇的心态看中国及运河,但当他受伤之后心态有了明显变化,对运河产生了特殊的情感。在弥留之际,小波罗深情地诉说他这一生对运河的眷恋和依赖,将他国的运河变成了自己的运河,并从运河悟出了生死之道:生死有命,无须强求。他认同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命哲学,可以说完成了中华民族人格的思想归化。八国联军侵华事件过去一百多年以后,到了21世纪,大运河的故事仍在延续,新生代的“运河之子”在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之际用自己的方式捍卫着运河前世今生的荣耀与辉煌,这是中华民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种使命感在守护大运河上的体现。谢望和希望通过影像和人物故事来记录和歌颂大运河,是运河故事的“讲述人”;周海阔热心于创办与大运河有关的小博物馆和连锁性民宿客栈,是运河文化的“传播者”;胡念之是专门研究大运河的考古学家,是大运河往日辉煌历史的“重现者”。这些人物群像对运河的守护即是对中华民族文脉的守护,他们或高尚或平凡的责任感是中华民族人格最精确的表达。
(二)崇尚自由与平等的美利坚民族人格
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河流叙事视角下,和河流同行的两位少年哈克和吉姆无疑是美利坚民族人格最重要的化身。
哈克是自由精神的坚定追随者。他不屑于学校和社会的管教与规训,不屈于父亲野蛮的暴力打压,不忿于封闭自锢、肮脏险恶的现代社会,只想追求理想意义上的精神独立。同时,哈克的聪慧与勇敢也给予他摆脱现状和逃脱危险的可能性。这是在哈克作为社会成员对自由的追求。哈克对精神层面自由的追求也表征着成长中的美利坚民族人格富有活力的一面。它既没有对自然和人类社会公认的的外在规则表示屈就与服从,又没有对人类主观能动性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在漂流旅途中,哈克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立的认知,努力摆脱陆地上污浊思想的同化,保持自我判断和选择意识的独立与自由。所以,哈克一直是作为一个探索的、成长的形象出现的。而密西西比河正是让这位少年的灵魂“野蛮生长”的空间,作为追求自由道路上永恒的陪伴者和栖息地出现在哈克的成长旅途中。
而吉姆,一个美国殖民历史背景下被拟出的少年形象,一度成为美国文学在种族主义思潮难以退却时期不敢触碰的逆鳞。他虽然身处被剥夺作为人的尊严与权利的泥淖中,但仍然在挣扎着从自然中汲取养分,从社会上“缺失”的文明里掌握了作为人应当具备的技能与经验,同时生出当下文明所难以涵盖的,对自然万物的敬畏之心。吉姆的不幸与哈克的冒险在其二人的旅途中是互补的,他更像是哈克的精神导师,引导哈克恣意追寻自由的精神走上正确的道路。他教会哈克以敬畏之心面对自然,以平等的态度对待生灵,进而以真诚的情感对待所有人,从而对哈克原本存有的白人中心主义的种族观念有所改观,使得二人在河流空间的“逃离”之旅成为民族人格塑造的契机。
四、河流叙事与民族文化
(一)近现代中华民族文化转型与复兴
从宏观上追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文化兴衰,从“锁国守旧”到“开眼看世界”,从“独尊儒术”到“新文化”强调的民主与科学和对儒学仁义道德的猛烈抨击,中国民族文化曾在难以承受的战争苦难和社会转型困境中走入迷茫之境,在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国民族文化亟须一场深度的转型与复兴。以运河文化为例,晚清时期漕运从式微到废止,标志着运河文化的没落。一方面由于河道干涸、改道、淤塞,兵匪河霸猖獗,战争频繁破坏,水运成本和风险越来越高;另一方面火车等陆上交通和海上航运快速发展,兼之清政府财政匮乏,漕政弊端日重,1901年清廷颁布废漕令,又裁撤相关机构及人员,结束了历代相沿的漕运制度,大运河的繁华也随之落幕。与之相关的系列产业和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命运都发生了重要改变。《北上》在描写运河风物的同时也透露着荒芜气息,展现出现代转型时期古老中国的老暮之气[4]。
然而,运河文化并未因此而埋没,大运河的生命力有如中华民族文化的生命力一样亟待重新发芽,破土而出。河流作为地理空间的意义在于,作为流动的时间的参照物,见证着时代环境变化,从而依托新一代运河人与运河风物实现文化转型。百年过后,运河故事的后代成为当前时代运河文化的追梦人,小说最后在大运河申遗成功的喜讯中落下帷幕,大运河获得了新生的契机。作为近代运河人的后代,谢、周、胡等人都是在充分挖掘运河延续下来的文化传统和其中蕴含的文化价值后实现了他的新生。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民族文化走过的复兴之路的缩影。
(二)现代美国民族文化认同的形成
美国文化与中国文化最大的差异在于,它不是在悠久的社会历史实践中积淀形成的,而是美国国家的奠基者、文学书写者以及财富追求者有意“创建”的结果,《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有意识地把美利坚民族风貌凝聚于河流,因此密西西比河对于美国文化认同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一定时间里美国被认为“没有文化中枢”,因为即便是在地缘,法律和政治上作为一个国家而存在,一个分散在无边无际的北美大陆的民族就像是从同一个体点散射出来的光线,难以聚焦的文化认同使得这些光线虽然存在,但热度已经消失[5]。
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叙述了哈克和吉姆、国王、爵士和其他人物在密西西比河上的漂流和冒险故事,在河流空间中培养了他们共同的情感和文化意识。在这部小说中,河流以一种现代的冒险精神使密西西比河充满活力,为新的文化身份阐明了其含义。它必须有足够的力量来抵制陈旧的观念,同时也要保护新的文化身份不受非理性潮流的影响。哈克和吉姆所经历的逃离、危险和成长象征着文化的进步和发展。小说以“冒险”为核心价值的精神体现可以类比“新边疆主义”精神在美国现代的具象性文化认同。密西西比河上发生的探索和冒险,与美利坚民族一代又一代开疆拓土的经历形成了内在的精神联系。正如哈克在河上面对未知的探索和漂流一样,美国的边界也在不断地在未知中打开,新的文化身份也在这样一个坚实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五、结论
本文根据中国小说《北上》和美国小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多角度、多侧面展示的“河流”这一宏大叙事主角,通过发掘其叙述主体性、历史传递性以及民族共同体的功能,集中阐释了河流叙事是如何建构国家民族形象这一关键问题。
中国是诗意的,包容的,绝处逢生的。河流不仅影响着本土居民的生活生产方式和价值取向,更展现着“河润万物”的包容性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外来居民经过河流文化的浸染逐渐产生对这一方水土的依恋和归属感,足以体现中华文化强大的影响力和包容性;中华民族是浴火重生的民族,中华儿女以面对潦倒贫苦的生活时艰苦奋斗的姿态和面对信仰危机时持之以恒的精神坚守,完成了百年来民族形象的崛起和民族文化的复兴。美国是探索的,进取的,开拓的。密西西比河的书写记录即是对美利坚民族成长过程的记录。无论是新兴阶级对流域中社会秩序的探索与尝试改变,还是民族共同体对流域附近国家疆土的开拓都构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美国形象。因为历史经验积淀尚不足,所以积极探索;因为不满社会现状,所以欲意改变,因为坚定富裕和强大的梦想,所以勇于开拓新领地。河流给文学创作以灵感,更具有时间和空间的双重身份,河流叙事的角度给本文研究國家民族形象提供了全新方向。
参考文献:
[1]Fadiman Clifton.The New Lifetime Reading Plan[M].New York:HarperResourse,1997.
[2]颜红菲.地理叙事在文学作品中的变迁及其意义[J].江汉论坛,2013,(03):33-36.
[3]徐则臣.北上[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
[4]蒋林欣.河流叙事与国族文化想象建构——以徐则臣《北上》为中心[J].扬子江文学评论,2020,(01):70-77.
[5]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开拓历程[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