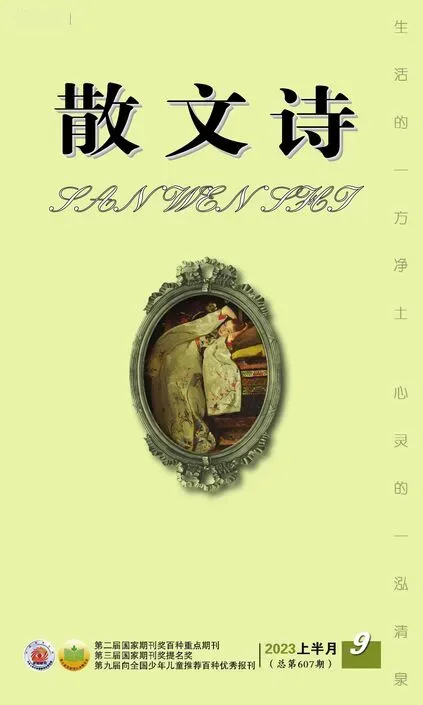散文诗的民族性文本写作初探(二)
◎黄永健
三 散文诗的非西方世界文化变体
其次,散文诗的民族性变异必然发生在非西方世界。在中国由于源远流长的骈体文的影响,散文诗传入中国之后极易被误以为是讲究形式美感的短篇散文或辞藻华丽的抒情小散文,而且在中国的散文诗坛确实也产生了一大批唯美浪漫带有古典人文情调的散文诗,朱自清、冰心、艾青、郭风、刘湛秋,以至当代台湾的张晓风《春之怀古》、许达然《瀑布与石头》 等大量作家的散文诗,影响很大,以审美现代性眼光加以打量,很难说是散文诗,实际的情形是,这些作品曾经入选许多经典散文选本,同时,也被当代的散文诗选本选中,试看张晓风①《春之怀古》:
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的:从绿意内敛的山头,一把雪再也撑不住了,噗嗤的一声,将冷面笑成花面,一首澌澌然的歌便从云端唱到山麓,从山麓唱到低低的荒村,唱入篱落,唱入一只小鸭的黄蹼,唱入软溶溶的春泥——软如一床新翻的棉被的春泥。
那样娇,那样敏感,却又那样混沌无涯。一声雷,可以无端地惹哭满天的云,一阵杜鹃啼,可以斗急了一城杜鹃花,一阵风起,每一棵柳都会吟出一则则白茫茫、虚飘飘说也说不清、听也听不清的飞絮,每一丝飞絮都是一株柳的分号。反正,春天就是这样不讲理,不逻辑,而仍可以好得让人心平气和的。
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的:满塘叶黯花残的枯梗抵死苦守一截老根,北地里千宅万户的屋梁受尽风欺雪压犹自温柔地抱着一团小小的空虚的燕巢。然后,忽然有一天,桃花把所有的山村水廓都攻陷了。柳树把皇室的御沟和民间的江头都控制住了——春天有如旌旗鲜明的王师,因为长期虔诚的企盼祝祷而美丽起来。
而关于春天的名字,必然曾经有这样的一段故事:在《诗经》之前,在《尚书》 之前,在仓颉造字之前,一只小羊在啮草时猛然感到的多汁,一个孩子放风筝时猛然感觉到的飞腾,一双患风痛的腿在猛然间感到的舒适,千千万万双素手在溪畔在江畔浣纱时所猛然感到的水的血脉……当他们惊讶地奔走互告的时候,他们决定将嘴噘成吹口哨的形状,用一种愉快的耳语的声音来为这季节命名——“春”。
鸟又可以开始丈量天空了。有的负责丈量天的蓝度,有的负责丈量天的透明度,有的负责用那双翼丈量天的高度和深度。而所有的鸟全不是好的数学家,他们吱吱喳喳地算了又算,核了又核,终于还是不敢宣布统计数字。
至于所有的花,已交给蝴蝶去数。所有的蕊,交给蜜蜂去编册。所有的树,交给风去纵宠。而风,交给檐前的老风铃去一一记忆、一一垂询。
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或者,在什么地方,它仍然是这样的吧?穿越烟囱与烟囱的黑森林,我想走访那踯躅在湮远年代中的春天。
张晓风这篇《春之怀古》 与朱自清的名作《春》 都可以当作散文诗加以界定,张文与朱文东方审美情调十足,是为共同点,不同点是一古色古香,一白话味醇厚,所谓古色古香,是说张晓风的这章散文诗带有文言的凝练老辣,同时融入白话文的语感(如关联词语联袂出没),所谓民族味醇厚,是说朱文脱胎于文言而将白话文的阴阳顿挫和音节节奏拿捏到位,两章散文诗都具有温柔敦厚的品性,画面感、音乐感十分强烈,在现代汉语读者之中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我们完全有理由认定他们是用现代汉语写作的优秀散文诗作品。如果我们从语言的诗化处理和审美感染力着眼,20 世纪80 年代作家张洁的散文名篇《我的四季》,甚至也可以看成是民族化的当代散文诗:
生命如四季。
春天,我在这片土地上,用我细瘦的胳膊,紧扶着我锈钝的犁。深埋在泥土里的树根、石块,磕绊着我的犁头,消耗着我成倍的体力。我汗流浃背,四肢颤抖,恨不得立刻躺倒在那片刚刚开垦的泥土之上。可我懂得我没有权利逃避,在给予我生命的同时所给予我的责任。我无须问为什么,也无须想有没有结果。我不应白白地耗费时间。去无尽地感慨生命的艰辛,也不应该自艾自怜命运怎么不济,偏偏给了我这样一块不毛之地。我要做的是咬紧牙关,闷着脑袋,拼却全身的力气,压倒我的犁头上去。我绝不企望有谁来代替,因为在这世界上,每人都有一块必得由他自己来耕种的土地。
我怀着希望播种,那希望绝不比任何一个智者的希望更为谦卑。
每天,我望着掩盖着我的种子的那片土地,想象着它将发芽、生长、开花、结果。如一个孕育着生命的母亲,期待着自己将要出生的婴儿。我知道,人要是能够期待,就能够奋力以赴。
夏日,我曾因干旱,站在地头上,焦灼地盼过南来的风,吹来载着雨滴的云朵。那是怎样地望眼欲穿、望眼欲穿呐!盼着、盼着,有风吹过来了,但那阵风强了一点,把那片载着雨滴的云吹了过去,吹到另一片土地上。我恨过,恨我不能一下子跳到天上,死死地揪住那片云,求它给我一滴雨。那是什么样的痴心妄想!我终于明白,这妄想如同想要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大地。于是,我不再妄想,我只能在我赖以生存的这块土地上,寻找泉水。
没有充分地准备,便急促地上路了。历过的艰辛自不必说它。要说的是找到了水源,才发现没有带上盛它的容器。仅仅是因为过于简单和过于发热的头脑,发生过多少次完全可以避免的惨痛的过失——真的,那并非不能,让人真正痛心的是在这里:并非不能。我顿足,我懊悔,我哭泣,恨不得把自己撕成碎片。有什么用呢?再重新开始吧,这样浅显的经验却需要比别人付出加倍的代价来记取。不应该怨天尤人,会有一个时辰,留给我检点自己!
我眼睁睁地看过,在无情的冰雹下,我那刚刚灌浆、远远没有长成的谷穗,在细弱的稻秆上摇摇摆摆地挣扎,却无力挣脱生养它,却又牢牢地锁住它的大地,永远没有尝受过成熟是什么一种滋味,便夭折了。
我曾张开我的双臂,愿将我全身的皮肉,碾成一张大幕,为我的青苗遮挡狂风、暴雨、冰雹……善良过分,就会变成糊涂和愚昧。厄运只能将弱者淘汰,即使为它挡过这次灾难,它也会在另一次灾难里沉没。而强者会留下,继续走完自己的路。
秋天,我和别人一样收获。望着我那干瘪的谷粒,心里有一种又酸又苦的欢乐。但我并不因我的谷粒比别人干瘪便灰心或丧气。我把它们捧在手里,紧紧地贴近心窝,仿佛那是新诞生的一个自我。
富有而善良的邻人,感叹我收获的微少,我却疯人一样地大笑。在这笑声里,我知道我已成熟。我已有了一种特别的量具,它不量谷物只量感受。我的邻人不知和谷物同时收获的还有人生。我已经爱过,恨过,欢笑过,哭泣过,体味过,彻悟过……细细想来,便知晴日多于阴雨,收获多于劳作。只要我认真地活过,无愧地付出过。人们将无权耻笑我是入不敷出的傻瓜,也不必用他的尺度来衡量我值得或是不值得。
到了冬日,那生命的黄昏,难道就没有什么事情好做?只是隔着窗子,看飘落的雪花,落寞的田野。或是数点那光秃的树枝上的寒鸦?不,我还可以在炉子里加上几块木柴,使屋子更加温暖;我将冷静地检点自己:我为什么失败,我做错过什么,我欠过别人什么……但愿只是别人欠我,那最后的日子,便会心安得多!
再没有可能纠正已经成为往事的过错。一个生命不可能再有一次四季。未来的四季将属于另一个新的生命。
但我还是有事情好做,我将把这一切记录下来。人们无聊的时候,不妨读来解闷,怀恨我的人,也可以幸灾乐祸地骂声:活该!聪明的人也许会说这是多余;刻薄的人也许会敷衍出一把利剑,将我一条条地切割。但我相信,多数人将会理解。他们将会公正地判断我曾做过的一切。
在生命的黄昏里,哀叹和寂寞的,将不会是我!
张洁的这篇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散文曾经打动过无数读者,至今在网上浏览,依然可以找到它的不同年龄段的崇拜者和追随者。通常,我们会说要把散文写得像诗一样美,而从不说把诗写得像散文那样美,因为为数众多的中国作家并不了解散文诗的审美现代性内涵,只是从形式上想当然地认为具有诗的表现特征(节奏感强烈、意象密集、象征、暗示、隐喻),篇幅不太长,以分段形式为外部标志的文本就是散文诗,以至于散文和散文诗的界限纠缠不清,张洁的这篇作品具有若干诗歌元素,如果将它选入散文诗集,也应无不可。
具有影响力和个性特征的散文诗文化中国变体,应以鲁迅、许地山以及当代台湾林清玄的创作为代表。我们认为,对于20 世纪中国现代文学来说,鲁迅的《野草》 是一个凸现中国主体性存在的中国化、东方化的现代文学文本。鲁迅的《野草》 是在中国特殊历史语境下,一个思想型作家试图以西方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来表现中国社会由五四运动的革命高潮转入低潮之际的感伤和颓废的时代情绪,它的内容是中国的和民族的。在20 年代象征主义思潮风靡中国知识界的话语氛围中,鲁迅《野草》 其现代意识的表现卓尔不群,比如其对现代人生存的荒诞感的揭示,以及这种揭示的深度比之于晚出了30 年的西方荒诞剧 《等待戈多》(Samuel Beckett 塞缪尔·贝克特)也不为逊色,其中名篇《影的告别》 和《过客》 所表现出来的荒诞感:缺乏目的,怀疑目的自身,都应视为鲁迅在现代历史境况之下,对生命的存在主义式的叩问。西方的荒诞感源于人在承认上帝之死后的终极追问,而鲁迅所处时代的荒诞感产生于旧的价值体系受到彻底拷问而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的间隙,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当时的心灵困局,它和西方人面临上帝之死而产生的荒诞感截然不同。②因此,我们看到,鲁迅《野草》 中的名篇《死火》 《失掉的好地狱》 里,杂错连缀禅佛意象如:大乐、三界、剑树、曼陀罗花、火宅、火聚、牛首阿旁等,而他本人并不将禅佛理念作为其价值评估的终极依据。这让我们联想到东方的文化信念崩溃之际而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起来之前,作为一个东方文化的承载者其心灵彷徨无着的虚无境地。
许地山的《空山灵雨》 44 篇作品,基本上控制在一千字以内的篇幅,叙述和对白的成分较多,但并不妨碍每一篇中强烈的诗意的传达,如《春的林野》 《疲倦的母亲》 《海》 《爱的痛苦》 《香》《蛇》 《蝉》 等,甚至像《乡曲的狂言》 和《处女的恐怖》 这些带有故事情节的篇什都寄寓着作者相当独特的诗思,《空山灵雨》 散发着浓郁的禅佛意味,在中国散文诗历史上,如此明显地以禅佛的空观建立别样的审美趣味,并试图以佛家的理念来消解舒缓时代的苦闷,从而使散文诗这种从西方横移过来的新文体从哲理意蕴到语言风格都实现了中国化的转换,在此前虽有刘半农的尝试在先,但许地山应该才是这种“另类写作” 的代表性作家。
在台湾现代生活的背景之下,林清玄的散文诗正如他的名字一样,给诗坛送来一股清玄之风,清凉解火,如果说商禽、痖弦、苏绍连的自由诗和散文诗揭示了现代生活的无奈和困顿,那么林清玄的散文诗恰是在体验观照之余,以禅佛的智慧眼给万般烦忧中的现代人指点迷津。另外,林清玄化解人生苦恼特别是现代人苦恼的终极根据为禅佛的苦空观以及伤情优生的悲悯情怀,这对于血液里积淀着禅佛文化心理基因的中国读者来说,自能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共振。从这个角度来看,以禅佛理念和禅宗美学观点进入散文诗的立意取境,比起从国外引进的象征主义和超现实表现手法,则或许更加容易契合中国人的接受心灵,或者可以说象征主义和超现实风格的散文诗,暴露现代心灵的骚动不宁和千疮百孔,但苦于没有治病的良方和解除痛苦的药石,而以禅入诗的散文诗则以宏阔的生命意识、自然观和宇宙观从容化解生活中的万般困扰,让饱受创伤的现代心灵得以从容解脱,跳出火炉进入清凉一片天。在中国散文诗历史上,许地山和林清玄的散文诗写作最具本土性,因为他们以东方的智慧——禅佛理念对现代自由诗、散文诗中的主要审美观念——反讽、悖论,进行了以空破实的化解,其哲理含蕴和艺术价值又绝不在象征主义或超现实主义诗歌文本之下。③
散文诗在印度和阿拉伯文化语境中同样发生文体变异。泰戈尔和纪伯伦两位世界级大诗人,用散文诗形式传达东方宗教情感,泰戈尔获诺贝尔奖的作品英译诗集 《吉檀迦利》(1912-1913),是泰戈尔本人用英文从孟加拉语诗作《吉檀迦利》 《渡船》和《奉献集》 里,选择部分诗作而成,《吉檀迦利》 的孟加拉语诗作是韵律诗,而翻译成英文之后变成自由诗(散文诗)。《吉檀迦利》,原意为给神的献诗,共有103 首,其中大部分是献给神的,此神与彼神(上帝)不同,此神是一个无形无影、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精神本体(大梵天、佛性),它既是宇宙本体,又是宇宙万有。《吉檀迦利》 宣扬平等、慈悲、自由的生命观和宇宙观,这种异质性的生命态度和生活模式,让沉陷于现代迷宫中的西方人获得了新的启示,所以孟加拉语韵律诗《吉檀迦利》 翻译成英文之后一度风靡英语世界,瑞典科学院决定给予泰戈尔这一奖赏,以表彰“其诗作所揭示的深沉意蕴与高尚目标”,以及他“用西方文学普遍接受的形式对于美丽而清新的东方思想之绝妙表达”。
黎巴嫩的卡里·纪伯伦是阿拉伯近代文学史上第一个使用散文诗文体写作的作家,纪伯伦青年时代以小说写作为主,定居美国后以写散文诗为主,从上世纪20 年代起,陆继发表散文诗集《先驱者》(1920)、《先知》(1922)、《沙与沫》(1926)、《人之子耶稣》(1928)、《先知园》(1931)等,《先知》 是他的代表作。当代有专研纪伯伦的学者指出,《先知》 是一部“圣化文本”,纪伯伦的散文诗对于圣经文体的采纳,主要表现在体裁、结构形式、叙述风格和神秘主义四个方面。可以描述为:(1)采纳了智慧文学体裁——如寓言、比喻、谚语和格言在《沙与沫》 之中的广泛使用;(2)采纳了先知书(天启体)的体裁形式,《先知》 采用先知宣讲的形式,标示着这一话语文本的圣神性和神秘性,阿尔穆斯塔法(Almustafa)始终在代神言说,传谕从生到死的26 个圣神启示,使人感到具有不可怀疑、不可争辩的真理性;(3)模仿福音书的结构形式,《先知》 中出现的三组人物阿尔穆斯塔法、城里的百姓和女预言者爱尔美差与四卷福音书的 《马太福音》 的 “登山训众” 人物结构关系如出一辙,“登山训众” 人物为耶稣、信众和门徒;(4)简约含蓄的叙述风格;(5)神秘主义特征。
纪伯伦以散文诗形式来表达他的新宗教——爱、美与生命,这种宗教没有一般宗教形式的外壳,却包含了每一种宗教的实质,即对于终极存在的感悟和认知。有论者指出纪伯伦后期作品(包括《先知》)表现出来的苏菲主义思想隐秘、超验、人神合一等,在因陷入二元论困境而导致唯我论和怀疑论的现代西方人面前,成为了一种打破主客二元对立模式的、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西方学者安撒里·阿里在专著《苏菲主义和超越:在20 世纪末科学之光中的苏菲思想》 一书中指出:苏菲思想抵抗了“我们的” 生物进化观,同时,它是“非二元的”(non-dual),它使我们发现,在我的精神(psyche)中,有一种天然的力量,驱使我们不断扩展一种最终的自由,这自由将使我们从“我” 和“你” 的二元对立模式中解放出来。试看《先知》 中的部分诗句:
也有人施与了,而不觉出施与的无痛,也不寻求快乐,也不有心为善;他们的施与,如同那边山谷里的桂花,香气在空际浮动。——《施 与》
在万山中,当你坐在白杨的凉阴下,享受那远田与原野的宁静与和平——你应当让你的心在沉静中说:“上帝安息在理性中。”
当飓暴卷来的时候,狂风震撼林木,雷电宣告穹苍的威严——你应当让你的心在敬畏中说:“上帝运行在热情里。”
只因你们是上帝大气中之一息,是上帝丛林中之一叶,你们也要同他一起安息在理性中,运行在热情里。——《理性与热情》
灵魂如同一朵千瓣的莲花,自己开放着。——《自 知》
那在殿宇的阴影里,在弟子群中散步的教师,他不是在传授他的智慧,而是在传授他的忠信与仁慈。
假如他真是大智,他就不命令你进入他的智慧之堂,却要引导你到你自己心灵的门口。——《教 授》
你们曾听说过,像一条锁链,你们是脆弱的链环中最脆弱的一环。但这不完全是真的。你们也是坚牢的链环中最坚牢的一环。
用你最小的事功来衡量你,如同用柔弱的泡沫来核计大海的威权。用你的失败来论断你,就是怨责四季之常变。当我到泉边饮水的时候,我觉得那流水也在渴着;
我饮水的时候,水也饮我。不要忘了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来。
一会儿的工夫,我的愿望又要聚些泥土,形成另一个躯壳。——《拔锚启航》
西方文化一贯重理抑情,可是在纪伯伦这儿,“上帝安息在理性中”,同时,“上帝运行在热情里”。上帝——那个超越性的精神性存在合情合理,情理并包,而且芸芸众生的我们也无须回避欲望的纠缠,因为,我们和上帝一样安息在理性里,运行在热情里。当代学者马征论及纪伯伦艺术精神的独特性时指出:纪伯伦作品中的审美观,构成了与西方现代审美观的根本差异,与西方在不和谐的丑中展示个别的、特殊的美不同,通过运用“通感”“应和” 手法,纪伯伦在文学创作中表现了人、自然与神之间相互应和的和谐之美、普遍之美。这种审美观实际上蕴涵着 “神圣” 的审美体验,与纪伯伦文学的生命神圣主题构成了呼应。④
拉丁美洲卢本·达里奥、塞萨·瓦叶霍、路易斯·博尔赫斯、巴勃罗·聂鲁达、奥克塔维奥·帕斯等散文诗人的作品总体上表现拉美风情,尤其是塞萨·瓦叶霍的散文诗,高度浓缩着印第安人的宇宙观、生命观和死亡意识,⑤他的散文诗《骨骼点名册》 《良知》 《时间的暴力》 《一生最危急的时刻》 《生命的发现》 《渴望停止了……》 《有一个人变成残废》 《那房子没有人住了》 《我想讲一讲希望》 《把离开你的人跟你……》 表达了另外一种审美现代性(相对于波德莱尔),即现代原始思维对于现代文明规约的抵制和控诉。实际上,印第安人并不喜欢现代的文明生活,他们宁可生活在自己的生活模式和价值时空,在塞萨·瓦叶霍的散文诗里,原始的巫术思维模式进入散文诗的语言经纬,使得我们习以为常的语言感受短暂“断路”。在《有一个人变成残废》 这章散文诗里,比柯上校,“残废退伍军人会” 会长,因为爱被火药吃掉了嘴巴,死面孔在活躯干上,这面孔变成了头颅的后脑勺,头颅上的头,“有一次看见一棵树转背向我,另一次看见一条路转背向我……”这种情感模式是属于拉丁美洲的,作为生活在现代文明环境下的瓦叶霍,以祖先的情感认知来解构现代文明规约,在散文诗美学视野之内,我们可以认为他在进行一种另类的审美现代性诉求。
台湾散文诗人瓦历斯·诺干(泰雅族)的散文诗 《Atayal》(《争战1896-1930》),以近似原始思维和原始语言来想象、建构泰雅部落反抗日本殖民但最终被殖民地化的神秘野史,中间描写族人与殖民者的激烈对抗、袭击、杀戮,敌人的诡诈、伪善等等历史事象,不着痕迹,却又惊心动魄。试看其中的句子:“炮弹越过一座座山头,将山坡种满一朵朵火花,四溅的硝尘玷污了金黄色的田园”、“Modu 的小米不懂得躲避,族人的躯体却藏得像一片叶子,从绿阴中,箭镞像雨水洒在敌人的眼睛”、“当敌人的统帅来到太鲁阁断崖巡视,一支历史的箭,刚刚完成进出总督那一双小腿的任务”。这种高度凝练、错位的语言表现手法也只能出自秉承着原始思维习性的泰雅族诗人,因此,散文诗散文其形、诗其内质的文体个性在原始思维里,可以得到更加出神入化的发挥。⑥
(连载完)
注:①王光明 孙玉石:《二十世纪中国经典散文诗》,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页299。②王晓华:《西方戏剧中的终极追问和荒诞意识》,载胡经之编:《艺术创造工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年,页138。③黄永健:《中国散文诗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页124。④马征:《文化间性视野中的纪伯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页279。⑤卢本·达里奥 等著 陈实译:《拉丁美洲散文诗选》,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页19-36。⑥王光明 孙玉石:《二十世纪中国经典散文诗》,武汉:长江出版社,2005,页330-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