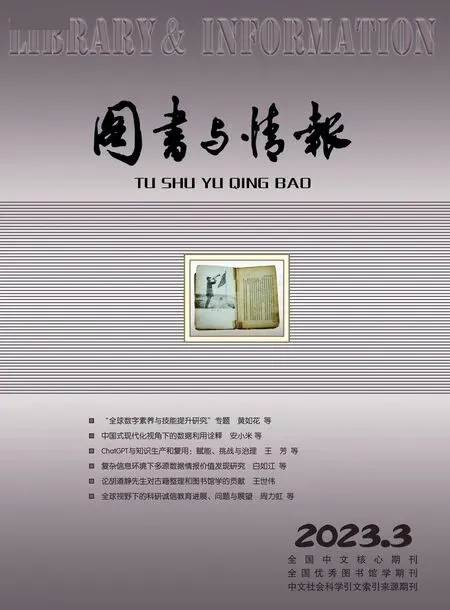复社的红色文献和史料价值研究
黄 超
(1.首都博物馆 北京 100045)
1937 年11 月,上海沦陷后形成了“孤岛”①“孤岛”是中国现代史上特定的一个名词,特指淞沪会战后沦陷(1937 年11 月12 日)到太平洋战争爆发(1941 年12 月8 日)期间在上海的租界。由于这一时期的英、美、法等国对日本侵华战争保持中立,日军在攻陷上海后没有立刻占领这些国家在上海的租界。租界就成为被日军四面包围但相对安全的特殊区域,被人们称为“孤岛”。,不少进步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利用租界的特殊环境,创办了一些中国出版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出版机构,出版了一批在中国出版史、文学史、抗战史上有重要影响的经典图书。复社就是这一时期成立的一家出版机构,复社自成立起存续时间虽然不长,但却是党在沦陷区的重要舆论和传播阵地。近90 年来,这些珍贵的文献史料散落各地,如今除在博物馆、展览馆和旧书市场尚可见些零星书影外,民间收藏也鲜见。复社及其出版的《西行漫记》(图九)《续西行漫记》(图七)《鲁迅全集》是党在沦陷区的一缕曙光,这束光存续时间虽短,但其战斗性和特殊性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对《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鲁迅全集》的出版及经费等进行了梳理,特别对在复社的史料中未曾提及的私家藏品复社遗存文献《中国革命性质及动力》(图三)及《鲁迅全集》编号纪念本遗存情况进行了考证,希望能补益党史研究。
1 复社的运行与业务
1936 年,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历经艰难险阻到陕北根据地考察采访,写出了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1937 年该书在英国出版后,引起巨大反响。因为国民党对共产党消息的封锁,大家都急迫关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情况。当时身处上海的胡愈之在斯诺住处读到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后,敏感地意识到这部书稿的价值,在党组织的支持下,胡愈之决定翻译出版《红星照耀中国》,由于租界当局已开始查禁该书的英文版,出版该书的中文版需要冒很大风险,即使翻译完成了,也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为了该书能够顺利出版,胡愈之联合郑振铎等人发起创办了复社。
1.1 复社的社团性质
从严格意义上讲,复社并不是正规的出版机构,而是一个“为推动文化界在抗建期内对出版等事业做些有力的工作”[1]的社会团体。中共中央非常重视文化战线斗争,在抗战期间尤其注重团结和推动社会有声望地位的人士“同时应推动社会上有声望地位的人出版一定的刊物,由我们从旁给以人力和材料的帮助。”[2]从复社成立以来的一系列活动来看,其从事的活动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1937 年11 月11 日,也就是日军占领上海的前一天,在中共江苏省文委领导下,以上海各界救亡协会名义创办了《团结》周报。周报编委会由各界代表组成,孙冶方、王任叔(巴人)、胡愈之等中共党员参与报纸编务。“潘汉年、刘少文等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刘晓、刘长胜、沙文汉等省委领导经常为报纸撰稿。”[3]复社则是根据具体工作需要和实际斗争需要而成立的机构。“江苏省文委还以复社、每日译报社、每日译报图书部和风雨书屋的名义,秘密翻印了部分《列宁选集》以及毛泽东《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新阶段》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的著作”[3]。根据《复社社约》[4]:复社以“促进文化、复兴民族”为宗旨,由社员和社友组成,社员由本社创立会推选,对本社负有完全责任,社友由购买本社出版物的读者以及参与本社出版工作的作者、编者、印刷人、发行人组成。关于复社社员的构成,现有研究成果说法各异,1939 年4 月1 日《复社第一届年会记录》中就出席年会社员名单和年会拟通过加入的社员有完整记载,这是目前看到的最为权威的史料。据此推断:复社社员有郑振铎、胡咏骇、胡仲持、黄幼雄、张宗麟、倪文宙、卢广绵、王任叔、冯仲足、沈体兰、吴耀宗、胡愈之、黄定慧、萧宗俊、姚惠泉、严景耀、王纪元、金仲华、吴涵真、林旭如、陈志皋、周予同、李健吾、吴承禧、孙礼榆共25 人[4],这些人都是文化、教育、工商等界别中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著名爱国人士。
1.2 复社的秘密运行模式
复社设在胡愈之家,为了避免敌人查封,复社的创办、运行、停业都是秘密进行,除了出版图书的版权页有该社名称和假地址“香港皇后大道”外,该社主持人、成员、地址等具体信息,外界一概不知。郑振铎在《记复社》一文中不仅对该社的创办、停业有形象地描述:“复社起来的时候,像从海面上升起的太阳,光芒万丈,海涛跳涌,声势极盛;但在这时候,结束了时,也立即烟消云散,声息俱绝”[5];而且就复社的秘密存在做过如下记述:“敌人们大索复社,但始终不知社址何在。敌人们用尽种种办法,来捉捕复社的主持人,但也始终未能明白究竟复社的主持人是谁”[5]。从郑振铎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复社成员以及与复社有业务往来的人员都有极强的保密意识。正是由于复社始终是秘密运行,关于复社的停业时间也出现了两种说法:一种是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因日军占领租界而停止出版活动[6];另一种是1939 年胡愈之家被查抄后,即停止了出版活动[7]。笔者目力所及复社最后出版发行的图书是1939 年4月25 日再版的《续西行漫记》。1939 年4 月1 日《复社第一届年会记录》中提到的再版《鲁迅全集》、翻译出版《高尔基全集》等图书,实际上并未出版,由此推断第二种说法比较准确。
1.3 复社的出版业务及遗存
为了推动出版业务开展,复社成立了由5 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其中社长、秘书、编辑主任、出版主任、发行主任各1 人,社长由胡愈之担任,秘书由地下党员张宗霖担任。为了给开展业务工作提供经费保障,根据《复社社约》:社员每人要缴纳50 元的社费,作为复社的流动资金;复社还设立了基金,主要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每月月底结账时抽取营业额的10%;二是每年年底结账时抽取本年所获全部净利润。据《复社第一届年会记录》,25 名社员中有5 名是新加入的,也就是说在复社成立初期社员缴纳社费仅1000 元,但是到1939 年4 月1 日,复社已有毛利约1.7 万,年营业额约3 万[4]。这两组数据说明:复社在成立一年多时间内,所出版的《西行漫记》《鲁迅全集》等图书的销售取得了较好业绩。正是由于这些图书发行获得了成功,复社在第一届年会上提出了筹备出版百科全书、翻译出版《高尔基全集》、继续出版《列宁选集》和《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再版《鲁迅全集》以及其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书籍,计划至少出版5 部图书。
通过对复社的现存文献进行梳理,可以确定复社自成立以来先后编印了《西行漫记》《鲁迅全集》《中国革命性质及动力》《续西行漫记》《列宁选集》《联共党史》《左派幼稚病》等一批红色文献和进步图书、印刷品。
2 从《西行漫记》到《续西行漫记》的复社红色文献出版梳理及《中国革命性质及动力》考证
上海孤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复社在党的领导下,出版的《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等记录红军长征的图书,数次再版。这些图书和复社一样,成为党开展对敌斗争的有力武器。新近从私人藏家藏品中发现的一本复社出版的红色文献《中国革命性质及动力》,在现有复社的史料中均未曾提及,有必要对其文献文本等进行考证。
2.1 复社红色文献《西行漫记》的出版与遗存
《西行漫记》是复社于1938 年出版的第一本图书,又名《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于1936 年6 月至10 月对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考察后,根据考察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完成的一部纪实文学作品。斯诺作为一个西方新闻记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作了客观评价,并向全世界作了公正报道。全书共12 篇,主要内容包括:关于红军长征的介绍;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主要领导人的采访;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红军的军事策略;作者的整个采访经历和感受等。《西行漫记》的初衷是希望国人在阅读此书后对中共和红军有正确的认识,以支持中国共产党及当时的抗日爱国运动,从《西行漫记》传播的实际影响力来看达到了预期效果。关于《西行漫记》的书稿、翻译、出版、版本等有多种说法,本文依据馆藏文献史料进行梳理研究。
2.1.1 《西行漫记》的书稿来源
英文版《Red Star Over China》和中文版《西行漫记》的署名作者均是埃德加·斯诺,但是这其中还有斯诺第一任夫人尼姆·韦尔斯(Nym Wales)对书稿的贡献。如韦尔斯1937 年前往延安的重要使命就是为斯诺做补充采访,《红星照耀中国》中关于朱德的一手资料和照片,就来自于韦尔斯1937 年6 月托人带给斯诺的采访笔记和胶卷,因为斯诺是1936 年6 月至9 月在保安(现陕西志丹县)采访,朱德是1936 年10 月率领部队到达陕北,他们二人未曾谋面,因而《Red Star Over China》中对朱德的阐述并非斯诺采访所得。另外,《西行漫记》翻译的底稿也并非《Red Star Over China》英文初版,胡愈之在《西行漫记》的“译者附记”中就此写道:“英文初版发行后,作者发现有许多错误,决定在再版修正。第十一章中删去了一个整节。第十章中关于朱德的一节完全重写过。此外还改正了许多字句。现在中译本系照作者修订本译出。有许多字句与英文初版不相同的地方,都是作者自己改正的”[8]。复社出版的《西行漫记》得到了斯诺的大力支持,他不仅把该书版权转让给了复社,而且提供了《Red Star Over China》英文版没有的大量珍贵人物照片,斯诺在《西行漫记》的“序”中写道:“据我所了解,复社是由读者自己组织起来的非营利性质的出版机关。因此,我愿意把我的一些材料和版权让给他们”[9],斯诺提到的“材料”主要指的是图片,胡愈之就人物照片在“译者附记”中则写道:“中译本所用图片,差不多全部是英美版本所不曾登载过的。其中许多人物照片,还是破天荒第一次公开登载。这些图片,大部分是作者供给的”[10]。从胡愈之、斯诺的上述表述中可以看出《西行漫记》的书稿与《Red Star Over China》英文初版书稿,无论是文字,还是图片,都有很大不同。
2.1.2 《西行漫记》的译介发现
关于胡愈之从斯诺处借阅的是英文初版样书还是正式出版物,现有研究成果两种说法都有。
据胡愈之的回忆:他从斯诺处得知伦敦戈兰茨公司寄来了一本著作的样书,就向斯诺借阅了该样书,阅读后发现是一本难能可贵的著作,产生了翻译这本著作的想法,这本著作就是英文初版《红星照耀中国》;胡愈之由于对斯诺的详细情况不了解,对著作中所记述的内容没有把握,就找上海地下党进行了核实,获知斯诺确实到过陕北,而且毛泽东亲自接受了斯诺的采访,斯诺整理出来的谈话内容翻译成中文稿后,毛泽东也进行了审阅修改,胡愈之据此决定翻译出版《Red Star Over China》[11]。此段回忆不仅明确提到了从斯诺处借阅的是样书,而且说明了在决定翻译出版前曾找党组织进行过核实。
关于参与《Red Star Over China》翻译的有多少人以及胡愈之是否参与了翻译,现有研究成果也有多种说法。1938 年2 月初版《西行漫记》(封面图)扉页背面“译者”(图六),署名依次为:王厂青、林淡秋、陈仲逸、章育武、吴景崧、胡仲持、许达、傅东华、邵宗汉、倪文宙、梅益、冯宾符,共计12 人,由于翻译底本只有一本样书,就拆开来,各拿一部分翻译,其中“陈仲逸”是胡愈之的笔名。据初版《西行漫记》记载内容以及有关史料可以推断:胡愈之作为组织者,做了大量翻译者与作者之间的沟通协调工作。作为翻译者,他不仅直接参与了书稿的翻译,而且负责书稿的审定润色,并代表所有译者撰写了“译者附记”。书稿的翻译过程危险重重,但这些译者靠着高昂的热情,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向胡愈之交来译稿。每个译者所翻译的人名和地名常有不统一的情况,胡愈之则负责统稿,他把自己关在阁楼,用了13 天的时间日夜兼程,修改、校正错译和笔误,终于完成了全书译稿统稿。胡愈之后来回忆说:“为把译稿校对的通顺无误,我一天只睡3、4 个小时,13 天瘦了5 斤多。”[12]对于《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译法,斯诺自己曾取了中文名字“施乐”,名字经胡愈之译为“斯诺”,“斯诺”第一次出现在复社版《西行漫记》上,伴随着《西行漫记》的传播和影响,名字从此家喻户晓。斯诺也认可了胡愈之为其所译的新中文译名。
斯诺喜欢中国,在延安的采访中被中共领导人的气度和平实所感染,被广大红军指战员坚定的革命信念所折服[13],因而斯诺笔下的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都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都在为真理和信仰而活着,都在为了更加美好的明天而拼搏,进而写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并不像国民党所描绘的那样是一群‘赤匪’,而是一股团结一致的、拥有忠实的农民追随者的力量。”[14]的客观公正报道,并感言“只有最优秀的军队才吃得消红军战士这样紧张艰苦的日常条件”[15]。此后的斯诺和很多中共领导人最终成为了一生的朋友,他为了让世界更好了解真实的红军真相,决定把《西行漫记》版权无偿赠送给复社。
2.1.3 《西行漫记》的发行策略
《Red Star Over China》中文版出版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书名。因原书名《红星照耀中国》太“红”,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极易引起租界当局的注意,不利于出版后的发行。书名《西行漫记》是受范长江作品启发而来,当时范长江著的《中国西北角》一书颇为流行,使“西北”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代名词。《西行漫记》书名中的“西行”即借用此寓意,“漫记”是用游记的形式来掩护其中红色的内容。《西行漫记》从1937 年12 月开始翻译到1938 年2 月出版,前后也不过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完成书稿翻译后,经费是复社面临的重要问题,为了解决出版经费问题,复社发动读者预订筹集经费,估计出版后定价1 元,按照这一标准共筹得1000 元,复社用这笔钱购买纸张。为了解决排印问题,复社找到商务印书馆尚未内迁的印刷厂,请工人们先印刷、出版后再支付费用,工人们欣然答应并迅速印刷。《西行漫记》第一版仅印刷了1000 册,由于发放了预售劵,读者凭券领书,不在书店出售,出版后很快就发行完毕。正是由于翻译、印刷、发行都是采取了比较特殊的方式,所以胡愈之说:“这是复社出版的第一本书,也是由读者自己组织、自己编印、不以营利为目的而出版的第一本书。这种由读者自己组织出版的事业,是一种冒险的却是成功的试验”[10]。也正是由于《西行漫记》试验的成功,后来《鲁迅全集》的推广也采取了同样的模式。
2.1.4 《西行漫记》的版本情况
关于复社的《西行漫记》版本问题,胡愈之在1985 年曾回忆到:“第一次印1000 本,很快就卖光了。开始大家不知道书的内容,当知道是写共产党、写红军、写延安的书,买的人就更多了,近半年就印了五六版,卖到八九万本,还远到香港、南洋去卖,轰动了当地华侨。随后我们又翻译出版了《续西行漫记》,同样受到国内人民和华侨的欢迎”[16]。其中提到了“五六版”,因此许多研究成果都认为复社出版了六个版本的《西行漫记》。
从目前能查询到的第四版、第五版版权页来看,《西行漫记》初版、再版、三版、四版先后于1938 年2月10 日、4 月10 日、10 月10 日、11 月10 日出版,第五版为“增订五版”(图八),出版时间是1939 年4 月10 日。第五版之所以叫增订版,是因该版不仅对原版的十二章作了修订,删掉了第十一章中《那个外国智囊》关于李德的相关内容,而且增加了第十三章《旭日上的暗影》,从“日本的战略”“致日本的红色敬礼”“战争中的战争”“没有征服的中国”“日本见了红”“中国战略上的任务”六个方面,简要地论述了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从出版时间来看,第四版出版时间已是7 个月之后,超过了胡愈之回忆中的“近半年”,综合第五版出版时间和复社停业时间,可以推断出复社共出版了五版《西行漫记》。
《西行漫记》后来成为美国政府研究中国问题的重要材料,“1938 年美国版的《西行漫记》发行,得到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关注,1942 年、1944 年、1945年,斯诺3 次被罗斯福召见,可见《西行漫记》在美国政界的影响力绝非一般。”[17]斯诺也因为《西行漫记》成为中国与美国之间的使者,斯诺于1972 去世,2009 年被评为“100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2.2 《续西行漫记》节译版单行本《中国革命性质及动力》之考证
2.2.1 从《西行漫记》到《续西行漫记》的出版
1937 年4 月至10 月期间,《西行漫记》作者斯诺的第一任夫人韦尔斯冲破重重阻碍,辗转到达延安,历时四五个月,把在陕北的采访见闻和个人感受写成了纪实性作品 《Inside Red China》(图十五)。《续西行漫记》是《Inside Red China》的中文译本,此书中文名原译《红色中国内幕》,借鉴《西行漫记》出版后的译名而改译为《续西行漫记》,是继《西行漫记》之后让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状况的伟大著作。
韦尔斯在陕北不仅采访了朱德、彭德怀、徐向前等红军将领,还同毛泽东、洛甫等讨论了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与康克清、贺子珍、丁玲等革命妇女进行了深入交往,参加了红军的集会,观察了红军普通士兵的生活。韦尔斯将采访笔记整理后在《Inside Red China》的“序”结尾写道:“这在我是一个有着新发现的旅程——我所发现的是在地球最老最无变化的文明的心脏创造着新的世界、新的精神、新的人们”[18],这段话可以说是韦尔斯在陕北四五个月采访得出的结论。
1938 年底到1939 年春,由胡仲持、冯宾符、凌磨、席涤尘、蒯斯曛、梅益、林淡秋、胡霍8 个人合作,将《Inside Red China》一书译成中文,根据英文原名应译为《红色中国内幕》,因复社此前已出版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再加之两本著作内容有延续性,1939年4 月15 日,复社就以《续西行漫记》为名出版了《Inside Red China》中文版(图十二),4 月25 日再版(图十一)。《续西行漫记》的翻译出版方式与《西行漫记》基本相同,均出版了平装本与精装本,该书内容由 “到苏区去”“苏区之夏”“妇女与革命”“中国苏维埃的过程”“中日战争”五章构成,附录了“八十六人略历”(分政治领袖、军事领袖、开除党籍者三类),插入了64 张照片,全景式呈现了韦尔斯在陕北采访的成果(图十六)。
2.2.2 《中国革命性质及动力》是《续西行漫记》节译版单行本
新近发现的《中国革命性质及动力》一书,是一本22 页的小册子,封面书名下分两行分别署“毛泽东谈”“韦尔斯记”,底部署“复社出版”,正文采取问答形式呈现,因该书无版权页,具体出版时间不详。经过内容比对发现,《中国革命性质及动力》一书正文与《续西行漫记》初版第四章“中国苏维埃的过程”第二节“中国革命的分析”下“中国革命的性质”完全一致,因此可以断定《中国革命性质及动力》是《续西行漫记》的节译版。
2.2.3 《中国革命性质及动力》单行本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对于《中国革命性质及动力》一书,以下三个价值需要说明:
一是为什么出版这本小册子?《中国革命性质及动力》扉页背面的“编者附言”写道:“中国革命,是一切关心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事业的人们所关怀的重大问题,但中国革命是一个复杂不容易了解的问题。究竟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是怎么样的呢?中国革命的动力是什么呢?中国各阶层的本质及对革命的关系与作用怎样呢?中国革命为什么是长期性的呢?这都是一般人们所急于明白的问题”,附言结尾写道:“这是一篇相当宝贵地研究中国革命的资料,特编印以此供大家参考”。从中可以看出:编者出版该小册子旨在回答民众最关心的关于中国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即革命性质和革命动力。
二是采访对象都有谁?《中国革命性质及动力》的封面和扉页均印有“毛泽东谈”,“编者附言”中也有“毛泽东先生的谈话虽系一新闻记者自己的记录,而且未经过毛泽东先生的校对和修改”的表述,表明编者认为该采访内容均是毛泽东所谈。《续西行漫记》第四章关于“中国革命性质”部分就韦尔斯的采访有如下说明:“毛主席很高兴回答这些问题,并答应写一本关于中国革命的小册子,这在目前是非常有价值的。他于七月四日第一次跟我会谈,但是七月七日发生了卢沟桥事件,他没功夫继续跟我会谈,把共产党的历史家洛甫和毛氏的副手吴良平介绍给我”[18]。从中可以看出:《中国革命性质及动力》正文内容的采访对象除毛泽东外,还有洛甫和吴良平,书中关于统一战线、托派的内容,都来自于对二人的采访。因此,《中国革命性质及动力》只署名“毛泽东谈”并不准确。
三是采访是什么时间?《中国革命性质及动力》正文部分在题目“中国革命性质及动力”下有“(一九三七年六月在延安)”的字样。根据上段《续西行漫记》一书中的表述,韦尔斯围绕“中国革命的性质”采访毛泽东的时间是七月四日,采访洛甫和吴良平的时间也在此后,其中韦尔斯于1937 年7 月14 日围绕“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支持统一战线”采访了洛甫[29],并以《为什么中国共产主义者支持统一战线——洛甫访谈录》为题发表在《太平洋事务》1938年第3 期上。虽然韦尔斯先后于1937 年6 月24 日、7 月4 日、8 月13 日对毛泽东进行了三次采访,但是《中国革命性质及动力》正文内容是1937 年7 月4日及其后对三人的采访,因此,《中国革命性质及动力》正文“一九三七年六月”的时间并不准确。另外,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及动力》的出版时间,依《西行漫记》正式出版前已出版了《毛泽东传》,再加之该小册子“编者附言”对出版主旨的说明,推断出版时间应该在《续西行漫记》初版出版之前。
2.2.4 《中国革命性质及动力》单行本符合当时的传播需求
要把《续西行漫记》和单行本《中国革命性质及动力》必然联系说清楚,就应该把《西行漫记》和《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毛泽东自传》的传播先作一讨论。
在复社推出译本《西行漫记》前,斯诺就延安采访的内容,曾先后以《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毛泽东自传》(图一)对外传播了其在延安采访的部分内容。1937 年3月,北平东方快报印刷厂以上海丁丑编译社名义秘密出版发行了《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该书收录了斯诺、韩蔚尔、史沫特莱三位外国记者关于红军、长征、根据地等方面报道的文章,其中包括斯诺的《毛斯会见记》《红党与西北》《红旗下的中国》。《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收录了《Red Star Over China》没有收录的内容,如毛泽东与斯诺共有6 次谈话,《Red Star Over China》只收录了1936 年7月16 日围绕抗日战争的谈话,再如《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配发了32 张照片,而《Red Star Over China》只配发了16 张。《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是斯诺关于苏区介绍文章的第一次结集出版,也是斯诺关于根据地报道的第一种中文本,斯诺说该书“向无数中国人第一次提供了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情况”,斯诺的妻子海伦则说该书“对中国像一道闪电,它唤醒了人民”[20]。1937 年9 月、11 月,延安的文明书局、上海的黎明书局先后出版了《毛泽东自传》,内容与《西行漫记》第四章《一个共产党员的来历》基本一致,包括“一颗红星的幼年”“在动乱中成长起来”“揭开红史的第一页”“英勇忠诚和超人的忍耐力”四部分组成,并附《毛泽东论中日战争》《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小传》。《毛泽东自传》作为毛泽东自述、斯诺记录的毛泽东第一本传记,正式出版后,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出现了两次出版高潮,共涌现出了50 余种版本。《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毛泽东自传》两本书的推出说明了《西行漫记》并非斯诺著作最早的中文版图书。同时也给了复社版韦尔斯遗存文献《中国革命性质及动力》的存在做了合理推论:《续西行漫记》和《中国革命性质及动力》的内在联系是参考了《西行漫记》与《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毛泽东自传》的传播模式;《中国革命性质及动力》是在复社所出版的红色文献推动了上海马列著作出版热潮、各种马列著作单行本不断问世这一时期复社所出版的红色文献。
3 复社进步文献《鲁迅全集》的出版与考证
复社在出版发行《西行漫记》取得成功后,为达到扩大鲁迅精神的影响,胡愈之和许广平等人决定出版《鲁迅全集》,当年从延安派来上海开展秘密联络工作的刘少文曾为此事专门请示并获得中共中央同意,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复社很快便承担起了《鲁迅全集》的出版任务。
3.1 复社《鲁迅全集》的版本及遗存
《鲁迅全集》由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叶圣陶、茅盾等70 余名委员组成的“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复社仅用了三个月时间,就完成了20 卷、600余万字巨著的出版工作,鲁迅夫人许广平在《〈鲁迅全集〉编校后记》中赞称“六百余万言之全集,竟得于三个月中短期完成,实开中国出版界之奇迹”[21]。在三个月时间内,复社共出版了三种装帧版本的《鲁迅全集》,第一种是1938 年6 月15 日出版的普通版,红色纸面布脊、书脊烫银色书名;第二种是1938 年8月1 日出版的甲种纪念版编号本,红色布面精装、书名烫金字;第三种是1938 年8 月1 日出版的乙种纪念版编号本,紫红色胶皮封面、黑皮书脊烫金色书名(图十四),为防止落灰采用了真金滚顶口的书顶烫金工艺(图二)。三种版本中乙种纪念版编号本装帧最为豪华,用纸特别讲究,内文用重磅道林纸,环衬用仿鸡皮纸,插图用铜版纸,纪念版编号本共印制200 套,每套版权页标有“纪念本第X 号”,全套外装一楠木书箱,书箱上盖有“鲁迅全集纪念本 蔡元培题”字样(图十),许广平生前将001 号赠上海鲁迅纪念馆珍藏。《鲁迅全集》是读者十分向往的图书,1938年1 月12 日,毛泽东在给艾思奇的信中说:“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华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22],复社20 卷《鲁迅全集》出版后,毛泽东辗转得到一套编号为058 号的纪念本,放在延安的窑洞里时常翻阅、爱不释手,在转战陕北时,毛泽东始终带着这套《鲁迅全集》,这套书辗转到了西柏坡,后来随毛泽东赴京进了中南海。
3.2 复社《鲁迅全集》的出版经费来源
出版三种装帧版本尤其是纪念版精装的《鲁迅全集》,需要大量的经费,仅靠复社社员缴纳的社费以及《西行漫记》销售盈余是不够的。为了解决经费问题,《鲁迅全集》的编辑、出版、发行机构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复社、生活书店采取了募集捐款和预收书款相结合的方式。
一是通过刊发广告预售。1938 年5 月16 日在上海出版的《文艺阵地》最早刊载《鲁迅全集》出版的广告称:“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为使人人均得读到先生全部著作,特编印鲁迅全集,以最低之定价,(每一巨册预约价不及一元)呈现于读者”[23]。1938 年7月1 日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刊发了《鲁迅全集》的预约广告:“全书定价二十五元,六月底前预约仅收十四元。另加寄费二元。愿在香港或上海取书者不收寄费”[24]。
二是通过图书推销方式。周恩来、茅盾、黄炎培、巴金、沈钧儒、陶行知等采取各种方式在国内、美国、南洋等地推销,如沈钧儒在武汉举办茶话会,共筹得数万元,周恩来依托在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宣传推介,一次就预售掉二三百部,获得几万元。由于普通本定价极为低廉,需要纪念本填补亏空,胡愈之在香港拿到《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主席蔡元培、副主席宋庆龄为向海内外人士募集纪念本的通函》《鲁迅全集募集纪念本定户启示》后,持此通函和启示向社会贤达和官员按照甲种本50 元、乙种本100元推销纪念本,通函和启示中明确写道:“本会编印《鲁迅全集》,目的在扩大鲁迅精神的影响,以唤醒国魂,争取光明,所以定价低廉,只够纸张印费。但为纪念鲁迅先生不朽功业起见,特另印纪念本,以备各界人士珍藏”[25]。
郑振铎就该书出版的预售有如下回忆:“最可感动的是,处处都可遇到热情的帮助与自动的代为宣传,代为预约”[5]。正是读者对预售的积极响应,预售的数量相当客观:“普通本预约达二千三百部,其中上海约占一千部,内地各处一千三百部。纪念本共销去约一百五十部”[24],为该书顺利面世筹得了所需基本费用。复社初版《鲁迅全集》进入发行环节后,读者竞相抢购,顷刻销售一空,虽然复社再版的计划因战事未能实现,但是“《鲁迅全集》的出版者们,为了便于全集的再版流布,将《全集》打了两副纸型,上海沦陷后,分藏两处,妥为保管”[23],抗战胜利后至新中国成立前,鲁迅全集出版社、作家书屋、光华书店等出版机构多次再版重印了《鲁迅全集》。
3.3 复社《鲁迅全集》编号纪念本遗存新考证
2021 年,在鲁迅先生诞辰140 周年之际,笔者就《鲁迅全集》编号纪念本存世量调研,惊喜发现《鲁迅全集》编号纪念本虽经历了革命炮火和岁月的洗礼,但80 多年后仍有不少存世。除上述编号第001和058 号已知藏家外,公藏单位尚有上海市档案馆藏编号第2 号,北京鲁迅博物馆藏编号第17 号,绍兴鲁迅纪念馆藏编号第24 号,中国印刷博物馆藏编号第169 号,绍兴鲁迅纪念馆藏编号第180 号,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编号第190 号。编号第35 号、第40 号、第50 号、第61 号、第82 号、第96 号、第118号、第122 号(图十三)、第128 号(图五)、第136 号、第143 号、第149 号、第172 号、第174 号系私人藏家收藏。
另外,还有两套编号不明。一是周恩来总理20 世纪60 年代赠送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系许广平女士捐献其自藏;二是出版家王益所藏,该套全集已于20世纪80 年代捐赠与中国版本图书馆。2021 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之际,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出了5 个《鲁迅全集》编号纪念本(图四)①《鲁迅全集》编号纪念本存世量数据来源:一是笔者经眼出版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播思想火种 铸文化伟业”出版专题展展出的5 个编号纪念本;二是出版专题展策展人介绍;三是出版家王益先生的儿子王晖参观出版专题展时笔者有幸聆听;四是在私人藏家处经眼6 个编号纪念本。此数据是在这些调研基础上统计的,并和出版专题展策展团队分享。。《鲁迅全集》至今已再版多次,其传播对当代的影响再次印证了精神比肉体更能抵抗时间的消磨。
4 结语
上海“孤岛”时期,复社是党在沦陷区的一束曙光,复社在巩固发展统一战线,宣传动员民众抗日,起到了促进和推动的作用。复社存续时间虽短,但其影响力却是很多专门做出版的机构所不及,发动社会多方力量出版的《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鲁迅全集》等红色文献和进步文献,传播了红色文化和先进思想,让国人看到了希望,尤其是当时文化界的进步人士,对党在沦陷区领导各方力量开展斗争、唤醒民众抗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仅对考证新发现的《中国革命性质及动力》作为《续西行漫记》推出前所发行的单行本、《鲁迅全集》纪念本的遗存情况进行了深入调研及阐释。但复社留给后人的文化遗产,尚需学界进一步探讨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