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宁大地上的村庄话语
邓家鲜 张霁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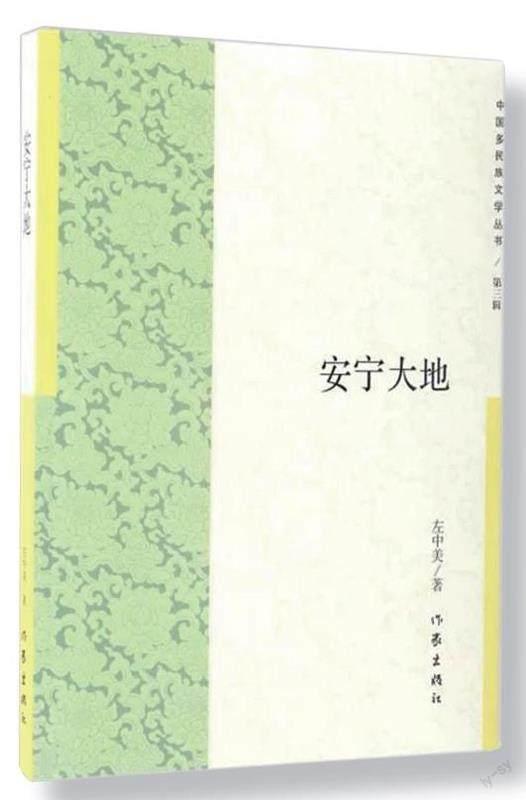


彝族作家左中美是近年创作较为活跃的云南籍女作家。其作品依托坚实的云南红土地,以女性的感知、母性的情怀和诗意的笔墨,展现着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漾濞彝乡民众的生产生活过程和状态,因其深刻的历史记忆和现实人文情怀而受到广泛的关注。《安宁大地》以作家对彝乡的浓烈情感、童年的视角、朴素而真挚的笔触表达着对家乡大地及其生养她的村庄中的风物、对村庄生命的赞美和怀想,呈现出独特的生态审美意识。
前言
合上彝族女作家左中美的《安宁大地》散文集[1],有一种莫名的感动,文章中那个浇菜、打猪草、赶雀、扬麦的“我”,一下子也把读者“我”带回到自己的村庄,不由得想起了“我”的村庄、“我”的奶奶、村庄的风物和人情世故。虽然生活于不同的年代,但源于同样的乡村、童年生活的经验和体验,更源于左中美特有的笔墨展示出的乡村世界。这便是作家“运用现实的体验作为写作的材料”[2]渗透了自己骨血的情感的表达。这种情感不会因阔别家园而被淡化,相反,它会像陈年佳酿,随着离别家园的时间越久,就越发浓郁,最终凝聚于作家的笔端而成情绪深厚的文字表述。正如著名的乡土文学作家贾平凹所言虽是城里人了,但“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鸡一样,那是乌在了骨头上。”[3]左中美在用自己的独特的文字结构和情感方式表达着“乌在了骨头上”的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山乡大地的特殊情感,把一个安宁的生态和谐的村庄大地呈现在读者眼前。
一、对山村大地和大地的风物的深情书写的生态美
《安宁大地》散文集由“大地·序章”“大地·生长”“大地·生命”“大地·歌谣”“大地·未央”五个部分48篇散文组成,其主体就是大地上的村庄及其大地上的鲜活生命。山村和大地是中国作家,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乡土作家写作和叙述的重要内容,是少数民族乡土作家成长的母体。许多有成就的作家心里,都有一块魂牵梦绕的大地。鲁迅之于绍兴,沈从文之于湘西,贾平凹之于秦地等,无论得意时还是失意时都会想到它,这一思乡母题深刻地镌刻在作家心理,表征着一种文化的力量,空间和时间是阻隔不了这一思乡情结的出现,不仅不会使其褪色甚至会愈久弥深弥坚。对于作为作家的左中美而言,对家乡的这种感情不能仅依靠模糊的童年记忆和乡土轮廓,更需要寻求一个情感的立足点和标记,而乡土风物在其表达方式的选择上就成为最好的路径和内容。其作品,在不断地“在家”的叙述中表达着“离家”的感情,把彝乡女儿对“地母”不褪色的情感隐藏在对家乡村庄的人、事、物的精雕细刻中。“几乎从我离开村庄的那一天起,我便开始一遍又一遍,向人讲述我的村庄”因这个村庄里,有着“我的母亲、我的家人、我的牛羊、我的村路、我的熟悉和亲切的村邻、我的春种秋收的土地”[4]它不仅被填写“在某一张表格的某一个窄窄的空格里”。还被作者“像剥水果糖纸一样小心剥开”在其众多的作品中“细细展露里面的春风桃花,稻香秋月”(《未完成的村庄》),作者不厌其烦地把这块大地上生长的木耳、菌子、山果、野草、瓜豆,甚至蚂蚁、蚯蚓、鸟雀、谷虫、狗、猪、牛羊展露出来,它们既是村庄为之骄傲的名物,更带着一种山乡质朴的感动。还有那浸染着作者的人生体验的山村中的一条条的小路、一座座的小桥、一棵棵的大青树都成为其回忆的对象,成为其笔底下典型的反复出现的动人的生态意象,成为左中美乡音、乡愁、乡情的情感寄托物,既传达着对彝乡大地的守望,又表达着对安宁大地生态美的体认,诉说着人与天地、与自然、与万物的和谐关系,表现出独特的天人合一的生态美。
可以说,山地意象和村庄情结是有着农村经历的作家坚守的最后情感高地。左中美的《安宁大地》如同刘亮程所写的村庄文学一样,邻里和谐安宁,民风淳朴而自然。在《安宁大地》里山地和庄稼是彝民生存的根本,是村庄形成和建立的基础。彝族农民唯一的依靠和收入就是土地上那点可怜的庄稼,有地就有了一切。因而,山地被寄予了美好期望而被取名为“月亮地”“金豆地”“凹槽地”等,与生活和生命联结的一亩五、八亩三、四亩五的山地,虽然没有平原上农地恢宏的气势,却让边地彝乡安宁的大地上有了一番别样的、充满了生命力的生气。夏天彝乡村寨的山地上到处长满了庄稼,苞谷地里的向日葵开出灿烂明媚的花,攀着苞谷秆的四季豆结出一串一串的豆子,一缕缕青烟在一片片地头缓缓升起。在“苞谷初熟的时节,一片一片地里都是看苞谷、赶鸟雀的同伴,‘嗒嗒的竹嗒声和‘喔喔的呼赶声此呼彼应”。[5](《守住一块地》)当夏天过去,天空开始一天天晴朗起来,成熟的秋黄渐渐在田野上呈现,山乡会“再次忙碌起来,人们拔豆子,撇苞谷,割稻子,稻把打在灌斗上,此起彼伏的‘嘣嘣声,像一支欢快的丰收进行曲。人们在劳动的汗水中,把一整个丰盈的秋天搬进了家门,搬到了楼上”。[6](《大春》)在这幅大地上的夏秋的生态图景中蕴藏着作家油然而生的亲切感和自豪感,荡漾着一种生活在经历了时代变迁而站在彝乡新的生活高度的获得感、幸福感。使得其作品在热爱家园、遵循四季轮回中,蕴含着一种依赖自然,敬畏自然的思想,正如阿米尔所言:“一片自然风景是一个心灵世界。”[7]左中美在一篇篇蕴含着对生命体验中的家乡的山地景观风物的诗情描绘文本中,传达着她对这片山地的深厚情感。山地上的牛、羊、猪、狗、鸡都会牵动作者的神经,甚至她还会为那山地上生存的蚂蚁、蚯蚓、滚牛粪的屎壳郎的命运而慨叹。屎壳郎如同一个沉默的武士,“只要粪球还没有最后推回到它的家里,它便会一次一次地放下失败,重新返回到牛粪堆旁,从头再滚一只牛粪球,再奋力地推回家”[8],西西弗斯式的毫不气馁,目的是让它的孩子在暖暖的粪球里出生后,睁开眼睛就能有吃的(《村道上的西西弗斯》)。可以说作者是带着女作家的母性在写山乡的,使读者频频感受到其平白语言里散发出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让人不由然升腾起莫名的感动,这些自然呈现出的生活场景就是其笔下生态美的内核,散发出感人文字力量。
另外,其文本还告诉读者,在作者生活的多民族小杂居的山乡永远与风俗相连,风俗可以说是中国乡村文化的延续,更是乡村的精神血脉。中国自古就重视风俗的传统,它不仅仅浮于人们生活的表面,是蕴含着丰富的含义的。风俗不仅反映出一个地区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反映出整个社会面貌,左中美深深懂得风俗常常是作为与生产关系并行存在的联结纽带和方式的一种“精神的”气候和环境而存在,是山乡精神中不能缺失的条件和方式。因此,她在散文写作中,总是不经意间就描绘出了纷繁多样的山乡风俗,并通过对风俗中蕴涵的人文历史和典故的描述,传达着她对山村风物的关照,表达着彝乡乡土精神的坚守和对新的希望的追求。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其笔下的彝族村庄是被浸染了其他的民族文化的仍然保持着浓郁的彝族文化的村庄。在其散文中,时常看到作者为读者介绍彝族人取名的习俗,“‘阿务在彝语里指老大儿子,在这个称谓里,同时也寄予了一种庄重的使命或者期待。在村里,但凡有儿子的人家,几乎每家都有一个阿务,后面的老二、老三、老四分别称为阿来、阿巴、阿切”等。对孩子的排行称谓也会平等地用到牛的身上,阿务牛是顶梁柱,犁地要唱牛歌(《守住一块地》[9])。每家都有自己的“木拿库”,人人都要遵守古德(《木耳》);还有对民族禁忌如有关喜鹊、乌鸦等的描写(《鸟雀》);解除病痛要修桥(《桥》);火把节要在门上插驱虫避秽的花椒枝,祈求五谷丰登(《庇佑》);每年有许多祭祀活动,如祭树神、上坟、祭祖;对彝山的特殊感情,使得他们丢了牛羊要祭山(《把鸡鸣留给村庄》)等。在《养一头猪过年》中,在表達彝乡人民对于红火日子期待的同时,也包含着乡里人对生命——包括动物植物的生命的看重和怜惜。散文写到为了过一个丰衣足食的年,奶奶每年都要从猪仔里挑出一头猪喂养,并像爱孩子一样溺爱这头猪,给它加食,还不让别的猪来觊觎它的好食。但当年关临近,按照彝乡风俗择日要杀猪过年时,奶奶一大早像往常一样给这头猪喂早点,还用手探一探那盆面食的温热后,最后一次去喂,“她守着猪食盆看着猪吃食的眼神没有了往日的开心和笑意,她的手依然轻轻抚摸着猪的脊背,眼神里充满了落寞和怅然……”[10]。当一切准备就绪要杀猪时,奶奶是不看的,她会故意离开去豆地或麦地里,时近晌午奶奶才抱着一抱猪菜回来。在这传统的年俗中,我们看到了善良的奶奶们对生命饱含怜悯和敬畏,也感受到作者在对家乡风俗的娴熟书写,从中可见出,因为生态思想的投射,其笔下的生命是的空灵与高远的是可触可感的,呈现出对生命个体的审思与关照。
二、讴歌勤劳、质朴的人性,呈现出和谐之美
村庄的人物、人性、人情是作家描述和解构的重要内容和对象,几乎是所有的乡土作家在对山乡描述的过程中不可缺失的方面,是表达乡村情结、皈依乡村生活的重要的方式。村庄里的人和事、理和情、爱和恨是乡村的精神和灵魂所在。在诸多同类作品中,写美好的景、美好的人、美丽而动人的故事,一直是作为正能量写作的作家们的重要价值选择和追求。对乡村人物的塑造是左中美《安宁大地》中表达乡村情感的重要方式。其散文写人往往是写人物生活中的某个片段、一段平常、一些琐碎,真实性较强,呈现出自然朴素之美感。
在左中美的散文中,所有的生活都是诗意的。作家对生活诗意表达的并不仅仅是个人对生活诗意的理解,而是一群体的集体体验和表达,是对变化了的和正在变化着的生活、生态和环境的解读,是对变换了的山水林田湖草等生活条件和环境的记忆和追述。虽然作者生活的新地(县城)与故土(乡下)的空间距离实际并不遥远,特别是在作者所居的彝乡,经过四十过年的进步和发展,从时空上大幅缩短了联系的距离,但作为心灵的“离居者”左中美在城市的蛰居中,却常常通过对山村人物的塑造来传达自己的情感,填补自己“不在家”的情感空缺。
细读左中美的散文,能真切地感受到她对美好人性的赞美。在其笔下,邻里和谐安宁,民风淳朴而自然,人人勤劳而朴实。哑巴阿老妹孤寡但遵循古德,阿从专替人放羊,是沉默而勤劳的,长发大伯是篾匠也是制香的手艺人,表叔阿台老乐观并不断为人们修桥(《桥》),此外还有劁猪匠罗四发(《劁猪》),给山村带来新奇的照相小伙子(《照相》),还有常穿白衬衫会做竹笛,常吹着《敖包相会》、听着收音机,对生活充满希望的哥哥和他的伙伴们……其中着墨较多的是奶奶、母亲和“我”。勤劳、善良一生的奶奶有对母亲、对“我”、对生活充满朴素的情感,她不仅会各种农事,还会捂芭蕉,会做出好多好吃的食品,养猪、养鸡,勤劳而善良,她让家里充满暖暖的爱意和勃勃生机。在对母亲的不少笔墨中,母亲不仅承袭着奶奶的勤劳和善良,还能做出许多的好菜——火烧茄子凉拌(《菜地》),做豆乳香肠,扬麦、纳鞋底样样精通,是从来闲不住的人,“夜里,一家人在火塘边闲聊时,母亲的手总是没有闲着,要么缝补,要么绕麻线”。(《葫芦及其他》),母亲是急性子之人“永远都在急着赶在时间的前面。每天,她总要赶在天亮之前起来,下地干活儿……她要赶在太阳下山、赶在天黑之前,把活多干一些,再多干一些”。[11]庄稼一般会在盛夏旺长,“别人家只管割,而母亲一定要赶在草抽穗之前割,说等抽了穗,草芯就硬了”。(《季节》)母亲生命中的大半时光都是在艰苦的劳作中过去的,母亲是勤劳的也是勤俭的,她总在“言传身教于我们最深切的一件事,就是勤劳、勤俭,始终信奉不移的信仰就是勤劳和汗水”。(《轮回》)散文贵在情感的真诚与率真,在这些细碎的生活描绘中,让读者看到了平凡母亲的不平凡。总之,在其笔下所述的人物都是彝乡大地上的代表,他们勤劳、勇敢、善良、智慧,邻里和睦,让平常甚至贫穷的生活却丰富多彩、井井有条,赋予了边地彝乡以强大的生命活力和乡村文化的传承力,在对这种生命活力的礼赞中传达和敬仰之情溢于言表。
左中美散文的诗意表达来自对所生活的坚实的云南红土地的热爱。在以女性的感知、母性的情怀和诗意的描述中,展现着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漾濞彝乡民众的生产生活的过程和状态,传达出深刻的历史记忆和现实的人文情怀。当然,这种看似平淡却隐藏着深深的情感爱意的表达,必然也直接地来自对家乡的父老乡亲的美好心灵与操守,以及山里人之间那种深厚真挚的情感的“真意真情”的书写话语体系。左中美深深懂得“散文贵在有我”,她以目击证人为叙述者的第一人称“我”来行文,即时传达作者的感受,增强文章的真情实感和现场感。“我”不仅是作品的叙述者也是作品中一个极为鲜活的彝家小姑娘。“我”见证着父辈们的山乡生活,也是这种生活的亲身体验者。“我”乖巧地会充满好奇地帮大人打猪草、提水浇菜、去赶雀、学扬麦、找蚯蚓、看屎壳郎推艰难地推粪球,感受到父辈的艰辛和生活的智慧,“我”还是一个有些调皮的有心计的丫头,在帮奶奶剥芋头时,使些小计谋专拣小的剥来解馋,“我”会迫不及待地偷吃奶奶还未捂熟的芭蕉,也会偷吃奶奶藏好的东西的一部分,再放回原处而不让奶奶发现(其实奶奶发现了也不说)等。左中美的散文不仅让我们看到村庄里淳朴的民风还感受到一种淳朴的人性和宁静和谐的生活。
三、用诗化而温婉的语言传递浓郁的情感之美
语言表达是作家的重要特质和特征的外在表现,是作家自我养成和塑造选择的结果,传达着作家不同的文化心理取向和特有地域文化信息,也是呈现作家风格个性的利器。散文“至诚不饰”的特点需要作家用质朴的语言真诚袒露磊落的心怀来传递浓郁的感情,这不仅是左中美《不见秋天》《时光素笺》《拐角,遇见》散文集中的特色,更是其《安宁大地》的特色之一。在其作品中常常能看到作者用极具地方特色的乡土地域文学的标示符号方言进行写作,采用不加修饰的接近彝乡山村的本真的农民常用之话语,来传达彝乡人的生活,从而使其散文具有了浓厚的地域色彩和乡土原生态味儿。
在其作品中,大量的方言口语会跃入纸面。如:“撇苞谷!”“没单子(可怜之意)”等。这些当地方言很土,但它承载着厚重的地域文化,成了这一方水土的一个标签,折射出特定地區地域的人们真挚淳朴的言谈以及勤劳的品质。文中还随时有俗言俚语呈现,如“善猎者亡于山,善游者去于水”“惊雷滚,鸡枞出”等。这种打着地域性的差异实体符号,经过左中美的审美过滤运用到其创作中,带来的不仅是一种语言形式的更新,也是一种叙述方式的更新,是边地文学一种特有的语言架构形式。正像美国生态作家瑞切尔·卡森所说:“如果说我的关于大海的书有诗意,那绝不是我有意赋予的,而是因为,假如非要不诗意的部分删去,就没有人能够真实地写出大海。”[12]左中美的散文就是一种发自深处的生命意识,用与自然契合的方式、独具个性的心灵表述,领悟生命的美与博大。
山乡情结、乡土情趣是左中美散文的灵魂所在,与作家的生活经历、生命体验和艺术追求紧密相连,密不可分。“这种莫名其妙的深切体验,乃是儿童时期经历过一连串情感体验的再次萌发”。[13]出身农村的左中美,自幼在农村长大,家乡的山水林田湖草就是她童年的乐土,是她生活、生态的重要组成元素。由其童年记忆重组而成的散文集《安宁大地》,就因回忆的时间跨度、作家的心理和思想的变化而带有固有的心理距离,而“这种‘距离达到一种‘陌生化”[14]的效果,这种“陌生化”使隔着岁月帘幕回望童年有了一种缥缈美,朦胧美和诗意美。也正是因为有了“心理距离”的存在,作家更能看清被忽视的事物的另一面,使生活中的思考和思想变得现实和深刻。所以在文字的述说中,虽有艰辛却没有抱怨,一切过去了的都变成了美好的记忆,这些美好的回忆给生活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中的作家提供了一个精神栖息地。
家园是每个人心中挥之不去的记忆和眷恋,是铭刻着欢乐与伤痛的长卷,乡愁是游远在外的游子时常涌起的心理冲动和心结,乡情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文学感动,乡音给我们以充满着泥土芬芳的语言表达话语,安宁与和谐是作者描写的世界也是她心中的祈愿。当然,作为散文作家,左中美的散文也还存在一些缺憾,作为一位少数民族作家,其语言上过多地使用方言土语,使其作品要走出这块大地在文化传播上受到限制和影响。左中美的创作有对往昔美好时光的回忆,她向读者呈现的是一个理想的乡土山村,用了较多的笔墨书写村庄中安宁的一面。在彝乡经历了伟大的脱贫攻坚革命实现了全面小康后,在持续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中,美丽的云南红土高原大地上的变革和变化,每天都在生长着新的故事,续写美丽彝乡的新人新事新风貌,也是作家在这个时代的使命和任务。我们期待作家写出更有力度的作品以飨读者。
注释:
[1] 2016年获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重点作品扶持,2020年6月获“第六届中华宝石文学奖”.
[2]贺雄飞主编.守望灵魂:上海文学随笔精品[M].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256.
[3]洪治纲.困顿中的挣扎——贾平凹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0,42.
[4][5][6][8][10][11]左中美.安宁大地[A].作家出版社,2017.2,P222、7、59、112、125、167.
[7][法]丹纳.藝术哲学(中译本)[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34.
[9] 《安宁大地·守住一块地》第9页.获中国国土资源报“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全国征文特等奖.
[12]王诺.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29.
[13]金元浦主编.当代文艺心理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5.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西南少数民族文学生态意识研究》(19XJA75100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西南少数民族文学边地书写与话语体系研究》(22XZW02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邓家鲜(1965—)女,白族,大理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张霁薇(1989—)女,白族,任职于滇西技术应用大学,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