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艳与忧伤,幽微与赤诚
何奕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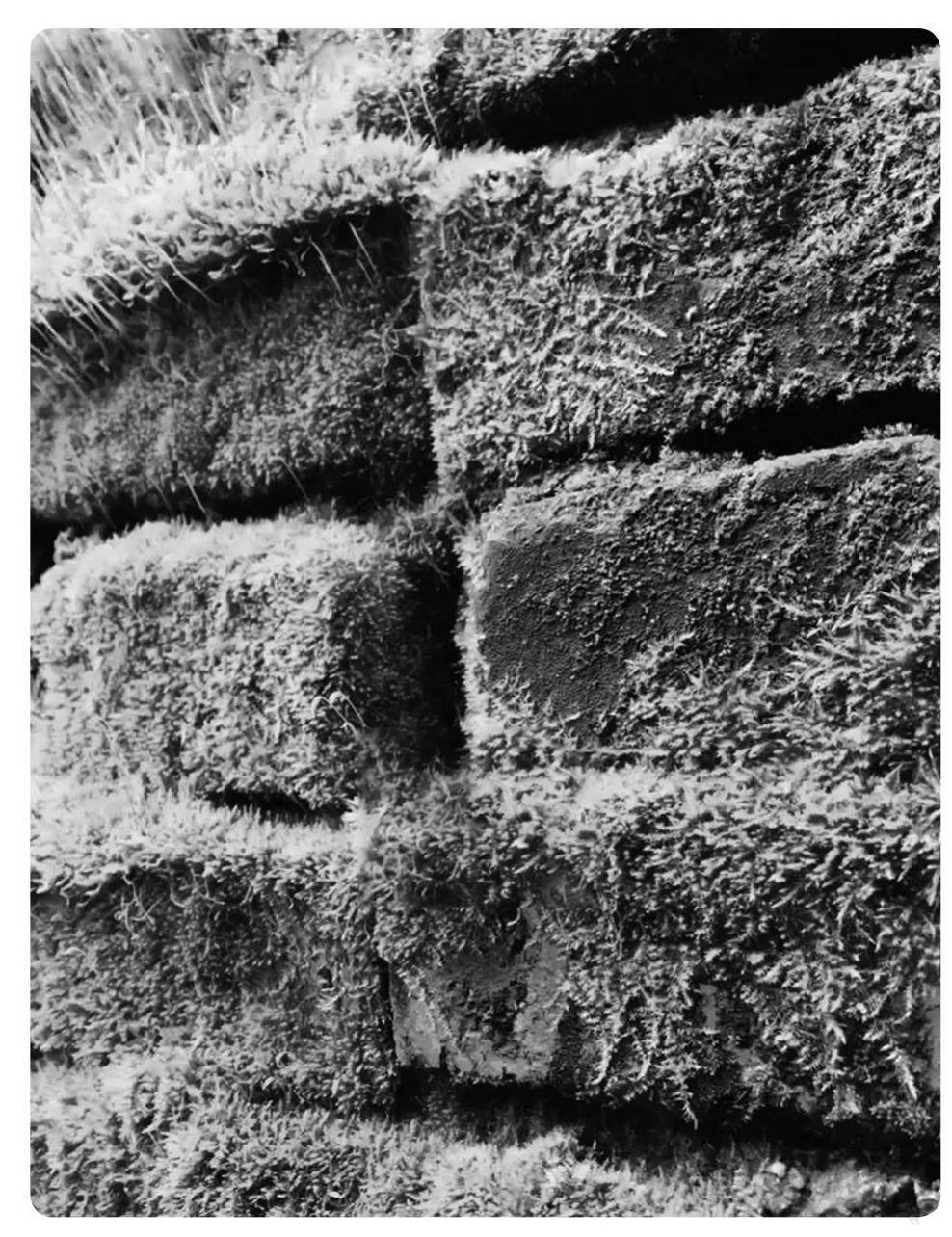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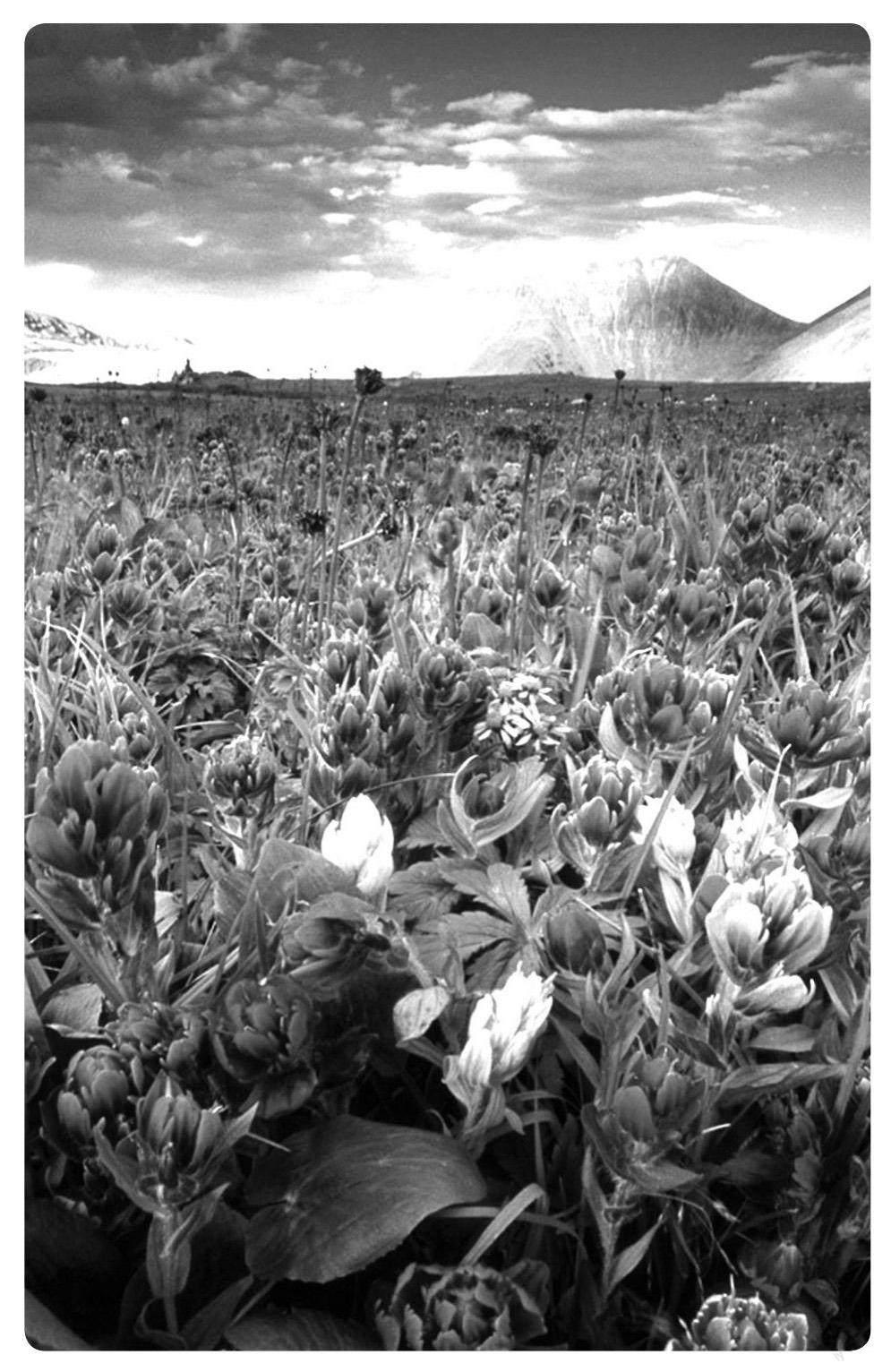
一、主题:暂时的明艳与恒久的忧伤
文珍擅长以舒缓自如的笔调去推进如生活倒影般琐碎而又亲切的故事,适度地抓紧、放下,让人物故事“在最痛苦或最欢乐的一刻戛然而止”。她曾在《后记:行云作柒,止风入水》里写到,这些“都是我失去的时间……几乎和做过的梦一样不可复得”,即使它们并不全是真的。这些人物皆有着恰到好处的明艳与忧伤,他们想要成长、抵达自我,就面临着“更多可能性的不断脱落与失去”。不少学者倾向于将她的小说主题归结为“逃离庸常”,而将其内在原因指向“现代人的精神危机”,这固然是没错的,但笔者更愿意用“暂时的明艳”与“恒久的忧伤”这样两个较抽象的词汇来概括《柒》这部小说集中的作品所共有的特征—不仅是隐含作者塑造人物、剪裁故事时表现出来的审美倾向,还体现在真实作者想要通过这些赋予现世人生的别样意义以及带给读者的启发上。
当代女作家张天翼(笔名“纳兰妙殊”)曾在一篇随笔中写道:“她的小说集《柒》是一本绿书,她自己讲这绿是‘黑暗之心的丛林里静静烧起的磷火。”(《文珍:珍馐其文,赤子其人》)笔者认为,文珍本人给出的这句解释恰恰暗合了“明艳与忧伤”的主题,“黑暗之心的丛林”即代表浓重的精神孤独与荒凉感,“磷火”则是那虚幻的爱、自由与希望。文珍站在一个小资女性的鲜明立场来写作,着眼于婚姻爱情和情感关系,但并不旨在赞颂浪漫圆满的爱情神话,而是将爱情作为当下人际关系书写的切入点,承载社会历史事件的支架。不难发现,她所写的主人公与普罗大众是有一定距离的:自命清高的女研究生,如徐冰、曾今;事业有成的已婚女性,如苏卷云、陈季风—她们或受过良好的教育,美丽温柔,才华横溢,是女神般的存在;或有一份稳定的高薪工作,甚至还有一个爱她至深、忠心能干的丈夫,生活富足,令人艳羡。即使是唯一一篇站在男性视角反观女性的《肺鱼》,其主人公也拥有过硬的博士学历与不错的工作能力。他們不约而同地有过暂时的明艳风光,却在更为长久的生命里收获无人能解的孤独、忧伤,甚至绝望,便将这种精神上的苦闷与困顿诉诸于追寻所谓的“爱与自由”,隐隐流露出作者对现代人的精神实质抽丝剥茧后的悲哀情绪。小说中的人物一边崇尚自由,身为隐含作者的文珍也一边反省自由。
(一)“曲高和寡”的幻灭
《牧者》中的徐冰外表高挑出众,成绩优异,在大学里特立独行,唯有如寒梅般有着一身傲骨的青年教师孙平才能入她的眼—她将师生之间对专业问题的讨论视作“渔樵问答”,并颇有“高山流水遇知音”之感。可是身为其精神引领者的老师并无意挑战道德底线,也拒绝与她有超出师生关系的亲密举动,反而像牧者一样,放飞了这个与自己有深度精神共鸣的优秀女学生,不惜顶着流言也要送她去哈佛当交换生,并以这种方式弥补了自己年轻时未能留学的遗憾。这般始终克制着的情感,真的能称之为“爱”吗?笔者认为,他们之间其实更像是两个桀骜的孤独者对彼此的惺惺相惜,若真成了恋人,也并不一定就合适。如孙平所说:“我们这类人,太自私了,根本不配谈爱情。也真的没必要。……彼此之间什么都没有,更纯粹,也更长久。我还等着你学成归来和我同事。”小说结尾,徐冰望着孙平在楼道内渐行渐远,而他们的关系也一如隐喻般,令人意难平。而这正体现了文珍处理故事之妙,她给了人物以最合理的结局:故事到此为止,一切尽在不言中,不多也不少,却余味无穷。
与之相似的另一篇小说《暗红色的云藏在黑暗里》中,女主人公曾今年轻靓丽,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有着青年艺术家不加掩饰的锋芒与自信。她原以为“草根”出身、有着独特大胆之风的画家薛伟是和她一样敏感而又孤独的人,因他“最初想要在世上安身立命时极度渴望他人认同的强烈欲望”,两人成了最好的知己。但在薛伟眼中,曾今是他“向上爬”的最佳跳板,是他游走名利场的进阶通道;他经由她认识了许多业界知名人士,并在利用完之后毫不留情地放弃了这个曾经的朋友,他追逐艺术梦想的动机已然不纯。薛伟身上很明显存在着一种底层人物的生存困境:虽然也曾怀着一颗滚烫的心来到大城市奋力拼搏,然而面对经济的重压与物欲横流的现实世界,他无力改变眼前的残酷现状,便自甘与之同流合污,在苦苦挣扎之中丑态毕露,其自私、阴暗、暧昧的行径让一心想要保持自我之纯粹的曾今瞠目结舌。薛伟身败名裂之后,曾今重又退回到了孤独的领域,顾影自怜。
以上这两篇小说中的女性都是强悍而孤高的,她们年轻、优秀,丝毫不弱于自己所倾慕之人,但也正因如此,她们所追求的东西(爱情、前途)才更显得理想化;她们越是明艳,就越容易对身边的人乃至整个世界失望。
(二)“美满家庭”的叛逃
《你还只是一位年轻人》中,正处在事业上升期的女强人苏卷云有着众人艳羡的幸福婚姻,却因为坚持“丁克”被丈夫视为异类,并在一场精心设计的约会中意外怀孕,从而得了抑郁症。她说:“没人比我更厌倦这个看似井然有序按部就班的世界了,也讨厌所有看上去充满希望的东西……我痛恨这个世界所有命中注定的循环往复、政治正确和不得不。”而实际上,童年时原生家庭教育方式的缺陷,青春期过早明白的人情冷暖,都给内心敏感又脆弱的她带去了影响一生的痛苦和不安,再加上成年世界的生存压力以及对于养育本身的恐惧想象,方方面面叠加起来,成了她抗拒怀孕的理由。她不相信自己能给孩子带去健康安稳的爱,她也不相信自己的生活会因孩子的到来而变得更美满,她只是不希望自己曾经历过的一切再在孩子的身上重演罢了。这种无处申诉的精神困境让她最终选择了不告而别,在举世同欢的元宵之夜,谁也不知道她是绝望地杀死了自己的孩子,抑或留下这条可怜的生命,继续走完这荒凉无助的余生。
《开端与终结》中的陈季风同样年轻有为、生活安稳,也有一个真心爱她的丈夫,但她每时每刻都想要逃离。在物质生活得以满足之后,她便想要寻求精神上的认同感:她一个人看话剧,一个人看画展,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走在北京街头。然而,丈夫萧元并不理解她的这些小资爱好。直到遇上同样喜欢诗歌的许谅之,她才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他—因为他们有着惊人相似的孤独,并且能在这种无聊但隐痛的生活中互相填补精神的空洞。令人感慨的是,两个表面风光的成年人对情感的背叛,只是叛逆、任性,不满足于轻易得到的东西,一味地追求更多自由与可能性,从而在焦虑与快感中找寻真正的自我、重塑个人秩序。但也正如标题所言,他们之间再怎么拉扯也注定不会有结果,是一场没有“开端与终结”的虚妄之爱。
(三)明艳其外,忧伤其中
相比之下,《夜车》和《肺鱼》虽未将笔墨重点放在刻画女性角色上,但依然没有脱离“明艳与忧伤”的范畴。《夜车》中的老宋重病将死,“我”却与他不顾一切奔向东北,在无法确信未来的迷茫与虚空中抵死缠绵,只为完成生命中最后的旅程,留下美好的回忆。不幸的是,病魔终于还是夺走了老宋的生命,而“我”在他的葬礼上,首先想到的却是“穿橙色、化淡妆、吃黑巧”,只因老宋生前喜欢—这些人物是多么渴望在外部世界留下自己存在过的光鲜痕迹,试图以物质上的丰足掩盖自己精神上的孤寂,即使面临生离死别与失去挚爱的无边忧伤,亦不例外。《肺鱼》中始终与妻子无法沟通的“他”借工作之便换了一个又一个寄托情感的对象,好像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证明自己并不孤独,但“他”其实只是没有找到与妻子交心的相处模式,因而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被爱,于是“想找人说说话”,以期获得精神上的交流和抚慰。然而,当“他”在外风流消遣适意之后,回到沉寂的家中,依然要面对妻子身体与情感的双重拒绝与冷漠。
《风后面是风》里“我”虽然也曾有过轰轰烈烈的爱恋,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斩断情丝、努力工作、独立自主。失恋后的“我”沉迷于做各种美食,充实了自己的单身生活,已然不再惧怕孤独,但仍会因为这个社会对大龄单身青年的种种不善而感到发自内心的无力和无奈。
总览这七篇小说,笔者认为人物身上“恒久的忧伤”是文珍竭力想要展示的现代都市人的精神状态。她用理性现实而略带伤感的笔触写出了繁华都市中的社会人生百态,人们沉浮其间,虽则各自有过风光时段,却始终如一座座孤岛般,在日复一日的庸碌中独自漂泊流浪。他们似乎永远保持着一种清高优越的姿态,探寻着心目中最纯粹赤诚的爱,只因爱是他们扰攘生活的最后寄托,是精神荒漠里唯一的月牙泉。他们渴望与世俗划清界限,追随本心,逃离庸常,可是逃离之后发现,“山后面仍然是山,风后面仍然是风,生活背后仍然是生活,世界尽头也仍旧是日出日落”(刘梦瑶、相龙烽《起来呵手封题处,偏到鸳鸯两字冰—文珍作品主题分析》)。
二、叙事:洞察幽微,书写赤诚
文珍有一种叙事天赋,她擅于把握人心里那些隐秘而微妙的复杂情感,却总以简洁准确的语言将读者带入其中,身临其境般体察那些熟悉又陌生的故事,以及有趣但真实的情感细节。她的小说,虽未直接触碰宏大的社会历史事件,但因其大多着眼于青年人的日常生活,读者或多或少总能在里面找到自己和身边其他人的影子—换言之,她的小说所产生的文学效应,是颇具群体性的情感认同的。金赫楠评价道:“文珍的小说那种体贴入微的叙事,正是通过其强大的代入感和感染力,实现了一种叙事效果:让大时代、社会、他者与我们自己的生活与情感发生了一种心意相通,发生了真切的关联。”(《关于〈柒〉,关于文珍的小说》)她关心社会现实,也关注流行文化,注重女性意识的昂扬,也同情小人物的艰难命运。文珍便是一直秉持着“洞察幽微”与“书写赤诚”的态度来写作,且她的文笔显然也是令人惊喜的—可古典,可俏皮,可如哲人,亦可亲民。她并未刻意模仿张爱玲的华丽与苍凉,也并非太平盛世下的无病呻吟,而仅仅是将目光投向我们最容易忽视的俯仰之间,便描绘出了生活的真实、厚重与饱满。
《夜车》中的老宋与“我”在年轻时互相猜忌、挑刺,放纵感情大吵大闹,直到离婚时“我”才得知老宋已患上绝症,于是两人言归于好,相约最后一次去往远方,悔恨当初没有好好珍惜彼此,虚度了时光。这样两个明明相爱却把最尖锐的棱角指向对方的人,最终达成和解竟是在生离死别之前,委实令人扼腕。如他们这般,宁愿相互折磨也不甘守着岁月静好,自以为爱得轰轰烈烈的有情人,实非世间罕见。《肺鱼》以男主人公的有限视角看待自己沉默的妻子,他觉得她就像虾一样冷漠,总是背过身去,隐藏情绪、拒绝沟通,于是他也眼睁睁地看着婚姻出现隔膜而无动于衷,宁可出去花天酒地,甚至还反过来质疑妻子的忠贞,以确立自己在家庭中的强势地位,并不断彰显自身的优越与权威—种种劣迹皆反映了女作家对现代社会依旧盛行的男权中心文化的深度反思。《开端与终结》中的陈季风并非不曾真爱过自己的丈夫,也并不想真正放弃自己原有的幸福家庭,她只是厌倦了每日下班回家坐在电视机前追剧的庸俗丈夫,而对突然出现的,与她有着惊人一致的小众爱好的许谅之感到新奇和喜悦,仿佛已经黯淡的生命中乍现了一颗流星。
文珍的叙事是碎片化的,而以人物心理的流动来弥补情节上的断续之感,恰恰也是這些小说人物之间缺乏沟通的真实写照。这几个短篇中出现的感情问题,多半是由于倦怠、怀疑、嫉妒与隔阂,主人公自信于他们所掌控着的当下命运,肆意消磨一段感情最初萌生时的欣喜与纯粹,而用冠冕堂皇的理由粉饰自己违背道德的行为、抚平内心产生的罪恶涟漪,殊不知他们终是对悲剧的结果充满了无法挽回的无力感与迷茫感。文珍正是以这种方式介入社会与生活,打开文学的视野,让我们看到了现实而残酷的婚姻真相。她精心择取了生活的片段,捕获人物内心的微澜,以细腻自然、极少雕琢感的笔触,准确阐释了人物的内在行为逻辑与情感需求,这就很能体现出她在北京大学读创意写作学硕士后培养起来的专业优势以及兼具南北风格的写作特色。
2020年出版的小说集《夜的女采摘员》的封面,有这样一句评点:“为失败者安放心灵,为无名者立传,为孤独者道出深情,为脆弱者重建爱的秩序。”笔者认为用来概括《柒》里面的某些故事也很合适。文珍小说的精神内核就在于,她既能写出现实的黑暗与绝望,又能令人感受到爱的光芒与温暖。为了达到这个叙事效果,男性往往便是她小说中“苦难和悲哀”的代名词,他们给原本脆弱单纯的女主人公带来了可喜的成长,是围绕她们的情感诉求产生并加以塑造女性形象的,不太具备作为独立角色存在的鲜明特征,也普遍缺乏着立体性和变化性,不够充实和饱满。然而,正因为男性角色退居次要地位,女性作为主角时的精神感染力和情感冲击力便也突出了;在这一系列不算理想的男性形象的衬托下,女性角色所表现出的那种至善至诚的爱与救赎,便可轻易令读者感同身受。
总体而言,文珍在处理小说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的逻辑上是有效且合理的。她显然很能理解当下社会生活中还占据着主导地位的男性话语语境,因此在其小说创作中刻意忽视了男性人物的作用,让其叙事效果带上了鲜明的女性主义意识。她能够洞察幽微,擅长从生活的细微角度切入故事,刻画那些游走于喧嚷城市中的孤独灵魂,关怀那些游离主流之外的人群的生存状态,但其叙事的基调又不是一种漂浮的悲伤。她的文字敏感细腻,却是以一颗赤子之心,温情坦然地书写苦痛,字里行间起伏跌宕的情绪,都着实敲在了读者的心上,让人喜人物之喜、忧人物之忧;她真正做到了用一种充满包容性的文字,让出身迥异、经历不同的人发生共情,在故事里找寻自我的痕迹,并得以慰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