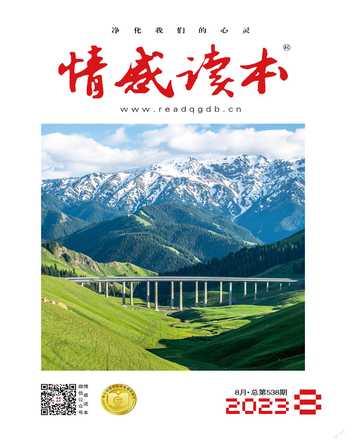下雪的时候很温暖
张曼娟
这个冬天,气温骤然下降,我站在教室外张开嘴,看见呵出的热气变成白色烟雾,孩提时代养成的习惯,借此探知季节的嬗递。学生从旁边经过,缩着脖子与我招呼:“好冷啊!说不定要下雪了。”“是呀,下雪就暖和了。”我说着,和他们挥手告别。想到自己说的话不禁好笑,下雪就暖和了,这算什么逻辑?但,这其实是我真切的感觉,窗外雪花飞舞,房里的火炉暖烘烘烤着面颊,圣诞树的灯光闪呀闪的,全家人守在一起,不可取代的奢侈。
两年前的冬天,父母去美国探望弟弟一家人,那是三十多年来我的第一次独居经验。刚开始是很兴高采烈的,每一餐都在外解决,快餐、西餐、火锅、客饭、定食、素菜、自助餐……调配着吃,看心情决定。当天气愈来愈冷,我把圣诞装饰花环挂在门上,邻居小朋友看见都很欢喜,总要跳起来拉一拉花环上小白兔的长耳朵,作为打招呼的方式。过不了几天,白兔的耳朵就成了灰色的,我把它另一只耳朵朝外放,这样的话它就会有两只灰耳朵了。我在一种莫名的兴奋情绪中等待圣诞节,等待新的一年把旧年翻过去。
可是,独居的新鲜感逐渐消失,我总是不能决定这一餐该吃什么,因为没有真正想吃的食物,觉得人如果不必进食就可以省掉很多麻烦。在不同的房间和床铺睡眠也不能令我睡得更好,偶尔做噩梦时,还记得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所以不必呼喊或者哭泣,反正不会有人关心,也不会有安慰。于是从悸怖中转醒,在寒凉的空气里轻颤,而后慢慢平静下来。百货公司的岁末清仓特卖,扶老携少的一家人使我停下脚步,不远不近地观看。曾经,我们也是全家出动逛街购物的一家人,然后一块儿开车去淡水吃海鲜。弟弟七年前去留学,接着就业、结婚、生养小孩,这个家的成员变多了,却分散在天涯海角,可以聚在一起的机会十分稀少。有一次,我们约了一起去香港旅行,弟弟一家三口从美国东岸历经长途飞行,在机场相见的时候,一岁半的小侄儿毫不认生地扑进我怀里,大人都吓了一跳,这小孩儿用什么样的能力去辨认,或者去记忆一种特殊的血缘牵系?于是,一向羞怯的他并不迟疑,在流动的人群中,摇摇晃晃地,奔向我站立的方向。那几日同游时,小男孩对我的依恋成了一种新鲜明锐的感受,仿佛开启生命的另一扇门。
小时候我羡慕别人有爷爷奶奶疼惜,有叔叔姑姑可以撒娇,如今,弟弟不太可能回家鄉来,就像我也不太可能放下工作或者写作,到美国去放长假,都是不可能的,所以不能团圆,不能在一起。所以,我看着那一大家子嚷嚷闹闹买东西的时候,有一种渴望蠢蠢欲动。当我走过那些华丽的橱窗,璀璨的灯花,自己一个人穿越马路时,格外感觉到寂寞和孤独。
人,是生而孤独的。但人并不一定非孤独不可。
什么是最重要的呢?我一遍又一遍,反反复复地问自己。终于,我向学校申请了留职停薪,一整年的时间。一年没有薪水呀,朋友劝我仔细考虑,但我觉得无比富有,因为这一年里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我的。听说我要离开,关心的人劝我三思,难道不怕目前拥有的会发生变化?我谢谢这些好意,打电话去航空公司订了机位——美国东岸,和我最亲爱的家人在一起。临走前接受访问:“什么重要的原因使你必须离开?”我说:“因为想跟全家人在一起,共度一个冬天。”这答案显然令主持人迷惑,这有什么重要?而我偏偏觉得,在这时候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了。
再相见的时候,小男孩已经三岁了,更有自己的主意,更想要人陪。他以前不敢一个人到楼下来,自从我住楼下,他有了探访的对象和理由,楼上楼下跑得相当勤奋。窗外开始飘雪,我开始写作,他把自己的蜡笔全数搬运下来,坐在我的腿上,陪我写稿。这样的陪伴因为太彻底,所以常常演变为我放下钢笔,拿起蜡笔和他一起画图。写作进度严重落后,小男孩被限制在姑姑下楼时不准追随,唯有要吃饭时,他可以下来通告,他得令下楼,搬运一堆蜡笔,完全不提吃饭这码子事。结果演变成楼上的在饭桌旁痴痴地等,楼下的色彩缤纷画得不亦乐乎。
因为冰雪封天盖地,我们把逛百货公司当成重要的娱乐和运动,全家六个人声势浩大,四处采买圣诞装饰,想把门窗装扮成最出色的。夜里我们开着车在社区巡视,看看别人的创意与巧思,有时候开几十分钟的车去其他的社区参观学习。百货公司有位圣诞老人,等着和小朋友合照留念,我们的小男生心向往之,却羞赧得很。每天每天,我们陪他观看很多小朋友和圣诞老人拍照,通通平安无事,直到他愿意尝试了。我写给朋友的信上说:“这个星期每一天我们都去看圣诞老人,左看右看,前看后看,今天,咱们家的小男生终于肯拍照了,然而在圣诞老人温暖的怀抱里,他的表情竟然是惊恐的。”这有什么重要?我觉得重要就好。圣诞节那夜下着雪,我们坐在一起聊天,小男孩把椅垫塞给我们每个人,撒娇并且扯赖地,在我们的拥抱与亲吻中爬上爬下。爷爷、奶奶、姑姑,我想,他的成长记忆里可能会有这一段,就算忘记了围绕在身边的人是谁,但,曾经被爱过的感觉是不会忘记的吧,这样也就够了。
我也不会忘记,当天气愈来愈冷,我在回忆的炉边烤火,觉得很温暖。
冷远思摘自《孤独,刚刚好》
(北京联合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