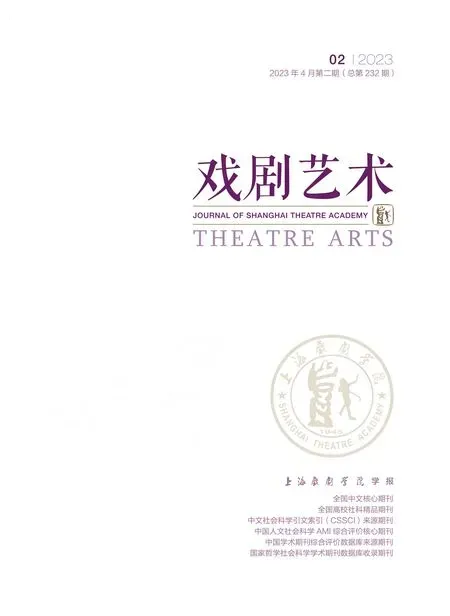欧阳予倩“红楼戏”审美形式新探
王聿霄
文艺作品的“审美形式”,是指“把一种给定的内容(即现实的或历史的、个体的或社会的事实)变形成一个自足的整体(如诗歌、戏剧、小说等)所得到的结果”(1)[美] 马尔库塞: 《审美之维》,《审美之维——马尔库塞美学论著集》,李小兵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211页。。马尔库塞的定义,揭示了作品审美形式的内在构成机制: 其一,作品的“审美形式”蕴含了创作者有关社会人生的观念;其二,创作者所使用的艺术表现手段,遵循审美形式自身的逻辑,而不是给定内容原本的逻辑,所以当给定内容被纳入艺术形式之中时,需要遵循其规定性;其三,创作者构建作品完整的审美形式,就是将“给定内容”与“艺术手段”两个层面融合为一个整体。
欧阳予倩自编自排自演的“红楼戏”是其早期舞台生涯的代表作。“红楼戏”审美形式的构成与特征是欧阳予倩研究的重要话题。从上述内在构成机制来看,“红楼戏”完整的审美形式实际由两个层面构成: 欧阳予倩融入这些作品的社会人生观;欧阳予倩在创作中使用的艺术手段。不过,目前学界并未对上述两个层面做整体分析、关联研究,前辈学者大多只选取某个层面进行讨论,或是讨论“红楼戏”中所叠印的主体内面,或是讨论“红楼戏”的表现手段。前者认为“红楼戏”通过剧中人物的命运,尤其是女性人物的遭遇,表达了欧阳予倩反抗封建礼教的社会观,或颓废避世的人生观;后者认为“红楼戏”的情节结构符合西方戏剧的本体特征。
一、 学术史检讨
关于“红楼戏”中主体寄托的研究,有以下两个主要观点:
曲六乙认为: 欧阳予倩创作“红楼戏”的首要原因是,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大背景下,“有意识地把这部封建贵族兴衰史的小说,运用戏剧形式再现于舞台之上,通过视觉形象向广大群众宣传反封建、反礼教的进步主张”;欧阳予倩“把林黛玉等的形象作为武器,向封建主义进行冲击”,所以“红楼戏”不是唯美主义作品,而是现实主义作品。(2)曲六乙: 《欧阳予倩和红楼戏》,苏关鑫编: 《欧阳予倩研究资料》,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第302页。针对这个观点,陈建军提出:“在五六十年代《红楼梦》被看作反映封建社会没落的伟大作品的情形下”,当时的研究者自然会将欧阳予倩的《黛玉葬花》《黛玉焚稿》等作品“当作反封建的作品来解读”;从欧阳予倩的人生经历和“红楼戏”的内容来看,“唯美主义”的解读“更接近欧阳予倩的原意”。(3)陈建军: 《论欧阳予倩早期艺术人生中的唯美主义》,《戏剧》,2012年第2期。陈建军结合欧阳予倩创作“红楼戏”时所处的历史背景、遭遇的家庭变故,指出这些作品实际上表现了创作者“苦中作乐”的唯美主义立场: 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欧阳予倩心中充满颓废的情绪,于是以消极避世而不是主动进攻的态度,反抗来自外部环境的压力。(4)陈建军: 《欧阳予倩与中国现代戏剧》,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07页。
本文在此列举这两种观点,并突出二者之间的抵牾,不是为了评判孰优孰劣或谁对谁错,而是希望说明如下事实: 观众或批评家可以对作品中的思想观念做出不同的解读。这些解读无论是相互一致,还是针锋相对,终是各有其理。虽然不同的解读者有不同的视角和理论依据,但是我们的解读不能脱离具体的人物形象和艺术表现手段,而只从创作者的个人经历中提取一些观念作为“红楼戏”审美形式的特征。这些抽象的观念与创作者融入审美形式的社会人生观未必完全一致。
比如,在创作《黛玉葬花》时,欧阳予倩“从各种角度体会黛玉那么一个人,那么一个父母双亡的孤女,寄居在荣国府那么一个阔亲戚家里,她的心情是怎样的”(5)欧阳予倩: 《我自排自演的京戏》,凤子等编: 《欧阳予倩全集》第6卷,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267—268页。。也就是说,创作者集中表现的还是人物具体的感情、心理。此外,近年来研究者“反封建”的解读主要依照1990年出版的《欧阳予倩全集》中收录的《馒头庵》一剧。据陈建军考证:“1949年以后欧阳予倩的各种选本及全集中的《馒头庵》剧本已经被改得面目全非,与原初的本子相差很大。”(6)陈建军: 《欧阳予倩与中国现代戏剧》,第101页。我们从《戏考》和杨尘因所编《春雨梨花馆丛刊》所载的《馒头庵》剧本来看,相较于《全集》中收录的版本,人物的感情、心理状态确实有明显不同。
但是“唯美主义”一方的观点也未必完全符合“红楼戏”所表现的思想观念。在欧阳予倩改编的《黛玉葬花》中,宝玉的行动弥补了黛玉内心的缺失,最终两人心意相融。这部“红楼戏”并非传达“颓废的情绪”,而是突出了一种积极的因素,即爱情的“实现”。此外,欧阳予倩自命的“唯美”有其特定内涵: 坚持艺术以情动人,反对为了政治宣传在表演中插入与剧情无关的演讲。而对于自己创作的艺术作品,欧阳予倩“无论遭遇怎么不好,从不肯自名为沦落以显其颓废的美”(7)欧阳予倩: 《自我演戏以来》,凤子等编: 《欧阳予倩全集》第6卷,第48页。。所以“外废内颓”式的“唯美主义”,也不能概括欧阳予倩在“红楼戏”中传达的情感意蕴或思想观念。
总之,如果忽略了作品中具体的人物形象,以及创作者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所用的艺术手段,我们对于审美形式的认识便会比较笼统。同样,我们也不能无视作者对社会人生的认识而单纯地将“艺术表现手段”等同于审美形式。比如,有前辈学者通过分析“红楼戏”的剧情组织结构方式,论证其审美形式具有现代性特征。这种思路有一个值得商榷之处: 我们深入作品审美形式的内在构成机制,探索“表现手段”与“思想观念”的融合过程,是否意味着可以直接将审美形式中的元素等同于某种社会学术语呢?
陈珂指出: 欧阳予倩创作的“红楼戏”,审美形式方面最突出的特征是“其编剧的原则,更是以戏剧性而不是叙事性作为基础的”(8)陈珂: 《欧阳予倩和他的“真戏剧”》,北京: 学苑音像出版社,2007年,第92页。。刘汭屿对此观点进一步拓展,指出“红楼戏”是以“西方主流戏剧的精髓”,即“戏剧性”改造中国戏曲,使其“‘艺体’发生根本改变”,展现了欧阳予倩“西体中用”的戏曲改良思路。(9)刘汭屿: 《南欧北梅——民初京剧红楼戏与戏曲现代化的两种路径》,《文艺研究》,2020年第12期。刘汭屿认为“红楼戏”实现了戏曲本体层面的变革,因而其审美形式具有现代性的特征。针对“戏剧和叙事”的本体之别,谭霈生指出在戏剧中“居于主体地位的是人,是人的内心与行动的契合”(10)谭霈生: 《戏剧本体论》,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81页。。刘汭屿以此为据提出:“质言之,西方典范戏剧是人文人本精神的产物,戏剧中个体的人的主体性高扬”,而欧阳予倩的“红楼戏”是以“戏剧体”创作的,所以这些作品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即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关于“人”的本体观。(11)刘汭屿: 《“两栖兼通”“西体中用”——欧阳予倩戏曲革新理论研究》,《戏剧》,2019年第3期。然而谭霈生在此所言的“人”,专指“戏剧人物”,是戏剧艺术形式结构的要素。其所谓“人的主体地位”仅限于研究领域之内,专指“戏剧人物”在戏剧形式结构中的定位。而“人文人本精神”中的“人”,是现代哲学或社会学的术语。“人本精神”是否能概括现代社会的特征,不属本文探讨范围。我们在此强调的只是:“艺术作品具有怎样的形式结构”和“哲学、社会学中如何认识人的本质”,并非同一领域的问题。人物在戏剧艺术形式结构中的定位,只能证明在不同的艺术门类之间,塑造人物形象的方式不同,而不能证明某部戏剧作品在哲学上、社会学上具有“人本精神”或“现代性”。所以,我们不能将审美形式中的元素与一种社会学、哲学术语相混淆。仅从作品的情节结构出发,我们无法触及作品整体审美形式的特征。
通过对前辈观点的辨析可以发现,抽象的“思想观念”和单纯的“表现手段”,都不是作品审美形式的特征。从审美形式的内在构成来看,思想观念和艺术表现手段是无法剥离开来的。两个层面相融,才能构成一部作品完整的审美形式。探索欧阳予倩“红楼戏”审美形式的特征,对两个层面的分析缺一不可。本文所谓“新探”,意在借鉴和反思前人成果,通过将上述两个层面贯通考察,对欧阳予倩“红楼戏”审美形式的特征做进一步探索。前人的成果给我们奠定了充分的基础,并启发我们深入研究某些根本性问题,比如欧阳予倩在其早期舞台生涯中持何种社会人生观念,或者“红楼戏”与欧阳予倩的戏曲改革思路有何种关系等。
欧阳予倩共创作过九部“红楼戏”作品。对于那些没有剧本存留的作品,我们可以根据史料推测主要情节。但是仅仅依据情节,我们无法看到作品中具体的、完整的戏剧场面。而在现存的“红楼戏”剧作中,只有京剧《黛玉葬花》《黛玉焚稿》《馒头庵》三部作品的版本相对可靠。《欧阳予倩全集》中收录的《晴雯补裘》剧本,剧情与欧阳予倩在《我自排自演的京戏》中的回忆有明显出入,所以该版本存疑,在此不多作考辨。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大东书局出版的《戏学汇考》中收录了《宝蟾送酒》的剧本,但欧阳予倩的回忆录中说这版剧本“虽明明写着是我的剧本,可是和我的不同”(12)欧阳予倩: 《自我演戏以来》,凤子等编: 《欧阳予倩全集》第6卷,第56页。。《戏考》中也收有《宝蟾送酒》的剧本,但是并未注明作者,而且其情节与欧阳予倩回忆录中所描述的有较大差别。笔者另外发现一部名为《晴雯撕扇》的剧本,据杨尘因称欧阳予倩“手编此本”(13)杨尘因: 《春雨梨花馆杂剧·欧阳予倩之〈晴雯撕扇〉》,《新世界》,1918年12月14日。,但是在欧阳予倩的回忆录中并未提及此作,所以该剧作者待考。本文将以《黛玉葬花》《黛玉焚稿》《馒头庵》三部作品为考察对象,分析欧阳予倩“红楼戏”审美形式在主体寄托和表现手段两个方面的特征。
二、 审美形式特征之一: 对“家”的渴求
在创作“红楼戏”时,欧阳予倩基于自身的社会人生观,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感情体验。他将这种感情作为核心人物的动机,融进了作品的审美形式中。所以“红楼戏”审美形式的特征之一,在于通过核心人物的动机,表现创作者基于社会人生观产生的感情体验,即对“家”的渴求。
“感情”是欧阳予倩戏剧理论中的关键性概念。他指出戏剧的表现对象“不在知识,而在情绪。艺术是拿感情情绪对感情情绪的东西。譬如我们读诗,诗中的情绪引起我们的情绪,彼此相接触,而成兴味,并不是诗中有哲学的理论,或者科学的方法”(14)欧阳予倩: 《戏剧改革之理论与实际》,凤子等编: 《欧阳予倩全集》第4卷,第29页。。欧阳予倩所说的“感情”,至少有如下三种特性。
其一,“感情”与“知识”有本质区别。艺术创作者的“感情”与数理科学中的“知识”不一样: 前者必须通过感性的艺术形象表现,无法用数理公式说清楚。
其二,“感情”源自创作者积极的社会观与人生观。欧阳予倩认为艺术作品中的“感情”并不完全等同于日常生活中的情绪,而是“含有很深的道德和宗教的意味”(15)欧阳予倩: 《戏剧改革之理论与实际》,凤子等编: 《欧阳予倩全集》第4卷,第30页。。欧阳予倩提出这一观点的本意,不是要宣传道德观念或宗教教义,而是强调艺术作品中的感情,是能够帮助人“认识人生,认识自己”,能够“帮助人类生长”(16)欧阳予倩: 《戏剧改革之理论与实际》,凤子等编: 《欧阳予倩全集》第4卷,第22页。。所以他所说的“感情”虽然不是科学知识,但必定源自创作者积极的社会观、人生观。
其三,“感情”体现创作者的人格。欧阳予倩指出艺术中的感情需要有“个性”。而其所谓“个性”,便是创作者由具体的“遗传、环境、经验、修养、时代”而成的人格。(17)欧阳予倩: 《戏剧改革之理论与实际》,凤子等编: 《欧阳予倩全集》第4卷,第30页。
根据欧阳予倩的“感情论”,一方面作品中的感情源自创作者自身的社会人生观,另一方面创作者的感情体验只能通过艺术形象表现出来。所以“红楼戏”的创作一定与欧阳予倩的社会人生观念有关,但是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与创作者的思想观念,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反抗封建礼教”的社会观,“因现实黑暗而颓废避世”的人生观,以及欧阳予倩对于《红楼梦》原著的认识,都是他在创作“红楼戏”时的感情来源,但“来源”并不是“感情”本身。欧阳予倩基于这些社会人生观念而产生了具体的感情体验,又将这种“感情”作为核心人物的动机,融进“红楼戏”的审美形式中。所以在作品的审美形式中,真正直观可感的并不是某种明确的思想观念,而是作为人物动机的“感情”。由此可知,我们从表现对象的层面探索审美形式特征,并不是看“红楼戏”直接表现了哪一种明确的社会人生观念,而是先看欧阳予倩将什么样的感情作为核心人物的动机,再将这种动机与他对社会人生的独特体验进行关联。
欧阳予倩在创作“红楼戏”时,将原著小说里“可以编戏的材料全给搜寻出来”(18)欧阳予倩: 《自我演戏以来》,凤子等编: 《欧阳予倩全集》第6卷,第67页。。这些材料中,必然包括很多与爱情有关的情节。《黛玉葬花》《黛玉焚稿》《馒头庵》都可以被视为“爱情戏”。但是爱情并不是戏中黛玉葬花、焚稿的动机。《馒头庵》中智能委身于秦钟,也有更为深层的动机。前文已述,欧阳予倩在创作《黛玉葬花》时,主要是从“寄居孤女”的身份出发,体验黛玉的感情与心理。事实上,作为《黛玉葬花》《黛玉焚稿》《馒头庵》等剧中的核心人物,“寄居孤女”是黛玉、智能的共同身份。在剧中,她们常常哀叹身世如浮萍飘絮。但欧阳予倩并没有让这些女性人物只是哀叹身世,而是让她们表达出强烈的渴求——对“家”的渴求。这种渴求即是欧阳予倩在“红楼戏”中表达的感情体验。在创作中,他将这种感情作为黛玉、智能等“孤女”的动机,去完成葬花、焚稿或追求爱人等行动。
在创作《黛玉葬花》一剧时,欧阳予倩通过增加场面,让黛玉葬花的动机与原著不同。在原著中,黛玉与宝玉之间的关系,因为一个误会而陷入矛盾。但这个误会只是引发黛玉悲伤情绪的“偶然条件”。在小说此后的情节中,两人之间的误会解除,而黛玉的情绪却没有随之改变。因为黛玉心中的悲哀,源自她通过“花开花谢”体悟到一种宿命: 眼前的繁华景象终有一天会衰落颓败。《黛玉葬花》的剧本先由张冥飞、杨尘因合编,后由欧阳予倩增补。张、杨的本子延续了原著的情节与精神内核。欧阳予倩在按照这个剧本演出之后,认为“宝黛二人当时引起误会的事实,没有明场交代,因此末了解释误会就没有根据”(19)欧阳予倩: 《我自排自演的京戏》,凤子等编: 《欧阳予倩全集》第6卷,第267页。。所以,他又增加了一个场面: 黛玉月下访宝玉,却被关在了门外;听着怡红院内宝玉和宝钗吟诗唱曲的声音,她感到被宝玉轻视,又联想到自己寄人篱下的处境,于是悲从中来。通过明场的直观展现,欧阳予倩让这个“误会”成为引发黛玉激烈情绪的根本原因。黛玉的情绪,也从原著中对宿命的感悟,变成对自己身世的哀叹: 无家可归、寄人篱下。她原本希望生前身后都有人陪伴,但是这个误会让她对宝玉非常失望。所以此后黛玉“葬花”的行动,揭示了她心中对“家”的渴求。围绕这一动机,欧阳予倩将张、杨所作剧本中的场面均做了修改。在最后一场戏中,随着误会解除,宝玉的真情也弥补了黛玉内心的缺失,让她心中对“家”的希望获得实现。
在《黛玉焚稿》一剧中,欧阳予倩改变了原著中“宝玉成婚”的原因,从而重写了黛玉焚稿的动机。原著中宝玉必须和宝钗结婚,是因为阖府上下都需要“金玉良缘”冲喜。但是在欧阳予倩的剧本中,结婚的必然原因不是“冲喜”,而是不同人物怀着不同的目的,赞成宝玉与宝钗结婚。该剧名为“焚稿”,却在黛玉出场之前足足铺垫了四场,作用即在于将这些目的一一展现: 王夫人是对儿女事“越地牵肠”,所以急着办喜事;王熙凤是为了显示自己在贾府的地位;贾母是出于自己的喜好;袭人是为了自己的私情私利;贾政是为了能够放心离家上任——戏中的“大观园”,不是一个笼统的“封建礼教体系”,而是不同的人面对“金玉良缘”时表现出的具体的内心真实想法。所以在欧阳予倩改编的《黛玉焚稿》中,“宝玉成婚”这一事件对黛玉的心理冲击,在于让她产生了一种绝望的想法: 在大观园里,包括宝玉在内,根本无一人替她着想。在最后一场戏中,黛玉在知道宝玉成婚的消息后回到潇湘馆。与原著不同的是,欧阳予倩在此为她增加了一句念白:“我哪里有家!”(20)欧阳予倩: 《黛玉焚稿》,凤子等编: 《欧阳予倩全集》第3卷,第62页。这句念白说明黛玉感受到与外部世界彻底的隔绝与对立,也感受到心中与“家”有关的希望最终破灭。
与宝、黛两个人物相比,原著中关于秦钟、智能的情节要少得多。所以欧阳予倩创作《馒头庵》时,有更大的改编空间。在这部作品中,智能被塑造为一个敢于追求爱情的女性形象。欧阳予倩认为:“逼着一个小女孩子去当尼姑,我总觉得是残酷的。”(21)欧阳予倩: 《我自排自演的京戏》,凤子等编: 《欧阳予倩全集》第6卷,第271页。“馒头庵”对于智能来说就是监牢和火坑——小尼姑要么被“当丫头使唤”,要么被“当做摇钱树”。通过人物的念白,欧阳予倩揭示出智能对“家”的渴望。智能一出场便哀叹自己的身世:“可怜生小便无家”,如“弱絮随风荡”(22)欧阳予倩: 《馒头庵》,杨尘因编: 《春雨梨花馆辑刊·二集(剧本)》,上海: 民权出版社,1917年,第2页。。在随后秦钟和宝玉“争茶”一场戏中,智能发现两人完全不顾“送殡”的大事,而是都钟情于她。但她想到,“宝二爷是富贵人家子弟”,“只怕他中途要把我忘记”;“秦二爷乃是寒素人家,只要他能够将我救出火坑,我就拼着一死也要跟他一世”(23)欧阳予倩: 《馒头庵》,杨尘因编: 《春雨梨花馆辑刊·二集(剧本)》,第8—9页。。智能的心思表明了她的爱情观: 跳出火坑,摆脱孤苦无依的处境,给自己找一个稳定的“家”,而不是图一时的荣华富贵或者情感满足。所以在此后的场面中,秦钟真正打动智能的行动是发誓对她施以援手、让她这个“无家女”从此以后有所依靠。
从以上分析可知,在欧阳予倩“红楼戏”的审美形式中,人物具有与原著不同的内心感情。黛玉和智能的“爱情”并不是源自心中的“情欲”,而是对“家”的渴求。如果说原著通过“情灭身死”的人物结局传递了一种“色空”的宿命观,或者通过展现黛玉、智能等人的遭遇控诉礼教,那么对于“红楼戏”中的黛玉、智能来说,能否得到“爱情”,意味着“家”的希望或是实现或是破灭。欧阳予倩在创作“红楼戏”时,通过对核心人物动机的再创造,传达了自己由社会人生观念而来的感情体验。
1915年至1918年间,欧阳予倩在上海做职业京剧演员。他曾这样回忆这段经历——“生意很不错,可是精神上极不痛快”,“我那个时候的生活,只有‘穷’‘愁’两个字可以包括”(24)欧阳予倩: 《自我演戏以来》,凤子等编: 《欧阳予倩全集》第6卷,第65—66页。。《黛玉葬花》《馒头庵》《黛玉焚稿》等几部“红楼戏”正是创作于这段时期。从欧阳予倩的回忆看来,“穷”和“愁”都不是指生活拮据,而是指内心的苦闷。这种苦闷,除了由于家庭变故,比如父亲和祖父相继去世之外,更多来自他在“艺术人生”中的遭遇。在日本留学时,欧阳予倩与其他春柳社成员对日本新派剧演员的社会地位非常羡慕。他说:“日本新派优伶,泰半学者,早稻田大学文艺协会有演剧部,教师生徒,皆献技焉……国家所以礼遇之者亦至隆厚。”(25)佚名: 《春柳社演艺部专章》,《北新杂志》,1907年第30卷。但是回到自己的国家之后,欧阳予倩却发现,对艺术家礼遇隆厚的现代社会并未真正建立起来,戏剧和戏剧人的社会地位并没有得到真正改变: 人们普遍认为戏剧“除供人消遣而外,丝毫没有价值”,或者“戏剧本身,没有什么价值,因为能够作社会教育的工具才有一部分价值的可称”(26)欧阳予倩: 《戏剧改革之理论与实际》,凤子等编: 《欧阳予倩全集》第4卷,第20页。。当他成为职业京剧演员后,遭遇的歧视更为强烈——“我要‘下海’演京戏,就连平日同在一块儿演新戏的朋友也来反对”,“还有不少人见着我就作怪相,还会说些冷言冷语”(27)欧阳予倩: 《我怎样学会了演京戏》,凤子等编: 《欧阳予倩全集》第6卷,第240页。。所以当时的欧阳予倩虽然能够以自己的爱好为职业,却无法获得一个理想的戏剧人的社会定位,而只能充当消遣手段、教育工具。“红楼戏”中黛玉、智能等人物的遭遇,确实表现了欧阳予倩对女性的同情、对社会黑暗现实的控诉,但不可否认这些作品从“家”的层面去书写人物内心欲求、情感遭遇和命运,而这明显源于欧阳予倩由人生经历、社会认知而来的更为具体的内心体验。
三、 审美形式特征之二: 服务于动机呈现的场面开掘
在“红楼戏”中,欧阳予倩对原著人物动机的再创造,是在具体的戏剧场面中实现的。“红楼戏”审美形式的第二个特征,即在于通过戏剧场面的开掘与铺排,增强人物行动的感情张力,从而完整呈现人物动机。
戏剧场面的开掘与铺排,是欧阳予倩在艺术表现手段层面进行的重要探索。他认为中国现代戏剧的演出“不能没有剧作者为之设计”(28)欧阳予倩: 《再说旧戏改革》,凤子等编: 《欧阳予倩全集》第5卷,第16页。。所以,欧阳予倩将剧本视为综合艺术的“设计蓝图”。其所谓的“设计”,是指剧本不仅要为演员表演提供文字依据,还要对戏剧情节的组织结构进行整体的先期规划——“一个剧本编成”,需要“组织一个相当的故事,排列而成结构”(29)欧阳予倩: 《戏剧改革之理论与实际》,凤子等编: 《欧阳予倩全集》第4卷,第40页。;“编一本戏必然要有中心意识,有完整的故事,再有精密适当的分场”(30)欧阳予倩: 《再说旧戏改革》,凤子等编: 《欧阳予倩全集》第5卷,第23页。。由此可见,剧情的组织结构即是由戏剧场面的开掘与铺排形成。
欧阳予倩提出,戏曲创作应按照西方戏剧中“五段三节”式的情节结构进行戏剧场面的开掘与铺排。所谓“五段三节”,是指创作者根据戏剧冲突的发展,将剧情分为“发端、渐进、顶点、转降、收煞”五个阶段,或者“开场、中段、结局”三个部分。(31)欧阳予倩: 《戏剧改革之理论与实际》,凤子等编: 《欧阳予倩全集》第4卷,第41页。但是在“红楼戏”中,戏剧场面的开掘与铺排并不符合“五段三节”。在创作《黛玉葬花》时,欧阳予倩确实是有意识地追求情节的集中与完整,但他也回避了“宝黛钗三人见面”这种能够激化矛盾、形成冲突的场面。这部作品的情节集中于宝黛二人关系的变化。这组人物关系虽然经历了从矛盾到心意相融的过程,但矛盾并未激化成“冲突”。而从《黛玉焚稿》来看,欧阳予倩将原著中的“宝玉成婚”“黛玉焚稿”“黛玉之死”等情节,通过戏剧场面完整呈现出来。但是这些场面主要围绕黛玉自身的感情变化,而不是黛玉与其他人物的冲突。在这部戏中,黛玉虽然内心情感强烈,却从未与身边的人爆发激烈冲突。再从《馒头庵》来看,秦邦业和智能、秦钟之间确实爆发了激烈的冲突,但是这部作品场景切换频繁,人物关系复杂多变。所以戏剧场面的开掘与铺排,并不是围绕单一冲突进行的。
欧阳予倩的“红楼戏”创作于1910年代。他明确提出有关“五段三节”的理论主张是在1929年。“红楼戏”的剧情结构与该理论主张不一致,并非由于这十多年中欧阳予倩的戏剧观发生了根本变化。至少在场面的开掘与铺排方面,其前后的主张是一致的: 他所演的“红楼戏”,“是照新戏分幕的方法来演,因为嫌旧戏的场子太碎”(32)欧阳予倩: 《自我演戏以来》,凤子等编: 《欧阳予倩全集》第6卷,第68页。。事实上,“五段三节”只是一种理论表述,而非欧阳予倩提出理论主张的初衷。他提倡用“五段三节”安排场面,并不是要将情节素材套进一种创作公式中,而是要寻求一种创作更为集中的结构的方式。欧阳予倩认为当时的戏曲作品“一来不善于用暗场;二来不懂行为进展的道理;三来除了平直的叙事,不懂得分析式的技巧”(33)欧阳予倩: 《戏剧改革之理论与实际》,凤子等编: 《欧阳予倩全集》第4卷,第56页。。他希望改变场面的开掘与铺排方式,只是囿于主客观条件,在理论表述中暂时选择了“五段三节”。或者可以说,在欧阳予倩的创作实践中,“五段三节”并非实现其初衷的唯一方式。当然,我们在表现手段层面探索“红楼戏”审美形式的特征时,并不是要在“五段三节”之外,再总结另外一种场面开掘与铺排的具体方式,而是要找出欧阳予倩在运用这些方式时所遵循的内在逻辑。
法国美学家杜夫·海纳指出: 审美形式的内在逻辑与数理学科的逻辑有本质不同。虽然后者也是一种“形式逻辑”,但是这种数理学科的“形式逻辑”并不包括具体的感性对象,而是一种空洞的公式或定理,即数字、符号之间的关系。而“审美形式”的逻辑则是通过具体的感性对象,表现创作者的感情体验,即创作者在作品中表现的是其“内心经验过的世界,一个只有情感才能使我们进入的不可模仿的世界”(34)[美] 杜夫·海纳: 《哲学与美学》,孙非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25页。。
欧阳予倩将自己的感情体验作为黛玉、智能等人物的动机,所以“红楼戏”表现手段运用的内在逻辑,就是让戏剧场面的开掘与铺排成为这些人物动机完整显现的过程。但这种“完整展现动机”的过程,并非围绕某个人物完整统一的行动线展现其不同的心理层次。在“红楼戏”中并没有集中统一的行动线。“葬花”“焚稿”是核心人物在感情高潮时做出的行动,而不是人物贯穿全剧的行动。在《馒头庵》中,智能有贯穿全剧的行动,但是这部作品中有多条行动线,智能的行动线仅是其中之一。
欧阳予倩的“红楼戏”实际是在戏剧场面的开掘与铺排中增强行动的感情张力,进而实现核心人物动机的完整呈现。剧情内的“时空转换”,不仅依靠角色唱词或者身段进行表现,还通过场面之间的衔接、铺垫、照应与对比等方式更为直观地呈现出来。这就使得戏剧场面中表现人物生活实体的时空得到拓展,从而让行动所揭示的感情更为丰富强烈。所以观众在欣赏“红楼戏”时,如果要充分感受人物动机中所包含的感情,就不能只凭角儿的几句唱词或几个身段,而是要欣赏场面开掘与铺排的整体过程。
在《黛玉葬花》中,欧阳予倩运用明暗场的交替衔接,揭示黛玉的内心情感。在这部戏的演出中,欧阳予倩运用了幕布和实体布景。这些舞台装置的成功之处,并不在于还原某种现实环境,而是让观众更为明显地感觉到舞台上的时空转换。在第一场戏的末尾,黛玉黯然离去。在第二场戏开幕后,黛玉重新登场,景片已从怡红院门前切至潇湘馆内室,剧情中的时间已是第二日的白天。明显的时空转换,让黛玉“下场”与“重新上场”之间,产生了一个暗场戏: 黛玉在吃了宝玉的“闭门羹”后,这一夜是如何度过的。作者将黛玉在这一夜中忍受的内心煎熬放到暗场,让观众去想象。在第二场幕布重开时,观众看到时间和地点的变化,便会带着自己的想象,并联系黛玉在上一场中所受的冷遇,听她念出那句引子——“春去无痕,莽天涯,怎不销魂”(35)欧阳予倩: 《黛玉葬花》,凤子等编: 《欧阳予倩全集》第3卷,第6页。。这原本是感时伤春的平常言辞,但是在暗场戏引发的联想中,却有了深邃的感情意蕴: 前一天傍晚的落花之景,在宝钗眼里还是“落花无主春骀荡”(36)欧阳予倩: 《黛玉葬花》,凤子等编: 《欧阳予倩全集》第3卷,第4页。,可是对于黛玉来说,一夜狂风过后,已是“春去无痕”;前一晚宝玉那扇关着的门、门里面传出的笑声,是黛玉看到的眼前之景,而一夜过后,她的思绪已从“眼前”到了“天涯”——无论在哪里,黛玉都找不到自己的“家”。通过明暗场的衔接,这部作品让观众充分调动自身的想象力,体验黛玉内心的感情是何等激烈。
在《黛玉焚稿》中,欧阳予倩通过前场戏对后续场面的情绪铺垫,让黛玉死前对宝玉的念白极富感情张力。欧阳予倩突出了“宝玉成婚”一事对黛玉内心的打击。与原著不同的是,在这部“红楼戏”里,黛玉是带着具体的“心事”出场的: 她虽然不知道宝玉即将与宝钗成婚,但是敏感地发现大观园中已没有了往日的热闹——“这边厢怡红院室近人远,那边厢蘅芜院衰草残烟”(37)欧阳予倩: 《黛玉焚稿》,凤子等编: 《欧阳予倩全集》第3卷,第58页。。黛玉怀着如此“心事”听说宝玉成婚的消息,其内心的感受便从原著中在平静的心态下“突遭打击”,变为“噩梦成真”。从戏中黛玉的唱词来看,她的精神状态不是原著中所写的恍恍惚惚,而是非常清醒——“从前错认真情种”、“今日恍然醒大梦”(38)欧阳予倩: 《黛玉焚稿》,凤子等编: 《欧阳予倩全集》第3卷,第59页。。这样的人物状态和唱词会引发观众的一种心理期待: 黛玉急急忙忙地去质问宝玉时,一定会有酣畅淋漓的大段唱词,以及激烈的外部冲突。可是在接下来的场面中,欧阳予倩沿用了原著中的情节,并没有为黛玉增加唱词、念白,也没有安排过多的身段。当黛玉直面宝玉时,只是笑着坐下,又说出了两句非常简短的念白:“宝玉,你为什么病了”,“这就是我回去的时候了”(39)欧阳予倩: 《黛玉焚稿》,凤子等编: 《欧阳予倩全集》第3卷,第61页。,之后便起身离去。然而,欧阳予倩的处理方式并不会让观众感到心理期待落空。由于之前场面所做的铺垫,在这个场面中恰恰只有通过温和的表情与简单的言语、动作,才能揭示出黛玉心中的绝望之情——黛玉的笑,反衬出心中的悲苦;而她的念白越简单,揭示的绝望之情就越强烈。
在《馒头庵》一剧中,欧阳予倩则是通过场面的对比与呼应,揭示了智能心中巨大的感情落差。这部作品共有五场戏,前两场戏与后三场戏的氛围截然不同。第一场和第二场通过智能与宝玉、秦钟的调笑,揭示出她内心对于跳出火坑的喜悦之情。场面中的氛围轻松欢快。而在后三个场面中,智能到秦府寻找秦钟,却在遭受恶仆调戏、秦邦业辱骂之后,被公差驱逐。“无家女”对“家”的希望最终落空,场面中的氛围悲惨凄凉。同时,在全剧第一场中智能的念白与唱词,与最后一场中她的念白与唱词遥相呼应。在第一场中,智能一面希望通过虔诚的祷告寻找一片宗教式的净土,一面却渴望在尘世中找到一个“家”。在最后一场中,智能同样是一面说着自己“万念了心已成灰”“弃红尘大限同归”,一面却希望秦钟不再做“负心人”,而是与她在另一个世界“比翼双飞”(40)欧阳予倩: 《馒头庵》,杨尘因编: 《春雨梨花馆辑刊·二集(剧本)》,第25页。。但与第一场不同的是,这个场面中的智能已经从一个活泼的、内心充满希望的女孩子,变成了存在于幻象中的、内心充满失望的孤魂。在演出中,扮演智能魂魄的演员由钢丝吊下,还能同时做出身段,并唱出大段唱词。这类舞台技术虽然在民国时期的海派京剧中不算罕见,但是其独特作用在于突出了前后场面之间的对比和呼应,揭示出智能因为“家”的希望落空,从喜悦到失望的情感变化。
结 语
从内在构成机制来看,欧阳予倩“红楼戏”的审美形式具有这样的特征: 在场面的开掘与铺排中,增强行动的感情张力,完整呈现人物动机,表现创作者基于自身社会人生观念产生的感情体验,即对“家”的渴求。“红楼戏”是欧阳予倩在其早期舞台生涯中进行的艺术探索实验。虽然欧阳予倩曾称“红楼戏”剧作是按照“旧套子”编的;舞台表演也沿用了“道家门”“定场诗”等戏曲程式;核心人物的行动,诸如“葬花”“焚稿”等,更是以戏曲身段、唱词表演的,但这不代表“红楼戏”毫无创新,审美形式的变革便是最大的创新。可见,在“红楼戏”的剧本创作和舞台演出中,欧阳予倩已经在践行他对于戏曲改革的构想。诚然,“红楼戏”并不能涵盖欧阳予倩戏曲改革思路的全部主张,但是“红楼戏”审美形式的特征足以给今天的现代戏曲创作以启发——将创作主体对于现代社会人生独特的感情体验合理地传递出来,是彰显现代戏曲独特艺术品格的必备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