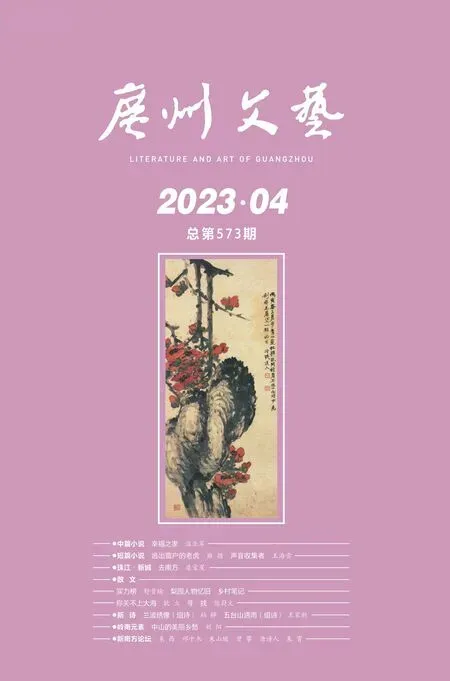主持人语
2023-10-09 08:25:15蒋蓝
广州文艺 2023年4期
钱穆先生《国史大纲》开篇说:“所谓对其本国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而舒晋瑜恰是被“温情”与“敬意”两个词打动的人。她不但亲身采访、见证了艺术家的艺术历程,更有一种超拔于艺术之上的精神氤氲,在字里行间慢慢蒸腾。我感怀于《梨园人物忆旧》里的那种特有的平实语调,没有高起高打,而是由旁观者逐渐过渡为参与者的角度转换,从而把舞台艺术的绝技与活色生香,与记录的文字达成了一种通感般的传递。比如:“如何争取更多的观众,继承和创新是最重要的两点。‘继承’是为了保留京剧的传统文化特色,‘创新’则是在此基础上以今天观众的需求和时代发展的需要,增添新鲜血液,丰富新的剧目。耿其昌总在琢磨,如何能更好地将二者结合起来,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感染。正如建筑,所谓‘修旧如旧’,就是在几乎不着痕迹的细微改动中达到最好的效果。”
这些观点,恰是艺术家毕生的结晶。
在《乡村笔记》里,舒晋瑜展示的是个人记忆里的四个往事片段,写得曼妙而抒情,但依然有她的撷取角度,那种“往事不再”的过往,在作家的回忆里得到修补、续接、放大,让我们恍然:原来感动一个人的东西,未必需要电闪雷鸣,它们多是平常生活碎片,但一旦获得了文字的加持,它们就发出了火光。想起张爱玲的话:“真正的成熟大概就是,喜欢的东西还是喜欢,只是不再强求拥有了。害怕的东西还是害怕,只是敢于面对了。”
理想的艺术表达,并非只有苏东坡《聚星堂雪》“当时号令君听取,白战不许持寸铁”那样孤高遗世。舒晋瑜感叹:“最佳的艺术就是这种不经意的自然流畅,好比是书法作品,看似没有安排,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其实有极大的奥妙。”我想,散文何尝不是如此呢!
猜你喜欢
中华诗词(2023年4期)2023-02-06 06:06:00
无线电通信技术(2022年3期)2022-05-22 12:31:44
中国美术(2021年4期)2021-10-30 19:23:57
中华诗词(2018年2期)2018-06-26 08:47:32
中华诗词(2018年1期)2018-06-26 08:46:44
小小艺术家(2018年3期)2018-06-11 15:31:46
小小艺术家(2018年2期)2018-06-06 16:26:48
小小艺术家(2018年1期)2018-06-05 16:55:48
小说月刊(2014年1期)2014-04-23 09:00:01
小说月刊(2014年4期)2014-04-23 08:5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