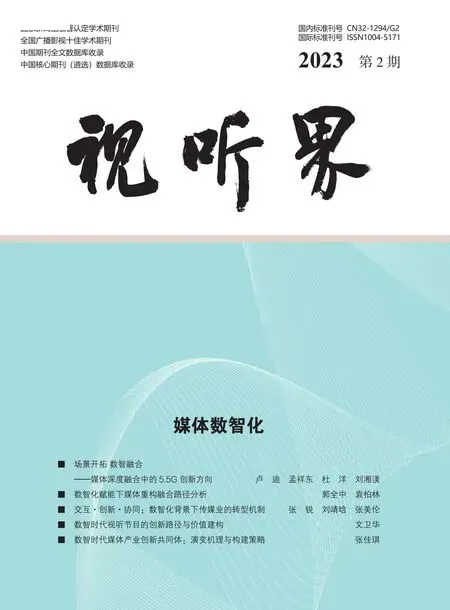特殊儿童题材纪录片的创作要点
吴 珂
人们将在智力、感官、情绪、肢体、行为或言语等方面低于正常儿童的孩子称为“特殊儿童”。在我国,社会对于特殊儿童的关注度逐渐提高,许多孤残儿童有了生活上的保障,这些弱势群体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许多关心,也涌现出一些与特殊儿童相关的报道。然而,特殊儿童题材纪录片数量有限,首先家人会出于对孩子和家庭的保护,不愿意将有缺陷的儿童推至镜头前;其次特殊儿童会存在一些心理或生理问题,在屏幕化呈现的片子里,他们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以致公众鲜少能看见特殊儿童真实的生活环境和心理世界。如何在尊重拍摄者、守住伦理底线的前提下,进行真实的拍摄记录,通过纪录片的形式,真实展现特殊儿童的生活,是每一位创作者要多重考虑的问题。
著名结构主义理论家塞默尔·查特曼说过:“叙事是传播,因此它预设了两方:一个发送者,一个接受者,每方都有三个不同的人格位。在发送一端是真实的作者、隐含的作者和叙述者,在接受一端是真实的受众、暗含的受众和叙述对象。”[1]我们在制作特殊儿童题材的纪录片时,作为发送者,要能准确地将故事说完整,传递正确的主旨思想,进行正向的价值引导,让观众在另一端获得最真实的感受。
一、不触碰创作中的“灰色”地带
特殊儿童往往会被社会定义为“弱势群体”,在采访这样的弱势群体的时候,一些创作者会抱有“等差之爱”的眼光来记录被访者,甚至有的创作者为了博人眼球,会放大这类人群的“特殊性”,在镜头前更多地表现残障。这会导致很多作品偏离了本有的主旨思想,引起被拍摄者的不适,形成此类纪录片创作中的“灰色地带”,同时也会引发伦理道德问题。随着新媒体的发展,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创作者和传播者,人们拿起手机随手拍摄,就可以发至网络平台,与社会共享。无论是拍摄节目还是生活捕捉,在面对特殊儿童人群时,我们应当思考,创作者和拍摄主体如何相处,在创作的艺术性与纪实性中如何取舍。
在特殊儿童题材纪录片的拍摄过程中,拍摄者和被拍摄者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而双方的关系有时直接决定了影片的成败,拍摄者在交流上的“尺度”拿捏很重要。拍摄者往往想要更加接近拍摄对象,近距离记录拍摄对象。而拍摄者在创作过程中会发现与被拍摄者的亲近,并不是无限度地深挖被拍摄者的故事。比如记者采访一位盲童,她的眼球只能感知太阳光,但是她却有个音乐梦想,小小年纪,已经取得很多的钢琴奖项。记者在与盲童的交流过程中,问她在家里最喜欢谁的时候,受到了她的抵触。因此在交流过程中,并不是无限度地接近被采访者就是对影片有益,有的时候反而会使影片看起来很刻意,给观众造成不好的观感。
在对特殊儿童单独拍摄和采访时,他们因为身体的缺陷,心理戒备心比较强,当记者想问及一些私密问题时,他们经常不作答或不配合,不能按照设想继续拍摄下去。而当他们置身在家庭环境中,与他的朋友和家人在一起时,就显得很放松和自如,这个时候采访他本人或者他身边的人,也不会抗拒,有时“意外”的搭腔,还会制造出更愉悦轻松的氛围。
对拍摄对象保持充分的尊重还体现在话题的取舍上。盲童还有一个弟弟,却在影片里未曾露面,一个原因是弟弟长期与父母出海不在家,还有个原因是弟弟也是个盲人,还存在智力低下的问题。所以创作者在与其家人的前期沟通中,就避免了弟弟的话题介入,以免给被拍摄家庭带来不好的感受。这也是为了影片在传播过程中,观众能够充分尊重被拍摄者的家庭,让社会与家庭有积极向上的沟通方向。
创作者在话题取舍上要充分考虑到,镜头是否拥有权力,或者是否有这个能力去改变拍摄对象的生活,且改变的结果是拍摄对象所愿意接受的,如果不能,创作者就不要触碰交流中的“灰色”地带,对特殊的主人公保持充分的尊重。
作为创作者,对故事的构建不是简单地串联素材,而是有脉络有条理地讲述故事,描述人物。在条理中,尽可能多地展示主人公的人格魅力和导演的创作手法。如今拍摄设备先进而便捷,让更多拍摄者有了创作和分享的机会,比如在抖音上就经常能刷到随手拍摄的记录类短视频。拍摄者和被拍摄者的距离因此拉近且亲密,而这种距离的拉近使得拍摄中的“灰色”地带增多。随手拍摄,随意上传,将视频呈现在成千上万的网友面前,并不意味拍摄者和被拍摄者建立了有效的交流关系,也可能是侵犯了被拍摄者的隐私。便捷的拍摄方式和分享平台,为拍摄者提供条件的同时也可能引发法律和伦理问题,被拍摄者会产生被侵犯、不被尊重的感受,觉得自己成了工具被利用、被消费、被道具化。纪录片的创作也应该注意保护拍摄对象的隐私权,充分尊重拍摄对象,多交流多沟通,避免创作者陷入法律和伦理问题的泥沼。
二、秉持不伤害的原则
不伤害原则,就是不伤害被拍摄者的利益,是纪录片传播伦理中备受重视也是被创作者广为接受的一个基本准则。一般认为,拍摄者有义务保护拍摄对象,尽量避免拍摄对象被拍摄行为所伤害是最基本的道德责任。[2]
国外纪录片《我曾是个士兵》是一部口述纪录片,几位口述者都因为战争失明了。在这个纪录片里,他们揭开伤疤,讲述了在战斗中失明的过程、失去视觉后的感受,以及对光明的渴望。观众通过画面和讲述,能切身感受到讲述者内心的痛苦。有个片段是这些士兵讲述了他们的梦境,梦境里,他们的眼睛是能看得见的。一位士兵说,我从来没有做过看不见的梦。另一位士兵说,我的梦不是灰色的也不是黑白色的,我的梦是色彩斑斓的。还有一位士兵说,我看到果园和盛开的鲜花。画面中他们的形象和讲述的梦境产生一种反差,让观众感受到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导演将它们挖掘了出来,通过镜头展现给观众。这些士兵虽然获得了观众的怜悯,但是伴随他们的痛苦是无法磨灭、永久存在的。而纪录片的制作,使他们的痛苦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展现,影像的伦理命题再一次使创作面对两难的境地。
对于特殊儿童,有的时候真实的记录也是双刃剑。当创作者反反复复挖掘他们的“痛点”,对于观众,会有感官上的刺激,但对于特殊儿童本人而言,很容易产生心理上的阴影。在特殊儿童题材的纪录片创作时,如何引导他们拍摄,才能最大程度地“不揭伤疤”,却又能真实地展现生活,让观众更多地关注他们的生活和成就,而不是与他人不同的缺陷,是创作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自闭症儿童纪录片《守护星星的人》展现主人公艰难求学历程。该片通过采访自闭症儿童张翰生的父母,记录日常生活场景,展现自闭症孩子的生活状态。全片28 分钟,没有额外的配音,贯穿始终的是父母的讲述和背景轻音乐。在父母接受采访的过程中,张翰生会在一旁发出不成句的声音,这是他在表达,父母也很关注儿子的动作和声音。简单的记录,呈现的是一家三口积极生活的画面,让观众感受到他们对当下生活的接受和对未来生活的努力。
被拍摄者本身的自我保护本能应该得到肯定,也就是他们想要不过分曝光的心情是正常且需要保护的。纪录片是由拍摄者与被拍摄者共同完成的,拍摄者在纪录片里充分地展现真实,在合理范围内进行艺术创作的同时,也要秉持不伤害被拍摄者的原则。
其实特殊人群纪录片的呈现,无论是观众表达个人主观道德倾向的观后感,还是拍摄者有关伦理道德的被问话,都是正常存在的。一部纪录片在道德准则上的评判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在创作中,尤其要注意不伤害被拍摄者,避免陷入伦理道德的舆论中。
三、将伦理道德统一于创作理念中
在特殊儿童题材纪录片里,创作理念与伦理道德从哲学角度上来讲,没有绝对的对立,任何事物都有对立、统一的方面,且这两个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可以相互转化,前者主张追求真实,后者主张保护隐私,虽然有这样的矛盾,但这两点融合既有为社会服务的统一,也有尊重被拍摄对象与承担大众舆论压力的平衡。
作为特殊儿童纪录片的创作者,既要坚持真实性,也要有艺术性地再创作。那么,真实和二次创作如何相辅相成?这就要回到拍摄对象本身。当大众提起特殊儿童的时候,他们的刻板印象大多是可怜、无助、没有希望。而创作者去拍摄特殊儿童时,他们会发现这些特殊儿童身上的标签已悄然改变,积极乐观、自强不息、开朗大方都可以用来形容他们,甚至完美诠释了那句名言:上帝为我关上了一扇门,却打开了一扇窗。所以创作者也希望通过作品,让观众看到这些特殊儿童不一样的一面。因此,创作者不要渲染“可怜、无助”的氛围来吸引观众,而是应该真实地展现这类特殊儿童的正能量一面。比如在创作过程中,不需要再另加配音把创作者的主观感受过多地加入进去,有的时候只用同期声和画面,就能展示这些特殊儿童充满希望的生活,同时,也能让观众对他们美好的未来产生期待。
聚焦儿童听力障碍的纪录片《听风的孩子》,真实记录了听力障碍儿童的生活。孩子们带着人工耳蜗,“如果不是耳后细细的线,根本不会发现他们和别的孩子有什么区别”,这是来自片中的旁白。片中还特别展示了听障孩子阳阳的跳舞天赋,“阳阳在学校也是一个被其他孩子所羡慕的孩子,主要是他的特长街舞,阳阳对音乐节奏的感知能力很强”。通过这样的旁白加上阳阳跳舞的画面,让观众感受这些孩子的闪光点,弱化了“听障”的缺陷。
纪录片的创作理念是真实地记录生活,在纪实中,通过镜头语言、声音语言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纪录片创作者应该始终保持初心,保持一种谦卑、敬畏的态度,在创作过程中要做到对客观事实负责。虽然任何一部纪录片的产生,离不开纪录片创作者的多层主观筛选、加工和再创造。创作者通过带着架构的思维和画面故事,创作出一部完整的纪录片。很多时候一部纪录片蕴含的是创作者个人的主观表达,有着创作者强烈的主观意识。所以创作者在创作中应该平等、尊重地看待拍摄对象,不能有优越感,这种优越感缺少了对拍摄对象的人文关怀,也否认了纪录片独特的价值追求。尊重拍摄对象,在乎角色感受,是创作者必备的道德素养,也是纪录片的创作理念,两者在这一点上形成统一。
四、保持良好的沟通
特殊人群纪录片应当认可一个观点,即通过拍摄行为给被拍摄者带来益处。但很多特殊儿童纪录片,当素材拍摄完毕,素材的使用和剪辑都全权交给了后期,被拍摄者即与影片割裂开来。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需要思考,被拍摄者如何从影片中获得益处,如何与影片创作始终保持良性沟通。被拍摄者在自愿的情况下利用自身角色的优势,表达对社会的期盼,是影片应当给予他们的权利,也是对他们最基本的尊重。
同时,在观看过程中,观众如何和影片保持良好的交流,也是创作者需要思考的。拍摄对象往往会在镜头的刺激下做出许多本能的反应,以至于忽略了镜头背后的观众和社会。在传播的过程中,拍摄对象所有的性格特征、行为方式都暴露在观众的视野里,每一个细节都会受到观众的关注,从而对拍摄对象产生全面的影响。有的时候观众的这种关注会存在强烈的主观性和非理性,甚至有窥探的心理。为了避免出现负面的影响,创作者应该在影片中进行正面的价值引导。
央视纪录片《我不是笨小孩》是一部长时间观察阅读障碍儿童成长的纪录片。在第一集开始,片头就出现这样的字幕:“在适龄儿童中,大约5%~8% 的孩子有阅读障碍困难,他们常常会被误认为笨或者懒。”短短的一句话,其实已经在向观众说明:片子说的是阅读障碍的孩子,这样的孩子有一定的概率。带着这样的思维去观看片子,观众就更容易理解片中孩子的行为,当看到孩子因为读书障碍造成家庭困扰时,观众更能感受父母对于阅读障碍孩子的积极努力。
五、结语
特殊儿童,既是社会的弱小群体,又是儿童中的弱小分支。创作者是影片的记录者,同时也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传播者。不触碰拍摄的“灰色”地带,保持充分的尊重,秉持不伤害的原则,处理好创作理念和伦理道德的关系,是面对这样的群体所需要坚守的。很多的特殊儿童虽然残疾却热爱生活、积极乐观,通过创作者的镜头能够让观众知道他们、走近他们、了解他们,而不是一味地怜悯或是满足观众猎奇心,才是特殊儿童题材纪录片的创作目的。
注释:
[1]塞默尔·查特曼.媒介研究的进路:经典文献读本[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122.
[2]刘忠波.纪录片的道德困境和伦理风险[J].中国电视,2012(8):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