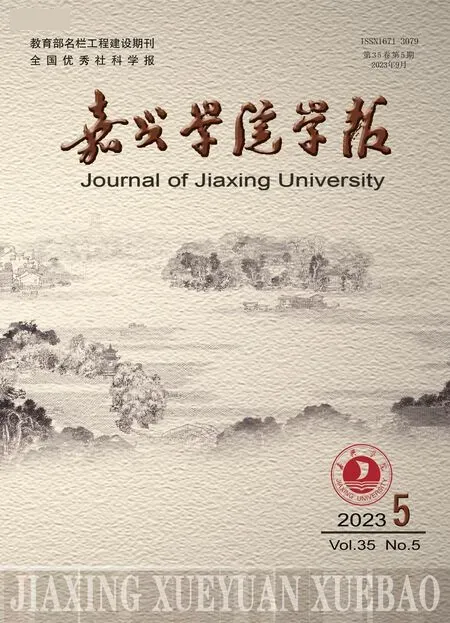项穆书学观念谫论
——以《书法雅言》为例
杨 刚,逄淑美
(嘉兴学院:a.设计学院;b.图书馆,浙江嘉兴 314001)
项穆,生卒年未详,大约生于公元1550年,卒于公元1600年前后,与董其昌为同时代人,初名德枝,后改名德纯,最后易名穆,字德纯,号兰台、无称子,亦号贞玄,入清后为避清圣祖玄烨讳,史书中多作“贞元”,著有《贞玄(元)子诗草》等。
项穆为嘉兴秀水人,系著名收藏家项元汴之子。项氏一门在有明一代的江南地区堪称豪门甲第,不仅家资巨富,而且百余年中科第、登仕籍者绵延不绝。项元汴庋藏书画、书籍、文玩的天籁阁更是以藏蓄广博而声闻海内。项穆自幼受到家庭文化的熏染,偏爱吟咏,兼善翰墨丹青,于晋唐名家无不窥览从习,其书法艺术更是颇有时誉,与其伯父项元淇(少岳)齐名于世,是明末嘉兴地区的重要书家。
项穆操翰之余亦注重书学理论的著述,有《书法雅言》行世,盖为其晚年所作。《书法雅言》所见版本甚多,最早的版本为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槜李项氏的家刊本,之后,有明崇祯年间何伟然所辑的《广快书》本,清代有竹斋《重刻书法雅言》抄本、《四库全书》本、《浙江采集遗书总录》本、《艺海珠尘》本等。
一、《书法雅言》各篇章介绍
《书法雅言》全书共分为17个篇章(附评1篇),分别为“书统”“古今”“辨体”“形质”“品格”“资学”“规矩”“常变”“正奇”“中和”“老少”“神化”“心相”“取舍”“功序”“器用”和“知识”。
“书统”篇是对书法统序的探讨。项穆认为,王羲之书法会古通今,为书统之正宗,其以王羲之为参照,对唐、宋、元、明等历代的书法之风作了宏观的批评。
“古今”篇实际上是“书统”篇的延续和深入,是项穆对书法古今问题的探讨,有助于细化和深化书统的理论。
“辨体”篇重在论述和辨析书法体势与审美的关系。
“形质”篇重点论述书法体状的问题。项穆认为,人的人性、禀赋、气习的不同,导致了其书法风格和体状的差异。
“品格”篇是项穆对书法品第和格调的集中论析。项穆在前人书法品格论的基础之上,根据书家天分的高低和功力的深浅,将书法的品格划分为正宗、大家、名家、正源、傍流5个层次。
“资学”篇重点论述书家天资与学力在书法学习中的作用。
“规矩”篇着重论述书法的规范。在项穆看来,王羲之的书法体裁独妙,学书者不以此为规矩很难成为上品。项穆对六朝以来的书家进行批评,认为唐宋以后以怀素、赵令穰、米元章为首的书法家们变乱法度,规矩出于二王之外,逐渐走向了诡厉鼓努的异端。
“常变”篇是对“规矩”一篇中的理论的不断深入。项穆用行军布阵作类比,说明字无定形的道理,当然,项穆也清醒地认识到虽然字形可以千变万化,但基本的规则体势是不能逾越的。
“正奇”篇重点讨论书法中的守正与奇变的问题。项穆提倡心手精熟、胸襟谙练,自然能从容中道,得天然之巧,不赞成书家刻意求变求新。
“中和”篇是项穆将儒家中庸思想运用于书法艺术。“中和”也是项穆贯穿于整部《书法雅言》的崇高审美理想,其后几篇也多有论及。项穆先是讨论了不同书体的“体”与“用”,进而得出结论“会于中和,斯为美善。”项穆对唐代的陆柬之、张旭、颜真卿、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诸家的书法也作了相应的评析。
“老少”篇重点探讨了书法的“老少”问题。项穆指出,书法的“老”与“少”是相对而言、相待而成的,不可偏废。“老”而不“少”或“少”而不“老”,都不是审美的理想境界,这也与项穆一贯的“中和”标准相统一。
“神化”篇实质上是在探讨书法的崇高境界。项穆认为,书法的创作是精神抒发、心性排遣的过程,因此,书法只有达到了随心所欲的程度,才是最为崇高的境界。
“心相”篇是对“书为心画”理论的升华。项穆指出书法与心性的关系,并定义了“书之心”和“书之相”,他以人品作比喻,讨论了不同身份的人应有的心灵和仪态,提出了“人正则书正”的观点,他还将儒家“三纲八目”理论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一一落实到书法的相关问题上。
“取舍”篇主旨在于帮助学习者建立正确的审美价值观。他认为苏、米等人虽然天资高迈,但学力疏漏,只能通过夸张的外形来遮蔽功夫的粗疏。世人如果不能明辨取舍,恐有效颦之嫌。王羲之会古通今为一代大成,学习者只要以王羲之书法为参照,优劣立现。若学习者不能辨析这些书家的优劣长短,则会“徒拟其所病,不得其所能”。
“功序”篇重点论述学习书法的基本过程,认为历代书家和评论家们一味地追求浮华并未抓住书法学习和鉴赏的内理,为此,项穆提出了“三戒”和“三要”的书法学习观。
“器用”篇重点讨论书写工具与书法艺术之间的关系。项穆用排兵布阵来比拟身、心、手、指与纸、笔、墨、砚之间的关系,对《笔阵图》中关于纸、笔、墨、砚的比喻进行了修正,对“能书不择笔”等观点进行了反驳,对社会上一些假借书法之名行卖弄杂耍之实的江湖骗子发出呵斥。
“知识”篇重点论述关于书法鉴赏的内容。提出了“心鉴”“耳鉴”“目鉴”之说,还对社会上一些低劣的鉴赏行为进行了批评,并且再一次强调“中和”的重要作用。
全书从不同侧面和角度系统论述了书法史论、批评、学习、鉴赏、器用等方面的内容,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书学理论价值,是项穆书学观念的集中体现。《四库全书提要》评项穆《书法雅言》“虽持论稍为过高,而终身一艺,研求至深,烟楮之外,实多独契。衡以取法乎上之义,未始非书家之圭臬也”。[1]
二、《书法雅言》体现的书学观念
对《书法雅言》诸篇章进行梳理发现,项穆的书学观念可以大致概括为:尊书道而重书统、敦心性而尚德行、贵新变而用中和。
(一)尊书道而重书统
自古以来,我国有重文字而轻书法艺术的传统。汉字可包容天地万物,能记载历史、交流思想、传递文化、传播文明,能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起到宣教化、助人伦的作用,因此,汉字使人膜拜,甚至历史上曾有“天雨粟,鬼夜哭”的神话传说以彰仓颉造字之功。后来,汉字又掺入了易卦的神秘内容,有人甚至认为汉字起源于八卦,汉字遂被蒙上了一种神秘迷幻的色彩。
与之相应,一直以来,古人对汉字的书写艺术并不是很重视。在商周秦汉时期,书法的艺术性未能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书法艺术基本上都是从属于文字之学。汉代学者赵壹甚至认为,过于偏重书法的学习会“背经而趋俗,此非所以弘道兴世也”,[2]1认为书法的工用十分有限,书法的优劣亦无关大雅,“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把过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书法艺术上是志趣狭隘的表现,长此以往,徒劳费工,如同俯下身来扪虱,不暇见天,实为可笑之举。[2]2-3这与汉代学者扬雄“诗赋小道,壮夫不为”的思想基本一致。汉末魏晋时期,随着文与艺的自觉,文艺理论蓬勃发展,书法艺术逐渐从文字之学中脱离出来,其身份逐步确立。唐代时,唐太宗李世民对一代名臣、著名书家虞世南进行评价时,论之以“五绝”:一曰德行,二曰中直,三曰博学,四曰文词,五曰书翰,将虞氏书法之优排在末位。[3]唐人孙过庭也认为,君子立身,务修其本,应该将修身齐家、经世治国放在首位,翰墨之精粗则在于毫末。[4]10北宋书法理论家朱长文在《续书断序》中明确了以人论书的书学思想,认为书法是“英杰之余事,文章之急务也”。[5]宋元以来书法类的著述,基本上归于子部艺术类,可见书法艺术在中国古代整个文化体系中的地位并不高。
与大多数古代学人的观点不同,项穆十分尊崇书法艺术。他认为,书法艺术绝非文人在茶余饭后消磨时光、遣兴怡情的微末伎俩,而是关乎国运人伦、圣贤学术和人心正邪之大道。项穆曾说:“然书之作也,帝王之经纶,圣贤之学术,至于玄文内典,百氏九流,诗歌之劝惩,碑铭之训戒,不由斯字,何以纪辞。故书之为功,同流天地,翼卫教经者也。”[4]72他将书法的作用上升到“同流天地”“翼卫教经”的高度,可见项穆对于书法的重视。在项穆看来,书法“可以发天地之玄微,宣道义之蕴奥,继往圣之绝学,开后觉之良心”,[4]172因此,学习书法有其重要价值,书法艺术不仅是出于书写的实际需要,还可以涤荡恶趣、净化人心、佐助教化、匡正王道:“正书法,所以正人心也。正人心,所以闲圣道也。”[4]73在项穆看来,书法艺术之功德可与礼乐同休,书家之名自然也可与日月并曜。[4]172
尊崇书道,必然重视书统。项穆认为,书法之统绪在书法艺术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统绪不明、学书无益,故《书法雅言》的开篇章节即为“书统”。隋唐以降,帝王的推重加上历代书家的拥戴与践行,王羲之书风几乎独尊天下。书法领域建立起了以王羲之为“宗主”,以王献之、智永、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颜真卿等名家为“羽翼”的书法正宗。项穆对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以及以其为正宗的书法史观十分认同。他在《书法雅言》中说:“宰我称仲尼贤于尧、舜,余则谓逸少(王羲之)兼乎钟、张,大统斯垂,万世不易。”[4]72这里,项穆将书圣王羲之与儒家的“大成至圣”孔子相并举,认为王羲之书法集历代之大成,裁成今体,贡献巨大,其书风不激不厉,风规自远,可谓万世之楷模。项穆还认为:“书不入晋,固非上流;法不宗王,讵称逸品。”[4]127事实上,项穆在品第历代书风时,也确是以王羲之书法作为参照标准,他在论及唐宋以来各代的书法风气时说道:“第唐贤求之筋力轨度,其过也,严而谨矣;宋贤求之意气精神,其过也,纵而肆矣;元贤求性情体态,其过也,温而柔矣。”[4]72
明代末期,社会受到“阳明心学”“童心说”“至情论”等文化思潮的影响,一些外来文化也传入中国,当时的社会矛盾较为突出,在此社会状况下,书坛奇象百出。书家们多强调以书写心,书法艺术独出机杼、戛戛独造者十分普遍,甚至审美迷失,以丑为美,甚至以恶俗诡厉自标新奇。项穆对社会上的这种现象表示十分担忧,他说:“独怪‘偏侧’‘出王’之语,肇自元章一时之论,致使浅近之辈,争赏毫末之奇,不探中和之源,徒规诞怒之病。殆哉书脉,危几一缕矣!”[4]128可见,项穆对王羲之一脉的书统传承极为重视。他对社会上的种种乱象进行了批判:“后世庸陋无稽之徒,妄作大小不齐之势,或以一字包络数字,或以一傍而攒簇数形;强合钩连,相排组纽;点画混沌,突缩突伸……正如瞽目丐人,烂手折足,绳穿老幼,恶状丑态,齐唱俚词,游行村市也。”[4]129这些,都说明了项穆对自李唐以来以王羲之为宗主的书统观念的推重与维护。
(二)敦心性而尚德行
蔡邕在《笔论》中言:“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6]王羲之在论书法时,以行军布阵作比,言“心意者将军也”,将“心意”置放于最为核心的地位。[7]30虞世南则说:“心神不正,书则欹斜。志气不和,字则颠仆。”[8]虞将“心神”“志气”等置放于相当核心的位置。由此可见,汉唐以来,人们普遍关注到心性与书艺之间的内在关联,认为书法艺术统摄于作者的心性之中。书家们的性情、性格、心理状态、先天禀赋等会直接影响到书法艺术活动,乃至影响到书作的优劣成败。
中唐以后,儒学逐渐吸纳佛教“本体论”的思维方式。两宋以降,儒学逐渐形成了以二程、朱熹为中心的“理学”派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派。在“心性论”的大背景之下,书学理论也因之而变。书家们的德行、学养、性情等内在修养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书法艺术逐渐由注重实用转为注重书家的内在修为,走向了内涵式发展的道路。迨乎明代,“心学”之风愈演愈烈,王守仁继承了陆九渊“心即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思想,提出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哲学主张,海内风行。书法艺术受其影响,也将“反求诸己”“发明本心”作为书法学习的方法论,故而心性与书艺之间的内在关联被进一步关注,书法写心、字如其人的观念被进一步放大。
受到传统儒学、宋明心学以及当时社会时风的影响,项穆书学思想的构建也以“心性”为根,认为书法与道德、文章、勋猷、节操等一样,都是人心性的外化。书家若想在书法艺术方面有所成就和突破,就应该深入挖掘自心。项穆在《书法雅言》开篇的“书统”篇中即提出“人正则书正”的观念,又在后面的章节中专门论述心性与德行的关系:“夫人灵于万物,心主于百骸。故心之所发,蕴之为道德,显之为经纶,树之为勋猷,立之为节操,宣之为文章,运之为字迹。”[4]90-91项穆十分注重书法艺术的人格化,他坚信:“有诸中必形诸外,观其相,可识其心”。[4]182在项穆看来,每个人人品不同、性情不一,不同的人品和性情会在运笔中展露,因此,项穆时常以人喻书:
盖闻德性根心,睟盎生色,得心应手,书亦云然。人品既殊,性情各异,笔势所运,邪正自形。书之心,主张布算,想象化裁,意在笔端,未形之相也。书之相,旋折进退,威仪神采,笔随意发,既形之心也。[4]181-182

项穆深刻理解心性与书艺之间的内在关系,十分注重书家个人德行的修为。不论是书法学习还是书作鉴赏,他都认为“正心”“诚意”为修身之本,是学书、鉴赏之基,书家只有做到“心端澄神”“勿虚勿贰”,才能真正悟透书法艺术的内涵。[4]183因此,他化用《大学》中“三纲八目”的内在逻辑论书法:“故欲正其书者,先正其笔;欲正其笔者,先正其心。”[4]182同宋明理学的伦理天道化、天道伦理化一样,人品与书品,心性与书艺的贯通是艺术道德化、道德艺术化的重要表现。项穆无疑是这一思想的接受者,同时是这一思想重要的推动者和传播者。
(三)贵新变而用中和
创新是艺术的生命。中国书法之所以能千百年绵延不绝、万古常青,与历代书家对书法艺术的继承与新变密不可分。项穆十分重视书法的创新,认为书写的过程犹如行军布阵,字的结构与篇章是建立在审时度势的权谋与决断的基础之上,并以军阵比之书法:“兵无常阵,字无定形;临阵决机,将书审势。”[4]139
同时,项穆认为,新变是有一定限度的,书法的新变要遵循书法艺术的内在规律:“然阵势虽变,行伍不可乱也;字形虽变,体格不可逾也。”[4]139项穆认为,青天白云、和风清露、朗星浩月、寒雪暑雷,是自然之常态,而迅霆激电、霪雨飓风、夏雹冬雷、扬沙霾雾,是自然之变态,这就好比书法,中正平和、不激不厉为其常态,奇崛雄肆、诡厉惊奔为其变态。书法也好,自然也罢,都应该以常态为本,以变态为用,绝不可逆其道而为之。[4]139
新变的关键在于对传统的取舍。如何取舍?项穆认为,须有“中和”的审美观,这显然是受到传统儒学观念的影响。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9]《中庸》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10]足见儒家先贤将“中庸”“中和”视为道德活动、行为规范和审美原则的最高标准。书法之美的关键也在“中和”,所谓“中和”,实际上就是书家在书写活动中对于各种尺度的把握。如书法创作中笔势、空间的顺与逆、藏与露、曲与直、方与圆、肥与瘦、疾与涩、收与放、疏与密、大与小、向与背等矛盾的处理,都离不开“中和”的准则。王羲之在论及书法审美的总原则时,言:“字贵平正安稳。”在论书法的字形结构时,言:“不宜伤密,密则似疴瘵缠身(不舒展也),复不宜伤疏,疏则似溺水之禽(诸处伤慢)。不宜伤长,长则似死蛇挂树(腰枝无力)。不宜伤短,短则似踏死蛤蟆(言其阔也)。”[7]35实际上,王羲之也是在强调“中和”的审美准则。
项穆的书法审美观深受儒家“中和”思想的影响,他在《书法雅言》一书中将书法艺术的等次划分为:正宗、大家、名家、正源、傍流等5个层次。[4]105项穆在论及“正宗”时说道:“会古通今,不激不厉;规矩谙练,骨态清和;众体兼能,天然逸出;巍然端雅,奕矣奇解。此谓大成已集,妙入时中,继往开来,永垂模轨,一之正宗也。”[4]105显然,项穆是将不激不厉、骨态清和的“中和”之美视为了书法审美的最高标准。此外,项穆言道:“然中固不可废和,和亦不可离中,如礼节乐和,本然之体也。礼过于节则严矣,乐纯乎和则淫矣。所以礼尚从容而不迫,乐戒夺伦而皦如。中和一致,位育可期,况夫翰墨者哉!”[4]156
项穆还时时处处用“中和”的标准去评判历代书法艺术之优劣,如他在谈论书法用笔的方圆和奇正等问题时言:“圆而且方,方而复圆,正能含奇,奇不失正,会于中和,斯为美善。”[4]156又言:“奇即运于正之内,正即列于奇之中。正而无奇,虽庄严沉实,恒朴厚而少文。奇而弗正,虽雄爽飞妍,多谲厉而乏雅。”[4]147在论及书法的老少时言:“老而不少,虽古拙峻伟,而鲜丰茂秀丽之容。少而不老,虽婉畅纤妍,而乏沉重典实之意。”[4]163
从这些论述中可以清晰看到,项穆所追求的书法艺术境界是修短合度、轻重协衡、阴阳得宜、刚柔互济。这与儒家“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的“中道”思想是一致的,然而,要达到“中和”的境界非易事。项穆在“取舍”篇中,以唐人为例,认为著名书家如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李邕、颜真卿、柳公权、张旭、怀素、陆柬之、徐浩、孙过庭等都未能达到尽善尽美的“中和”境界,至于宋人,由于过于高标尚意,注重个性与创造,更是与“中和”的审美观念越走越远。故此,项穆十分鄙视苏东坡、米芾等人的书法:“苏似肥艳美婢,抬作夫人,举止邪陋而大足,当令掩口。米若风流公子,染患痈疣,驰马试剑而叫笑,旁若无人。”[4]191项穆反对学习苏轼、米芾等人书法,并非其一时过激之论,而是有其美学思想作为思想基础:“苏、米之迹,世争临摹,予独哂为效颦者,岂妄言无谓哉!苏之点画雄劲,米之气势超动,是其长也。苏之浓耸棱侧,米之猛放骄淫,是其短也。皆缘天资虽胜,学力乃疏,手不从心,藉此掩丑。”[4]190可见,在项穆看来,苏、米等人之所以能成为名家,主要得益于他们超拔的艺术天分,而天资平庸的人如果盲目地去学习苏、米等人的书法,最终只能落得个东施效颦的结果。这也正是项穆在资学关系中更强调“学”而非“资”的原因。项穆坚信,有学而不能者,未有不学而能者;天资超过学力,就常常会表现出癫狂的弊端;学力超过天资,尚且能够中规中矩地保存其规范。天资是学习书法不可或缺的,但是学力是首要的。学力功夫是可以努力实现的,天资禀赋是不能勉强的。天资放逸聪慧的人,或许可以通过卖弄机巧、标榜新奇,张扬冠绝于一时;学力深湛精熟的人,却能够恪守规范、循规蹈矩,成为万世的楷模。[4]114这也许正是项穆重王书而贱苏、米的内在逻辑。
三、余论
项穆书迹流传不多,文献中记述亦少,这大抵与其困顿科场、位卑言轻、晚年居所又惨遭回禄等有关联。从笔者所掌握的史料来看,有关项穆书迹的著录主要有:《石渠宝笈》卷十一收录的《楷书五言律诗一首》、《式古堂书画汇考》卷二十七中收录的行草书纸本《贞玄道人近作诗帖》、草书纸本《折杨柳诗帖》、《月下步虚辞》、明神宗万历二十六年(1598)所书的行书纸本《贞玄道人元旦诗帖》等。

项穆身处人心思变的晚明时代,其时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就书法艺术而言,流派纷纭、风格迭起。整体来看,明代书法复古者不及元人、新变者不及宋人,书法艺术呈现出颓唐之势。项穆奉王羲之书法为圭臬,崇尚中和的美学品格,这在奇态百出的晚明书坛确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他不仅维护了王羲之在书统中的崇高地位,而且对崇尚心性解放、寻奇猎怪的晚明书风也有所反拨。但是,他受到传统儒学审美观念的束缚,对社会上出现的新生事物往往持否定态度,很难接受书家“变乱古法”的行为,他对王问、杨柯、马一龙、张弼等人书风多样性的探索皆持批评态度,甚至使用了近乎恶毒的语言来攻击谩骂,这些未免有些过分。就书法艺术的实际成就而言,项穆的书法由于过于保守内敛,缺乏创造力和艺术表现性,虽小有时名,终未能开宗立派、在书法史上博得一席之地,实为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