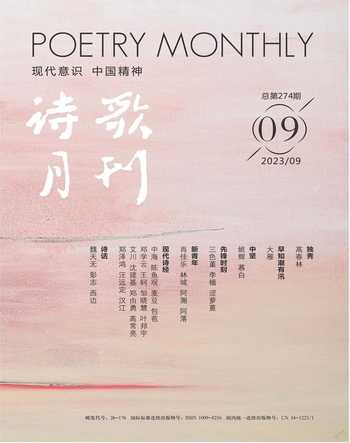反讽:进入新诗的一条路径
反讽(irony)是西方语言学、文艺理论与批评中的关键词之一,关于其语源、语义及其演变、运用的研究非常丰富。在现代批评中,由于新批评派理论家T.S.艾略特、I.A.瑞恰兹的重新阐发,它成为衡量文学/诗歌价值的一般标准。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在《文学术语词典》中说,反讽在大多数现代批评中仍保留了原意,即“不为欺骗,而是为了达到特殊的修辞或艺术效果而掩盖或隐藏话语的真实含义”。简单地说,反讽是“所言非所指”或“言在此而意在彼”。
我们这里要谈的是新诗,所以首先,反讽更多指的是“言语反讽”(verbal irony,又译字面反讽、词语反讽),通常是文本局部言辞的反讽,在一些精短的诗里也会出现“通篇性反讽”。其次,人们通常把反讽等同于讽刺、挖苦,不会把它看成现代诗的特殊表现手法,也就不会特别留意。再次,反讽在西方修辞学、诗学中源远流长,意涵丰富,以至有些哲学家,如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将它上升为人的生存立场和处事态度。
我们无须在概念里打转,还是结合具体文本来谈。下面是一首我们认为具有反讽意味的当代诗:
我来到临街的路口,用手中的
木棒画圆圈,我把自己围起来,
一个阴间就这样形成了。
在我的木棒下,在火焰像
雄鹿一样跨出四条腿之前。
我有些感伤。我们都活得过于自我。
一个人奔赴空寂时的得意。
天花板上就是尽头。你在深夜时
望着那庞大的阴影,一动不动。
我点着一张纸,它像蝴蝶一样张开翅膀,
在圆圈内,围绕我跳舞,
转瞬就变得暗红。它在向下落,
像你的骨灰带着火星,扑落在地上,
要隐身进土里去。
我知道它们听见了你的召唤。
余下的蝴蝶还在圆圈里空荡荡
牵着我行走,
接近了你住的地方。 (王天武《清明》)
诗题是“清明”(从全诗看,拟题为“中元节”更合适。无法揣测这是否有意为之。可能由于身体状况等原因,诗人在清明节无法到墓地去祭奠),我们很容易明白诗人在祭奠谢世的亲人,但诗的前半部却像是在祭奠自己,至少是把自己和亲人一同祭奠,直到第八行“你”的出现。“我把自己围起来,/一个阴间就这样形成了”,此“阴间”无比虚幻,但对诗人来说却极其真实,是他向往之地。这已有反讽之意。“一个人奔赴空寂时的得意”中的“得意”一词,反讽性很强。此句上一行用了“我们”,下一行首次出现“你”,因此,“一个人”当指逝者:逝者前往阴间时是欣喜的,因为终于脱离苦海,“我”却不得不苟活其中。这首诗的风格是写实的,其中的幻想(“火焰像/雄鹿一样跨出四条腿”)也写得历历在目,却给人以惊悚又感伤的梦幻之感:反讽手法强化了但同时抑制了感伤。这就接近I.A.瑞恰兹所言,反讽“存在于引起对立而又互为补充的刺激作用”,其效果是获得诗的“内在的平衡”。韦勒克则认为,反讽就是矛盾的形态,“矛盾是反讽的绝对必要条件,是它的灵魂、来源和原则”。在王天武的诗里,生与死是对立、矛盾的,感伤与得意也是如此,但诗的情感最终还是趋向难以摆脱的“空寂”或“空荡荡”。
不妨再读王天武的另一首诗《你的名字》,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清明》中“你”指谁,也可以比较一下具有反讽和不具反讽的诗,有什么不同:
我们知道,只有身份证和残疾证中
你的名字才被使用
现在死亡证和墓碑上你的名字又如同新生
你的照片代替你坐着
在我对面,类似于安静
我们知道,这是平常的死亡
你的名字將不再使用
但是在悲伤还没有完全消散之前
我们试图将那名字从死亡中拯救出来
你的名字,母亲
这是我们能共享的唯一的永恒
诗写的是诗人到墓前祭奠母亲的情景(也可能是回忆中的情景),他似乎在跟母亲说话,希望母亲再度获得新生。诗的声调、节奏与前一首基本一致,没有大的情感起伏,但多了一点黯然神伤:母亲留下的只是死亡证和墓碑上的名字,“这是我们能共享的唯一的永恒”。在《清明》中,反讽的加入使得诗的情感层次更为丰富;这首诗中,只需向母亲坦陈心中所想、所愿。当然,“平常的死亡”依然带有一丝反讽意味。
用王天武的诗来说反讽,也许会让有些读者觉得不够典型,与他们印象中的反讽有很大的差距。反讽手法是舶来品,用得好的新诗并不多见——被当作反讽手法谈论的那些新诗,在我们看来大多用的是讽刺;讽刺是反讽中的一个要素,但不加辨别地混用或换用,既取消了讽刺也取消了反讽的意涵。王天武也不一定认为,甚至会否定《清明》用了反讽。这是个悖论:倘若诗人的意图很明确,反讽意味太明显,诗会失去含蓄蕴藉,算不得好诗;倘若诗人自己没有意识到反讽的存在,解读者就有贴标签的嫌疑。此外,现代诗中,反讽极少单独出现,往往与讽刺、戏仿、戏谑等手法相混杂,这是它不易被澄清的原因。下面来看诗人夏宇写于1984年的《鱼罐头——给朋友的婚礼》:
鱼躺在番茄酱里
鱼可能不大快乐
海并不知道
海太深了
海岸也不知道
这个故事是猩红色的
而且这么通俗
所以其实是关于番茄酱的
夏宇的诗与王天武的诗,完全是两种类型和风格;把王天武的诗叫现代诗,夏宇的诗就要叫后现代诗,而解构性或后现代性,正是批评家谈论她时经常提到的。乍看上去,《鱼罐头——给朋友的婚礼》像一则童话或寓言,如果删去副标题,读者可能完全摸不着头脑;有了它,我们才能在鱼罐头与婚礼间建立联系。但别忘了,在后现代看来,所有事物间的联系都是即时、脆弱、不可靠的,是人为的权宜之计,是临时的修辞机谋。夏宇还有一首诗叫《腹语术》,写于1980年代中期:
我走错房间
错过了自己的婚礼。
在墙壁唯一的隙缝中,我看见
一切行进之完好。他穿白色的外衣
她捧着花,仪式、
许诺、亲吻
背着它:命运,我苦苦练就的腹语术
(舌头是一匹温暖的水兽 驯养地
在小小的水族箱中 蠕动)
那兽说:是的,我愿意。
它写的是“我”的婚礼,写“我”金蝉脱壳,去旁观婚礼进行时的“我”的一举一动。《鱼罐头——给朋友的婚礼》同样写婚礼,其中既没有“我”或“朋友”,也没有出现任何可暗示婚礼的语词。诗人、摄影师廖伟棠说它“很后现代”:
假如鱼罐头是比作婚礼的话,这时候你返回去看第一句就会知道:大海是什么?
本来我们拥有大海一样的爱情,我们的情感和大海一样宽广,然后你为了给爱情保鲜,自己躺到了番茄酱里,躺到了一个罐头里面。
其实这首诗有点讽刺那种观念:我们想象中的爱情最后该以婚姻来作为完满的结局。
因为你们相爱可能是为了宽广大海,但你的爱情却变成了番茄酱鱼罐头,那是蛮可悲的。
你以为番茄酱它永远那么鲜美,但实际上它加了多少防腐剂,加了多少味精在里面?
鱼罐头——婚礼——大海——爱情——防腐剂、味精,这些全然不相干的物质、非物质的东西,是怎么在诗中“搅拌”——像鱼罐头的制作——在一起,又“剑指何方”,廖伟棠已说得很通俗也很通透。某种程度上,是他的解读让这首怪里怪气的诗,在我们眼前焕然一新。两个核心物象/喻象即鱼罐头与海,一小一大,一密封一敞开,被诗人“暴力”扭结。我们可以称这种手法为后现代的拼贴,也可以用现代诗学术语称之为奇喻(又译曲喻)。在艾布拉姆斯看来,奇喻就是要在两个似乎不相似的事物或情景之间,确立一种“惊人的”“做作的”类似,具有明显的夸张色彩。新批评派则认为它是比喻的一种,是智性与感性结合的典范。《鱼罐头——给朋友的婚礼》体现了诗人的匠心独运,智性色彩更加浓郁,这是不可否认的,因此可能让一部分读者感觉陌生而新奇,另一些读者则可能觉得做作而不自然。
廖伟棠认为《鱼罐头——给朋友的婚礼》中有讽刺的观念,我们觉得用反讽的说法也许更恰当,而且属于“通篇性反諷”。从一般意义上说,讽刺是针对他人的、单向的,重点在讥讽他人的荒唐、丑陋,或某种事物、现象的不可理喻。反讽包含讽刺,但却是在讽刺他人的同时自我反思,重点在反省自己身上有没有所讽刺者的影子。认为《鱼罐头——给朋友的婚礼》只是讽刺朋友将婚姻作为爱情的完美结局,削弱了这首诗的力量。诗人是在这一过程中,反观自己是否也会如此,或者已然如此。诗人超越了所讽刺的对象,也超越了自我(有超越才会有自我反思),指向对当今社会制度化、仪式化的婚姻的反省。结合夏宇的《腹语术》,这一点会看得更清楚。扎加耶夫斯基晚期诗中有一首《成熟的史诗》,就内含对作为诗人的自己的反讽:
每一首诗,甚至最简短的诗,
也可能生长成一部成熟的史诗,
它甚至可能随时爆炸,
因为它随处藏着巨大的
奇迹和残酷库存,它们耐心等待着
我们的注视,我们的注视可能释放它们,
打开它们,就像高速公路的弓在夏日展开——
但我们不知道它通向什么,如果我们的想象
能够跟上它丰富的现实,
所以说,每首诗必须说出
世界的整体;唉,我们的
头脑在别处,我们的双唇是
薄的,筛选着意象
仿佛莫里哀的吝啬鬼。 (李以亮/译)
我们把反讽里的幽默,看作诗人再现,同时是应对生活的复杂性的必要元素。正因为生活如此复杂,诗人才需要时时反省,而诗是体现这种反省的最佳方式。
美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新实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理查德·罗蒂,把挑战、抵抗常识,拒绝使用诸如公正、科学、理性、革命、进步之类“终极语汇”(final vocabulary)的人,称为“反讽主义者”。他们始终担心自己是否加入了“错误的部落”,被教给了“错误的语言游戏”。而真正的文学,要求对既存的一切保持怀疑。就像诗人、作家苏珊·桑塔格所言,“比那个试图做(和支持)正确事情的人,更倾向于怀疑,也更自我怀疑”,包括对自我文学观念的质疑,因为“哪怕是最苛求和开明的文学观念,都有可能变成一种精神自满或自我恭维的形式”。在现实中,我们见到了太多“精神自满或自我恭维”的写诗的人,或者说,见到了太少具有反讽意识的诗人。今天说诗人是一个反对一切、睥睨一切的群体似乎不合时宜,也消除了这个群体的复杂性,但可以说,诗这种文体,天然地要求诗人具备反讽意识,甚至要有比以往更强的反讽意识,才能维护其中的个人视域,并让读者借助它来观察现实,反思自我。
魏天无,供职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