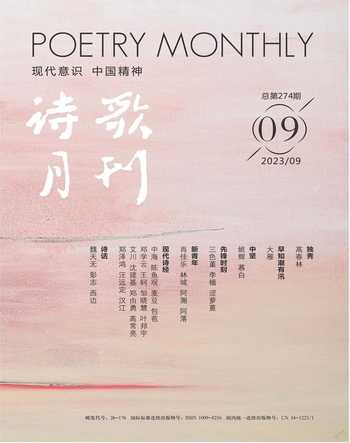橘花辞(组诗)
刮痧
它徘徊在盛夏的肌理间,
身体毫无征兆地签下投降书,
切入呻吟的人间与闪电。
酝酿的惊雷等待发作,
将暴雨前的因果一一偿还。
绷紧经脉放入迟钝的箭矢,
痉挛射向午后的靶心,
淡盐水洗不掉加重的黄昏,
仅存欲望更加琐碎,
无法完成一场黑夜中的谈话。
枕头长满生硬的白发,
在眉心交换一朵红玫瑰,
或在左右两肩各点一盏灯,
横亘脊背的一根琴弦,
被一双陌生的手拨动着。
心口的颤音起起伏伏,
不知所措地溢出紧闭的毛孔。
橘花辞
小时候,老家门前栽了一棵橘树,
爷爷说是从远方亲戚那移植过来的,
无核。咸甜。带着春天的信仰……
从开花到结果,橘树投入了
一生的愿望,可是大多数橘花
无法修得正果
有幸出现枝头的果子
被我写进放学路上的约定,
它们尚未成熟就被摘下
吃掉。青涩滋味留在舌尖上。
过去多年,橘花总是怪我无情,
青春游戏无法带入中年——
面对突然出现的十万亩橘花,
其中是否还有一朵,将我的青涩唤醒?
石化叶
这是世界上最后一片叶子,
沉积于湖底,千万年来煤的弃婴。
后来它躲在石头夹缝中,
随母亲一起嫁到了异性人家。
这些年,它只想投身于一场火,
以燃烧的舞蹈回到天空,
或为一棵树熟悉亲人的呼吸。
直到把自己淹留成腐烂的时间,
完成一篇献给叶子的悼词,
虽没有人愿意去阅读,
也不见有泪水从词语间溢出。
风在吹,叶子虽还是叶子,
可身后已多了一个句号
——铁制的不再转动的轮子。
此刻我手心就捧着这片叶子
容颜模糊,但纹理清晰,
那些被风吹干的岁月与命运纠缠。
面对它的所谓托付——
我不知道今夜将如何继续……
偌大城市边际,横亘着一条
让我剪不断、理还乱的地平线。
独坐
当一个人独坐时,决定写诗,
让妄想长出一对金色翅膀,
被我反复唾骂的文字成为兄弟。
从海底写到山顶和落日,
从一条河的源头到另一条河,
渐渐走远的脚步裹进冬天的棉衣。
黑夜填满一座阁楼的童年,
勇敢写诗吧,不知所从的孩子,
把一枚旗插到旷野中心,
等待大雁捎来变老的距离。
没有一棵树愿意为人类默哀,
写作者掌起灯,每个角落凸显陌生,
他们复制了我的堕落。
如果一切还能在人间继续,
那就写诗吧,在土地里抽出白发,
拴住一颗正准备出逃的星星。
近视
我们曾生活在混沌的世界里,
等待黎明投喂的帆影浮出海面,
將黑夜送往山的外面。
被过滤的人间如此虚伪,
除去冬日还能保持冷冽的清醒,
无法读懂残留身体中的细节。
当瞳孔经历雨水的洗濯,
一块巧克力在春风中虚化,
只要闭上双眼,我们就能回到
锈迹斑斑的青铜年代。
每次醒来,黑皮肤是唯一的圣洁,
光滑得让人捉摸不定,
吹口气,总有沙粒掉落地上,
青春的弹珠与黑夜的纽扣,
忘了写上编号的收藏品。
谁告诉我,花只能绽放一次,
而我眼里却没有一条路更加年长。
孩子长大后跨进了城门,
只有母亲还在寻找走散的魂灵。
陈鱼观,本名陈霜,”70后”。有作品发表于《诗刊》《星星》《十月》等。著有文化地理随笔集《雁荡归欤:乐清山水间的小声音》《溪山语境:一座南方小镇的诗意停留》、现代汉语诗集《台风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