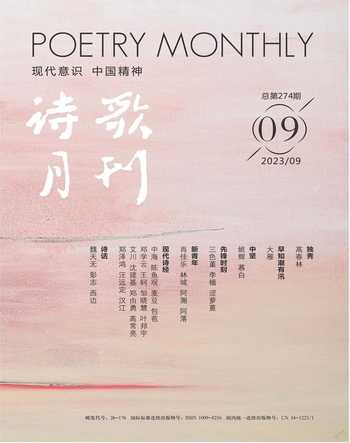诗,被灵光一闪的词语所照亮(创作谈)
高春林
诗是什么?似乎从来就未有一个定义。作为一个诗人,一定要给的话,要给出语言的形象。孔子曰“诗言志”,以及对《诗经》那个概述“诗无邪”。这几乎就是说,诗是对内心情感与世界认知的一种修辞学。汉字的出现意味着诗的出现——人类从蛮荒时代开始走向文明,人们开始了一个内在的唤醒——人类之初的本能欲念就是走出黑暗、走向光明。如此说也就回到了“本源”的艺术——形象、淳朴、本质。海德格尔说,艺术是本质的诗。事实上,诗就是最本质的语言。这是一种灵光——一种异己的神秘力量,带来了灵光闪现的一个瞬间,由此建构了诗的生命。
诗歌的“灵光一闪”是如何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呢?帕斯也曾发出过这样的疑问。在中国,《诗大序》中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志,是最初的记忆,也为一种精神存在——在诗人发出声音的这一刻,我们的精神有了另外的向往、意志以及由此生发出天地间的一缕光辉。最初的诗歌或许就是语言的启蒙,是人与词之间的彼此唤醒。
当代诗的语言,也即我们生活的经验。诗歌是一种本源的艺术,诗歌也是再造的语言。这里的二元论在于,一方面诗歌的艺术在指向本源的艺术,即它的语言在指向并揭示事物本质的时候,是指向世界的本质也是历史的本质,这正是诗之为诗的一个前提和终极所在。另一方面,就是我们为诗而求索的——语言的创造,这几乎是所有拥有诗歌意志的人的一个行动方向,当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一些事物或事件会突然呈现在面前,那种模糊的事物甚至是如此鲜明又可疑,我们的眼睛在最初的发现之时或许是漫不经心的,我们会误认为这不过是一些事物以及由事物组成的意象群,但我们说出这事物的含义的时候,语言便回到了它的本色——一种现实的存在。这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文学经验生成的过程。人们常说,生活模仿了艺术,历史的现象有着诸多的面孔。诗歌的语言就是我们生活的经历转化为诗时,日常经验生成了诗的情感、思想和指向,诗的经验就是这一过程中的语言创造。一首诗是被灵光一闪的词语所照亮的,一首诗更是当语言在深入我们生活内部时那些无法言传的事物促成的意会或指向。这时的词语即是生命,它行走于世界,它是世界的核心和灵魂。面对生活的日常,以及“冷风吹打的话语”,诗人埃利蒂斯写道:“我唯一关心的是我的语言,在荷马沙岸上……我唯一关心的是我的语言,带着黑色的震颤。”这就是语言的本性,有震颤之力。
如上所说,从最初的语言到当代诗的语言似乎都布满了神秘主义色彩。关于语言的神秘性,耿占春有过精辟的论断,他说:语言的神秘性也许在于“语言既是一种使事物更加神秘的力量,又是一种分析性的力量。语言是事物的隐喻,又是隐喻的分解或反讽。这是一种和经验领域接触而更加有效的语言神秘主义。”也许作为诗人的我们都是语言的神秘主义者,当我们开始写作,我们就是语言的幽灵,在语言的表征世界里,我们的意识像一个微分子,在游走、感知和唤醒,这时我们有了另外的知觉——当然重要的是我们的知觉只属于诗人独特的意识与极具个人性的经验。这是一个锐度,我们所拥有的词也即众多的尖锐簇拥着某个事物或事实。这时的词不仅赋予我们自身以清醒的知觉,更赋予了生活中的现实一种高辨识度和强感受力,因为语言不仅是一个内心生活的传达,关键还来自于对社会现实的形态化的叙述。这也可以说是诗歌语言的现代性,或直接说诗歌话语神秘的现代意义。词这时是诗的灵魂,语言这时是诗人的行动。事实上,我们的行动就像我们的经验总是处在未完成时的一个状态,换一种说法,语言在其行动的过程中有着持续的力量,以及持续的更高的品性要求。
有一种内在的精神一直贯穿在语言的行动之中,尤其是当修辞批评从社会、政治,甚至某些日常的场域退居到只有文学承载其旋律时,这种精神作为语言功能的存在,更是突显了诗性的力量,无疑这是一种诗歌意志。我们说,诗在远方,那么诗歌语言就是向着辽阔奔走,是从“此岸”到“彼岸”的横渡。诗的语言正是如此,像是普罗米修斯的呼唤,让词自由飞翔,之后方有一个阔大的远方。这是精神内部的声音,是冥冥之中语言的召唤,如曼德尔施塔姆的那句诗:“黄金在天空舞蹈/它命令我歌唱。”从历史上看,唐朝诗人杜甫就怀着这种诗歌意志“百年歌自苦”地完成了他的一生,让他的人和他的“史诗”一起成为一个时代伟大的存在。诗歌这种史诗般的见证,一次又一次地突显了语言的自由和正义的力量。百年歌自苦,新诗也正好历经了一百年,不得不說这一百年的语言探索,正是诗人们的诗歌意志在塑造一个象征的世界。
有一种语言的自觉是诗人所应有的诗歌意识,甚至是诗歌必须保持的写作状态。这是自古就有的一种文学自觉,鲁迅曾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这里的艺术是一种境界,在强调诗回到个人化的写作价值。汉末魏晋时期,是社会现实苦痛,但精神上的自由与探索最为个性主义的时代,一种人格化的艺术心灵与艺术追求建构了独特的“魏晋风骨”。《古诗十九首》为什么能够开一代诗声之先河,因为在对时世、包括日常的一种感喟诗学中,诗的语言“突出的是一种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的悲伤”,如李泽厚所论,一种生命意识、生死与现实的喟叹,“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这种诗的元音,是诗人的理性精神,也是一种语言的自觉。新诗百年,诗歌的语言是一个孤独的探索途程,语言在返回现场,语言在创造属于诗的世界。从五四时期白话运动的语言突围,到穆旦所呈示的语言的现代性;从20世纪80年代诗的理想化抒情语言放逐,随着90年代初的社会转型到个人化叙事写作;从个人经验出发的一种抒写到多元化、信息化的新世纪诗歌话语的碎片化解构性方式。诗歌的语言不再是狂欢,而是一个精神自觉的语言途程,语言的内质、境界都在营造一个象征世界的新可能。这种自觉是语言内部的,它既是语义上的一个确认,因为古今诗歌所承载的都是人类的精神史,诗歌语言就是自我精神价值的确认,同时它又是诗艺上的创造,“为艺术而艺术”,并抵达诗的一个境界——一个纯粹的情感升华与净化的过程。诗之所以为诗,就在于,在这个自觉的意识上赋予语言以诗性的节奏和华章。诗以其语言的自觉来完成诗的修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