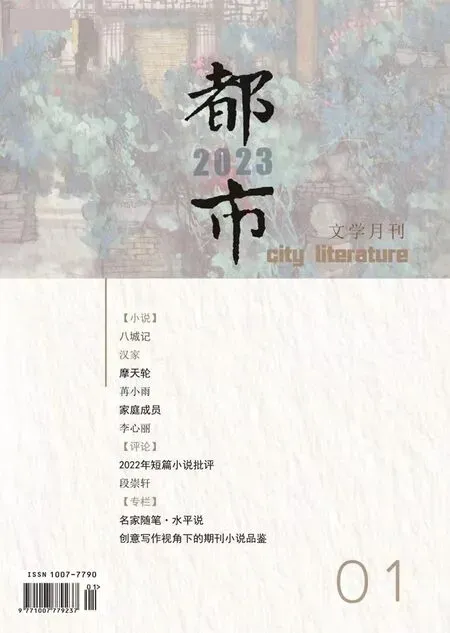静谧的谜语
文 陈思谚
1
此地民居惯带天井,在一楼用铁栅栏围起一块小小园地,有些人家在栏上开一扇门,与天井外的绿化带连通,稍加整理,铺上鹅卵石小路,里外一起设计成一个小花园。
也有人在绿化带的草坪上支起晾衣杆,天气好的时候晾晒洁净的衣物,这时候天井就可以当作洗衣房,很有趣味。另一些天井干脆开起店来做生意,理发店、收发快递、小卖部,或者搭成一间小小的茶室,常见到有人在里头打牌,一问,原来是房产中介的办公室。我还见到有卖杂粮煎饼的,细烟和香气从天井处飘出来,摊主一早出来,卖到十点半收摊儿。更常见的处置方法是干脆拿砖砌起来,加个隔热顶,置办上一些廉价家私,当作正常的房间出租给谋生的年轻人,平常屋子里只有三四个房间可供出租,如果加上天井改造出来的两个,可以租出去六个房间。这当然是违规的,但是如此坐享其成之法,还是诱惑了不少房东。
住进这处房东用天井改造成的一室户时,我正站在生活的路口,羁旅疲惫,行囊沉重。工作三四年,所得甚少,只养成花钱的习惯,又生疾病,住院、手术、疗养种种下来,好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敢打开银行卡软件页面看一眼余额。与曾经的恋人分开半年有余,仍旧少欢畅,多忧愁,一个人在上海,每每黄昏日落,看见家家窗户亮起灯来,心肠就像被揉成一团的宣纸,皱巴巴的,勉强展开了还不如团着。
正是这样的当口,原本一起合租的室友决定离开这个城市,我必须重新规划住所。说来惭愧,我在生活事务上长期习惯依赖别人,说是独立生活,其实总是得到别人的帮助,住的房子是室友找的,搬家是恋人帮忙的,连过冬的羊毛被都是上班地方的领导帮忙买的,在那之前,我连“天冷了可以换被子”都不知道,一个劲儿地喊冷。如果离开了各路好心人,我的日子指不定要过成怎样的一团乱麻。这一回我决心打起精神来,重新建立我的生活。寻寻觅觅,最后租下这个天井改造的房间时,与其说欠考虑,不如说是故意的,贪它看起来有意思。朋友朝我翻白眼,讲了不少住天井的坏处,一问价钱,更是觉得我脑子肯定不好使。无奈我就是被鬼迷了心窍,非要住下不可。想来我生活中的许多决定都是如此,糊糊涂涂,却莫名坚定,尽做些不经济的事情。
在一个春天,我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抱着一肚子破碎心肠搬进了这个天井违规改造房。随之而来的,当然是朋友向我预言的无尽麻烦,与一些偶得的趣味。
住在天井第一头疼的地方就是潮湿,江南地区的一楼,就算是朝南透气的房间也难以摆脱湿气缠绕的烦恼。尤其到了淫雨霏霏的黄梅时节,一不留神,墙上、家具上就会结上淡淡的霉斑。我那些皮包悄无声息地长满灰白的霉点,我拿酒精湿巾去擦,想着可以消毒,谁知过几天皮子就起了碎屑,破损了,我一筹莫展地瞧着他们,不愿去想为它们花过的钞票。更不用提我费了大价钱、大工夫搬进来的几箱子书。居室拮据,搬进来之后一直委屈它们待在箱子里,突然有一天发现有棕色的灵活小虫从箱子里钻出来,吓了我好大一跳,鼓足了勇气才敢打开箱子查看,虫子倒没看见,只是翻开书页,果然这里也难幸免于霉菌的侵害。若学古人晒书倒是雅事,只是梅雨连绵不见晴天,这几箱子书,成了负担坠在我心头。看来,读书固然是再民生不过的事了,但是买书藏书却属于贵族行径,需要居室宽敞,有人有闲来管理,才不至于浪费辜负。
不过潮湿天气也有好处,润物细无声。在湿润的空气中,日光流淌得也缓慢些,春天因而十分确凿。落地窗外的植物渐渐丰满,碧色由淡渐浓,好像拥有私人庭院,“细雨湿流光”之景唾手可得,再渐渐,淹没了我的窗口。玉兰、矮樱默默地抽枝拔条,开出繁盛的花,烟雨里吐露光芒,绣球不知不觉攒出新的花苞,让人心生期待。
意外的“访客”也叫人头疼。经常是晚上下班回来一开灯,地上横着一条胖乎乎的鼻涕虫,正慢慢地路过,长得是一副蜗牛抛弃了壳的模样,有两个小触角。看起来还算温和无害,翻着白眼拿纸巾把它捏出去就是了。有时候也能看见蜘蛛,第一次见到的时候差点吓死我,黑乎乎地趴在墙上,这种我是看都不敢细看的,更别说怎么对付它了。只能反复安慰自己,家里来蜘蛛是喜兆。不是有那种说法的嘛,晚上在家里看见蜘蛛,明天就会有客人来访。古人胆大包天,居然非常欢迎蜘蛛来访,称它们为“喜子”,七夕的时候还要捉小蜘蛛放在盒子里,第二天去看谁家蜘蛛网结得好。唐代的时候是看哪个网结得多结得密,到了宋时,好像就是看网的形状了。
《东京梦华录》里有一段:“七月妇女望月穿针:或以小蜘蛛安盒子内,次日看之,若网圆正,谓之‘得巧’。”我虽做不来这样的风雅事,但也不好不解风情地将它残忍打死(也是不敢),只好低声下气,恭迎恭送,试图与之和善相处。渐渐发展出一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智慧来,在一些我与蜘蛛沉默相对的夜晚,我总是想,如果我对别的不如意不欢迎之事也像对待这八脚客人一般,是不是会少很多无谓的烦恼?
天气晴好的时候外面已经是一副草木深深的做派了,草坪长成了草丛,昆虫藏在里面,因此收获了虫鸣之夜,虫鸣使对面人家窗口的灯光更有意味了,仿佛回到小时候,夜晚寄宿在农村外婆家,暗野中虫鸣四起,夜风中竹涛阵阵,望着若隐若现的灯火,我总是觉得这样的夜里酝酿着什么故事,就在那些窗口里、灯火中。黎明的时候听到外面机器声嗡嗡作响,拉开窗帘一看,是修剪草坪的工人,青草汁液的气味扑面而来,嗡嗡一阵过后,又是崭新的草坪。早开的花落英纷纷,绣球则日渐饱满,风景令人贪看。
夏日渐深之时处处浸在秾绿之中,花事不如春季繁盛,但四下葳蕤生光。雨一停,日头高悬,一切明晰可见,纹理昭然。闲下来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丛丛的绿色之中突然迸出点点白花,继而开成灿灿的一片。据园艺工人说这是大花六道木,花期很长,可以一直开到入冬。
小区里的猫有时候会来探望。这里的猫太多了,我也不记得曾跟哪一只打过招呼,反正就是有一只两只的,熟门熟路地经过我窗前的园地,遇上我在窗边的时候会停下来行一会儿注目礼,不知道是想打招呼还是想瞪我。猫的心情真是难以捉摸。
更多的是蚊子,我第一次发现蚊子还有这么多种类,有苗条脚长的、长着花斑的、其貌不扬的,还有细细小小成群结队的,从前课文里写“夏蚊成雷,私拟作群鹤舞于空中”,我没有这种童真心境,只能一边苦苦装纱窗,一边埋怨不知道躲在哪个角落里的蜘蛛室友,为何不勤劳捕猎,当作交租?
雨夜是很快乐的。屋顶是用空心的隔热材料搭成的,雨点落在上面敲出很清脆的声音,绵密不止,毛毛雨听起来像羽毛瘙痒,雨大了就像磅礴的钢琴声从巨大的琴腔里发出来,无休无止连成一片。读书读到人家形容大钢琴曲“如同群马踏过铁皮屋顶”,不住点头。小鸟来访时也有声响,是与雨声不同的咚咚声,有时候咚咚咚地跳着落到窗前来,能看见它的真面目,我见过一只,有身材高大的男生的手掌那么大,青灰色的身躯上饰以白色的羽毛,非常漂亮,落到草地上踱几步打个抖,侧头看我一眼,展开翅膀走了。
2
从我的房间开门出去,是晾衣服的公共区,搭着透明的屋顶,追着小鸟的脚步声抬着头出来的话,能看见它竹叶似的脚一下一下地印在屋顶上,也很有趣味。对面是另一个房间,租住着一位年轻人。我上班时间与他错开,少有见面的时候,偶尔见到,他也是沉默寡言。他总是背着个硕大的电脑包,附近有著名的互联网公司,公司建筑极具科幻色彩,两座楼体凌空而起,半空相会,仿佛时空通道。我猜想他是那里的员工,在那半空中的建筑里,一个一个亮亮的小格子里,有一个他的位置,他白天在那里敲电脑,夜晚回到这个天井。在我忙着晾衣服、扫地、晒书的日子里,对面总是紧闭门扉,如同一道沉默的风景,和四周的植物没什么两样,久而久之,我放下戒心,总是开着房门,以此来拓宽我的领地。
在这所房子里,还住着好几个人,但每一扇门都像石壁一样坚硬无言,我像是这片王国唯一的居民。开门进来,穿过阴凉的走廊,经过每一扇房门,拐弯穿过房间缝隙,才来得到天井,我总觉得自己隐居在山洞里,外面是平常的楼房街道,充满人间事务,洞中则别有一方小小天地,虽然逼仄拮据,却也刚好可以躲藏此身。
第一个与我搭话的邻居是隔墙的女孩。那会儿我正肆无忌惮地开着门,躺在床上煲着电话粥,突然探出来一个脑袋,皱着眉提醒我夜晚已深。我的山洞隐居幻想一下子被打破,此处尽管僻静,却不是无人,那些门后面、墙后面,另有一些生活在按照自己的节奏进行。这并不使我烦忧,反而抚平我心中某处的寂寞。我感到自己像一枚琴键,安静地待在自己的位置上,旁边是别的琴键,我们看起来一模一样,却拥有不同的声音。身处在一首乐曲中间,成为流动的声音中的一个音节,使我安心。
自从注意到隔墙的女孩,她的存在就越来越鲜明。我能听到那边细碎的声响,有时候还能闻到热气蒸发沐浴露那种特有的气味,我们在晾衣区的相遇也多了起来。渐渐地我知道了一些她的事情。她比我小一岁,在这附近的日企上班,出租屋条件有限,她仍然尝试自炊带饭,在狭窄的洗手间小心地洗干净肉和菜,唯一的桌子既当书桌又当料理台,切完食材倒进电饭煲之后再把桌面擦干净。她与我分享了不少简便的电饭煲食谱,有一道南瓜鸡块烩饭,确实方便美味,离开天井好久之后,我才想起来试试,可惜没机会与她分享心情。她有一个恋人在军中,偶尔休假过来,是一个高大黝黑的男孩,她带他骑着电动车去吃宵夜到深夜才回来,那会儿是她房中少有的喧闹时刻,音乐声和笑声人语一直起起伏伏,直到黎明。
但这样的时刻是很少的,大部分时候她非常安静,是一位时刻约束自己言行的好邻居,连晾衣服也绝不越界,常令我惭愧。我总是越界,我的衣服、鞋子、书,总是占据着公共区域的位置,她一直包容我,我老去找她,屋里有蟑螂啦,墙面有裂痕啦,洗衣机坏了啦,她不厌其烦地向我施以援手。秋天来的时候,她失恋了。那男孩眼看着就要退伍,却说家中另有一个女孩,与他的未来计划更加符合。这理由真是无懈可击,一个独自在大城市漂泊,容身于狭窄的出租屋里的女孩,她所有的优点,包容坚定独立种种,对他的未来生活其实意义不大。她使尽浑身解数,在洗手间和书桌间烹制的电饭煲料理,她所营造的那些,骑着电动车穿越夜色去吃宵夜的夜晚,播放音乐笑闹到天亮的夜晚,悄声讲电话舍不得睡觉的夜晚,确实是没有意义的。一个个房间像贝壳一样容纳着那些夜晚,这城市隐秘的历史只在这些贝壳的张张合合间吐露。一个音节融入乐曲之后,仿佛无声。
琪琪是后来搬进来的,住在房子最深处。她长着一张圆脸,眼睛周围种植着粗黑的假睫毛,小扇子一般扑闪扑闪。她是个安徽人,这个小区的外来者里约有一半来自安徽,我们总开玩笑,“上海是安徽的后花园”。琪琪在美甲店工作,美甲师们的手总是很晶莹很柔润,她们虽然用手劳动,但是这双手却是她们全身上下看起来最远离生活尘土的部分。琪琪嫌弃我的手糙,不知道保养,也不涂油彩,她给我涂抹护手霜的时候抚摸着我的甲床感叹,这样好的形状,留长了贴上水钻不知多好看,女孩子要对自己好一点,手是女孩子的第二张脸,茧子死皮,倒刺竖棱,一概不能有,命好的女人手都珍贵。从她手心传来的柔滑触感令我有些自惭形秽。
有一回,琪琪的母亲从老家过来,寄居在她的房间里。像所有的母亲一样,她一来,就洗了大堆的衣服被子,堆堆叠叠地晾在天井,我一打开门就吓了一跳,我的门口变成了染坊晾晒池似的,布料遮天蔽日,参差垂坠,那个正忙活着的黝黑瘦小的中年妇女见我出来,有些讨好地朝我笑笑。下午琪琪带她出去“逛逛上海”,回来的时候听到她抱怨上海人太多啦,路太窄啦,楼房太旧啦,这让我想起我的妈妈,她一直想看看我现在住的地方,我一直不敢,视频的时候都要先找好角度。琪琪和她母亲在我门口聊天,“妈,快收一些回去,占太多地方啦!”“怕什么,人家也没说什么。”
晚上我躺在床上想象着,在这样狭小的空间里,琪琪和她妈妈是如何挤在小床上入睡的,睡前在聊着这令人失望的上海吗?也许更多的时候是沉默的,小房间容不下太多的对话。她妈妈拿抹布把到处擦得干干净净的时候,把椅子上堆着的女儿没有闲暇和精力料理的大堆衣服和床单收拾起来丢进洗衣机的时候,怀抱着怎样的心情?我又想,如果是我的妈妈呢?恐怕这居所中的一切都要令她伤心的,上海的一切都要令她伤心的,在一座伟大的城市做一个观光者固然新奇有趣,还可以目光挑剔,但在她身边手足无措得像站错了地方,却是令人伤心的。琪琪妈妈在这里待了一个星期,她走后,琪琪看起来比加班到深夜回来的时候还要累,但她仍邀我去她房间做指甲。她将各式工具一一摆开,身处在它们中间,她露出主人般的骄傲,她的一双手,十指葱葱,柔滑如脂,如同某种理想生活的模型,从所有的疲惫和失望中延伸出来,凝聚着所有的希冀和想望。
3
门前有一条河,横穿过这个小区。我时常对这条河心怀感激。她光耀如练,岸边花木丰盛繁美,木槿映衬着垂柳,还有那些叫不出名字的水草,层层堆叠。穿过阴暗的走廊,尽头竟有这样一条河等待着我,简直如同小小的神迹。那年春天雨季很长,绵绵的雨笼罩着她,巨大的老树把那沉沉的影子投向她,淡薄的波光与如锦繁花交织出一个忧郁的故事,使我长久地踯躅在她身旁。到了夏季,一切晴朗起来,一切变得很深,夏季就是这样的,既清晰又神秘,河流在深深草木间闪着光,万物如同坦白的谜题。河边有人垂钓。太阳西偏的时候就有人来了,一直到夜深人静也还有人舍不得走,在岸边点一盏灯,一盘蚊香,长长久久地静坐。或许那就是想要解谜的人。
我认识其中的一个两个。常坐在北岸十三栋门口的那位陈叔是我们房东的丈夫,他的妻子是一位女王一般的人物,泼辣又狡猾。二十多年前他们刚来到上海的时候,她不顾劝阻从老家借了钱在这个小区买了好几处房子,如今每个房子都被改造成群居“洞穴”,她每天哗啦啦地带着一大串钥匙,逡巡在她的“领土”上。陈叔坐在他妻子的办公室——那间供房产中介们休息来往的茶室里的时候,一问三不知,这个过分普通的男人,像无数人到中年的男人一样,被自己的无能击败而不再惊讶,安于平稳的温和中带着一丝垂头丧气。但当他坐在河边的时候,仿佛摇身一变,变成了不出世的哲学家、高僧、武林高手,那些无能为力的事情统统在眉目不惊的等待中得到了和解。
另一位河边常客是独居的苏爷爷。他就住在我们对面,出出入入间,常有微笑言语。老人家的生活极其规律,我九点多出门的时候正好是他散步买菜回来的时候。到了下午四点多,他就会慢吞吞地带着一整套家伙,到河边去坐上两个多小时,他的动作里带着一种有条有理的缓慢,令人安心。他的妻子几年前去世了,儿子常年在国外,人生的暮年,他每天就这样安静地度过。那段时间,我刚从病中痊愈,推掉了很多工作,时日闲散,常常往图书馆跑,傍晚的时候坐在户外长椅上读书,眼前就是河流,苏爷爷坐在岸边。波光水影中,他的背影也微微荡漾起来。
这个小区,这个小小的人类聚居地,这里流动着的生活里潜伏着一个重要的主题。它有时候以“孤独”之名示人,有时候又使人感到“徒劳”,它还有个名字似乎是叫“荒谬”,它是一道静谧的谜语。每个人用自己的方法与它周旋,它却如影随形,越是对抗越是强烈。在房东阿姨叮当作响的钥匙串中,在深夜河边的点点灯光里,在一个个狭窄的居室里,在匆忙开着电动车路过的房产中介们身上,甚至是在那些茶室的牌局里,它展露神秘的微笑。我抬头望着河水旁垂钓的背影时,仿佛看到它坐在苏爷爷的身旁,微微荡漾。在诸种与之周旋的方法之中,也许苏爷爷找到了一条自己的道路,我愿意这样相信。一种节制的、规律的生活,一种把它请到身边平静共处的生活,当然还不足以解决它,但是在这种生活的深处包含着一种尊严,一种人栖身于万物之间应当拥有的尊严。
人有多少无能之事?又有多少可能之事?乐曲无时无刻不在流动,我感到那静谧的谜语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发肤,暮色从远处降临,草坪上有层毛茸茸的金光,低头读到宫泽贤治的句子:即使没有足够的冰糖,我们也能够品尝纯净透明的清风和桃红色的美丽晨光。为了拥有更多的快乐,我决定明天早上起得早一点,去品尝桃红色的美丽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