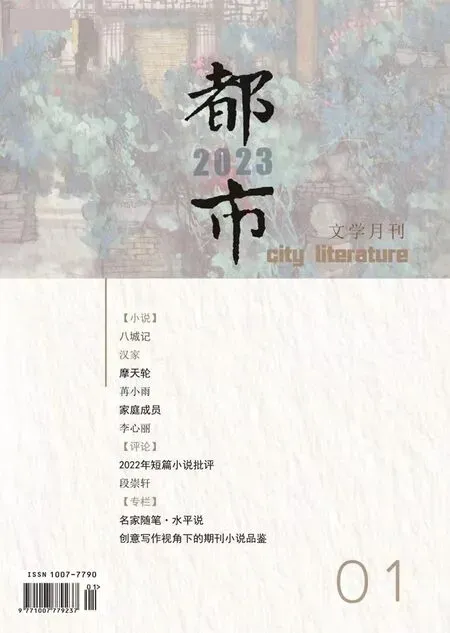解释一下什么叫专业
——读郑执《森中有林》
○钟小骏
钟小骏,1978 年生,祖籍浙江,长居山西。文创二级。小说、人物传记曾获奖,参与创作影视剧多部,有随笔、杂文等散见于国内各媒体。晋中信息学院创意写作兼职教师。
郑执的这篇小说原发《芒种》2020 年第10 期,被《小说月报》2020 年第11 期选载,出于很奇妙的原因,我今年11 月的时候才收到这期刊物,在同期有着梁晓声、蒋子龙和胡学文等大家在列的情况下,我还是被这篇《森中有林》给吸引了。所以尽管它是接近五万字的中篇,我还是一口气读完了。
人喜欢一篇作品,可能最深层的,或者说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这篇作品表现出来的“气息”,这个概念很接近“叙述者姿态”,比方说王尔德,比方说王小波。或者不仅仅是叙述者姿态,还有它的语言风格,比方说马克·吐温,比方说狄更斯。又或者也不只是叙述者姿态加上语言,还包含着叙述主题,比方说《1984》,比方说《局外人》。但必然的,作为读者,肯定是被某种独特的但又契合自身审美的表述给撩拨到了,激发了独特的神经信号甚至分泌了独特的激素,产生了短暂的上瘾反应。
反过来说,作者想要让自己的作品拥有这样的效力,肯定也不能单纯地只在某项或者某几项写作技巧上下功夫:只有宏大架构但没有大量的精确细节是不行的,语言出色但过度叙述是不行的,有明确的叙述目的但主题先行是不行的,有精彩的故事核但追求刻奇是不行的,有深邃的思想但难以对读者解释、不接地气是不行的等等等等。总而言之一句话,真想让作品向着“经典”靠拢,对自己放松要求是不行的,国外的库切和国内的毕飞宇两位已经给大家做了很好的示范。
要职业起来。
就像郑执自己说的:“《森中有林》,是疫情出不了门的时候写的。每天早上起床,我先照把镜子,跟自己说,这次写作对自己就一个要求:要脸。”
说实话《森中有林》的故事是比较俗的:一件凶杀案。这么重口味的故事核心或者说一切的源点在郑执的作品中太常见,以至于我觉得这甚至反过来束缚了他的表达——以他的笔力即使不使用这样的戏剧性元素也一样可以让人读到震撼,所谓于无声处听惊雷。但同样的,这样司空见惯的故事核,如何讲好也证明了他的能力。所以我们先看一下事件顺序,然后再来看郑执的处理。
机场驱鸟员吕新开打瞎了下岗狱警廉加海的一只眼睛,廉加海以此为桥梁把有视力障碍的女儿廉婕嫁给了吕新开,廉加海通过之前管理的犯人卫峰爱上了一个带着孩子的女人王秀义,王秀义跟着一个包工队头子郝胜利搭伙过日子,郝胜利有妻儿,所以对王秀义的儿子王放不好,还动手打他,郝胜利死了,为了掩盖动手者,在王秀义院里烧锅炉的卫峰帮助烧掉了郝胜利的尸体,但郝胜利植入头颅内的钛钢板被廉加海无意中发现,廉加海要报警,但闪了腰的他行动困难,于是把钢板交给廉婕送去警局,跟随廉加海的卫峰抢夺钢板时造成了廉婕的车祸致死,听到真相的吕新开偷了单位的打鸟枪要杀卫峰,卫峰联系了廉加海表示要抵命,廉加海制止了吕新开的报仇,但吕新开被单位的同事举报,最终因为偷枪被判刑一年,廉加海见证了卫峰的自杀抵命,从此一直在城市边缘种树,吕新开带着儿子吕旷总来陪伴,父子关系不好的吕旷成年后离开家乡,在从日本回国的飞机上认识了已经在日本落地生根的王放,离奇地产生了倾诉欲,对王放讲述了自己眼中的家庭史。
处理这个故事,如果按照一般的创作方式,难点在于哪里?
视角。也就是主人公。这个故事,唯一从头贯穿到尾的,是廉加海。可如果从廉加海的角度出发,一切就太清晰了,因为“全知”,这里的全知视角不是说作者的上帝视角,而是说故事当中的信息流全都“经过”他,在叙述时不可避免会产生“因果”关系,可这恰恰是郑执要避免的,因为“在生活这片森林里面,总有很多无法控制的偶然事件的发生。也许看起来毫不相干,但实际上我们早已因为自己的某些行为种下了新的林子”。在经典文学理论当中,“命运”被单列出来成为创作主题,由此可知这种“不可知”的宿命感是何其珍贵。可如果不使用廉加海作为主视角,其余的人物就不能建立与故事的足够联系。因此,单一视角不可取。或者说,可以使用廉加海的视角,但那会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那么,就是多视角叙事了。
可使用多视角来进行叙事,也有一个很大的难点,那就是如何拉住读者的注意力。毕竟,每一个视角,实际上都会让读者重新进入一个“片段”或者说一个“世界”。尽管每一个人物彼此之间有着联结,可因为故事的重点并非像《雷雨》那样借助“人物关系”,所以故事是在转换视角的同时进行时间线的跳跃,这对读者的兴趣是极大的考验,郑执的解决办法是“节奏”,“于我看来,节奏就是小说的一切,甚至是所有艺术形式的一切。创作此篇的过程中,我吃的最大的苦头就是不停地去调节奏”。真是出色的解释啊,“慢慢寻找它的生命节奏,最后才算一气呵成,中间坎坷,也懒得再回想了,每一个写小说的同行都懂”。
但节奏是一个整体概念,完成它在作者层面需要的是“思考”,在执行层面需要的就是“细节”。以我阅读时产生的感觉,这篇《森中有林》的五个章节——《黄鹂》《森林》《春梦》《女儿》《沈阳》,每一个都可以单独敷衍成篇,成为相当不错的短篇,“故事本身体量就大,笔下稍一走神,极易赘述,遍地臃肿。毕竟前前后后构思了一年多,太多东西堆积在脑袋里,有的甚至早落了灰,不倒不快,导致失去节制,中途一度写不下去,遂停笔反问自己,难道要写成一个长篇吗?答案是否定的。长篇不是这篇小说的命数,于是回过头来从头开始‘瘦身’”。太多东西啊,怎样进行取舍,尤其是素材本身出色,对故事确实有帮助的情况下,还要舍去它,对作者来说需要的就是更高层次的看待角度和更全面的局面控制能力了。
但无论如何删减,那些充盈在字里行间的细节是首先打动我的东西,那些被高声叫好的金句,比方结尾处的“王放说,我想你也走不了,年轻人。——吕旷闻见王放的酒味很重,又听他说,有人把你种在这片土地上了。”我没觉得多么惊艳——那是作家的基本功力。但“廉加海说,我眼睛是酒瓶子崩的。吕新开说,酒瓶子是我打的,拿气枪。廉加海眨了眨左眼,说,你挺准啊。”这句话映入眼帘时,我突然就蒙了一下,这不是个一般化的故事了,因为这不是个“一般”作家会说出的话。“卫峰说,我答应来,你也得跟我保证,保证不再动她娘儿俩。廉加海说,我谁也没想动,证据都没了,但我得给我女儿要个说道。”“廉加海说,历史不能倒退,那天我不该去医院,我的命不值钱。卫峰说,电话里说了,今天就是来偿命的。他从怀里掏出一包耗子药,又说,有备而来的。”这个劲儿,也不是“一般”人的劲儿。
在电视节目《一席》的演讲里,郑执说,有人曾问他,在他的故事里有哪些部分是虚构的,哪些部分是真实的,他说他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想有时候我们必须承认现实也是虚构的一部分,而虚构有时更为真实。网上针对郑执的评论中,有这么一段:“……在我看来,双雪涛和班宇的虚构是建立在观察之上,他们更多的是一个旁观者,而郑执永远都是故事里的一部分,他与故事中的每个人都很亲近,是一个参与者。廉加海、吕新开、廉婕,那些虚构的人,好像他曾与他们生活过。他清楚地知道他们的愤怒、痛苦、柔弱和良善,面对生活,那把尖锐的刀永远都刺向自己”。
我想,这也解释了一个疑惑,全篇这么多人物,郑执几乎对每个人都有主观视角的处理,唯独那个核心,那个让廉加海成为全篇故事连接点的原因,那个廉加海的女儿、吕新开的妻子、吕旷的母亲、卫峰的受害人——廉婕,却始终是客体,没有任何揣测,也没有任何黑色,在这个故事中安静而纯洁地存在着。这也许是因为,“有人说郑执写的是东北的边缘人,我不太认同。如果你说我写的是边缘人,也就是认为我站在主流的圈子里,但问题是他们所谓的边缘人就是我生活的主流,我就是在这些人包围下长大的”。让虚构和真实还存在的界限,也许就是这个“母亲”的形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