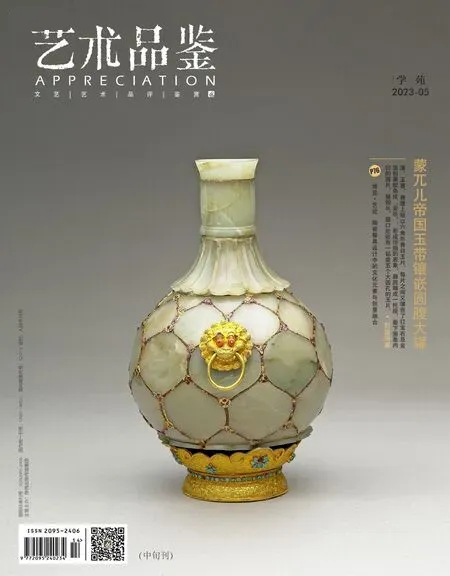主体转换与新类型公共艺术中关系美学的应用
栗千言(西安美术学院)
本文笔者使用《关系美学》中“关系的艺术”理论基础,伯瑞奥德重新界定的艺术家、艺术作品和观者之间的关系,并运用罗兰·巴特“结构主义美学”中社会结构的产物和“二元对立”理论结合主体之争来佐证新类型公共艺术中关系美学的重要意义,同时针对美学理论厘清新类型公共艺术中艺术家与群众的新型关系,为后续创作和新课题的讨论奠定基础。
自20 世纪20 年代的现代主义时期就有艺术家开始关注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20 世纪70、80 年代,各种文化思潮与文化运动的出现针对于此现状,使更多人讨论艺术的社会功能性。
笔者选用许多学者热烈讨论的案例《倾斜的弧》,意在论证艺术家和群众的关系,并针对于此案例提出的“谁是主体?”这一问题进行回答并提供论证思路。
一、“新类型公共艺术”的起源与发展
“新类型公共艺术”(New Genre Art)由美国著名策展人苏珊·雷西在她本人所著的《量绘形貌:新类型公共艺术》中正式提出。在此之前,欧美国家在20世纪70、80 年代,各种文化理论都相继出现,并在艺术观念的表达形式上不断创造出新的语言——社会参与式艺术、偶发艺术、互动性艺术相继出现,这些以社会议题为主的新的思潮与文化运动深深印象着同时期的艺术,于是出现了不同于以往壁画、雕塑、装置形式的艺术种类——新类型公共艺术,主要去探讨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及艺术行动在社会中起到的正向作用。
(一)“新类型公共艺术”的出现背景
20 世纪60 年代末和70 年代初,艺术走出了博物馆大厅,创造了更有意义的互动环境。“公共空间的艺术”是艺术创作中一个古老的概念。首先,它与环境相协调,以合理的规模和形式上的开放性为基础,让观者进入并融入环境。其次,它不仅旨在通过改变艺术家-艺术品-观众的传统生产/消费模式,与公众和谐相处,美化环境,而且通过强调公众参与,唤醒公众的美感。随着艺术的发展,一种“新型的公共艺术创作”正在出现,来自不同背景和视角的视觉艺术家们更深入和多样化地解决社会问题,并介入社区生活。
在此基础上,由苏珊·雷西(Suzanne Lacey)编辑的《量绘形貌》(Mapping the Terrain:New Genre Public Art)于1994 年首次出版,在中文版的前言中她指出“新类型公共艺术”一词没有正式名称,在艺术生产中经常与社会艺术、互动艺术、过程艺术、公民艺术、社会正义艺术、短暂艺术等相混淆,因此需要一个便于使用的通用术语,并在战略上加以利用。“新型公共艺术”一词并不是指传统上在公共空间展示的雕塑,而是指解决公共问题、与公众接触和互动并有助于塑造公共话语的艺术。它可以是物质的(如壁画和装置)或非物质的(如行动和表演),有些是永久性的,有些是临时性的,但都是基于公众利益,使艺术家能够更深入地思考社会现实,进而造福于社会。
(二)“新类型公共艺术”的特点
由于新类型公共艺术是传统公共艺术在当代的一种“进化”后模式,所以以下将以传统公共艺术为基础进行对比,以便于突出新类型公共艺术在本世代的特点。
在《量绘形貌》一书中,雷西并没有明确界定“新类型公共艺术”的概念及特点,因为新类型公共艺术作为一种当代艺术,本身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又因它关注各种社会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他会呈现各种不同的样貌;因此,追其溯源,在其强调群众参与的重要性同时,新类型公共艺术的产生,使以往的艺术创作模式——艺术家与群众的关系进行了巨大的转变,以此为基础,笔者凝练出四点试图来厘清新类型公共艺术的独特之处:
①物到行动的导向。
②社会议题为主体。
③注重参与的过程。
④艺术家关系转变。
(三)伯瑞奥德关系美学关于“关系的艺术”理论基础
基于笔者凝练出的新类型公共艺术的特点中艺术家与群众关系的转变,在伯瑞奥德关于关系美学的定义中找到相关支撑并不谋而合。他将关系艺术看作是一种反传统的互动形式,其表现的是观众的内在文化和外在行动的整体,以观众的群体经验代替美术馆的个体沉思。由此,反观新类型公共艺术中行动的目的在于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出能够使群众互动的元素,最后直接去探讨作品中的社会内容。
在新类型公共艺术的行动中,关系美学的艺术作品通常采用社会性、参与性和互动性的形式,如集体行为、实验性的展览、工作坊和表演等。这些作品的目的是通过创造一种新的社交空间,促进人们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以及重新思考社会关系。在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界限流动了,而不是固定的。他者被包括在自我里面。艺术家或群众的为主体的观点逐渐被突破,形成新的跨关系的、生态的、互动的特性。
简而言之,艺术家在利用新类型公共艺术为方式进行创作时,通常会设身处地为公众所考虑,带着改变社会的信心同时不忘针对不同的社群及个体去采取不同的创作手法,激发群众的积极性与城市的活力。
二、新类型公共艺术中的关系美学
长期以来,艺术作为权利及财富的象征,被少数人掌握在手中,一般公众无法轻易触及其本身,自然加宽了公众、社会与艺术的关系,并使艺术在社会中所发挥的能量减弱,成为少数人欣赏和交流的板块。现如今,针对新型公共艺术中的关系美学分析,艺术家与群众的关系引发了许多艺术工作者的思考,初步总结得到以下结论。
新类型公共艺术通常以“公众”为主体,给大众直接参与艺术行动的机会,艺术家和公众相互沟通,形成了相辅相成的创作关系。“公众”成为艺术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艺术家也不再是传统意义的艺术家,观众也不再是传统意义的观众,两者相互影响、相互启发、共同创作。
(一)主体转换所引发的新型关系探索
主体转换的美学观点不认为自己是价值的来源,而是鼓励创造性的参与。它的非关系性、非互动性和非参与性的取向不容易让人产生同情心和共鸣。与此相反,苏西·加布里克倡导一种"联系的美学"。他认为,“移情的倾听意味着为他人创造空间,给每个人一个声音,建立社区,使艺术具有社会责任感”。这种艺术不能通过个人表达来理解,因为它关注的是听众而不是视觉,只有通过对话才能充分表达。
新类型公共艺术中所引发新型关系的探索与过程艺术及概念艺术相似,是注重艺术创作过程而并非最终产出的物理形式。艺术家不再是某一物品的唯一生产者,而是化身为一位策划者及召集者,以项目为形式,与公众一起进行的一种行为体验。
(二)被群众所需要的艺术
自从1992 年立法通过资助艺术条例以百分之一公共工程经费设置的公共艺术,数量不断滋长,但在民众眼中的公共艺术,除了装置艺术展可能还被视为具有吸纳群众的功能外,多数则对静静站在街头的公共艺术,抱有冷漠的态度。究其原因,是社群与艺术家在其中关系的变化,在传统公共艺术中,艺术家介入社会议题时往往以本人为整个过程中的主体,此类情况有时引来非议。部分群众认为艺术介入社会议题时应多元化的进行创作,而不是单一思想的凝聚,群众作为社会中的一员急切想要加入创作并对此进行正向影响的心情迫切,由此,新类型公共艺术应运而生。
三、新类型公共艺术所产生的新型关系
(一)当下社会关系的探寻
所有这些都使笔者思考一个问题——艺术可以塑造社区吗?帕特丽夏·菲利普斯(Patricia C.Phillips)在她的文章《公共的建构》(Constructing the Public)中指出“公共艺术的边界位置与它促进社区和文化之间对话的能力相吻合”。尽管最近受到了强烈的反响,纪念碑式的公共艺术仍然是主流形式,其不变的作品和有限的位置可以彻底加强主导的审美态度和僵化的公共概念。这个变化的时刻,虽然困难和不确定,但也蕴含着希望的可能性。因此,作为一个社区活动,公共艺术必须更加谦逊、灵活和持久"。
与个人艺术生产的机制和传播不同,新类型公共艺术深化了有关公共领域的运作和美学的问题。“公共建构”意味着公共空间中的新型艺术是一个创造性视野的自由领域,正如文中所说,它不是为了制造一些被观看的东西,而是为了创造机会和情境,让观看者以新的视角和清晰的视野来看待这个世界,这样的形象非常符合公共艺术的功能性、私密性和批判性。
(二)“协商”与“共存”
依据传统型与新类型的公共艺术实践,笔者将新类型公共艺术中所提及的艺术家与大众的关系,并结合鲍瑞奥德的关系美学,进行以下两种关系模式的梳理。
第一种关系是协商。这是一种被引导的参与,大众在其中充当反应的集合单元,艺术家在其中起到引导性作用。整个计划由艺术家构想并在呈现过程中与其他人结合起来,最后再回馈到实际社会系统。艺术家的艺术概念为此类型中的核心,观众则按照艺术家的意愿提供材料组成作品。大众在制作的过程中分担一部分任务,或者作为艺术计划构成的一个要素,换言之,协作开始之前艺术家已经预设好了作品的样式。比较典型的作品是中国艺术家汪建伟的《生活在别处》,这是一个研究中国流动人口及劳动者的录影项目,作品综合了社会现实情况、人群的复杂性以及艺术家的视角,因此呈现出一种典型的协作模式,整个过程大众是被动的,或者只有一种有限的主动性,参与者依照艺术家的指示行动,由艺术家来控制作品的结果。此外,协作的行为可以是有意识的也可以是无意识的道具性的,例如,延斯·哈宁1992 年在哥本哈根创作的《土耳其笑话》(Turkish Jokes),蔡国强2017 年在费城实施的《萤火虫》(Fireflies)以及2019 年由罗纳德·雷尔和弗吉尼亚·圣·弗拉特洛的新类型公共艺术项目等,都是由观众无意识参与的反应而构成的,在参与途径和现场状态两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偶发性。
第二种关系是共存,这是一种创意性地参与,通常被认为是最有力的实现大众参与概念的工作路径,也是严格意义上的大众参与。作品的构想和实际创作都出自合力的过程,艺术家对作品的结果不会进行刻意地修正。这种严格意义上的大众参与艺术创作的目的在于对参与者的生命以及整个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参与者在与艺术家直接对话的过程中提供创意性的内容,共同决定作品的发展方向。与协作不同,合作起始于有意识的参与,合作者既具备参与之意愿又具备参与之能力。在合作中,艺术家必须参考参与者的意见来进行构思并且和他们共同完成作品,而这样的实践普遍具有疗愈性和教育性,所以也时常陷入“到底是艺术创作还是社会活动的争议之中”。比较典型的例子是苏珊·雷西在1987 年创作的《水晶拼布》及2015 年创作的《拳头与诗歌》这些计划的共同特点是从构思到实际发展的过程,始终将发动合作、引发公众理解之同情、激活公共空间作为核心问题来处理。
(三)新关系模式的产生
苏珊·雷西在另一本书中,将新类型公共艺术的方向进一步推进,并研究了新型公共艺术如何考虑新形式的关系的出现。她认为,新类型公共艺术关注的是艺术家、表演和观众之间关系的性质,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对“观众”或“参与者”的重新思考。笔者认为,正如《量化形貌:新类型公共艺术》中所讨论的那样,艺术实践中不断变化的身份和角色,正在导致艺术实践和评价标准的变化。艺术家身份和艺术实践的这些变化将新型公共艺术与其他艺术形式区分开来,并导致了多维空间的新艺术形式。
新类型公共艺术不仅在“新关系”上有所突破,同时通过开创性的社区艺术持续探索社会议题,并尝试发挥艺术在其中的行动意义。例如女性的生活和经历,以及老龄化等问题,作品《水晶拼布》就是其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它意在提倡社会参与的艺术实践,积极探讨艺术与社会干预之间的关系,质疑将精英艺术与大众参与区分开的界限。其开创性的职业生涯、参与社会的表演,不仅有助于推动并界定社会艺术实践,并在实践中理性、系统的发现并解决现存问题。
综上所述,新类型公共艺术在打破主体之争的主体导向的同时,建立艺术家与社区群众等的新型关系,吸收表演艺术、社区艺术、装置艺术、社会历史和城市规划的理念和经验,在这种极其大胆和发人深省的艺术形式中,为富有想象力的、对社会负责的、对社会有反应的公共艺术提供了极其有力的论据和呼吁。
四、结语
本文笔者将主体之争作为一个节点,初步探讨在公共艺术背景下,打破了以往以艺术家为主体的艺术创作模式,为新类型公共艺术的创作提供新的关系的探索,新类型公共艺术正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点,投入目光到建立新的社群关系,以关系美学为理论指导,将行动实现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使大众成为更加有力和有效地成为对话的主体,在艺术家提供的场域内,形成平等的行为或社会运动的界面。艺术家身份和艺术实务的变化是新类型公共艺术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的原因所在,同时也催生塑造了多维空间下新的艺术形式。
新类型公共艺术作为一个新课题在理论方面上不成熟,本文偏向于梳理新类型公共艺术在关系美学下所进行的史无前例的行动及关系模式,只做初步探讨,在某些方面仍存漏洞和疑点,正如理论家盖利克所说“正在努力地去发现更适合我们这个时代的新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