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冈兹格:如真心相爱,20年后仍要对彼此有欲望吗?
孙凌宇 乔雨萌 周思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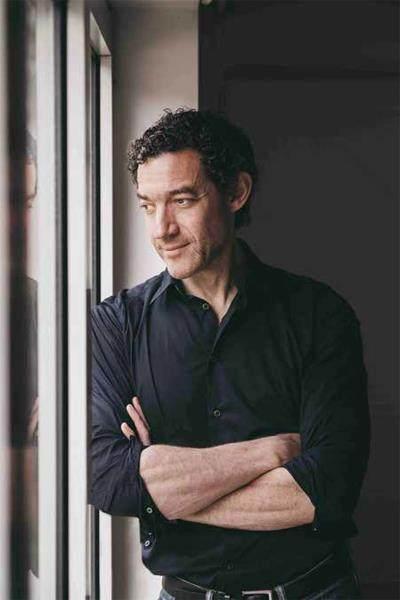
图/Pierre-Yves Jortay
把天神塑造成脾气暴躁、胡子拉碴、短裤满是油污的糟老头,不知道是怎么想到的,但反正电影《超新约全书》的编剧、比利时作家托马斯·冈兹格 (Thomas Gunzig) 这样做了。
不按常规、享受奇思妙想、向往逆反且充满矛盾的事物——无须通读他所有的文章,读者很轻易便能获得这样的印象。
有人曾问他理想的度假目的地是怎样的,他的回答是希望像布列塔尼一样,处于加勒比海的热带一侧,有凶猛的天气、碧绿的大海、异国情调的食物,以及,最重要的,很少的人;同时他又渴望平静,希望随时有人能在他的孩子想玩耍的时候现身照顾他们。“最后,我希望这个地方非常近,但让我感觉非常遥远。”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不论是否在旅途中,托马斯几乎总在早餐前醒来,通过躺在床上写一点东西来开启一天。就这样写到上午 11 点,余下的时间便充满了美妙的成就感。下午他会选择某项运动,“希望能够在一项痛苦、疲惫、非常耗费体力的运动中获得快感”,曾有报道称他为“才华横溢的作家和多才多艺的运动员”。
对他而言,格斗运动是笔尖灵感堵塞时最好的解决方法。“我一直喜欢让自己受伤的运动。这是否反映出了我与暴力的黑暗关系?我练了很多拳击、空手道(他是棕带选手),现在我主要练习巴西柔术。我真的很喜欢它,它不是一项击球运动,一切都发生在身体上,我们遵循平衡原则,以绝对效率为目标。不知何故,它可以实现冥想的效果——你不可能将注意力集中在消极的想法上,如果你不集中注意力,你很快就会发现自己被对手的身体压垮了。”
年过半百的托马斯每日思考的显然不是养生。不出远门的日子,他游荡在布鲁塞尔,“这是我出生、长大、生活的地方,也可能会是我死去的地方。”
他曾为一位叫An Pierlé的佛兰德斯歌手写了一首歌曲《Il est cinq heures, Paris séveille(清晨五点,巴黎在苏醒)》,这首歌的歌词非常准确地表达了他对自己所在城市的感受,“我不知道我是否喜欢我的城市,但我已经习惯了它。这是一座美丽、有活力、充满对生活和享乐的渴望的城市。”
“这里物价不高,人们热情好客,你几乎可以免费欣赏到非常棒的音乐会,有演着刺激节目的剧院、酒吧和正宗的餐厅。这是一座非常热闹的城市,因为它是比利时唯一一个弗拉芒语和瓦隆语社区交汇、相互欣赏和共存的地方。我喜欢圣吉尔区,那是送孩子上学后我写作的地方。那里生机勃勃,是一种移动的状态,有很多人来来去去,我就像在《晨间咖啡》里一样,一边工作一边观察我的城市。”
除了幽默,我尝试让它们充满情感
《晨间咖啡》是托马斯·冈兹格参与的一档电台节目。在当地,他是活跃于多个领域的文化界人士,但他并未仗着资历对所做的事情掉以轻心,仍然在书籍、剧本以及广播节目的专栏中努力寻找情感触动。“例如在广播节目中,我被要求发表幽默的帖子,但除了笑话之外,我还尝试让这些帖子充满情感,或多或少轻松愉快。”
“能够被记住的作家(我并不是说我会成为其中之一,但我希望如此)不一定是最伟大的那种以对社会的看法为小说基础的思想家,而是那些成功地创造了可信的角色、作品具有强烈现实感的作家,我认为这只有通过情感才能实现。这可能就是为什么人们仍然会阅读《基督山伯爵》,但让·保罗·萨特的读者随着时间逝去越来越少的原因,因为你觉得他的人物只是用来论证一个论点。”
他认为幽默是一个很棒的工具,是送给读者最好的礼物之一。“幽默的问题在于其不被评论家和文学奖项所信任,因为我们被教导说,一本伟大的书应当是严肃的,如果加入幽默,就不可能是严肃的,这在那些批评家心中是无法相容的。然而,有许多伟大的作家将幽默与严肃结合在一起:卡夫卡描绘的世界既悲惨又有趣,贝克特也是如此,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既宏伟又充满有趣的元素。这些作家在没有隔绝幽默的情况下取得了成功。”
2023年6月,國内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说集《太冷、太热、太早、太迟》,这本书里囊括了从未成功完成任务的杀手、前途无量却爱上异国叛逃运动员的钢琴少女、为心仪女孩而战的冷门运动冠军竞争者、领取养老金的门房大叔、沮丧的年轻野心家……25个“反英雄”式的人物被生活弄得筋疲力尽,在托马斯的安排下遭遇了现实的各种困境,又总能迎来幽默且意想不到的走向。
这本小说集叙事节奏明快犀利,平淡的背景设定随着情节的进展频频出现矛盾、离奇的场景,被引导至极限、悖论的方向,现代生活各种五味杂陈的荒诞瞬间生动地呈现在读者眼前。

托马斯对社会的讽刺尖锐且保留了趣味性,平衡了故事内核所反映的现代生活的虚无感,他观察到社会生态中的病态部分,驾轻就熟地使用苦涩的笑声,塑造出一批垮掉的当代人,用现代的视角审视个体与社会之间的暧昧关系。
在他的观察视角下,“德里克探长的目光就和威斯特伐利亚平原一样阴郁,和隆美尔师团的装甲车一样沉重,面包店女店主感觉就像1939年9月1日的波兰一样无助;这男人就像一个墩子,腿就像法院门口的柱子,胳膊就像火车车厢,胸膛就像中央高原;一张中世纪水手的脸庞,胳膊粗得像要塞城堡;这红棕色头发的男人长得真像猎狐梗,皮肤保养得极差”……借着介于社会批判和文学幻想之间的语言,这些故事顺利呈现出活泼、荒诞的风格,散发着古怪的黑色幽默。
从无到有写一个故事,是同理心的体现
2022年托马斯·冈兹格带来了新小说《动物之血(Le Sang des bêtes)》,这本书的灵感来自于他想到一切都有标签,“我们把每个人都依据标签放在某一个盒子里,而我想增加一个额外的衡量纬度:你会如何对待一个是人类但又不是人类的人?我想到了牛女。社交網络和算法想确切地知道你喜欢什么,以便提供有针对性的广告,这也导致我们倾向于完全按照算法希望我们工作的方式工作,即以数字化的方式生活。但人类是难以捉摸的,在不断地进化,并不固定在一个类别或一种确定的做事方式或存在方式中。我想要写一本能够调和人们之间细微差别的书,因为我们之间只有细微的差别。”
这些差异首先体现在外部元素,例如体形、种族、年纪,“我想写一些关于健身的事情,关于如何改变你的身体的事情。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小,很瘦,我喜欢在树林里跑步,希望通过运动改变这一点。我也想接近犹太团体的想法。历史上,犹太人总是被讽刺地描绘为矮小、虚弱、骨瘦如柴。最后,我还想写一本关于一对老年夫妇的小说。对于一对深爱着对方、真心相爱的情侣来说,20年、30年后,他们对彼此的欲望会变成什么样子?当你在25岁之前结婚时,你不会考虑这一点。但当你和这个人住在一起,和这个人生孩子,对他/她了如指掌,对方成为你家庭的一部分,就像你的母亲或你的姐妹一样。你不会想和你的姐姐或你的母亲一起睡觉,但社会的规定是,一对感情好的夫妻,即使是在一起生活20年后,应该仍然对对方有同样的欲望,仍然想要做爱,否则就说明他/她的身体不好。我想解决这个问题。”

托马斯·冈兹格编剧的电影《超新约全书》
“我想写一本包含所有这些角色的小说,这些角色和其他人一样,不是被框定的角色。”
他对当代的自传小说、自述等形式不感兴趣。“萨特的自传性小说对童年以及他认识文学的方式的描述确实很棒,但在我看来,这跳过了文学创作最大的困难,那就是从无到有阐述一个故事并设法写出来。写一个人生活中的经历与创作小说截然不同,我认为作者面临的挑战是设法重现我们生活中不一定经历过的情感,这是同理心的体现。”
写实在他看来没有挑战,因此他在各类体裁中竭力发挥想象的才能。有一回他和此前合作过的导演哈里·克莱文午饭时,一个想法出现了——“一个女人要生下一个隐形婴儿”,这让哈里立刻兴奋起来。哈里同样渴望拍摄特殊的、亲密的事物,与感情、感觉有关的……而非那些非常现实的事物,比如一辆汽车在下雨的街道上经过一栋房子前这种。
两人并不试图回答所有叙事性的或逼真的问题,而是试图给观众提供一种感性的、感官的体验。“它可能会扰乱期待着一板一眼事物的人,我们以一种相当原始的方式处理了‘隐形,即从隐形的诗意潜力的角度出发。”
创作之余,托马斯在比利时拉坎布雷国立艺术学院(La Cambre)教授文学,在布鲁塞尔圣吕克高等艺术学院 (Saint-Luc School of Arts) 教授故事写作。课堂上他也从未停止过表达对想象力的热情,以及视小说为自由之地的信念。
“我努力让课程变得有趣,我不能忍受我的学生觉得课程无聊。课堂上我讲了很多作家的轶事(可能太多了,一点也不学术,但我喜欢),我也对纯粹的对知识反馈的考验越来越过敏:在我的考试中,学生可以借助一切需要的笔记、电话、GPT(深度学习模型)等。我总是要求他们发明一些新东西,要求他们自己提出一个相关的问题并回答。我鼓励他们发挥创造力,而不是在给定时间内记住大量知识(然后很快就会忘记)。”
他对物质生活的要求相对简单,烤架上的牛排,用牛油烹制的薯条,一杯红酒,都能让他快乐。但自从写完《动物之血》后,这也成了一种非常偶尔的乐趣,出于对动物、地球和自身健康的尊重,以及最主要的小说中谈及的对动物福利的关注,他不再像过去那样吃红肉。
这本书依然延续了让人欢欣的幽默感,每篇短篇小说都讲述了一只友好而熟悉的动物遭遇灾难性命运的故事。他在笔下注入了一种黑暗的、常常是愤世嫉俗的幽默,但永远不会缺乏乐趣。
“我认识到生活已经非常艰难了,所以我更喜欢讲故事,而不是给读者增加压力。这实际上对我来说是一个改变。我刚开始写作时做得并不好,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有了孩子,逐渐改变了。我想要更多温暖温柔的东西,即使我们有时停留在有些黑暗的主题中。我不希望我的书给读者带来艰难的感觉。人们读完你的书多年后唯一记得的不是剧本或人物的名字,而是他们在作品中经历的情感,所以我试着带给我的读者情感,让他们哭,让他们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