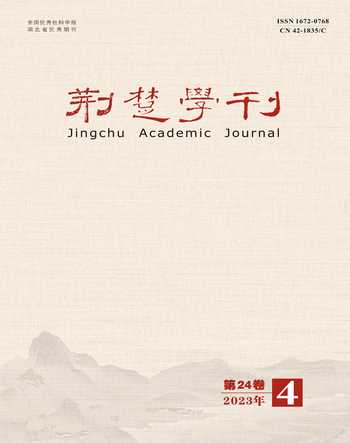试论中国古代形塑男子气概的三个面向
朱雪宁
摘要: 作为在某种文化环境中男性与其他人交往时呈现出的理想的规范、模式,男性气概不是单一、刻板、静态的气质呈现,它会在不同阶段动态变化,却又在深层保持着中国独有的文化期许。在中国古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学说指引下,向往献身于公共事业的文士反复地被儒家思想所浸染,他们的自我形象及其创作必定代表了中国理想的男性气概。以古代文学中典型的才子与英雄形象为重点,通过阐释儒学化的阴阳学说、才子与君子之间的张力以及文武二性的对立统一三个面向,联系其他类型的男性特质,共同探索传统中国社会理想的男性气概的建构过程和表现,是很有意义的尝试。
关键词:男性气概;阴阳学说;文人;同性社交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768(2023)04-0052-07
进入21世纪后,西方的性别研究理论逐渐传入中国。这种研究方法的确带来了看待传统问题的新角度,促进了诸如女性研究等领域的新发展。在如火如荼的女性主义进步运动中,学界将性别研究更多倾斜于女性研究,男性特质方面却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不同于西方理想的硬汉形象,中国男性呈现出自身独具的气质要求。宋耕《文弱书生》(The Frigile Schloar)[ 1 ]一书借助福柯“话语即权力”的观点,着重探究中国古代权力笼罩下儒家理想的男性气质表征,以才子佳人故事中的书生(才子)话语为中心,对同样反复被儒家学说所浸染而向往献身于公共事业的君子形象进行阐述,从政治化的阴阳体系解读了各类型男性气概的共通之处,揭示了男性之间社交的本质。这些观点都为探索中国古代的男性气概的发展演变提供了启示。
在古代中国社会中,“士”一直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他们是中国文化的创造者,也是中国社会的管理者。《说文解字》对“士”的定义是:“士,事也”[ 2 ],凡能事者皆称士,可见“士”与政治领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无论是“奏、议、书、表”等官方应用文体,还是“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抒情文学作品,士人阶层都是各类文本的主要生产者。到了宋朝,国家大幅增加科考录取名额,使得各阶层男性有更多机会进入仕途,士的范围也就随之扩大。在儒家学说的影响下,士人及其作品代表了传统中国理想的男性特征。这个由男性组成并书写的领域充斥着“阳”的特质,却在权力的笼罩下使得地位低下的男性转化为女性所属的“阴”。显然,西方学术传统的男/女、异性恋/同性恋等二元对立的区分法并不适用于厘清中国的性别问题,而中国与政治话语桴鼓相应的阴阳学说则提供了一个契合的切入口。
从社会学的角度讲,男性气概是男性在社交时所表现出来的、某种文化所期望遵守的规范和模式。盛行于中国古代晚期的才子佳人小说和戏剧给本文分析男性气概的建构过程提供了良好的案例。这类作品发展到后期已经成为“一见钟情,私定终身,拨乱离散,及第团圆”[ 3 ]的僵化模式,男主人公是年轻俊秀又有旷世奇才的大才子。元杂剧对才子佳人故事已较为热衷,在元代前期废除科举的背景下,本该处于精英阶层的文人以创作杂剧为生,可以说杂剧作品中的主人公在很大程度上是文人的自我投射,作者加之于男主人公的外貌、言语以及行为都表现出文人心中理想的男性气质。元代才子对同属于儒家文士的君子形象不得不说是一种颠覆,他对情欲的追求、对科举的搁置都显示出此期才子佳人作品的革新因子。但在这种暂时的对立后,才子又会回到正途,考中科举进入本属于他的领域。才子和君子的张力关系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男性气概,又在正统话语规训下代表着中国古代对男子气质的理想形象。
雷金庆(Kam Louie)在《男性特质论》[ 4 ]中聚焦于中国自古以来的文武二元的基本结构,将其作为中国男性气概的两种典型。文士(才子或君子)运用自己的文本生产能力展现儒生的优越感,文学素养也成为男性气概的基本素养。而文武这两种基本气质类型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借助塞吉维克(Eve Sedgwick)在《男人之间》(Between Men)探讨的“情欲三角”[ 5 ]概念,能更好地理解通过排斥女性来建立男性同性社交的共谋关系。
本文试图在以上三个部分探索的基础上,追寻传统政治语境对男性气概的影响;对比不同版本的文人形象,在男性与同性或异性的社交关系中解读男性达成共谋的原因,分析中国传统理想男性气概形塑过程的具体面向。
一、阴与阳
《春秋繁露》写道:“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 6 ] 325。董仲舒将阴阳关系改造为道德规范以及伦理关系,为汉王朝的统治提供强大的思想支撑。阴阳学说被儒学化,它们各自代表的特质与权力等同。以儒家学说为主要学习内容的文人受到其影響,将其男性气质反映在了对身体表现与权力交往的身份认同中,对这种权力地位的默许几乎贯穿了整个传统社会。
不同于以身体差异标准来判定生理性别,中国传统文学中的男性形象达到了男性身体与女性特质的平衡,呈现出“雌雄同体”的文学现象。先秦时期的屈原始创“香草美人”典故,在有着极强自传性的《离骚》中,屈原屡次将自己“雌柔化”,呈现出十分明显的女性特征:“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7 ] 17,以美衣秀服修饰男性躯体;“揽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 7 ] 25,伤心时表现出泪眼婆娑的扭捏姿态。这些描写无不体现出屈原或是作品主人公的女性化表征。然而,在这篇长诗的其他地方,屈原也会写到“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 7 ] 17的大臣形象,无疑是一种男性特征的表述。这种“雌雄同体”不仅表现在外貌上,更表现在屈原以弃妇比逐臣的经典话语中。屈原抱怨楚王“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馋而齌怒”[ 7 ] 9,“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 7 ] 10,听信小人谗言将我抛弃,背弃我而另有他约,《离骚》中的性别早已全然模糊。显然,生理特征不能作为定义中国传统文学中性别的依据,男/女二元的简单区分也不能解释弃妇逐臣的经典修辞。
阴阳学说是我国古代哲学的源流和基础。《周易·系辞上》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 8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点出本质:“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也”[ 9 ]。如此,宇宙万物具有既对立又统一的阴阳两面,不断地相互作用、共同运转。到了汉代,为了赋予儒家道德规范合理性并以此来统一思想、稳定社会秩序,董仲舒将阴阳学说与儒家思想两相结合,提出阴阳的等级伦理观念:“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 6 ] 350他成功地将阴阳哲学属性与儒家传统伦理相交融,以“阳之出也,常悬于前而任事;阴之出也,常悬于后而守空处”[ 6 ] 351等话语论证阳尊阴卑的思想,将“阳”置于绝对的优势与高位之上,为强化专制制度、巩固纲常伦理提供了强有力的终极支点。阴阳哲学已经被儒学化了。君臣、父子、夫妇关系皆取诸阴阳之道,每一对关系都遵循此原则,那么每一对关系中的男性都会处于兼有阴阳两性的情况。可见,阴阳学说可以成为解读传统中国男性特质的依据,性别由种种复杂的社会关系来决定,并且由男性的身体呈现出来。与此同时,这三种关系所传达出的家国同构的观念是古代中国社会的思想核心。无论是属于公共领域的“君臣”,还是属于私人领域的“父子、夫妇”,想要维持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就必须依照“阳”对“阴”的绝对控制以及“阴”对“阳”的绝对服从。在私人领域处于支配地位的“夫”和“父”,于公共领域面对君王时自动将自己降格为被支配的臣子,这种从阳到阴的转化表现出文人对皇权的绝对服从,阴阳话语即权力话语。
在儒学统治地位的笼罩下,家中的夫妇模式早已成为传统文人身处公共领域时面对权位较高者的基本模型。北宋时期,王安石大力倡导变法,宋神宗对其十分信任,却在其他大臣的劝谏下对变法有所动摇,王安石便写下《君难托》借闺音表哀怨:
槿花朝开暮还坠,妾身与花宁独异。忆昔相逢俱少年,两情未许谁最先。
感君绸缪逐君去,成君家计良辛苦。人事反复那能知?谗言入耳须臾离。
嫁时罗衣羞更着,如今始悟君难托。君难托,妾亦不忘旧时约。[ 10 ]
王安石未入宫之前,时为太子的神宗就已经听说他才气过人,登基后立刻任他为江宁知府,后召之入宫,可谓“相逢俱少年”;熙宁元年四月,王安石入朝为官,与神宗共同商讨治国之事,“可悉意辅朕,庶同济此道”[ 11 ],神宗支持新法让王安石感动,愿意追随君主,为国分忧;可是神宗却没有像王安石一样坚守初心,对他产生怀疑,这让王安石只觉难以托付,请求辞官。王安石和宋神宗同为男性,但在诗歌中面对至尊地位的君主,王安石自动降格为阴性,化身成痴情的弃妇抱怨变心的君王。在这里可以看到屈原与楚王君臣关系的影子。中国传统文学以女性之口代言已成为惯例,文人在君臣关系中的种种委屈在阴性的低位者身上找到了替代。汉代儒学独尊后,他们一再被君权驯化,置于屈抑的依附位置上,低位的男性被隐形地“阉割”了。在一些极端化的文学作品中,处于低位的、被动方的男性会自动扮演阴性角色,甚至换上戏子装扮,主动放弃“阳”的男性权力。在《弁而钗》的《情烈纪》中,“娇姿尽可倾城、妖娆绝胜双成”的文韵为了生计无奈成为戏子,与“貌胜潘安、才希苏轼”的云天章互相赏识。当文韵被石敢当欺压时,云天章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和英武实力帮他化解了危机。两人地位悬殊:一个是能文能武、“考过批首”的风流才子;一个是至卑至贱、招人轻薄的倡优隶卒。文韵想报答天章帮他免去牢狱之灾的恩情,他“内衣红绉纱襖,外穿白绉纱衣,盖以油绿披风,甚是标志可人”[ 12 ] 216,要为云天章搬演一出,自动换上了已经搁置月余的戏服,变为戏子“文生”,也是在这之后,文生“不脱女服”,二人完成了结合。在这个故事中,同性之间主动/被动角色与文韵的自觉阴性化就是权力等级关系的体现。云天章的名气地位高于戏子文韵,处于“阳”的支配地位,他必定是同性关系中的主动方;而供人娱乐消遣的文韵只能退居低位的“阴”,是这段关系中的被动方。基于权力的性别话语不断地加强阴阳政治二分法的有效力,强力巩固了权力等级制度,肯定了阳的终极地位。
儒家话语观照之下的男性“阴柔化”被默许甚至被夸赞,文人们进行“自我阉割”,面对位高权重之人自动降格,这必然对中国男性气质形塑过程中的“阴”产生了极大影响。由“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13 ]的阴阳相依发展到汉代的“阳尊阴卑”,阴阳学说的儒学化将政治与性别勾连在一起,作用于文人的身体和思想之上,以至于在文学作品中出现了男性和女性特质兼具的文人形象以及众多以女性之口代言的阴性书写。
直到风雨飘摇的清朝末年,这种政治化的阴阳学说终于被撼动。晚清时期上海租界内畸形繁荣,娼妓业也随之发展,本该是男性玩物的妓女们却将男性玩弄于股掌之间,上文探索的中国古代社会逐步建构的男性气概产生了巨大转向。在谴责小说《孽海花》中,阳失去了对阴的绝对控制。男主人公金雯青作为新科状元将红极一时的妓女傅彩云娶回家后,不能禁止她与书童阿福、德国军官瓦德西等男性明来暗往。本该是男性家内附属的女性踏出了私人领域,不再是“内人”。而在嫁为金雯青小妾的傅彩云口中,丈夫对她根本没有控制权:“我的性情,你该知道了;我的出身,你该明白了。当初讨我的时候,就没有指望我什么三从四德、七贞九烈……若说要我改邪归正,阿呀!江山可改,本性难移”[ 14 ] 151。面对妓女妾室的偷情行为,丈夫不再是以一纸婚书约束女性、占据主导地位的“阳”,而本該居于臣属地位的女性摇身一变,以自己妓女的身份来对抗妻子的身份,试图摆脱传统礼节对妻子身份的规训——她不要遵循三从四德、七贞九烈,毕竟,她的身体早已不属于一个男性,没什么可失去的了。而金雯青对这一切无能为力,他无法用他的状元身份来阻止妾室勾搭地位低下的优伶,还在痴迷中葬送了性命。甚至金雯青的丧事还未结束,傅彩云便决定要重操旧业。另一方面,文人引以为傲的聪明才智也不再是他们的专权。金雯青靠着八股走上仕途,想要报效朝廷,不惜重金买下了中俄界图,而阻止他的人却是本该不干政事的女性,傅彩云说:“老爷别吹……不要说国里的寸土尺地,我看人家把你身体抬了去,你还摸不着头脑哩”[ 14 ] 83-84! 她大胆地踏进男性的专属领域,出使欧洲时赢得维多利亚女皇的青睐,与军官瓦德西公开调情,无所畏惧地追逐着自己的情爱、经济的欲望,将男性特有的权力一一夺回。作者反复描述这类女性的颠覆行为,以妓女的浪漫冒险嘲弄了传统男性修身治国的一贯逻辑,她们成为威胁“阳”的危险存在。在傅彩云的对比下,晚清时期的男性黯然失色,正如《失身》(Lost Bodies)一书中所说:“女性化的、无产的、过时的中上层阶级男性被自信的、经济独立的下层阶级女性所压倒,她夺走了他的钱和他的荣誉”[ 15 ],他们的状元身份已然失效,面对女性的僭越无计可施。阳与阴的地位倒置对男性气概产生了极大的冲击,折射出清末动荡社会下男性的焦虑。
二、才子与君子
活跃于“阳”的领域的男性直接受到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个士人群体既包括在朝文臣,也包括以儒家学说为学习内容的“准文人”。大众心目中的文人形象本应是儒家学说中温润如玉的翩翩君子,但才子佳人文学作品中的男性形象却摆脱了情欲的约束,显示出与君子截然不同的姿态。他们在各具不同的男性特质的同时也代表了传统中国所期待的理想化的男性气概。
在《论语》中,“君子”这个高频词投射了儒家“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作为仅次于“圣”的文人群体,君子可以通过“礼”来约束自己的道德行为,无限趋近于圣人的水平。“修身”为君子男性特征的建构做了框定,“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 16 ] 49-50,不像圣人一般遥不可及,君子可以通过道德修养来与之靠近。《论语》提出“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16 ] 174,君子应该以“礼”作为外在行为规范的尺度,把“仁”作為内在的道德观念的指引,这样,内有德外合礼的君子形象就成为了儒家理想的男性气概符号。“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16 ] 113,君子需要遵从礼的要求加以节制,否则就会产生消极效果。
在阴阳学说的影响下,君子自觉由“阳”转“阴”,臣服皇权,服务于政治事业。士人群体不断地被这种学说驯化,活跃在公领域。作为该领域的构建者,男性(君子)的气质特征并不依赖于私人领域“夫妇”关系的认可,而是与“小人”相比照,突出君子的高风亮节的男性气概,对君子男性气概的强调重点放在道德政治层面而非性属层面。《论语》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16 ] 55,二者的区别即在于君子深明大义,小人偏好一己私欲,君子就是要做好公领域的事业,无视私欲,崇公抑私。政治化的儒家学说使得“夫妇”关系的私领域也被纳入公领域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揭示了真相:“修身齐家”的私人范畴应该完全服务于“治国平天下”的公共事业,在政治领域大有作为才是君子的根本任务。春秋时期的孔子并不是要打消人的欲望,而是以“礼”来维系整个社会的秩序。到了宋明时期,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浪潮对君子的守礼约束演变为“克制性欲”,提倡“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 16 ] 250-251。理学上升至官方正统地位,种种绑缚令人窒息。一方面,与君子对应的群体是道德不端的小人;另一方面,合乎礼节的君子形象代表了他对女性的合宜态度。如真君子的典型形象坐怀不乱的柳下惠,《论语》记载他“直道而事人”[ 16 ] 273,面对把持朝政的小人臧文仲,柳下惠仍直言不讳,虽多次被贬却始终服务于政治领域,孔子都因柳下惠之贤不被重用而气愤。而面对女性时,柳下惠展现出有礼有节的君子形象,陶宗仪《南宋辍耕录》写道:“夫柳下惠夜宿郭门,有女子来同宿,恐其冻死,坐之于怀,至晓不为乱”[ 17 ],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代表了后世人们对男性遵守男女界限的期许。君子的男性气概逐渐被定型,他们需要克制对女性的欲望,走上“正途”,融入国家机器的运行机制中。封建专制制度的发展反复加强了对君子的约束,抵制私欲,使得君子完全成为官方权力的臣属,他们被去性别化了,君子等同于公共领域的“无性人”。这种政治化的男性特质成为精英阶层固有的价值观,逐渐主导叙事。直到今天,君子形象仍等同于大有作为、不近女色的正直角色,这代表了古代中国官方话语的男性气概。
才子和君子的矛盾也由此生发。虽然二者同属士的范畴,才子也是大众心目中典型的理想男子形象,但是才子对女性、对情感的追求与对儒家礼法的僭越无疑是在对正统话语发起挑战。
《西厢记》中的才子张生无疑给读者留下了至情的深刻印象,这个“情”既指向“男女情欲”也指向“真心至情”。莺莺夜晚在花园烧香时[ 18 ] 30-31,张生便候在门外,“先在太湖石畔墙角儿边等待,饱看一会”,等及出来时便嗅到莺莺“风过处衣香细生”,他“踮着脚尖儿仔细定睛”,看莺莺“容分一捻,体露半襟”,迷醉于莺莺的仙姿玉貌,而后张生还对极具情色意味的小脚进行了想象,“料应来小脚儿难行”。这些逾矩放肆的情欲书写代表了一种公然的反叛,与君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守礼行为形成了鲜明比照。与此同时,在崔夫人发现崔张二人的隐情时,她认为“相国人家”不应做此勾当,张生没有可以与之比附的身份,崔夫人便要求张生考科举,张生毫不犹豫就启程了[ 18 ] 145-146。他在路途中以梦化解相思,科举及第等候圣旨御笔除授时,“唯恐小姐挂念,且修书一封”[ 18 ] 164;万分爱护莺莺转交给他的信物,卧床得了相思病,文本处处是张生的情迷形象。这种对于个人情欲的重视,甚至在张生一见钟情后放弃科考的决定,都对官方话语(君子)中崇公抑私的纲领发起了挑战。然而,才子的“情”与“性”没能舍离,作者写二人欢合之时莺莺“柳腰款摆,花心轻拆,露滴牡丹开”[ 18 ] 137,出门时“杏脸桃腮,乘着月色,娇滴滴越显得红白。下香阶,懒步苍苔,动人处弓鞋凤头窄”[ 18 ] 139,这种胀满情欲的书写仍在物化女性,完全把女性置于男女关系中的情欲客体,虽与“君子”礼仪有别,二者对男性主体性的强调却昭然若揭。
上文已经提到,私人领域的“修身”是为了“治国平天下”的公共领域目标服务,才子形象在这个过程中也表露出这种儒家思想的浸透。张生在进京赶考的路上与莺莺一见倾心而住进普救寺,将“科考大事”放置一旁。然而,在种种情节设计下,张生还是走上“正途”金榜题名,莺莺的出现仿佛是他“修身”的一场考试,故事中“情”和“性”的颠覆因素在他高中状元后即消失殆尽。从阴阳学说的角度看,张生是在“阴”的领域中放弃了“阳”的身份地位,“外像儿风流,青春年少……扭捏着身子儿百般做作,来往向人前,卖弄俊悄”[ 18 ] 40,不仅有着雌雄同体的身体修辞,甚至还会在莺莺和红娘面前下跪;而他最终还是返回了“阳”的世界,考中科举,凭借身份地位战胜了小人郑恒。“才子”形象所具有的颠覆性因素都被正统话语所收编,他脱离普救寺这个私人领域后走上正道,继续 “学成满腹文章”而后“得遂大志”。显然,抛弃杂念、报效家国的气质是儒家正统话语下的理想男性气概的最典型特征,在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反反复复地规训着男性的身体与思想。
三、文与武
《论语》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莫不有文武之道焉。”[ 16 ] 288可见,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了文武二分的概念。当时的“士”也有文士与武士的分类。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出:“故文德为贵,而威武为下,此天下之所以永全也。”[ 6 ] 351将文士的地位提高到了武士之上。然而在塞吉维克“情欲三角”[ 5 ] 27-28的解读下,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男性气质类型达成了男性的共谋,完全将女性排斥在外。
上文已经解读过以“文”为特质的代表即才子与君子气质的建构过程,而在传统文学中仍存在着其他类型的男性特质。与“文”相对的“武”的男性特质呈现为典型的“英雄好汉”形象,又与才子和君子一同走向公共领域。英雄好汉肩负重任,渴望获得政权或兴复大业,追求极“阳”的目标,与其他男性一起活跃于公领域;而大众心目中的文人形象的代表即才子张生,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表现出文人的典型特征。好汉聚义的英雄小说与写青年男女情恋的世情小说为男性特质的构建提供了完整的背景条件。本节将在《水浒传》与《西厢记》的对比下来解读文武两种风格各异的男性气概。
《水浒传》所呈现的好汉形象人们早已耳熟能详,他们不是优柔孱弱的才子也不是温润如玉的君子,而是魁梧有力、狂歌痛饮的英雄豪杰。如花和尚鲁智深“身长八尺,腰阔十围”[ 19 ] 29,李逵“不搽煤墨浑身黑,似着朱砂两眼红……力如牛猛坚如铁,撼地摇天黑旋风”[ 19 ] 341,都不是如风神俊茂的白面书生一般能够吸引女性的男性特征,但这些阳刚的高超武艺水平可以帮助他们服务于宏图大业。然而,“武”的男性特征的核心是忠义精神,这种特质远比其他特征重要。他们深明大义,忠于兄弟,以无所畏惧的刚毅精神与其他男性团结起来建功立业;而面对女性时,有着极端阳刚气概的好汉们不愿女性成为他们大业路上的绊脚石,只会冷漠甚至极力排斥她们。一方面,好汉忠于他们的结拜兄弟,坚守理想信念,向同性而非向自己的妻子或情人表白忠诚义气。宋江被唤作“及时雨”, “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赒人之急,扶人之困……能救万物”[ 19 ] 156,他的侠肝义胆、慷慨仗义代表了他的男性气概,为他带来了极高的声誉。当擒获扈三娘时,下属们以为宋江要独占她,小心护送上梁山,结果宋江却将扈三娘许配给下属王英,兑现当初与王英的承诺。扈三娘竟“见宋江义气深重”便答应了[ 19 ] 466。宋江此举赢得了兄弟们的忠心。另一方面,《水浒传》作为一个男性建构的世界,几乎听不到女性的声音,她们被虐杀至消失不见。换言之,“武”的男性气概通过克制性欲、漠视女性甚至仇视女性来彰显。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武松杀嫂。面对潘金莲的调戏,武松展现了极度的克制,他训诫道:“嫂嫂休要这般不识廉耻,为此等的勾当。倘有些风吹草动,武二眼里认的是嫂嫂,拳头却不认得是嫂嫂!”[ 19 ] 212厉声呵斥只是武松对潘金莲的警告。在西门庆与潘金莲毒死大郎的阴谋暴露后,武松以极其残忍的方式将其杀害:“……那妇人见头势不好,却待要叫,被武松脑揪倒来,两只脚踏住他两只胳膊,扯开胸脯衣裳……把尖刀去胸前只一剜,口里衔着刀,双手斡开胸脯,取出心肝五脏,供养在灵前。”[ 19 ] 242虽是报仇,这样触目惊心的杀人方式无不显示出武松这类“武”的形象对女性的极大憎恶。作为“武”的典范,武松以打虎来彰显十足的阳刚气质,又以杀嫂完成理想的“武”的男性气概。
而在《西厢记》中,尽管才子张生外表羸弱不堪,娇柔扭捏,但作为“准状元”,他仍然掌握着“文”这一武器与“武”相抗衡。能文善书的力量不是与“文”相对的“武”的优长,却代表了文人的绝对优势,“脸儿清秀身儿俊”的张生能够在关键时刻拿起自己的终极武器来处理危机。第二本第一折中,孙飞虎发号施令要“进兵河中府,掳莺莺为妻”[ 18 ] 46,为挽救局面,莺莺只好以自己为筹码来退军。就在“诸僧众各逃生”[ 18 ] 50之时,张生不慌不忙,联系故人白马将军杜确,“一封书礼逡巡至,半万雄兵咫尺来”[ 18 ] 58,虽然不似武夫般武艺高强,但正是因为他的书信才化解了危机,这个“笔尖儿横扫了五千人的”[ 18 ] 50桥段也给了张生成为莺莺夫婿的机会。
早在《左传》中楚庄王就提出武有七德:“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 20 ]这表明只有军事威力来壮大国家是与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行使这种力量的智慧。《西厢记》以文和武两种男性特质同台对擂,展现出前者的绝对权力。普救寺中的惠明是典型的好汉形象,他“吃酒厮打”,与《水浒传》中“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好汉如出一辙。张生从长老处得知惠明的性格,便略施激将法使“提刀仗剑”的惠明杀出重围,如期交信。在这一情节中,惠明只不过是文弱张生的利用工具,二者对比下只显示出惠明的有勇无谋,而手握书笔、心有谋略的书生正是古代社会理想的文人形象。
无论是文士还是武士,他们都为“治国平天下”服务,“士”被驯化为公共领域的群体。作为“阴”的代表,女性被男性所建构的“阳”的领域完全排除。男性之间的社交关系通过对女性厌恶或恐惧的态度体现出来,这也是“文”和“武”两种类型的男性气概的共通之处。在雷内·伊阿(René Girard) 《欺骗、欲望与小说》(Deceit , Desire , and the Novel) “情欲三角”(erotic triangle)理论的基础上,塞吉维克结合盖尔·鲁宾所提出“贩卖女性”(the traffic in women)的概念,对“情欲三角”进行了再次解读[ 5 ],将这种“两个男性争夺一个女性”的现象运用于探索同性社交关系中,由此也转化为“一男一女为另一个男性”展开的竞争模式。充斥着男性团结的《水浒传》与男性竞争的《西厢记》是“情欲三角”概念的典型表现。
在《水浒传》中,潘巧云这一女性形象与潘金莲有些许类似,也被归类为通奸之妻。石秀勘破结拜兄弟杨雄之妻潘巧云与裴如海有染,提醒兄弟要注意此事,杨雄却被潘巧云所蒙蔽,没能识破真相。石秀为了兄弟,伺机捉奸直接杀了裴如海,而对女性的处理却再次展示了“武松杀嫂”的暴虐:他说服杨雄亲手杀死潘巧云,“石秀便把那妇人头面首饰衣服都剥了……杨雄向前,把刀先挖出舌头,一刀便割了……一刀从心窝直割到小肚子下,取出心肝五脏,挂在松树上。杨雄又将这妇人七事件分开了,却将头面衣服都拴在包裹里了”[ 19 ] 428-429。有趣的是,杨雄在咒骂潘巧云时,最为在意的就是他的好兄弟:“你这贼贱人,我一时间误听不明,险些被你瞒过了。一者坏了我兄弟情分……”[ 19 ] 429经历过这件事,杨雄日后最为依赖的人一定是好兄弟石秀,而自己的妻子徒留邪淫放荡的毒妇骂名。雷金庆在《男性特质论》中也指出:“男人之间的感情之自然、之基本,令它凌驾于所有其他的人类感情之上。正是这种理解,为克服女性入侵所带来的挑战赋予了重要的意义”;“这种感情(异性恋情感)必须被剪除。无论是出自‘忠,还是出自‘义,对感情的忠诚只适用于男男关系”[ 4 ] 52。在这个情节中,塞吉维克所指出的“情欲三角”从“男-女-男”转化成为“男-男-女”,最终理所当然地指向了男性同性关系的建构上,男性气概反复从“厌女”的角度展示出来。在这里,“武”的男性类型以“厌女”为衡量尺度,但这并不代表“武”的男性特质与异性恋爱情不能兼容。《弁而钗》第二集《情奇纪》的男主人公张机恰恰是武士团结精神与浪漫因子交融的代表。在明代重视情感思辨的背景下,钟图南以“情”而不是“礼”作为标准,“今情已慊,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12 ] 164,张机也认可“情”的巨大作用,“兄言及此,真情人也。弟虽男子,亦裣衽甘为妾妇矣”[ 12 ] 164,模糊了性别和性向的边界。《浮浪之友》(The Libertine's Friend)一书中将这种与传统“武”的男性气概看作是儒家所指的“儒侠”,“《弁而钗》运用情色术语重新解释男性纽带的概念,发展了隐藏在《水浒传》中厌女的男性社交共谋意识。”[ 21 ] 76同时,这种男性气概的出现意味着浪漫书生和侠义英雄不是完全对立的,“在晚期的帝国小说中,它們经常根据一种融合(syncretic)的观念以互补关系来表现”[ 21 ] 8。
与《水浒传》中两相团结的男性同性社交关系相对,《西厢记》以相互竞争的同性关系来展示理想的男性特质,这也是“文”的世情文学与“武”的历史小说之间的对比,两者是殊途同归的。王实甫将“清贫书生”与“纨绔子弟”这两种充满张力的男性特质并置,且它们的代表人物都与异性莺莺产生了联系。“情欲三角”在这个故事中化身为“文人-女人-奸人”的模式,但仍未脱离它的主旨。《西厢记》前四折都在讲述崔张之间的情感发展,直至第五本第三折中,出现了张生与郑恒之间的斡旋。上文提到过,崔母由于张生“书剑飘零,功名未遂”便打发张生先上京赶考,而郑恒“祖代是相国之门”[ 18 ] 181,崔郑结合正是十分匹配。两人的矛盾聚焦在各自的权力身份上。就在郑恒上门提亲时,张生取得功名,晋升统治阶层,附加官方话语代表人杜确将军的金口玉言,张生在双方竞争中大获全胜。在这场竞争中,莺莺不再是对张生意惹情牵、大胆逾矩的那个人,她站在那里却缄口不言,成为男性视角下一件美丽的战利品。
文人和好汉的男子气概都以排斥女性而建立起来。“武”的男性气质将“忠义”放到了首位,这种忠义却是对于男性而言的;“文”的绝对胜利以胜过同性为标志,而他们所处的同性领域却对女性极度排斥。他们不断地规训男性本身禁欲,以不近女色作为“好汉”“君子”的标准;一边又不断约束自身竭力为公共事业服务,完成大业,理想男性成为了毫无私念、报效家国的符号,他们被“去性别化”了。
结语
在权力等级关系的笼罩下,阴与阳、才子与君子、文与武呈现出种种张力,本文在对三组张力关系的解读下探究了中国古代男性气概的形塑过程。男性可以是风神俊茂、能文善书却纤美柔弱的才子,也可以是恪守孝道、独占鳌头而又彬彬有礼的君子,更可以是抛尽阴柔、孔武有力又极具侠肝义胆的赳赳武夫。在以男性为主体的父权制社会下,种种男性气概都得到了主流话语的认可。是什么让他们殊途同归?这不禁让人觉得欲盖弥彰。女性成为这些男性气概建构中的“他者”:她的出现是情欲的客体,被男性主体当作碎片欣赏;她的消失是为了帮助男性走向公共领域,从而与其他男性共同“功成名就”。
男性气概不能以西方视角简单剖析。古代中国的官方话语、朝代更替等因素无不影响着人们对男性气质的期许与想象。时至今日,“男性气概”仍被大众看重甚至产生种种文化冲突。回溯封建帝国时期的男性特质后,更有利于反观现实生活,为当下男性气概的建构开放新思路。在欧美、韩流等流行文化风靡的今天,“娘炮”、“小鲜肉”等标签张贴在男性身上,让社会看到了更多版本的男性特质。在主流话语的背景下,真正的男人应该“不娘不弯”,展现出阳刚的一面。而当回溯传统文化中国的男性气概之后,这些多样化的男性气概的演绎给当今社会对男性特质的要求提供了更多提示。古代中国的阴阳学说接纳了阴柔并存的男性气概,也提出了“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和谐之道,这不得不说是当下男性气质构建的一条重要线索。
参考文献:
[1]Geng Song. The Fragile Scholar:Power and Masculinity in Chinese Culture[M].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4.
[2]许慎.说文解字注[M].段玉裁,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55.
[3]钱仲联.中国文学大辞典(修订本)[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0:1999.
[4]雷金庆.男性特质论:中国的社会与性别[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
[5]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吉维克. 男人之间:英国文学与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1:27-28.
[6]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1992.
[7]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8]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700.
[9]黄帝内经[M].姚春鹏,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31.
[10]王安石.王荆文公诗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508-509.
[11]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3:10543.
[12]醉西湖心月主人.弁而钗[M]//陈庆浩.思无邪汇宝.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台湾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1994.
[13]黄元吉.道德经注释[M].蒋门马,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2012:177.
[14]曾朴.孽海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15]Paola Zamperini.Lost Bodies:Prostitution and Masculinity in Chinese Fiction[M]. Leiden: Brill,2010: 139.
[16]论语译注[M].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 2006.
[17]陶宗仪.南村辍耕录[M]//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6186.
[18]王实甫.西厢记[M].王季思,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9]施耐庵.水浒传[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6.
[20]春秋左传注[M].杨伯峻,注.北京:中华书局, 1981:814.
[21]Vitiello Giovanni. The Libertine's Friend: Homosexuality and Masculinity in Late Imperial[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1:76.
[責任编辑:黄俊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