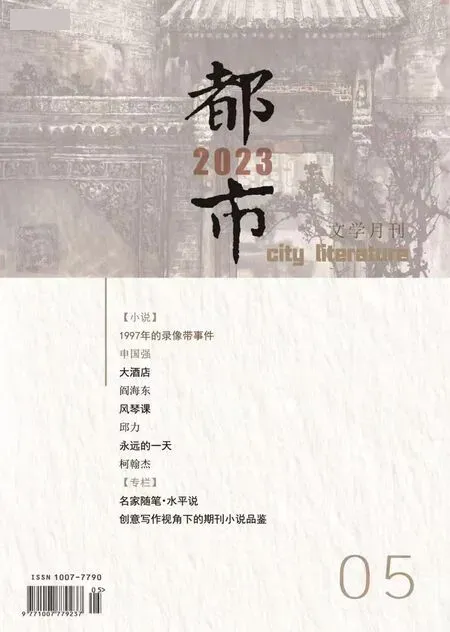劳动人的消息和风景
文 葛水平
壹
呼绿雄的故乡在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洛旗,地处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金三角”腹地,毛乌素沙地东北边缘,东与准格尔旗相邻,西与乌审旗接壤,南与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交界,北与鄂尔多斯市府所在地康巴什新区隔河相望。地处亚洲中部干旱草原向荒漠草原过渡的半干旱、干旱地带。
水蚀沟壑和坡梁起伏的故乡,风沙肆虐。
他说:蓝、绿、白三色勾勒了家乡,虽然是只有三种颜色的家乡,但却并不低调。如果你碰巧遇到了牧羊人,那他一定会请你去自家的土房子坐坐。一个黄土夯起的房子,加上一些稻草,这就是一个土房子。一个火炉,一个桌子,一个土炕,这就是摆设。
此时的家中只有两个人,父亲和呼绿雄。屋子里没有女人,父亲不是亲父亲是养父,是他的大伯,内蒙古人喊“父老老”。
他的大伯无妻,光棍一个,大伯的兄弟把第一个孩子过继给了自己的亲哥哥,是连筋带骨的疼爱。养父有手艺,也是一个聪明人,会木工活计,甚至懂一点阴阳八卦,遇见婚丧嫁娶也替人看好日子。按说怀揣手艺的人吃遍天下,可他的养父对自己的手艺并不看重,更多的时候是作为放松自己的一种方式,借手艺找一个可以喝酒吃席的热闹地儿。
养父怕孤独。
会木匠的人,屋子里没有一件自己的手艺活,土屋,灰冷的泥墙皮常常因鼠患“啪嗒,啪嗒”掉落。他就这样生活了几十年,屋子里没有女人的声音,没有香胰子味道,没有搽脸油的香气,有风时窗口上吹进来一缕花香,惹得人很馋。土屋里唯一的女人,出现在土屋深处八仙桌子上斑驳的绿色相框中,是一位清秀的女人,留海挂面似的挂在前额,豌豆眼睛,嘴角儿微微翘着,因了久远,照片上的女人眼睛迷离。
这个女人是呼绿雄的祖母。
很小的时候,下学回来的呼绿雄常一个人面对土屋,一天一顿饭,煮饭时多添一碗水留出晚饭。养父出门揽生活,走哪住哪,酒喝多了烂醉在外是常有的事。从童年开始,孤独一刻不离陪伴了他,白天的某一个时间,他常望着相片中年轻的祖母,他的心腹中,有一种难过始终蠕虫般地呻吟。
她微笑着。一个人死去,难道不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迎接她的到来吗?死亡在他的脑海中有一个不确定的交叉点,这是一道数学公式,如同一加一不能成为二,一减一也不能成为零一样,许多前人对魂灵回转的描述让他充满了期待。
饿极了,不想回家,走到同村叔叔屋前,屋子里的欢声笑语像一团火,弟弟回头看他的眼神很陌生,婶子走出屋招手要他进屋,那一瞬间,他和这个家有了一种距离,他退后一步跑开了。
十岁时开始学会生火做饭,生活所迫,他向日子屈服了。
自尊已经怯懦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每天只要经过叔叔的院子,见到声音传出,就心跳加速,十分害怕叔叔家人看见他,因为他无法避开心中的尴尬,或者说是怨恨。
上高中时家里已经有3000 元外债了。酒肉连带着的朋友,古话叫:酒肉朋友。民间叫:狐朋狗友。此时的外债是吃喝落下的,古话又说:吃不穷穿不穷,计划不到一辈子穷。读大学有什么用?花一堆钱,从哪里赚钱?有一次听见养父和叔叔吵架,关于他上学的问题,叔叔希望这个儿子上学,养父含糊其词不同意,兄弟俩为了争上风,为了把自己的道理挑明,争吵中有些话很伤对方,谁也无法说服彼此。固执真是似曾相识,弥漫多重语调的争吵导致最后兄弟俩反目。
呼绿雄还是在“父老老”家,只是在他的问题上井水不犯河水。
呼绿雄夹在亲情的缝隙中,看着立场透明的他们,会觉得世界突然就剩下了自己,有种无法解救的无助和孤独。在成长的年份里常常这样,一面享受着这种隔绝一切的孤独,一面对这个世界充满了不信任。有一次听当地的年轻人说:“想赚钱就去煤矿下井,来钱快。”
一次招工,他跟着熟人义无反顾地走了。
煤矿井下作业是一件十分艰苦的工作,也是一件十二分危险的工作。他没有高学历,到煤矿工作,一,凭仗的是年轻人,二,因为没有学历只能做劳务工。
如果你没有下过矿井便不知道井下事。黑笼罩了一切,黑煤的墙没有黑影,黑甚至可以淹没人们的羞涩,如果你愿意分享大自然的赐赏,将世间一切忧烦涤除荡尽,那么黑可以让你剥下身体上所有的累赘,还原自我。
2002 年,呼绿雄入榆林榆家梁煤矿下井,开始并不是在一线,只是井下打杂。一天的工资是17.4 元,正式工一月是6000元。正式工有班中餐,他没有,他是劳务工中的最下层工种。看着班中餐剩下的稀饭,他喝一口,准备喝第二口时他落泪了,一口稀饭再一次伤了他的自尊。
贰
一年后他去了榆林补连塔煤矿。背着家庭的3000 元债务,一年了,一毛钱没有还上,成长的自尊日日横亘在他眼前,怎么样省着花钱,钱都很难赚。
此时,家里捎来信说,养父酒后驾驶三轮车翻到沟里了。
那时的夜晚,白天忙于生计的人们显得异常亲切。人们放下白天的活儿,解开生活的枷锁,敞开心扉说话。呼绿雄希望和养父来一次长谈,当然是关于成年后日常生活的琐事,读书考学已经成为过去的想法。
养父从黑暗中拄着拐一颠一颠走回来,手里吊着养父的挚爱:酒和肉。生活的奢侈品是养父赊来的,对养父来说,只要是为了嘴前欲望,一切赊欠都值。养父的身后是村庄里一干闲人,他们被养父招呼来喝酒。礼貌、体恤、客气、悲悯都忘了。冷眼看着这些人,他们没有心肺地说笑,呼绿雄觉得自己的存在减轻了他们喝酒的快活。
熬夜是酒徒的日常,养父用筷子夹着煮熟的一块肉让呼绿雄吃第一口香。肉香冲鼻而来,口水泛起又咕噜咽下。他倔强地把脸扭向门口,那一瞬间他忍着情绪,甚至想一辈子不吃肉。
没入黑暗中的呼绿雄,独自一人走着,这时的夜不再恐怖,人不再孤独,他和夜较真,任由泪水跌落。哭着走往叫叔叔的(亲父亲)家中,他在夜色中听见了屋子里的欢声笑语,灯光是柔和的。他停下脚步站在院边,夜晚是回忆往事的最佳时间,而此时的夜空,新月如钩,钩在一丛缀满情愫的相思树丛外,钩出夜色的无限委屈。一个完美的充满欢声笑语的家,不属于他,站在窗外的他已经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
生活中的双重压力再一次让他选择坚强。他离开榆家梁煤矿去往补连塔煤矿成为一线采煤工人。在此,他干了三年,遇见了神东第一批劳务工转正考试,一共970 人参加的考试只录取25 个正式工。他考了第一名。
人生改变身份的一瞬间,亮晃晃的日头都和从前不一样,他小心翼翼托着命运给他的赏赐,用生命艰难地抗争着自己的定数,也提醒了他,假如按照现在的成绩,当初是不是可以考上内蒙古大学呢?
反复想,真是有意思的事,想到最后他给自己一个肯定:呼绿雄就是内蒙古大学毕业生。
井下的所有机械设备,只要正式工会操作的他都会。人心就怕长眼睛,多看多学是他超越他人的最后本事。他知道,这世界上只有不学的,没有学不会的。
2006 年2 月,呼绿雄拿到了转正工资6000 元,此时他已经是副班长。由17.4 元到1000 元,再变成6000 元,也许它的变化看起来比那些浮泛的所谓的幸福更有意味,但是,痛苦是不会飘散的。正式工是一张贴了金箔的名片,有如高中考上大学。
拿到工资的第一时间,他请班里的人吃了一次饭,让所有人点贵菜,贵菜是荤菜,他想到了养父。
一位神东矿矿工怀揣着转正后第一个月工资,回到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纳林希里镇其根沟二社。满怀喜悦地站在自家的土屋门口,面带笑容很真诚地和年老的养父说:“爸爸,我请你吃饭,我们喝酒吃肉去。”
养父吃惊地站在土屋门口,望着笑容满面的儿子,平生第一次没有抵触情绪的邀请让养父流下了眼泪。
呼绿雄的儿子这一年两岁了,和养父一起吃饭时他说到了孙子,说到了儿媳。养父第一次说:“我是会木匠的人,我没有给你打下一件家具,总想着有机会,可是现在没有机会了,一来人家都不时兴手工活了,二来我的眼睛坏了,看不清走线,身体也越来越糟糕。我是会掐算好日子的人,我儿子结婚不敢算,要别人算,我就怕那个日子算坏了。现在看来世上的日子都是好日子,我哪里能够想到有一天我儿子请我喝酒吃肉,这日子说到眼前就到了。”
呼绿雄看到养父已经不是当年的养父了,喝酒也少了,吃肉更少,似乎半天都不动筷子,酒和肉在眼前摆放着,也就是一个气氛。
呼绿雄说:“爸爸,我要带你出去看看身体有没有啥毛病,你从前可不是这样,酒肉放在眼前就没有命了。”
养父说:“我没有啥病,就是人老了。你妻子是一个好女人,不嫌弃你,她也等到你今天了。”
呼绿雄想到妻子,想到当年妻子来土屋相亲,土屋内家徒四壁。
叁
对自己妻子的任何赞美,都会显得虚假。平常和卑微、索取和奉献、尊严和地位,在爱情面前获得改写,赋予了具体而真实的内容才可谈得上爱。社会底层被人们遗忘的角落,这些普通的事物中,普通人的爱情就是亲吻泥土。
呼绿雄的妻子当年是神东煤矿酒店的一名服务员,2003 年通过朋友介绍认识呼绿雄,那时呼还是一名井下劳务工人。两个人有同样的背景——贫穷。或者说都是因为贫穷无法继续学业,过早走向工作岗位。呼绿雄还记得第一次领着女朋友回家,那时的乡村普遍修建了砖瓦房,他们家还是土屋。他有一种豁出去的感觉,就这样的家,就这样的人,接纳这个人就必须接纳所有的一切。
他捎话乡下的姑姑,要姑姑去收拾一下屋子。家徒四壁的屋子姑姑洒水扫尘,一边扫一边难过。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土屋内,最扎眼的是炕上的花床单,这是姑姑的杰作,也是他有生以来在土屋唯一看见的春天。
面对一切他不想虚弱地躲避什么,很直率地和女友说:
“我的家,回来之前让我姑姑收拾了一下,有些装点我们走后,姑姑要拿回她自己的家。我家的土屋没有色彩。你爱我这个人就一定要接纳我的家,我的父亲。这个家里我没有母亲,你是这个家里唯一的女性,我不想欺骗你,我的家里缺少正常家里的其乐融融,我父亲喜欢喝酒,酒后的父亲对家没有牵挂,喝酒是他一天里最快乐的事情,你如果爱我就不能嫌弃我的父亲,因为我的父亲内心很苦。”
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女友说:“每个人的家都不一样,但每个家庭都有说不得的苦。”
第一次拥抱女人,蜻蜓点水似的,没有电视剧中那样的煽情。
为了掩饰家徒四壁的羞愧,养父说:“农村人都这样,慢慢会好起来。”
结婚时不能免俗,岳父家提出彩礼钱,呼绿雄没有存款,这些年他一直在还债,旧债新债,天旱,养父刚打了机井又欠下债。岳父把一万元彩礼降到3000 元,可他也只凑到2200 元。他和岳父说:“没有钱,但是,我有一天会有钱。只要我努力工作,劳动不会亏待我。”
岳父家境也不好,但是岳父有岳母,有完整的家,聚气也是聚财。
巴掌大的村庄,住土屋的光棍儿子娶妻,生活的“里子”都成了问题,哪里顾得上这些“面子”。岳父顾忌他的面子悄悄递给他400 元,让他在人前宽裕一些。他不是少心没思的人,他记得人的好。住进土屋的女子带来了香胰子的味道,妻子让他要强的个性经住了命运的冲击。呼绿雄和妻子说:
“不改变我的现状,你爱我就没有意思了。”
2004 年结婚,2005 年有了娃娃,那时的工资一个月800 元,结婚、生娃,有一个月一分钱都没有了。他和朋友借钱渡难关,朋友怕他还不了钱,只借给他50 元,三口人一个月花了50 元。贫穷带来的不信任、怀疑、小瞧、防备等等,让他难过到了极致,但是,他得领人家50 元的好。
如前面所说,2006 年劳务工转正,他回乡请养父吃肉喝酒,但是他发现养父已经吃不下肉喝不进酒了。养父得了重病,肝癌。
一辈子喜欢酒肉的人,长一句短一句的吆喝变成了长吁短叹。人生经不起富裕生活的开始,假如一定要拿一个人的生命来换取他现在的一切,他宁愿回到从前。但是,人生永不会这么换算。
一顿饭吃得天都黑实了,呼绿雄在伊金霍洛旗登记了一家不大的宾馆,宾馆有热水,养父一辈子没有洗过澡,洗洗身上多半辈子的泥,也让他舒服舒服。
洗澡出来,浑身冒着热气的养父不好意思地说:“不怕你笑话,爸爸身上的泥也没有你想象的那样子厚,泥星星,浅浅的一层。有钱了真是好啊,一天洗一次,唉,一辈子要浪费多少水呀。”
父子俩笑,两个人的笑都控制着,生怕一动笑过头了又要生出什么幺蛾子来。
一个人的一生中会有许多幸运和遗憾,其中又有一两件特别刻骨铭心。而对一个煤矿工人来讲,许多幸事和憾事往往又与自己的奋斗有关。但是,对他们来说,很少听说某件事既是天大的幸运又是头号的憾事。
当一个人的胸口总是被两种极其矛盾的情绪一起纠缠时,对一个善良的人来讲,其难过是可以想见的。
2006 年,呼绿雄陪伴养父进京看病,其实看病已经成为一个借口,他就是想领着养父去北京看看,看看天安门、故宫、长城。一辈子没有离开过伊金霍洛旗,纳林希里镇的养父,在睁着眼睛时让他看看世界,看看天下的好。
这时候走路都开始气喘的养父,或许是儿子对他的孝顺让他感动,他坚持着在天安门看升旗,脸上始终都挂着笑。走到故宫时养父走不动了,停下来看着偌大的故宫,故宫行走的行人让养父说了一句有趣的话:“北京人不如咱们那里的人穿戴得好看,说明他们也有过穷日子。”
隔天,去看长城。书本上说“不到长城非好汉”,现在到了长城脚下,爬不动了,力气也有用尽的时候,哪里敢说自己是好汉!
望着高处的长城,长城像铁箍一样缠绕着山,任凭怎么想象也不为过。一道峁梁上,一位打扮得过火的陕北农民用粗粝的嗓子吼着什么,好像是在拍电视,那种表演的样子让养父周身战栗,仿佛觉得,虽然这老农打扮的样子很陕北,却感觉有点戏剧得煨煳了。来北京做啥来了?啥都不如安安稳稳待在家舒服。回。只有回家是正理。
养父和呼绿雄说:“明天咱就回家,你妻子带着娃在家,咱父子在北京游山玩水,情理上说不过去,回家,好吃好喝,自己家自己说了算,没有心情看这看那了,回,爸爸想回家了。”
呼绿雄也觉得北京太大了,这种完成任务似的看景搞得人很累,何况一个病人。既然养父想回,由着他,回就回。人到了熟悉的环境中也许才能压得住惊慌,才能找得到幸福。
回去的路上,丈母娘打来电话说,你媳妇怕是又怀孕了。呼绿雄告诉养父妻子又怀孕了。养父龇着嘴笑,笑着笑着泪出来了:
“爸爸真是没白养活你,你真是在爸爸脸上左一下右一下贴金了。”
肆
入冬,第一场雪下得早,天空是阴沉的铅灰,地上是天衣无缝的银白,似乎一切都已经冻结。汽车开过的声音显得黏稠和凝滞,雪花在空中纷飞乱舞,如千千万万格外活跃的精灵。家乡很难见雪,即使落雪的时候,事先至少也需要两三天的酝酿,然后才见零零星星的雪花飘落。室外温度骤降到零下30 多摄氏度,几乎是从秋天直接走进了三九。这场雪下得好,干裂的土地可以饱饮一顿了。
呼绿雄从医院接回养父。人已经坐不起,回家也就是等着准备后事了。拉开车门的一刹那,风雪成了无数把锋利的小刀在脸上浅表处横割竖割。衣服突然变得又轻又薄,风像冰水一样轻易地浸过外套和毛衣直抵五脏六腑。
四个小伙子抬着养父抬回土屋炕上,土屋内姑姑已经生了火,温暖的土屋,风雪给人的那种最初的激灵过去了。养父挣扎着伸出手招呼脚地上忙碌的呼绿雄过来,他似乎要说什么,抓住呼绿雄的手,仿佛抓住了温暖,儿子给自己带来了些许的生命延长和瞬间的坚定。他无力地大口喘气,眼睛漠然地停在某一处,似乎在等待合体的魂灵。往昔再一次闪现,那些顽皮的小事或者话语间的顶撞一遍一遍闪回。
歇息之后养父说:“爸爸要离开你了,这个世上你没有爸爸了。没办法,爸爸知道你的办法想尽了。爸爸要交代几件事给你。第一件事,别人家都修了新房,爸爸没有能耐修不起,土屋子显得寒酸,我死了,你别嫌弃它,从前的记忆都存放在里面,不要让土屋轻易塌落了;第二件事啊,我使唤过的农具就叫它们在,我和它们有感情。儿啊,人这一生还不如农具呐,人制造了许多长生不老的东西,人就是救不了自己的命,没办法;第三件事,家里喂养了20 多只羊,你卖了羊,换几个钱,爸爸没有给你留下一分钱,卖几个钱算几个钱吧。你不要埋怨爸爸不让孙子来看我,我脱相了,人鬼不分,害怕吓着他。”
该死的病魔就要夺走这个老光棍的命了。
努力是一个多么虚弱的词啊,养父的手慢慢没有了体温。
老天没有恻隐之心。
老光棍养父带着一生的福气走了。同时也带走了自己的苦难,走到一个再也不会回转的地方。
安葬了养父,在分配他身后事情时,呼绿雄把20 多只羊送给了他的亲生父母,他们给了自己生命。叔叔不要,呼绿雄赶着羊走到叔叔家大门口,跪在叔叔门前,门前立着惊慌失措的“父母”。呼绿雄说:“叔叔、婶,羊赶到门前了,我感谢你们给了我一个苦难的爸爸,羊是你们的了。”
说罢,起身头也不回走了。
那些干活的农具在墙角安稳地等待着自己的命运,因为长时间不用已经长了锈斑,农具有爸爸的手温,农具和泥土亲近才是它们的富贵命。呼绿雄在土墙上钉下一排钉子,用清油擦洗干净,挂上去的农具,像艺术品似的,与时间和意义无关,它们是养父在世的牵挂。
雪纷纷扬扬下着。
雪地上的土屋在积雪之下已经看不清眉目了。
钻天杨纵横交错地分割了连片的村庄,它们光裸的枝丫凝固在乌灰的空中,整体上保持着爆炸的姿势。一只乌鸦从土屋顶上飞起,将苍凉的聒噪带向广阔的草原。呼绿雄锁上门,对飘雪的天空充满敬畏,他第一次带着情感认真对视土屋,从前对他形成的那种苦寒的挤压突然消失了,一切显得那么温暖和令人不舍。
不住人的土屋子,很快就开始往下掉墙皮。呼绿雄害怕土屋子塌落,想着用一种什么方式可以阻挡四季对它的伤害。他最后想到了用塑料布把土屋子包裹住,大大的一个包裹,有水分在塑料布里面也许土屋子会活得长久一些吧。
有两年时间,伊金霍洛旗纳林希里镇其根沟二社,被包裹着的土屋子成为大地上一种风景。
两年多时间,每当呼绿雄回到故乡抬头看见它时,心中就有一种酸楚。两年时间,它就像他健在的一位亲人时时刻刻在告诉他什么、启发他什么,可是他一直无法读懂它的深意,也就无法读懂养父。
伍
几年后土屋子还是坍塌了,没有声息。
每次回乡,面对土屋子他一直有一种刀绞的感觉,养父的三轮车已经被雨水和阳光侵蚀得面目全非。从前,很大的一个原因很可能与贫穷见识少有关,因为呼绿雄清楚,贫穷让他忽略了土屋子的好,再好的日子也回不去了。但是,当他再次独自一人痴望它时似乎越来越悟出了一个道理:世界上有很多东西远比一大箱黄金珍贵,钱也许能买来奢华,但是绝对买不来亲情,买不来苦难和坚强。土屋子里的记忆让他受用一辈子,养父不舍得它的原因,也许让经了岁月的呼绿雄找到了答案。
2016 年,呼绿雄开始在土屋子的基础上修建新房,他要修建一座伊金霍洛旗,纳林希里镇其根沟二社最好的房子。修建好了房子,呼绿雄把养父的四轮车放在院子里,曾经土屋子有过的都放进去。伊金霍洛旗纳林希里镇其根沟二社的人们笑话他,这么好的房子就为了存放没用的旧东西。
只有呼绿雄知道,怀念自己的成长,不是钱能够称量的,没有钱花,可以通过劳动赚得,但人活着不能没有回忆,回忆中更不能没有亲人。劳动给了他知足,这份知足让他懂得了人活着更应该要知恩图报,世间许许多多的事、物、人,无不如此,每一个环节中,正是因为残缺,所以人们变得努力,生活也变得更美。
艰苦环境下工作的煤矿工人,形成了其特殊的群体品格。这种品格一旦形成就成了工友们共有的行为规则和行为方式,它甚至影响一个企业的生产力;这种品格会逐渐外化成一个企业的品格,它也影响了一个团队的凝聚力;这种群体品格又直接对应着这个行业的心态,并影响整个行业的走向。
文学是语言艺术,作品以故事取胜,打动人心的故事一定来源于最基层。在这个重要的年代里,伟大的文学不可能脱离政治,不可能失去同社会的联系和对人类命运的关怀,真正的作家是富于文化理想和道德责任的。面对生活的真诚和勇气,写作者内心有光才能看见喜爱光明的劳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