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语科幻的百年之路
程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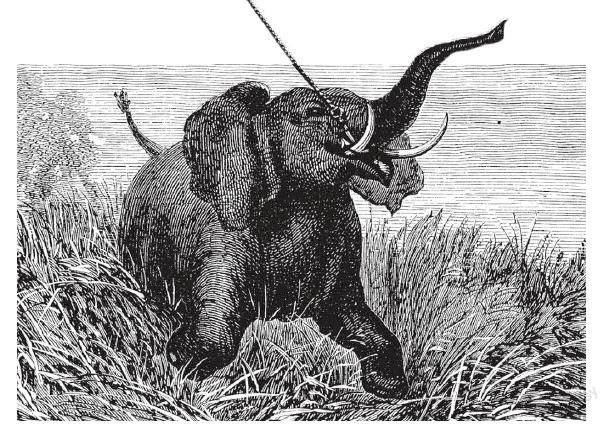
儒勒·凡尔纳小说的插图。百余年来,很多中国读者最初读到的科幻作品,就是凡尔纳的小说。《气球上的五星期》是凡尔纳的代表作之一。或许是受了凡尔纳的影响,在早期的华语科幻小说中,热气球也是一个经常出现的道具。
从《弗兰肯斯坦》一书的诞生过程来看,科幻文学的出现带有极强的偶然性。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幻文学都没有形成独立的创作纲领,带有相当大的随意性。相比之下,华语科幻文学作为其中的一大支流,从问世之初就承载着确切的梦想和期望。
飘摇世路中,独钓寒江雪
1900年,儒勒·凡尔纳的小说《八十日环游记》(现在通译为《八十天环游地球》)被译成中文,成为中国人最早接触的科幻小说之一。在中国,科幻小说起初被称为“哲理科学小说”,这个名称最早出现在1902年的《新小说》杂志创刊号上,为之命名的是梁启超。在梁启超的眼中,这个文学类型兼具了“科学上最精确之学理”和“哲学上最高尚之思想”,是有益于社会和人生的“新小说”。
带着开启民智的热忱,梁启超翻译了法国天文学家和作家佛林马利安的《世纪末日记》,又参与编译了凡尔纳的《十五小豪杰》。在“新小说”的热潮下,小说家吴趼人、包天笑等都曾翻译、改编过外国科幻小说。鲁迅不但翻译了凡尔纳的《月界旅行》(现在通译为《从地球到月球》)和《地底旅行》(现在通译为《地心游记》),还写下了一篇“辩言”,不仅称赞科幻小说弥补了科学的枯燥,丰富了文学的类型,而且把“导中国人群以进行”的理想寄寓在科幻小说上。
从这些来看,科幻小说对中国读者而言,似乎是不折不扣的“舶来品”,实际上,这个文学类型的种子一落到东方的大地上,就结出了别样的花果。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率先将作品的体例改编为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的样式,用“回”来命名每个章节,还给每一回都重新拟好对仗工整的回目,甚至在最后一回之前,给每一回的结尾都添上“要知以后情形,且听下回分解”之类的结束语,从而让小说文本适应当时大部分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译者所做的巧妙改编,无形之中将这个崭新的文学样式嫁接到了中国传统文学的古树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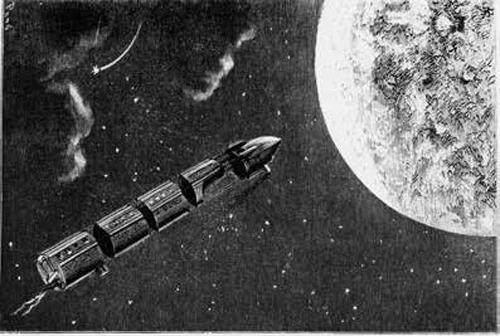
古树也在繁衍新枝。1904年,《绣像小说》杂志开始连载《月球殖民地小说》,作者署名“荒江钓叟”。小说连载持续了两年,共计35回,并没有结尾。“荒江钓叟”这一笔名此后再也沒有出现过。作品和作者的双重神秘感,给第一部原创的华语科幻小说平添了几分传奇色彩。
《月球殖民地小说》完全采用章回小说的模式,在展开情节和塑造人物上也颇有《水浒传》的遗风。从行文来看,荒江钓叟也和历史上无数生平不可考的作者一样,都有一颗关注现实的“发愤”之心,将对现实的愤慨付诸笔端。在小说的开头,主人公李安武和龙孟华一见如故,在客栈饮酒谈心,谈的就是当时中国百姓所遭受的苦难。李安武在后来的历险中,屡次说起自己的理想,直到第35回时,仍在重申志愿:“扫祖国百万里的烟尘,救同胞四百兆的性命。”这些不仅回应了梁启超、鲁迅等人对科幻小说的寄托,也将幻想的根源深深扎进现实的土壤中。

动画剧集《爱,死亡和机器人》中,《祝有好收获》一集改编自华裔科幻作家刘宇昆的小说。创作之外,刘宇昆也将华语科幻中的许多精彩之作翻译成了英文。

动画剧集《三体》的主要情节改编自小说《三体II:死亡森林》。

电影《流浪地球》改编自刘慈欣的同名小说。

动画剧集《万神殿》改编自刘宇昆的作品。
百余年之前的小说作者们,也试图将志怪、神魔等传统题材融入科幻小说之中。海天独啸子所著的《女娲石》,就在开篇把追求进步的女性称为下凡的“真人”,把从天而降的陨石附会为“女娲石”,小说在展现种种新奇的发明创造时,故事的展开也和神魔小说中“斗法”情节如出一辙。这些描写,或许会让如今的读者忍俊不禁,却也是早期华语科幻小说的重要特征。
活水不断,清流涓涓
随着时代的变迁,华语科幻小说也迈入了新的阶段,从面向大众的“开启民智”转为面向少年儿童的“启蒙童心”。
1955年,郑文光的短篇小说《从地球到火星》刊登于《中国少年报》,“科学幻想小说”这个名词随之诞生。从此以后,以小说的形式传递科普知识,成了许多读者对科幻小说的基本印象。
一些科普作者也从此身兼二职写作科幻小说。在小说《古峡迷雾》中,童恩正不仅把考古学知识融入一波三折的惊险情节之内,而且把对古国文明的热爱与担忧之情也融入人物形象之中,这种对现实的深切关照,也呼应了荒江钓叟等前辈作者的心声。叶永烈在20岁时就成为经典科普作品《十万个为什么》的作者之一,不久又写出了科幻小说《小灵通的奇遇》。这部小说在尘封多年后,经过修订,于1978年出版,更名为《小灵通漫游未来》。此书一经出版,便收获了来自社会各界的无数好评,故事的续集《小灵通再游未来》《小灵通三游未来》也在读者的呼唤中接连问世。这些故事点亮了无数青少年的心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幻小说也被归为“儿童文学”中的一类。
就如同小小少年,终将长大,通过一批又一批作者的不断开拓和探索,华语科幻小说悄然成长、转变,渐渐走出“科普故事”和“少儿读物”的簡单框架,开始思考人性的弱点、关照社会的角落乃至描绘更为广阔的时空。
与此同时,翻译文学也在不断给华语科幻小说带来新的启迪。吉尔吉斯斯坦作家艾特玛托夫的长篇小说《一日长于百年》就是其中格外引人瞩目的一部。小说从三个不同的层面展开:一个普通铁路工人在草原上过着单调的生活,古代人物的宿命悲剧被后人不断传唱,宇航员在空间站里终于接收到外星文明的信号。从故事开始到结束,地球上的时间只过去了一个昼夜,而浩瀚宇宙中无尽的沧桑已经在如此短暂的时光中得到了极致的演绎。
将当下、历史与幻想紧密结合,这种独特的创作手法,在华语文坛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路遥的长篇现实主义小说《平凡的世界》的后半部分,主人公孙少平与外星人发生了对话,这一情节既包含着对艾特玛托夫的致敬,也反映出,“科幻”这一元素已经被华语主流文学所吸收、接纳。
伴随着文学风尚的变化,那些曾经被科幻小说照亮了心灵的小读者们,渐渐长大成人,步入社会,也开始用方块字记录自己对宇宙的幻想和对世界的思考。那些诞生在20世纪最后10年与21世纪最初10年之中的作品,如今看来,许多都成了读者心目中的佳作名篇。“科幻迷”热衷于在这些作品中发现前辈大师的遗风,指出其中何处是对阿瑟·克拉克的致敬,何处是对道格拉斯·亚当斯的怀念,会为自己收藏了某本书的第一版而得意,也会为那些昙花一现的作者而嗟叹不已。

不同的人在城市的不同层面流动——许多科幻作品都描绘过这样的场景。科幻作家郝景芳的《北京折叠》也是这样一部作品。该小说由刘宇昆译成英文,于2016年获得雨果奖“最佳短中篇小说奖”。
比如柳文扬,这位作者虽然没能留下鸿篇巨制,但却以匠心独运的短篇小说引得读者不断回味。他的代表作《一日囚》,讲述了一个颇具荒诞色彩的故事:一个身世不明的人,被迫重复同一天的生活,并且,每当这一天将要结束的时候,他就会死亡。这篇小说在文本上和《一日长于百年》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和巧妙的互文关系:如果说《一日长于百年》是将一个昼夜的时间无限延展,使之足以包揽宇宙最深处的哀伤,那么,《一日囚》就是把人生的无数种可能都限制在一天之内,最终将其压缩为一场无法逃避的命运悲剧。跨越文化与时空的对话,就这样通过科幻创作而发生。
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一些读者成了作者,有一些读者成了编辑,还有一些读者成了研究者。随着华语科幻小说的成熟和读者群体的扩大,对这个文学类型的整理和研究活动也开始了。“科幻迷”站在新的世纪里,回顾过去,重新发现那些被时光掩埋的先行者和曾经燃烧在他们心中的梦想,又发现那些梦想如何跨越风雨飘摇的时代,绵延至今。
涓涓细流,汇成奔涌的江河。正是站在前人的肩上,华语科幻小说中终于出现了《三体》这样令世界为之震撼的作品。
回首过去,心向未来
《三体》之后,华语科幻小说何去何从?这似乎成了一个亟须解答的难题。文学的命题从来不是由某个定理或公式来给出一锤定音的解答,而是由作者们用文字来共同回应。他们不仅继续描绘未来世界的景观,而且不忘用笔墨打捞时光的回音,用奇思妙想填补历史的空白点。
梁清散将“新新日报馆”系列的背景设置在清末的上海,也把种种当时尚不存在的发明创造挪到了那个“平行世界”中。作者用想象为“荒江钓叟”勾勒了具体的身世,让这个埋没在故纸堆中的神秘人物化身为一个思想前卫、头脑聪慧的少女,“科幻迷”在读到以后,免不了要露出会心一笑,并且感叹这一身份和“科幻文学之母”玛丽·雪莱何其相似。不仅如此,就连雨果·根斯巴克本人也在小说中登场了。乍一听,这种“关公战秦琼”的手法仿佛又预示着一个“无厘头”故事的上演,实际上,对于那些曾为梦想献出了一切的人而言,这只是一份别样的纪念。在小说中那个光怪陆离的世界里,有人借助超前的科技点缀自己的生活,也有人试图凭借这些来改变家国的命运。虽然故事的结局仍然回归了真实历史的记载,但是在这样的书写下,梁启超、鲁迅以及无数“荒江钓叟”们在百年前写下的寄托,得到了淋漓尽致的重新演绎。
也有作者将回望的目光投向更为遥远的时代。2017年,青年作家慕明发布了小说《宛转环》,将“莫比乌斯环”的概念巧妙地与传统书画、园林的技艺相结合,聚焦于明末士大夫的人生抉择,以轻巧的形式承载起厚重的历史感,也将人与人之间的种种羁绊嵌入叙事中。尽管这个故事是虚构的,其中的人物却能够在历史上找到相当确切的原型。虚构的形象和真实的人物生平交相辉映,故事在亦幻亦真的背景下展开,读者步入其中,逐渐发觉,在封建王朝鼎革的历史重负之下挣扎着的,不再是一个个陌生的名字,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恰似当代人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那么普通,又那么生动。读者就这样走入了这些历史人物的内心,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不知不觉间,故事已然终了。如此的阅读体验,也如同一场“莫比乌斯环”之旅。
科幻的笔法虽然无法真正改变历史,但却能够启发人们以当下的视角审视过去,也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传统题材和科幻文学之间的关系。沿着这样一条线索回溯古代文学,就不难从中发现华语科幻的早期萌芽,那些神话传说中的英雄事迹,那些笔记小说中的只言片语,那些章回小说中的插科打诨,其中都蕴藏着无限的想象,朴素而又灵动,离奇却又合理。近年来,《酉阳杂俎》《平妖传》等书得到多次再版,从装帧来看,都不再仅仅是面向研究者的古籍,而是面向广大读者的通俗读物,“王谢堂前燕”就这样悄然飞入了“寻常百姓家”。读者们以“阅读科幻小说”的思路去重新打开这些书,也赋予了它们新的生命。
百余年前,译者们和作者们为把传统素材纳入科幻小说做出了种种尝试,这些都在而今的作者笔下和读者眼中得到了答复。挑着过去的梦想和当下的期望,华语科幻就这样一步一步攀登蜀道,走向未来的广阔天际。
(责编:李玉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