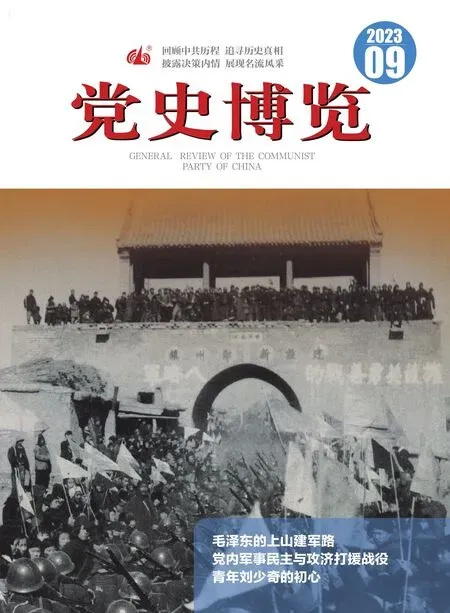茅盾谈“红军贺电”
■林传祥
先说“东征贺信”的发现
关于鲁迅和茅盾于1936年联名致红军贺电,坊间多有传闻。1951年,冯雪峰回忆说,红军长征抵达陕北的时候,鲁迅和茅盾“转转折折地送去一个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庆祝胜利的电报”。1952年,冯雪峰又在出版的《回忆鲁迅》一书中写道:“鲁迅先生和茅盾先生共同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庆贺长征胜利的电报,也正是我动身的前几天才转到瓦窑堡的。”自此,鲁迅、茅盾祝贺红军长征胜利的信件,引起了史学界的广泛关注,几十年来研究者们孜孜以求,都在寻找相关材料。
1995年8月,西北大学教授阎愈新在位于北京西郊的中央档案馆查到了该馆馆藏的中国共产党西北中央局机关报《斗争》 (《斗争》 原为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红军长征期间停刊。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复刊,复刊后的《斗争》从第74期至第102期落款为中国共产党西北中央局机关报;从第103期至第127期改称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1936年4月17日出版的《斗争》第95期,封面目录上印有 《中国文化界领袖××××来信》标题。在无法获得第一手信件档案的情况下,这一份显然是最有说服力的,把它当作众多学者多年来所要追踪查找的“原始”依据也未尝不可。署名“××××来信”的,正是鲁迅、茅盾,由于当时鲁迅、茅盾居住在国民党统治区上海,故用“××××”代替。刊于《斗争》的信件全文如下:

1936年4月17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西北中央局机关报《斗争》 第95期
读了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 《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中国共产党《告全国民众各党派及一切军队宣言》、 中国红军为抗日救国的快邮代电, 我们郑重宣言:我们热烈地拥护中共、 中苏的号召,我们认为只有实现中共、 中苏的抗日救国大计, 中华民族方能解放自由!
最近红军在山西的胜利已经证明了卖国军下的士兵是拥护中共、 中苏此项政策的。 最近, 北平、 上海、 汉口、 广州的民众, 在军阀铁蹄下再接再厉发动反日反法西斯的伟大运动,证明全国的民众又是如何热烈地拥护中共、 中苏的救国大计!
英勇的红军将领们和士兵们! 你们的勇敢的斗争, 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的更大胜利。 全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 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 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热烈的拥护和欢迎!
全国同胞和全国军队抗日救国大团结万岁!
中华苏维埃政府万岁!
中国红军万岁!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 ××一九三六·三·廿九
这是一份“东征贺信”而非“长征贺电”。冯雪峰的回忆可能有一些出入,但其所说的“动身的前几天才转到瓦窑堡”是指他于1936年4月20日“动身”前往上海,也就是说,这份“贺信”大概在4月15日前党中央就收到了。从时间、内容上看比较符合事实。也就是说,这份“贺信”是真实存在的,“贺电”可能指的就是这份“贺信”。
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一份报载消息而非原始信件档案,可信性不高。他们举冯雪峰多次提到的“贺电”(指长征电报)一说,以及当事人茅盾的一贯说法,确认鲁迅是从史沫特莱那里得到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是她提议驰电致贺,经鲁迅、茅盾议定联名致电及电文内容,或者由鲁迅拟文,茅盾未参加也未见过电文,“长征贺电”由史沫特莱设法经巴黎转陕北,这才是公认的说法。但这份“长征贺电”在哪里?它至今尚未被发现。不过,这份非原始信件档案——“东征贺信”即便是真的,也不能因为它的被“发现”而否定“长征贺电”的存在,也就是说“贺电”“贺信”可以并存。
再看茅盾谈“红军贺电”
关于“贺信”“贺电”,作为关键“当事人”之一的茅盾,他是怎样回忆的?又是如何看的?
首先,我们来看看茅盾写的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在《1935年记事》里,茅盾回忆:“1936年春节后的某一天,我照例到一些老朋友家去‘拜年’,也到了鲁迅家中。告辞时,鲁迅送我下楼,走到楼梯中央,鲁迅突然站住对我说:‘史沫特莱告诉我,红军长征已抵达陕北,她建议我们给中共中央拍一份贺电,祝贺胜利。’我也停住脚步道:‘好呀!’鲁迅继续往下走,又说:‘电文不用长,简短的几句就行了。’我点着头,转念又问道:‘可是电报怎样发出去呢?’鲁迅说:‘交给史沫特莱,她总有办法发出去的。’”由于茅盾还要到别家去“拜年”,此事便暂时搁置。“后来因为忙于别的事,见到鲁迅也没有再问起这件事,以后也就忘了,直到4月底冯雪峰从陕北到了上海,才告诉我:‘你们那份电报,党中央已经收到了,在我离开的前几天才收到的。’由此联想,史沫特莱一定是把电报寄往巴黎,再转寄莫斯科,才发电报到陕北的,所以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这份“红军贺信”,在茅盾看来是一份“贺电”,而且他认为是由史沫特莱发出去的。1940年5月,茅盾离开新疆,举家来到延安。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张闻天对茅盾说:“你和鲁迅给中央拍来的贺电,我们收到了。”当时茅盾说自己只是“漫然听之”,因为在他看来“那早已是历史陈迹了”。所以,“没有想到要去追问电文的内容”。“谁能想到这份电报在全国解放后竟成了一大‘疑案’,而且成了鲁迅研究的一大节目。”
从茅盾的回忆文字看,他确实是将“红军贺电”作为一般寻常之事“漫然”对待的,并没有使用特别的语气强调,如此反而增加其提供“史料”的可信程度,至少在他看来“红军贺电”这一史实是存在的。
其次,除了回忆录,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里,茅盾还在回答朋友或研究者的书信里对“红军贺电”做过多次阐释,或简或详。
1963年,上海的一位学者翟同泰(笔名艾扬) 写信给茅盾,提出了几个具体问题:(1)这份电报是谁发起的?(2)由谁执笔起草的?(3)是在谁的家中商量起草的?(4)电报是祝贺长征胜利还是祝贺红军东渡黄河?(5)电报是由地下电台还是托人送达中央的?如果托人,托的是谁?(6)电报在当时国内外报刊是否披露过?(7)起草这份电报的时间是否还能记起?
这位学者问得仔细,茅盾回答也相当干脆:“电报是祝贺长征胜利,即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师。鲁迅和我有了发电报的意思,由鲁迅起草电文,几分钟就办完了。在鲁迅家中。电报后来交给史沫特莱设法拍发。她用什么方法拍发,我可不知道。大概是在国外的报刊上登过。”
1977年4月,茅盾在给作家孔罗荪的一封信里也专门谈到了“红军贺电”一事:(1)史沫特莱把长征胜利事告诉鲁迅,并建议鲁迅去电祝贺。(2)鲁迅把此事告诉我,但那时电文未拟就。当时我有别约,时间已到,未及详谈,只说电报如何拍出去。鲁迅说,这就要史沫特莱办了。(3)此后,因为忙于别的事,跟鲁迅相见时……就没有再问鲁迅电贺的事,鲁迅也未提。遇见史沫特莱时,也没有谈及此事。(4)进入1936年,当前要做的事更多了,我把电贺事完全忘了,鲁迅似乎也忘了,都没有再提。(5)解放后,成立鲁迅博物馆,预展时,我看到有一幅画是我与鲁迅在拟电文(贺长征胜利),大为惊异,当即告诉他们,事实不是两人合拟而是鲁迅一人拟的,且我那时未见电文原稿,也不知有哪些人(除鲁迅外) 在电尾署名。(6)当时鲁迅博物馆拿不出电文全稿或其抄件,只说是解放前某根据地的报上(似是《晋冀察日报》) 载的一条消息有此一句——即1976年版《鲁迅书信集》上所载的。⑺史沫特莱如何转发此电,史沫特莱回忆录未谈及,且根本未提及她建议鲁迅发电事。所谓从巴黎转云云,都是解放后知有此事者的猜想……只能猜想史把电文弄到巴黎,然后由巴黎法共转到莫斯科,最后再转到陕北。

1933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时, 鲁迅(右一)、 林语堂、 伊罗生、 蔡元培、 宋庆龄、 萧伯纳、 史沫特莱(左一) 等委员合影
1977年6月,茅盾在回复南京大学教授叶子铭的信中写道:“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国民党还封锁消息,但在上海之国际友人却已知之。史沫特莱告诉了鲁迅,并建议发电致贺。我未见该电原文,但知甚短,且交由史沫特莱设法拍出,史用什么方法拍出,我不知道……现在流行一说,谓史将此电原文邮寄巴黎,再转陕北;此乃猜测,但比较合乎情理。最糟者,现在没有人曾见到此电全文,只留下那一句而已。而此一句的出处则在晋冀鲁豫《解放日报》,时为抗战初年。”
从回复的各类信件看,茅盾也始终是将致贺的“文件”当作“电文”来看,虽然前后说法有一些差异,如说电文“几分钟就办完了”,又说“电文未拟就”等,但总体是清晰肯定的。为什么茅盾对“电文”二字有如此之深的印象呢?
第一,鲁迅转述史沫特莱的话(红军长征已抵达陕北) 给了茅盾明确信息,一是“长征”,二是“陕北”;第二,鲁迅说“拍电文”“电文不用长,简短几句就行” (“简短几句就行”与“只留下那一句”,从电报行文及内容来看比较吻合),而茅盾回复的信息也是“电报”“贺电”用词;第三,1936年过完“春节”后的某一天,茅盾还在忙着“拜年”,说明“年”还没过完(查1936年春节为公历1月24日),红军东征行动尚未开始;第四,茅盾特别说明电报是“祝贺长征胜利”“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师”,指的就是“长征”。
当时的情况,是红军到达陕北后,“国民党还封锁消息”,但史沫特莱作为国际友人,她在法租界信箱里(或许还有别的渠道)或许会得到相关的消息,但她收到的“消息”恐怕已经严重滞后,而转到鲁迅那里可能又延迟了一段时间,直至1936年的春节。
史沫特莱建议鲁迅发电报祝贺,鲁迅有没有拟电文?这一点和茅盾的回忆是有一些小出入的,但他始终未见电文内容,则说明鲁迅“拟”或“没拟”两种可能性都存在。由于茅盾是“当事人”之一,鲁迅若拟“电文” (可能性大),应该会与茅盾商量,至少让茅盾知道电文的内容,因为那段时间他们经常见面。或者鲁迅自己拟就,署上茅盾名字,交由史沫特莱处理,却未告知茅盾,这也有可能,因为他事前已经跟茅盾打过了招呼。当然,如果鲁迅未拟“电文”(可能性小),也就无从告诉茅盾,所谓的“未见电文原稿”只能是茅盾一方“想象”。最后“电文”是如何到达陕北的?茅盾认为通过巴黎转陕北的可能性较大。从茅盾后来回忆时的叙述语气看,“贺电”一事极其普通,哪有现在看得那么“崇高”与“神圣”,而且竟成了一大“疑案”。
“长征”还是“东征”
“长征” 的指向性更大些
1947年7月27日出版的太行版《新华日报》,从第五版到第六版刊载“本报资料室”编写的《从红军到人民解放军英勇斗争二十年——一九二七、八、一至一九四七、七大事年记》。“大事年记”1万余字,分为9个部分。其中第四部分是“为实现抗日而奋斗”。这一部分开头称:“一九三六、二、二十:红军东渡黄河,抗日讨逆,这一行动得到全国广大群众的拥护,鲁迅先生曾写信庆贺红军,说:‘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新华日报》是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不是茅盾所说的《解放日报》。这里的“曾”,既可以说是祝贺红军“长征”,也可以说是祝贺红军“东征”,但“长征”的指向性更大些。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10月28日,《红色中华》在出版追悼鲁迅专版时,刊登了来信中“英勇的红军将领们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的更大胜利。全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热烈的拥护和欢迎!”一段,并注明“摘鲁迅来信”,即刊于1936年4月17日《斗争》上的信件的“第三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出版的《鲁迅书信集》,刊载了鲁迅贺电的一句话,“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并注明“此件为鲁迅获悉中国工农红军经过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发的贺电,是通过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发出的,时间大约1935年11月间”。电文正是根据太行版的《新华日报》所转引。
鲁迅研究专家林志浩的《鲁迅传》于1981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是改革开放时期最早的一部鲁迅传记。该书也提到了“贺电”一事:“这一年(1935年)十月,红军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克服无数艰难险阻,胜利地到达陕北。当鲁迅于翌年二月得知这个消息时,他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请史沫特莱托人转道巴黎致电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热烈祝贺这个伟大胜利。”同时,他也摘引了《斗争》 的“第三段”,以及太行版《新华日报》 “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一句话,并注明该资料载1936年10月28日陕北出版的《红色中华》,转引自1979年6月9日《人民日报》 上面刊载的中央党校教授唐天然的《新发现的鲁迅佚文》文章,这篇文章把发现的“佚文”认定为“长征贺电”。
由于“新发现”的“第三段”系悼念鲁迅的文字,且先于1995年发现的《斗争》 机关报第95期“东征贺信”,所以被认定为“长征贺电”也是很自然的。
如果是这样,这段文字形成的时间就要早于“3月29日”的“东征贺信”,至少是在茅盾所说的1936年“春节”这个时段。茅盾一再说他“未见该电原文”,这段“文字”是不是就是茅盾“未见”的“原文”呢?茅盾还说虽然他未见原文,“但知甚短”,“最糟者,现在没有人曾见到此电全文,只留下那一句而已”。“那一句”就是“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所以这“最糟者”又让人觉得“但知甚短”背后的意思,有可能指的就是这“第三段”的“甚短”的文字。

1979年6月9日, 《人民日报》 发表唐天然文章《新发现的鲁迅佚文》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悼念鲁迅”的文字是从《斗争》“东征贺信”中摘引而来,作为“长征贺电”使用的。
这里有一个疑问,如果这“第三段”早于“东征贺信”,那就说明它很可能是另一种形式的存在,即红军“长征贺电”。
把“东征贺信” 当作“长征贺信” 也未尝不可
作为“当事人”,茅盾自始至终认定这是一份祝贺红军的“长征贺电”。1963年他在答复信件里就特别指出“与陕北红军会师”,否认可能的“东征贺信”。学术界一般认为,红军长征作为震惊中外的大事件,鲁迅、茅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通过国际友人史沫特莱发去“贺电”,指向性非常清楚——“长征”。但在国统区的上海,这样一份“贺电”,必须要用特殊的办法来处理。这种“特殊”带着“神秘”,以至于“处理”之后,大家不再提起。1956年,茅盾在收到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中国美术学院)的一幅预展的鲁迅与茅盾在拟电文(贺长征胜利) 的画作时说:“我是反对把我和鲁迅画在一起的,因为我不配和他画在一起。这是纪念鲁迅的画,不应当给人们一个不相称的印象。因此,我认为如果要用这个题材,只画鲁迅一人也就可以了,或者另外找一题材。”“长征贺电”“特殊”,茅盾更是“低调”到不愿提及自己。1936年初,茅盾要处理的事情很多,比如“左联”解散问题,成立“文艺家协会”问题,茅盾都直接参与,“贺电”不过是一件“小插曲”,茅盾的回忆录也是在章节的最后才附带了一段文字。
1936年4月17日《斗争》上的“贺信”,提到了红军东进且在山西获胜的消息,应该说这是一份没有疑义的“东征贺信”,但为什么到了冯雪峰那里却成了“长征贺电”?是口误,还是叫法上的“约定俗成”?史学界一般认为,“长征”是一个事件,也是一个概念。作为“概念”,它有一个界定,即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这个阶段包括东征在内等都属于长征范畴,正如一些学者所称的具有“泛指性”“宏观性”一样。“长征”一词最早出现于1935年2月23日红军总政治部于贵州发布的《告工农劳苦群众书》:“我工农红军从江西转移作战地区,长征到川贵边地域……”朱德于1935年5月22日在冕宁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 称:“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1935年12月,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将“长征”比作“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从词性看,它虽具象却宏阔气壮。因此把“东征贺信”当作“长征贺信”也未尝不可。冯雪峰“说法”的“出入”,在于其“宏观”所指。
“东征贺信” 的发现并不能证明“长征贺电” 不存在
如果是这样,茅盾所说的“长征贺电”是不是也不能排除指的就是这份“东征贺信”?从时间点来说,虽然与1936年1月下旬的春节相隔甚长,但都属于“宏观”范畴。

茅盾
不过,在“时间点”上,一些学者还是作了区分,将茅盾所说的“长征贺电”认定为“东征贺信”,且举相关例证——
博古在《红军在山西》 (刊于1936年4月20日出版的《斗争》第96期)中引用“贺信”中“第三段”文字。
杨尚昆的记录是:1936年5月5日东征红军回师陕北,中共中央于5月8日在延川交口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作《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 的报告,指出,“东征动员了全国,鲁迅、茅盾等都公开拥护”。
1936年5月20日,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12人联名发给正在长征途中的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并转各负责同志的内部长电中,提到鲁迅、茅盾的来信:“红军的东征,引起了华北、华中民众的狂热赞助,上海许多抗日团体及鲁迅、茅盾、宋庆龄、覃振等均有来信,表示拥护党与苏维埃中央的主张。”
杨尚昆于1936年7月24日写的《前进!向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前进——纪念1936年的“八一”》一文中,也引用了“贺信”中的“第三段”文字。
认定鲁迅、茅盾的“长征贺电”就是这份“东征贺信”,只是“时间点”往后挪移,至于“贺信”怎么形成的,如何到达陕北中央,是否如茅盾所说,则需再作推考。
这些“摘引”,将茅盾所说的“长征贺电”置于“宏观”下的“东征贺信”予以确认,从而厘正茅盾的“说法”,但这是否就符合“当事人”茅盾真正的本意?因此,有学者坚持认为“长征贺电”存在的可能性,否则如何理解茅盾说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师”?如何理解鲁迅与茅盾的“楼梯说”?又如何理解新中国成立后最早披露且多次谈到鲁茅“长征贺电”的“相关人”冯雪峰说的“转转折折地送去一个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庆祝胜利的电报”?并且这“转转折折”用茅盾的话说花了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东征贺信”的发现并不能证明“长征贺电”不存在。
仔细分析茅盾不同阶段的回忆,把握其“长征贺电”的措辞表述非常重要,而围绕该电所言及的时间、地点、内容、转递……尽管略有差异,但已经相当审慎,保持了逻辑的一致性。同时,茅盾又是将其视作寻常往事,答问朴实。茅盾甚至不愿谈及他与鲁迅的“联名”,含蓄内蕴中有“淡化”处理的意味,透出他对鲁迅的另一种尊重,反而增加了可信度。由于未见电文内容,“结果”成“谜”,但经他呈现的事实“过程”,却让人们对“结果”抱怀信心。这份“长征贺电”存在的可能性很大,继续寻找和发现,仍是史学工作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