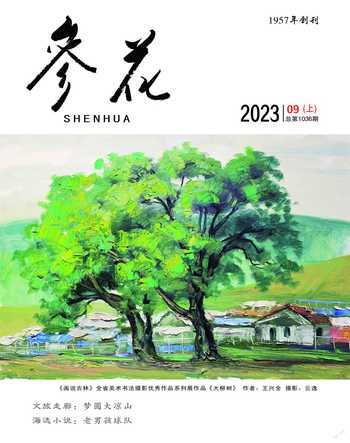给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曾经围绕在身边的幸福,突然之间就变得遥不可及。当我不再“嗯嗯”着,以应付的态度听妈妈讲那些过去的事情,当我开始主动奉上一双倾听的耳朵时,却再也听不到妈妈讲那些过去的事情。
头天晚上还伫立于阳台目送我离开、叮嘱我慢点的妈妈,第二天就不能和我说话。二十七天后,妈妈离去,撇下我,一头扎进与她相处的那条时光之河,终日洄游、浸泡,深深地拥抱并亲吻每一朵水花,每一层浪。
能够记起最初的浪花,是拍打在很多年前的糖果厂里。那时候,云朵宛若白莲花,一阵阵快乐的歌声被晚风吹来,没有高高的谷堆,即便有,我也不会坐在旁边,抱着腿或托着腮,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天上都是脚印”“满世界瞎跑的顽童”“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这些从前的事情,只能化作催眠的曲子。
那只黄黑相间的母鸡,是学生时代听来的故事,青春的记忆中,为此多了一丝温馨。
“六八年去云南探亲,一长排房子,晚上就我一个人,怕得很,我就去市场上买了个母鸡给我搭伴儿。是个黄母鸡,杂了些黑色羽毛。”
“爸爸到哪儿去了?”
“出任务去了。”
出什么任务?为什么天天晚上出任务?这些问题我好像都没问过,我更感兴趣的,是那只黄里夹杂着黑羽的母鸡。
“那个鸡乖得很!”妈妈的眼眸已然又见到陪了她半年的那只鸡,一个“很”字,加重了语气,很响亮。“每天都要生个蛋,热乎乎的。一唤它就咯咯咯地过来了,不喂它吃的就不走,挨着我,听我说话,真的像听得懂我的话一样,有时候站着,有时候趴着。晚上想着它也在屋里,在我身边,心里就踏实些了,也没那么怕了。”
而那条蛇,是我所聽次数最多、也听得最认真的,是妈妈二〇一五年讲给我的。她说着她早逝的妈妈,说着静静伏在她脚边的那条蛇。那时候,不到十一岁的妈妈辍学了,一个人在灶前煮饭时,翻看着她妈妈给买的连环画——《大闹天宫》。家中仅有的两本连环画,都是她妈妈买给她的,一本是一次期末考试得了第一名,一本是她十岁生日的时候。锅里的稀饭咕噜噜地唱着曲子,这时候,稀饭溢出来了,这才回过神来,刚一站起,便“妈妈呀!妈妈呀!”地喊起来。
蛇,花花绿绿的,是菜花蛇吧。它正安安静静地盘在妈妈脚边,与一只跟随了主人很多年的猫狗无异。这蛇,仿佛是走累了进来歇歇脚的,又仿佛是交情极深的老朋友,不拘礼节地来串门子。是什么时候来的?又是怎么来到脚边的?妈妈一无所知,她一边往门外跑一边扯开喉咙喊刘婆婆。刘婆婆是妈妈的邻居,我的外婆去世后,刘婆婆就让妈妈晚上去她那儿,和她睡一床。
“英儿崽,做啥子,做啥子?”刘婆婆点着个粽子小脚,快步走了过来。
妈妈也不说话,只把脸侧一边去,指着小凳子脚边那条并不因为她的惊慌而失措的蛇。刘婆婆拍着妈妈的肩,说,“莫怕莫怕!英儿崽,这个蛇就来看一下你乖不乖。”
年少的妈妈相信刘婆婆的话。
我打算把妈妈的这段童年经历写成小说,我一次次把问号抛给妈妈。比如我问妈妈,刘婆婆见到那条蛇的时候怕不怕?妈妈毋庸置疑地告诉我,不消说,肯定怕。虽然她已经记不得了。妈妈性格外向,爱说爱笑,上了点年纪后,越发爱唠叨,说过的事情可以重复若干遍。谁知道几年前,妈妈忽然变得不爱说话,老是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沉着脸,半天不吐一字,见到熟人,且不说像往日那样热情似火,连打个招呼点个头都一并省略。一家人赶紧带上她去医院探病。母亲渐渐恢复过来,但时好时坏,情绪高时不等人问就说起从前的事,情绪不好时怎么问也不搭理。而这一两年,记性越来越差,许多过去的事情,甚至转过眼的事情,都记不得了。阿尔茨海默病之先兆?立刻行动起来,网上、书里查资料,我按照网上教授的方法在母亲的大脚拇指上找穴位给她按摩,并瞪起一双极度感兴趣且没有表演成分的眼睛,缠着妈妈,鼓励妈妈,要她讲她曾经非常喜欢讲的那些事情。
可是,任凭我如何想听,她都只字不提。
吃饭的时候常常想起妈妈。最后一个上桌子的人是她,汤煮少了就坚持不喝的人,也是她。
掐菜的时候要说起妈妈。从前的蔬菜很少打药,自然虫子就多,尤其是藤藤菜。每当我见到虫子后,都会惊骇地扔下菜,高呼妈妈,但见妈妈微微一笑,身影一晃,便赤手擒得虫子,弃之。
妈妈的泰然自若,我女儿都记在日记里。诸如,徒手驱赶檐下蜘蛛、用拖布头追逐屋里盘旋的蝙蝠,脚踩粮食囤偷吃的老鼠等等。
妈妈离开后,再遇此类令人惊惧之物,仿佛只剩恐惧盘踞心底,再无指望了。
在妹妹家厨房里,她捯饬小龙虾,我拾掇西兰花,说起妈妈从容对付菜青虫的事。西兰花本是农民种来自家吃的,没打农药,菜青虫说着说着就来了,我一声尖叫,菜被扔到一边。妹妹用两张抽纸包住虫子,迅疾丢掉,然后继续择菜。我才明白,原来怯懦是来自依靠。
女儿放假在家,我与她在一起的时间最多。看电视的时候想起妈妈。无论电影还是电视剧,母亲最常问的一句话就是,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若是体育栏目里出现了易建联,她便会抬手一指,“嘿,易建联,真的好高。”妈妈姓易,因此一看见姓易的人就觉得特别亲切,没看过《品三国》,但知道易中天。
妈妈走了之后,我开始和爸爸聊天,她那些自编自创的故事在爸爸这儿都有了完整的结局。年轻时,父亲不在身边,她把自己内心的苦编织成一个又一个美丽的故事。黑黄母鸡是他,送票员是他,雨中送伞的也是他。我们说着妈妈从前的那些事情,仅仅是说给我们自己听吗?当然不是。
出了父亲的房屋,我仰望湛蓝的天空,看见白莲花般的云朵里仿佛有千千万万个故事穿行,一会变换成母鸡,一会变成人,一会化成伞。
作者简介:杨莙,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重庆市作协全委会委员,作品见于《解放军文艺》《星火》《散文选刊》《散文百家》《青年作家》等刊物。
(责任编辑 肖亮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