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学》70年:文学是人学
宋春丹
在上海巨鹿路675号的外墙上,挂着“上海市作家协会”“收获”“上海文学”“萌芽”几块招牌。其中,《上海文学》作为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创刊最早的综合性文艺刊物,今年迎来了70周年华诞。
在《上海文学》的编辑部里,有一把做工考究的西式扶手靠背椅,迄今已走过近百年历史。自创刊以来,巴金、靳以、魏金枝、钟望阳、茹志鹃、李子云、周介人等前辈都在这把椅子上坐过,率领《上海文学》走过当代文学史的每个阶段,见证了新中国文学变迁的风风雨雨。
《文艺月报》时代
《上海文学》的历史,始于1953年1月创刊的《文艺月报》。
1952年,华东文联和上海文联在巨鹿路675号合署办公。下半年,巴金、黄源、唐弢、王西彦、石灵、刘雪苇、靳以、赖少其、魏金枝九人组成编委会,开始筹备机关文艺刊物《文艺月报》。巴金任主编,但不负责具体工作,黄源、刘雪苇、唐弢任副主编。九位编委都是20世纪30年代成名的青年作家,多数编过同人刊物。他们当年都是“鲁迅身边的青年作家”,“文艺月报”四字就是经刘雪苇提议从鲁迅书法中集字而来。
《文艺月报》自创刊后就有强烈的同人色彩。“编者的话”表示,要以反映人民的斗争生活和推动各地的文藝工作为方针,同时认为,除一些政策性文章外,其它文章所言并不都是结论,提倡让不同的意见都有充分发表的机会,互相商榷,互相探究,以达到正确的结论。对这些多少有些“异端”的理念,《文艺月报》采取“迂回”策略,在表现形式上力求委婉。
初期的《文艺月报》生气勃勃,陆续刊发了巴金的《坚强战士》、师陀的《前进曲》、卞之琳的《采菱》等老作家作品,也推出了王安友的《追肥》、陈登科的《离乡》、高晓声的《解约》、昌耀的《诗两首》等新人新作。
在圈内看来,《文艺月报》对外严,对内宽;对新严,对老宽。在一次编辑部会议上,有编辑提出某位老作家的作品描写了大量生活琐事,显示不出主题思想,一位编委举出别林斯基的话加以反驳:“只有描写日常生活的才是天才,追求轰轰烈烈斗争场面的是庸才。”
《文艺月报》自创刊伊始,就存在所谓的“胡风派”与“周扬派”一说。主编巴金和第一副主编黄源都鲜少介入编辑事务,编委中的真正主事者是副主编刘雪苇和唐弢,其中实际主持工作的刘雪苇得到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彭柏山支持,唐弢则受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夏衍支持。早在30年代,夏衍和周扬就名列“四条汉子”之中,而刘雪苇、彭柏山则一直得到鲁迅和胡风的帮助,与胡风素有私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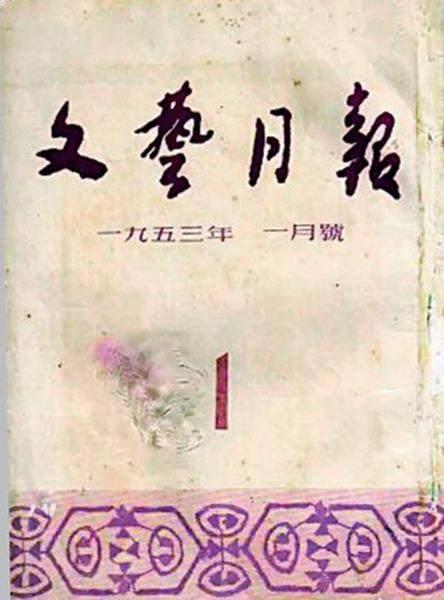
1953年1月,《文艺月报》创刊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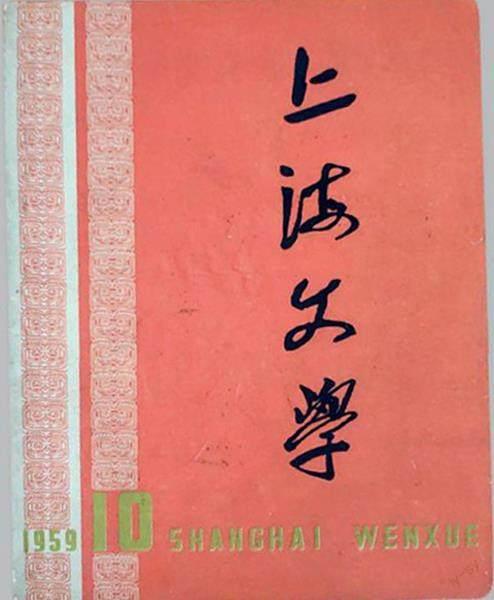
1959年10月,《文艺月报》更名为《上海文学》。
不久,刘雪苇不再兼任《文艺月报》副主编,唐弢成为实际负责人。1953年12月,上海作协第七次主席团会议决定改组《文艺月报》编委会,由巴金、唐弢、靳以、魏金枝、王若望、王元化、叶以群、孔罗荪八人组成新的编委会,刘雪苇不再担任编委。
刘雪苇性格强势,敢于任事;而唐弢则缺少革命资历,性格圆融。1955年刘雪苇被牵涉进“胡风案”中,被列为该案的第二号人物,蒙冤24年,直到1980年才获平反。
经过这些变化,《文艺月报》的同人色彩逐渐淡化。1954年底,《文艺月报》展开自我批判,检讨报纸不恰当地去追求艺术的“完美”,而忽视了生活里天天在茁壮成长的、来自群众的新生力量。
1957年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文艺理论家钱谷融写出了长篇论文《论“文学是人学”》。 当时苏联《文学原理》认为:“人的描写是艺术家反映整体现实所使用的工具。”钱谷融则提出,文学当然能够而且也必须反映现实,但反对把反映现实当作文学直接的、首要的任务,尤其反对把描写人仅仅当作是反映现实的一种工具、一种手段,否则其结果就是,“那被当作反映现实的工具的人,却真正成了一把毫无灵性的工具,丝毫也引不起人的兴趣了”。这篇文章成为大力提倡“双百”方针期间影响最大的文学评论文章之一。
《文艺月报》理论组组长傅艾以曾回忆,当时编辑部认为这是一篇很有理论价值但有可能招来非议的文章。唐弢一贯谨慎,他估计到可能产生的后果,在文章发表之前让编委们传阅,又派人去与作者沟通,并将文章打印50份,分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有关领导以及一些著名文艺理论家和教授审阅。各方反馈不一,但无一人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最终,文章发表在1957年5月的《文艺月报》上。
此时恰逢“反右”运动前夕。很快,《文汇报》率先发表批评文章,更广泛的批评随之而来,还专门集结出版了《<论“文学是人学”>批判集》(第一集)。《文艺月报》观望了两个月之后,在8月号上发表了吴调公的《论“文学”与人道主义》,在9月号发表罗竹风的《人道主义可以说明一切吗?》。两篇文章基本没有超出学术争鸣范围,在版面处理上也与其他刊物不同。此后,《文艺月报》没有再发表批判《论“文学是人学”》的来稿。
傅艾以曾说,唐弢文风酷似鲁迅,为人处世亦都处处以鲁迅为楷模。鲁迅好友沈尹默多次讲过:“鲁迅深于世故,妙于应付,也同他所擅长的古文词一样,为当时士大夫之流所望尘莫及。”钱谷融幸免于难,没被打成“右派”,除诸多因素之外,与唐弢在发文前采取了一些措施、特别是广泛征求了各方面意见也有一定关系。
几度易名
“大跃进”之后,读者开始厌倦假大空的文艺作品。同时《文艺月报》常被读者误以为是文艺报纸,发行量大减。编委会研究决定,《文艺月报》的内容和刊名都要作出更改。
1959年10月,《文艺月报》更名为《上海文学》,定位为全国性大型综合性文学月刊,以创作为主,面向全国,突出上海特色。《文艺月报》在创办了6年9个月、出版了81期之后画上句号。
1964年1月,《上海文学》又改名为《收获》。
早在1957年,刘白羽、邵荃麟、巴金、靳以等创办了新中国第一本大型文学杂志《收获》,巴金和靳以担任主编。该刊受到“同人刊物”“独立王国”的批评,又受到经济困难形势的影响,于1960年停刊。因此《上海文学》改名为《收获》后,人们称它为“新收获”或“小收获”。
“新收获”期号重新起算,标为“总第1期”,发表了《毛泽东诗词十七首》、浩然的《艳阳天》、乌兰巴干的《燎原烈火》、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等作品,但仅坚持了两年、出了14期,便于1966年5月被勒令停刊,编辑部成员相继下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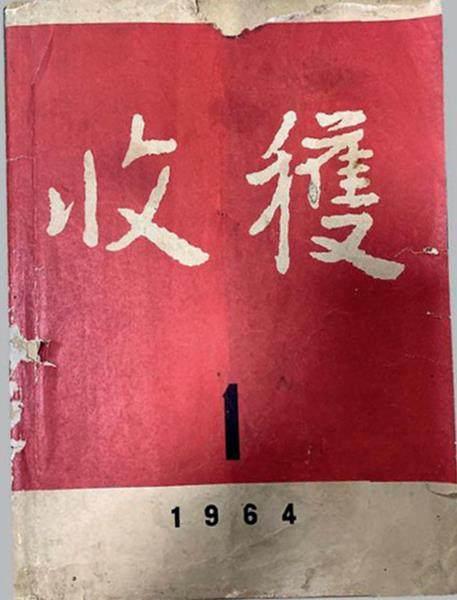
1964年1月,《上海文学》更名为《收获》。

1977年10月,《上海文学》复刊,刊名为《上海文艺》。

1979年1月,《上海文艺》改回原名《上海文学》。
1977年10月,《上海文学》在沪上老牌文学刊物中率先复刊,主编仍是巴金。彼时“四人帮”的影响尚未肃清,《上海文学》的编辑们认为旧刊名存在风险,反复讨论后定刊名为《上海文艺》,发刊词称:“鼓励艺术上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提倡艺术上不同见解的自由争论。我们首先要求作者创作出反映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作品来。”
1979年1月,《上海文艺》改回原名《上海文学》,沿用至今。
黄金岁月
编辑彭新琪曾回忆,《上海文学》一复刊就恢复了活力。编辑部很注意培养上海的青年文学力量,花了大量心血培养扶持作家,经常组织作者采风,安排每月一次的文学交流活动。编辑部还编了一份《写作参考》,用于和文学爱好者交流。
1982年初冬,在上海一家工厂工作的蔡翔向《上海文学》投了一篇稿,应邀去编辑部面谈。第一次去,他在上海作协三楼304室见到了年轻清瘦、朝气蓬勃的理论组组长周介人。第二次去,见到了副主编李子云。李子云五十岁出头,衣着清爽,一口京腔,正半倚在黑色牛皮沙发上看稿,在蔡翔看来连抽烟的姿势都有一种从容不迫的优雅。
李子云曾长期担任夏衍的秘书,她待人真诚,说话耿直,与钱谷融是至交。她是一个很有见地的文学评论家,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在全国文学界都有很大影响力,培养了陈思和、王小明、陈德培等一批文艺评论家。
有时候,蔡翔觉得李子云有点过于“政治化”了,但后来他发觉这是她身上一种非常可贵的品格。李子云对编辑要求很严,极其厌恶以权谋私,她不反对编辑写作,但不同意编辑在自己刊物上发表文章。在80年代,她是写检查最多的人,而且写得乐乐呵呵,从不怨天尤人。这些都深刻影响了《上海文学》团队。
那时304室每天都很热闹,有时会看到王蒙、邓友梅、冯骥才、李陀、吴强、茹志鹃、王安忆这些知名作家,还有陈思和、王晓明、南帆、李劼、殷国明等一批优秀学者。经常有一些人被叫来改稿,如吴亮、王晓明、程德培、蔡翔等民间草根评论家,主持谈稿的通常是周介人。
冬日中午,很多人会到304室围炉取暖,在这里交流各种消息,分析形势,有时喜形于色,有时忧心忡忡。
作家陈村曾撰文写道,当时自己不认识任何文学界的人,是自发来稿作者,态度“嚣张”,更无送礼一说,尽管艺术见解有不同,但《上海文学》的编辑都很宽容,敬业爱才。
他回忆,于炳坤1979年因《两代人》成了他的第一位责编,于炳坤删稿时陈村坚决不肯,逐字逐句顶嘴,于炳坤删完了让他重抄一遍,他就把删了的又给抄回去。曹冠龙更是自己跑到印刷厂,理直气壮地把删掉的字句改回来。小说尚未发表,两人就以不肯改稿出了名。
李子云曾把陈村召去,想说服他把小说中过于消极的“苟活”一词改掉,陈村退让说改成“存活”,李子云和蔼地追问,为什么不能说“生活”? 陈村听说周介人删了他《蓝色》中的一句话,赶去把周介人从午休床上叫起来,说:“老周你太老了,根本不懂!”周介人经不住缠,只好把那句话勾了回来,要他文责自负。
有一段时间,陈村是在《上海文学》发表小说最多的上海作者,参加过编辑部组织的几乎所有笔会,获得三次小说奖。1985年,上海作协终于争取到五个专业作家名額,茹志鹃没有为自己的女儿王安忆争取,而是叮嘱陈村快办调动手续。有一两个月,陈村是上海唯一的专业作家。
这一阶段,《上海文学》出版了一批颇具影响的中篇小说,其中有池莉的《白云苍狗谣》、朱苏进的《金色叶片》、王安忆的《香港的情与爱》以及刘醒龙、张欣等人的作品。这些作家大多被视为九十年代文坛的中坚力量。
文学评论家吴亮曾回忆,1985年后文学期刊出版异常繁荣,他和程德培整天泡在作协图书室里,每个月的新期刊都会翻看,莫言、韩少功等会有什么作品出来,他们都能事先得到消息。
1990年12月,《上海文学》编辑姚育明到北京组稿,专门去拜访了作家史铁生。当时已是晚上十点半左右,史铁生刚从地坛回来,他们闲聊了一阵。直到临别时,姚育明本能地问了一句:“最近在搞什么呀?”史铁生似乎有话想说,迟疑了一下,最终说道:“嗯,算了,以后再说。”
姚育明没想到,回上海不久就接到史铁生寄来的一封厚厚的信,里面是稿件《我與地坛》,约15000字。当时《上海文学》发表的散文一般在六七千字,史铁生在信中问,稿子是不是太长了,对不对《上海文学》的路子。
姚育明读完激动万分,冲到副主编周介人办公室,近乎喊叫地对他说:“史铁生来稿了,写得实在太好了!”周介人看后也激动地说:“发,马上发!明年第一期。”
考虑到这期的小说分量还不够,缺少重点稿,周介人提议把《我与地坛》当小说来发表。他认为《我与地坛》内涵很丰富,结构也不单一,作为小说来发是成立的。但史铁生坚决不同意,说这就是散文,不能作为小说发,如果《上海文学》有难处,不发也行。
最终,《上海文学》定的栏目标题既不是小说也不是散文,而是“史铁生近作”,史铁生接受了。而这也引发了后续的《我与地坛》文体之辩。
《我与地坛》发表后,有读者说:1991年整个中国文坛没有文章,只有《我与地坛》立着。著名作家韩少功说:“我以为1991年的小说即使只有他一篇《我与地坛》,也完全可以说是丰年。”
文学批评重镇
李陀曾说,上海是80年代文学改革的主要策源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巴金在上海。1983年调入《上海文学》做理论编辑的蔡翔曾回忆,当时《上海文学》的理论版面非常活跃,经常组织重要的文学讨论,文学交流活动也很多。
即使在自己的黄金时期,《上海文学》的影响力也从来不如《收获》,更不如王蒙担任主编时期的《人民文学》。但《上海文学》更注重理论性,一度在体制中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在多个影响全国文艺理论发展的节点上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在很多这样的节点上都离不开李子云的作用。
1982年,作家冯骥才、李陀和刘心武曾以通信方式讨论“现代派”问题。“现代派”在当时属于敏感性问题,北京的文学刊物不愿意刊登,李陀等只好求助于上海,联系了李子云。这组通信如期发表于《上海文学》1982年第8期,三封信分别被命名为《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冯骥才给李陀的信》《“现代小说”不等于“现代派”——李陀给刘心武的信》和《需要冷静地思考——刘心武给冯骥才的信》。
这期刊物出厂当天,李子云早上刚到办公室就接到冯牧的电话,说目前该问题很敏感,集中讨论会引起麻烦,要她撤掉这组文章,但李子云认为讨论一下不要紧。冯牧说:“你知道吗?一只老鼠屎要坏一锅粥。”李子云说,我这老鼠屎还没有这能耐坏一锅粥吧。她说:“你管不着我,有市委管我。”
此后几年,冯牧不再理李子云,两人见面也不说话。后来李子云才知道这不是冯牧的意见,冯牧打电话来是为了帮她。为此,她在《我经历的那些人和事》一书后记中专门向冯牧道了歉。
1984年12月,上海作协和《上海文学》负责人茹志鹃、李子云、周介人在杭州策划举行了小范围的“新时期文学:回顾与预测”座谈会,再次当了排头兵。
参加这次会议的作家有茹志鹃、李陀、郑万隆、阿城、陈建功、韩少功、陈村、李杭育等十几位。与会的十几位评论家中,来自上海的就占了六位,分别是吴亮、程德培、陈思和、许子东、蔡翔和南帆。
会上讨论了阿城刚在《上海文学》发表的小说《棋王》。韩少功听了两天会,一直沉默不语,只是说回去要弄点东西。第二年,他发表了文章《文学的“根”》,“寻根文学”于是被命名。此后几年,《上海文学》成为寻根文学的一个重要基地。
“杭州会议”不仅影响了当代小说走向,也使吴亮、许子东、蔡翔、程德培、殷国明等“上海批评圈”中一批先锋青年评论家崛起,引领了“85新潮”,成了“北京批评圈”之外一股引导文学发展的力量。
其中,吴亮和程德培都是没进过大学的工人业余作者,由于勤写评论文章受到李子云和周介人的注意,破格调入上海市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开始了职业批评家的生涯。吴亮曾说,《上海文学》推出了一大批年轻批评家,到1985年以后,他们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很多杂志都在争夺他们的文章,就像现在画廊都在抢那些出了名的画家一样。
而后,《上海文学》又在1985年第2期刊发了载入当代文学史的《冈底斯的诱惑》。作者马原一举成名,先锋小说也名噪一时。
80年代中期,周介人开始全面主持《上海文学》工作。他的日常工作逐渐“务实”,为了解决办刊费用而与企业家来往密切。蔡翔曾说,这无论对周介人还是对他们都是一个必要的过渡阶段,使得他们从80年代早期的某种个人幻觉中走出,进入真实的中国社会。
1998年,周介人因病去世,蔡翔接任《上海文学》执行主编。他在2000年1月号“编者的话”中表示,杂志仍将延续以往的严肃风格,拒绝媚俗,“让真正的思想和艺术在这里生长,叙述一个真实的中国,一个真实的世界”。
2003年4月,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接到上海市作协党组邀请,请他出任《上海文学》主编。
陈思和回忆,那时杂志陷入困境,欠了半年工资,主编辞职去大学当教授了。大约是为了平衡,就把他这个外来的和尚请去了。当时他周围的人都不赞成他去当主编,有的是担心他的身体,有的觉得这是是非之地。但他自己从90年代起一直在思考市场经济时代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发挥其作用,觉得这个职位能兼顾他感兴趣的教育、出版和人文学术思想传播,三位一体,构成了知识分子的理想岗位,于是最终决定接受这一职务,去牛刀小试。
上海文学批评界占据全国半壁江山,80年代陈思和等人的学术文章都是在《上海文学》上发表的,但90年代后上海批评家在本地找不到一家可以大量发表评论文章的杂志。有人认为理论文章过多会影响读者面,但陈思和认为理论文章绝不应退出《上海文学》,这是这本刊物的传统和责任。
与陈思和同一时期,上海作家赵丽宏出任了《上海文学》杂志社社长。
1978年时赵丽宏还是华东师大中文系学生,给刚复刊不久的《上海文学》投寄了稿件。有一天,他收到编辑赵自的信,约他到编辑部谈谈。赵自是老资格的编辑,文学生涯开始于上世纪40年代,当年是地下党,老革命。他的信是用毛笔写在宣纸信笺上的,很郑重也很讲究。赵丽宏带着赵自的信,第一次走进了《上海文学》编辑部。当时赵自就坐在那把已有近百年历史的西式靠背椅上,后来这把椅子一直在赵丽宏的办公室里。
赵丽宏刚接任社长时正逢杂志50周年社庆,他请自己尊敬的老师钱谷融为《上海文学》题字。虽然历经磨难,但钱谷融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观点,不说违心的话,写不愿意写的文章。在赵丽宏看来,这个名字是华东师大和上海文学界的骄傲,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
钱谷融用毛笔题写了五个大字:“文学是人学。”这幅字端庄有力,在赵丽宏担任《上海文学》社长的18年间,一直挂在他的办公室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