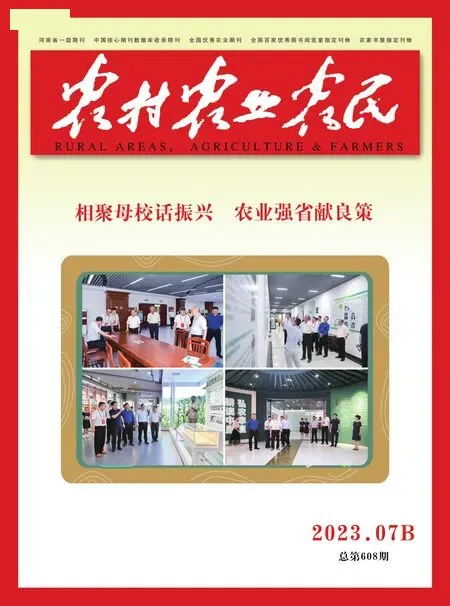日本综合农协的发展经验借鉴
——基于系统的视角
刘 风,段佳依
(河南农业大学文法学院)
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指出,要“建立健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政策体系,促进要素更多向乡村流动,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工作是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因此,畅通城乡间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就成为较关键的环节。农民合作社以其专业化、社会化的服务,为实现农民现代化、构建现代化农业生产方式提供专业的平台,在促进要素平等流动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农民合作社在改善传统的农业生产结构、提高农业生产的附加值和总产值方面提供直接支持,在改善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农民对日常生活产品的消费能力方面积累相应的财富资本。农民合作社能够改变传统的由城市向农村单向的贸易流动,促进经济融合,缩小城乡发展差距,进而实现农业农民共同富裕。
近年来,关于农民合作社的性质、定位及发展走向等议题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基于相似的阶段性发展特征,日本综合农协为中国农民合作社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日本国土面积小,人口密度大,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耕地少。日本的农业发展是典型的小农模式,以分散的单个农户经营单位为主要特征,缺乏有效支撑现代化农业发展的条件。日本综合农协是在经历明治维新之后逐步发展起来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农民进行农业现代化生产,提供纵向一体化的服务。日本综合农协的贡献在于缩小了日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维护了农民的根本利益,激发了农民的主体性,有效实现了城乡协调发展,这为中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经验借鉴。因此,借鉴日本综合农协的运作模式,推动中国农民合作社的国际化发展路径,为推进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乡村振兴进程、形塑农民的主体性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本文重点关注日本综合农协内部的运营生态,基于日本综合农协在日本乡村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以系统理论为解释框架,在描述日本综合农协的运行生态的基础上,阐述农民合作社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系;以激发农民主体性为着眼点,激活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能动性,从而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服务。
二、农民的视角:日本综合农协的发展经验
受19 世纪末欧洲农业合作化的影响,日本建立起一套独特的合作社发展模式,其彻底组织化的程度在国际范围内领先,并发展出集信贷、互助保险、生产投入供应、加工、运输、日常需求等为一体的多功能农业合作社,是世界上较有效率的农业合作社。日本战后农业的迅速发展与经济崛起离不开综合农协的发展。农民的主体性是指农民有意识、有需求地投身于农业发展中,由被动转为主动,实现从“要我如此”到“我要如此”的转变,成为乡村振兴建设的主力。综合农协通过组织化的运转,实现农民、合作社、政府之间的耦合发展,从而在农业农村发展的基础上,有效激发农民主体性。
(一)组织体系系统:激发、增强与维护农民的主体性
日本综合农协通过内部的组织系统运转将农民联合起来,实现农民收入增加、农业产业兴旺、农村社会发展的目标。在综合农协中,由农民投票选出的董事会面向社会招募从事具体农业生产、加工、销售业务的专业人才,为农户提供专业咨询和指导,农民参与农业生产的能力得到提升,主体性受到激发。本着“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互助发展理念,综合农协调动农户们在参与农业农村生产建设事业当中互助合作,通过与相关精英和专业人士的有效互动,农民逐渐具备较强的自我选择意识和主体意识,主体性得到提升。综合农协的主要目的是改善农民生计,在最大限度地整合资源,推动乡村产业化、合作化纵深发展的过程中,农民的经济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主体性得到提升。同时,综合农协还经营着报刊信息、出版文化等事业,在政府与农民之间发挥着协调作用。一方面,它代表农民的利益,在具体的工作过程中将农民和农业农村发展的问题反映给政府,督促政府制定并出台更加符合农民实际利益的政策。另一方面,综合农协提供政策解读、政策宣传的渠道,让农民更加清晰地了解政府关于“三农”问题的动向,从而让政策更好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一协调功能的有效发挥为农民提供直接的话语平台,增强并维护了农民的话语权,进而提升了农民自主参与农业事务的积极性。
(二)制度设计系统:保障农民的主体性地位
综合农协的背后有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制度设计系统为农民主体性的发挥提供保障。第一,日本政府通过立法确定了综合农协在农业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并通过《农业协同组合法》规范综合农协组织各方主体的权责,指导综合农协开展具体农业生产业务的活动,确立起定期检查和监督机制,根据检查的结果汇集成事例集发布在农林水产省官网,供社会成员查阅。翔实的法律规范保障了综合农协功能的有效发挥,推动了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发展,为农民主体性的发挥提供物质保障。第二,由于小生产者本身具有脆弱性,应对风险的能力不足。为解决农业生产发展的融资贷款问题,政府提高了基层农协的存款利率,使其高于一般银行的利率,同时为农户提供贷款优惠。第三,日本政府还大力扶持农协发展共济事业,发挥社会保障在生产生活方面的风险保障作用,提升综合农协面临危机时的恢复力,使其得以有序协调发展和可持续运转。第四,政府依托其强制力,通过制度设计和政策实施使农协的销售在全国处于垄断地位。
(三)集体行动系统: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
综合农协搭建农户合作的平台,实现农户的联合,形成了集体化的社会行动系统。具体表现为在农业生产的经济场中,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经济体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单个小农难以应对市场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综合农协通过将小农组织联合起来,发挥着共同支撑的作用,实现风险的共担。一方面,组织内部的民主决策制(如一人一票)可以最大化地综合全体会员意见,实现农民集体行动。另一方面,综合农协依托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和经济辐射力,与农业生产链条的上游相关部门进行谈判,统一购进生产原料,降低农业生产的成本,统一的销售网络实现农业生产与市场经济活动的有效对接,充分的市场信息避免生产的盲目性和市场的自发性,提升农民参与经济生活的能力和信心,保证了农民的经济权益。农民实现增收,会进一步提升自己作为农业生产和收益的主体地位的认知。
在农业发展的社会场中,以合作社为基础开展的疾病预防措施活动、农业作业工伤预防措施工作、区域饮食文化传承健身活动等将农民的健康纳入综合农协的发展事业,保障了农民的劳动权益和农业劳动力的质量,激活了地方社区活力。此外,综合农协依托外延社会业务,利用介绍农业、食品以及环境等方法,帮助社会成员尤其是青少年群体进一步了解农业及其重要性,使农业发展问题成为社会共识,在获得认可和社会福利倾斜的过程中,农民的自我意识和主体认知获得显著提升。
在农业保障的政治场中,政策语境与实际情境之间的张力容易使政策失真,作为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合作化组织,综合农协代表农民的利益展开集体化的农民行动,可以高效地反映农民的需求,将在开展具体的业务时遇到的问题和农民的需求反馈给政府,以促使政府完善并出台相应的政策。经由组织化的运转,实现日本农民与政府双主体对接,农民直接表达诉求,主体角色由“场外人”转为“场内人”。
三、农民合作社的系统推进:中国农民主体性的形成逻辑
后脱贫时代,中国政府在消除绝对贫困以后,面临的任务是如何将防止返贫和乡村振兴进行有效衔接,从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日本综合农协的内部运作机制可以为中国组织小农户进行农业现代化社会生产、激发农民参与农业农村事务的积极性、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一定经验。
(一)制度供给:搭建农民合作化的框架
综观日本综合农协的发展,离不开日本政府的强力支持,政府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自上而下地推动综合农协在基层吸纳农户,使得综合农协汇聚了全国的农民及其亲属,零散的小农经过专业的组织化与社会化迅速与现代化农业接轨。
那么,中国如何形成农民的合力?关键是打造农民利益相关的共同基础。传统的乡村重视伦理关系,农民共享着统一的乡村文化。随着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乡流动二元结构的松动,农村人口大量外流,传统的乡村共同体式微,难以实现农户们的有效联合。只有搭建共同的利益关联机制才能将农民与农民、农民与村集体较好地整合在一起。而农村集体土地产权确立了农民的利益连接点,以此为基础展开的利益分配机制可以有效调动农民参与集体分配和再分配的动力。要妥善建立起农村集体利益支撑点,搭建相关的分配机制,才能有效实现农民主体性的回归。
(二)组织化协同:激发农民主体性的动力
从日本综合农协的发展经验可以看到,综合农协内部会员能够获得产前资金支持、产中技术支持、产后销售网络等一条龙服务。因此,妥善解决好农业发展的机械设备、基础设施、技术指导、销售网络、运输设备等需求,保障农民参与市场经济的权益不受损失,才能重塑农民的自我认知。因为日本综合农协组织化程度彻底,囊括了农业、渔业乃至第三产业的方方面面,有统一的生产和销售网络,实现了日本农产品自销率100%,提高了农民的经济收益。单个农户自身具备的资源有限,无法有效应对市场竞争带来的经济波动,只有将农民组织起来,才能提升农业发展的空间。国内应继续坚持并大力推进农业组织化、合作化发展,通过统一的销售网络,以销定产,实现生产与销售的有效对接,保证农业再生产的可持续发展。依托组织化的集体行动提升农民的话语权,真实反映农民的呼声,促使政府出台更加有益于农业农村发展的政策,使农民切实感受到自身的发展与政策紧密联系,转换“边缘人”的社会角色,塑造主体意识。
(三)专业力量介入:培育农民主体性的平台
受制于农村发展不充分、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民长期处于社会边缘,生存福利难以有效为继,导致其缺乏主体性。改革开放以来,城乡间社会流动频繁,农村土地闲置化、农村空巢化、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的问题日益突出。同时,自上而下制定的社会政策虽然秉持着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但面临基层农村社会的复杂情境,很容易出现推行乏力甚至走样的情况,农民的利益和基本权益很难得到有效维护。社会工作本质上是一种福利性的社会服务,作为独立于政府的第三方平台,秉持着助人自助、公平公正的价值观,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专业化的社会服务,通过嵌入乡村振兴的发展过程整合社会资源,对政府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宣传,为农民组织化发展链接社会生产、销售、专业技术以及政策支持等相关资源,开展具体的符合农民实际需求的社会服务,保证农民的基本权益,充分发挥政府反哺乡村政策资源的作用,对农民赋能。这就要求进一步在农村推进社会工作服务站建设工作;利用乡村资源大力推动乡村产业化发展,提升农村社区经济水平,从而吸引更多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投入乡村振兴中;政府根据实际情况适度提高一线社会工作者的薪酬待遇,使基层社会工作服务站留得住人才;大力发展农村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后备力量。
四、结论与反思
文章梳理了日本综合农协的运作模式,尝试为提升中国农民参与乡村振兴建设的主体性、释放乡村建设活力和乡村发展内生力提供思路。不可否认的是,日本综合农协也具有明显的不足之处。例如,日本综合农协成员的去农化、核心业务的市场化等发展趋向,使得综合农协对农民难以提供有效的服务。与此同时,日本综合农协以维护小农利益为由,固守垄断农业发展的政策,实际上已形成利益集团:以政治身份的优势迫使政府进行贸易保护,提高关税,再以垄断性地位售卖高价粮食盘剥国内消费者;反过来,为维护自身政治优势,日本综合农协还与执政党的利益相互勾连。因此,日本综合农协是否能继续代表农民的利益,提升农业从业者的收入,发展好日本本土农业生产是目前面临的重要问题。为此,我国在推行农民合作社发展时,需要妥善处理好农民合作社内部的利益联结机制,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共产党立场,才能真正实现农业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战略目标。因此,下一步的研究应该着重将日本综合农协的发展经验与教训同中国国内合作社具体发展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探索出中国农村发展的组织化之路,以期更好地激发农民的主体性,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专业化、组织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