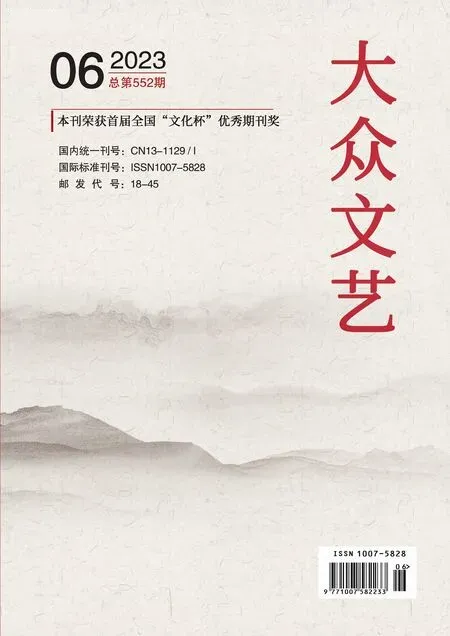《广岛之恋》:身体下的创伤叙事*
曹思思
(西安外国语大学欧洲学院,陕西西安 710128)
一、引言
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引发了人类对于理性与文明的思考,战争过后,人类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对人的境遇表现出空前的绝望与困惑。“新浪潮”(Nоuvеllе Nаguе)和“左岸派”(Rivе Gаuсhе)电影应运而出,他们背离传统电影的时间叙事模式,打破故事的时空线索,通过刻画非典型性人物的心理、呈现身体、画面重复与闪回、电影语言文学化等一系列手法,扩展电影的深度与广度,引发观众对人的处境的思考,《广岛之恋》正是这样一部代表之作。电影以丽娃的两段感情为线索,通过碎片化的呈现方式,充分展现了在二战法西斯战争的侵袭之下,身体在历史的进程中如何被残害,以及身体如何承载着创伤记忆。正如福柯所言,“身体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受到消耗、改造,欺凌、攫取,迁移,甚至是售卖、抵押等等,彻底沦为社会历史事件的烙印。”[1]《广岛之恋》中一副副因为战争而残缺变形的躯体恰如其分地体现了身体在战争中所遭受的深刻苦难,身体成了战争创伤的主体:在蘑菇云阴霾的笼罩下,太平洋里死去的鱼,城市里数以万计的畸形生物体,腐烂变质的食物,残缺的人体器官……这种惨烈的创伤通过电影画面的交错与丽娃重复性的叙述中不断震撼着观影者的心灵。本文将以身体为切入点,分析战争下饱受摧残的身体如何成为创伤叙事的载体。同时对电影所构建的创伤文化进行拆解,分析影片如何完整地呈现了创伤叙事,最后对电影隐藏在身体与创伤之下的深切愿景进行深入讨论。
二、身体:创伤叙事的主体
创伤叙事学认为,身体是创伤叙事的主体,在遭受创伤过后,患者会出现“失语症”“强迫性重复”、遗忘以压抑痛苦情感等一系列应激行为(即为创伤后应激障碍роst-trаumаtiс strеss disоrdеr)。有过创伤经历的“患者需要在帮助下重建一段叙事,或重建一段历史”[2]。比如在电影《广岛之恋》中,1944年德国士兵的死使丽娃处于失语状态,被关地下室8个月后的丽娃暂时压制了创伤记忆,开始了新的生活,但是战争所代表的创伤记忆并未就此消失,广岛与日本男人成为唤醒丽娃韦内尔记忆的引子,遗忘的记忆喷涌而出。
1.“失语症”与“强迫性重复”
德国士兵死去后,丽娃在尸体旁趴了一天一夜,她觉得浑身冰冷,仿佛已经死掉。被母亲带回家的她失去了身体某些器官的功能:她忘记了要如何言说,一语不发,只是不停地喊叫;她没有瞎,她仍旧在注视着,但她仿佛什么也没看见;她有耳朵,但是听不到,这种状态是典型的创伤后遗症。这种失语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对孩提时代的回归,出生的孩子并不具备说出话语的能力,对母体状态的渴望体现着受到创伤后对某种原始状态的回归。治疗好丽娃的疯狂的同样是孩子的到来,当她有了孩子以后,疯病也就不可避免的好了。在被拖去游街的时候,在围观的人群里她发出无声的叫喊,“这种叫喊从口型上来看像是在喊‘妈妈’这两个字”[3],这也是丽娃失语之前的最后一声呐喊。
同样,创伤叙事学认为,在遭受创伤以后,叙述者会出现“强迫性重复”(соmрulsivе rереtitiоn)行为,即“叙述者常常不由自主地重复某一段话、反复提到一个意象、一张图片乃至反复做出一个动作,企图由此化解创伤”[4]。影片当中丽娃不断提及内韦尔与广岛,德国男人与初恋经历,都是强迫性重复行为的体现。此外,除了人物叙事话语的重复,电影在表现人物创伤时同样是使用了这种重复性的展现手法。作为“左岸派”电影的代表之作,《广岛之恋》侧重的不是对故事情节的完整梳理,而是对人物心理的完美呈现,由此被称作是一种“表现内心的现实主义”[5]。在表现人物这种重叠错乱的心理状态时,电影画面的展现同样也采用了多重时空交叉出现的特殊手法,手、身体、房间、街道、河流、城市等画面在影片当中重复出现,电影画面就这样在内韦尔的花园、内韦尔的地窖、巴黎的街头、日本的广场、日本的旅馆之间来回切换。正是在这种人物、时空与事件的错位当中,观影者顺着一条条线索体验了法国女人的两段恋情,认识了内韦尔的广岛,广岛的内韦尔。
电影构建的正是两个重复性的空间与两段重叠的爱情故事:内韦尔与广岛相似的地理位置(都是河流穿过的城市)、德国士兵与日本男人相似的身份(两人都是二战时期的士兵,都属于法西斯阵营)、相似的追求人的方式(德国士兵跟踪丽娃以求芳心,日本男人同样如此)、相似的手……这些“巧合”为记忆的唤醒提供了可能,在日本男人这里,丽娃重复着那段未能完成的初恋。电影中出现了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重叠闪回画面:日本男人睡着时,手还在抖动着,德国男人临终时,手也在抖动着。抖动的手敲醒了记忆的门;德国情人的躯体与日本男人的躯体多次重合为一具,日本男人的手使得丽娃想起了德国男人,两人的手出奇的相像,在观察日本男人躯体的时候,德国士兵的身体不时出现在画面里,这躯体是一具濒临死亡的躯体,在烈日当头的河岸上,而房间里的光线则十分昏暗,日本男人躺在床上享受着爱欲过后的欢愉。一暗一明、一死一生、一悲一乐的对比,熟睡时轻微抖动的双手与临终前因痉挛而抖动的手,情感的张力由此体现。随着记忆越来越清晰地浮现,日本男人甚至直接化身成了德国士兵,他躺在床上与丽娃行使爱欲,在咖啡馆里引导着丽娃讲述过去的创伤,他成了在内韦尔与丽娃相爱的敌军、躺在河岸上的冰冷尸体。在这种重复之中,丽娃的内韦尔记忆被广岛完全唤醒,她的情感与欲望得到了复苏,并将其全部投注在这个日本男人身上。
2.遗忘与创伤治疗
创伤叙事学看来,遗忘是治疗创伤的重要手段之一。《广岛之恋》不仅是一部创伤的回忆史,更是一部回忆遗忘的历史。正如贝尔纳·班古为影片所做的结论:“某个人是怎样亲身体验‘忘却’的”。[6]遗忘是抵御创伤的手段,但是遗忘并非永恒的,被遗忘的记忆会通过各种方式重新回到主体身上。
丽娃并未在德国士兵死去以后选择殉情,她“错失”了这个为爱情而献出生命的大好时机,求生的欲望最终带领她走出创伤,甚至于让她逐渐遗忘了这段本不该被遗忘的感情,以至“从那时起直至今日,身在她遇到这个日本男人的广岛,她都犹如获准缓刑的人怀着‘淡淡的哀愁’,缅怀者那次决定命运的唯一机会”。[7]对丽娃而言,广岛的日本男人唤醒了她在内韦尔的痛苦记忆,播放广岛站到了的高音喇叭在内韦尔的画面上响起,内韦尔与广岛重合成为一个地点。她在广岛看到了一切,而这一切,关于蘑菇云、战争、民族残杀的一切罪恶记忆,在新的生活,在现代性建筑中被人慢慢遗忘了。
集体性的遗忘是不可抗拒的,关于遗忘的表现渗透在影片的方方面面,丽娃仿佛已经恢复了正常生活,结婚并孕有2个孩子;广岛如今高耸的现代化建筑、“因装有巨大的落地窗而显得很有美国特色”的咖啡馆[8]、日本男生所重复的那句在广岛人们什么也看不见。伤残的幸存者被集中管理起来了,街上人来人往,仿佛只有林立的创伤博物馆与激动的游行队伍还在记录着那些声势浩大的战争。遗忘本身是可耻的,幸存者为自己的遗忘感到羞愧,然而选择遗忘可以缓解创伤,只有渐渐遗忘,幸存者才能够逐渐走出悲伤,开始全新的生活。
然而,遗忘并非治疗创伤记忆的最佳手段。相反,对于创伤记忆的构建,才是抵御创伤的最佳手段。比如在电影中,人们建筑创伤博物馆,举行反对氢弹的示威游行,看望战后幸存者,拍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教育影片,等等一系列手段,都是为了避免遗忘。遗忘是注定的,注定遗忘的东西也将是永恒的,而对于创伤文化的构建能够从根本上抵御遗忘的侵袭。创伤文化的最后一环正是读者与观众。
三、观众:创伤叙事的最后一环
创伤叙事学认为,创伤的最后一环是读者与观众,“倾听者的在场对于创伤见证极其重要,见证正是由创伤幸存者的讲述和倾听者的参与而构成”。[9]作为创伤叙事的最后一环,电影《广岛之恋》呼唤读者进入创伤叙事,构建集体性的创伤文化。正是在倾听的过程中,内韦尔与广岛成为创伤叙事的焦点,按照创伤代际传播的模式,影片清晰地构建了一个关于战争的文化记忆。
历史创伤事件幸存者(第一代)——见证者(第二代)——倾听者(第三代)
文化记忆创伤代际传递的模式(转引自王欣 2013)
亲身经历战争中痛失爱人的丽娃成为二战欧洲战场历史创伤的第一代直接幸存者,战争埋葬了她的情感与记忆,留下了一具残缺的躯体。日本男人在窥探了丽娃的创伤记忆之后,成了法德之战与内韦尔记忆的第二代见证者。反之,广岛的日本男人在原子弹爆炸之际,因为参兵而躲过一劫,他是长崎、广岛蘑菇云笼罩下的幸存者,丽娃在广岛的各个地方寻找到了关于这场声势浩大的核武器灾难所遗留下的痕迹,她四次参观创伤博物馆:影片多次以丽娃的视角,展现了创伤重建后的广岛——躺在床上的身体残缺的幸存者、“新型”荒漠、蘑菇云爆炸后遗留下的各种物证、扭曲的钢筋、蜡制的被烧焦的人皮以及一对对烤煳了的头发……丽娃成了日本民族灾难的见证者。而在整个电影的观影过程中,观众成了第三代的倾听者,他们所倾听的并非一方的创伤记忆,而是男女双方,内韦尔-广岛、欧洲-亚洲、战争-和平等一系列的历史碎片。正是在整个创伤叙事的过程中,个人记忆通过三代传播机制,凝聚成为集体记忆,原初的历史创伤事件也随着记忆传递,被塑造成为文化记忆,创伤叙事的意义构建由此完成,而建立在集体创伤之上的,是对无意义的战争与虚伪的“民主政治”的控诉。
影片对战争的控诉并非单维的,而是通过塑造一个多维度的立体空间,跨越性别、国家和种族的障碍,将众多人物与事件整合在一个错位的时空体之中:德国士兵既是二战法西斯阵营的“加害者”,又是战争的“受害者”、日本工程师的家就在广岛,他既参与了二战的日本法西斯阵营,成为“施暴者”,又在广岛之战中成为“受害者”,“幸运”的是,他因为当时去打仗了,反而幸免于难:丽娃由此说道算他走运,而男人在斟酌着究竟回答“是”或者“不是”以后,终究回答了“是的”。女人也由此毫无疑问地补充了一句,她也很走运。走运的是在德国士兵死后,她只是被拉去剃了光头,并没有被夺走生命;身份的多重性赋予人物多重属性,然而不论处于何种社会身份,个体始终只是战争的牺牲品,德国士兵失去了生命,而丽娃与日本男人,即使在战争中存活了下来,人生轨迹也已经完全被这段创伤经历所改写。无休止的战争引发的是无休止的复仇:德国士兵侵略了法国人民的家园,在法国即将胜利的时候,法国人民对德国士兵实行了复仇——往花园里开了一枪;日军偷袭了美国的珍珠港,美国人对日本人展开报复——美军在广岛和长崎制造了蘑菇云。政治制度的不完善,接纳不了膨胀的欲望,从法国大革命开始的人权宣言到现在,战争、种族主义究竟给人类带来了什么?战争暂时停歇以后,遗留下的必然是无尽的虚无:关于内韦尔,所有的一切仅仅只是发生在1秒钟之内,德国士兵在花园里被人开了枪,丽娃扑倒在恋人逐渐冷却的躯体旁,一天一夜,第二天卡车装走了冰冷的尸体。内韦尔德国人的死亡展示的是“荒诞的战争正不加掩饰地笼罩在他们混为一体的身躯上”[10]。由此构成了编剧杜拉斯以及导演雷乃对这场反人道战争的强烈谴责。
结论
几只鸽子从日本女人黑色的上衣里飞出,这是影片最打动人心的画面之一。个人的身体在历史进程中被打上烙印,种族主义战争不会对任何人心慈手软。遗忘固然是个体抵御创伤记忆的重要手段,但是遗忘并不是永恒的。我们缅怀牺牲,构建创伤文化正是为了避免遗忘,避免重蹈覆辙。《广岛之恋》的原文原名为“Нirоshimа mоn аmоur”,片名直译为“广岛,我的爱”,影片看似是写广岛的丽娃在呼唤内韦尔的初恋,其实表达的正是导演阿兰·雷乃与编剧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呼唤,他们呼唤和平、呼唤平等、呼唤自由、呼唤民主政治,呼唤一个充满爱与鲜花的人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