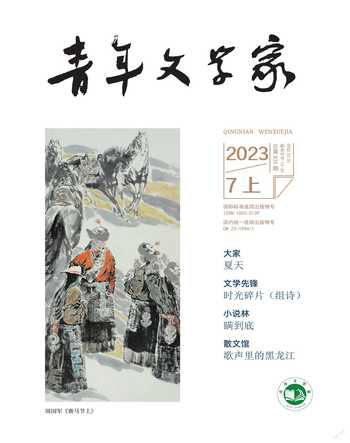童年的小卖部
纪元
小时候,我热衷于逛各种小卖部。
城里的小卖部用“逛”其实不太准确,它们一般都是楼区里某栋楼一楼临街的住户在家里阳台上开的。门面也简单:开辟一扇小窗户,窗户上用红油漆描出个“××食杂店”,旁边再嵌个黑底红心的小门铃,就可以了。这种小卖部的存在主要是为了便民,一般一个小区也就一两家,时间久了,也垄出些一家独大的骄矜来—物品?必需的倒都有;态度?不存在的,尤其是对我们这些小孩儿,像我家当时小区里37号楼那家小卖部就是如此。每当我们这些小孩儿倒腾着兴高采烈的小步子,攥着潮湿皱巴的、“处心积虑”攒出来的几毛钱,撅腚努嘴地爬上他家窗户下那高傲睥睨着我们的三级台阶,心急难耐地按几下窗旁的小红钮后,好一会儿才冒出个或惺忪或精明的人头,手里漫不经心地弹着前胸后背的泥球儿—“买啥?”居高临下的嘴巴一声吼,吓得我们抖三抖。或许,我们这些没啥大钱,又啥都想买的磨磨唧唧的小孩儿到哪个小卖部都会让卖家讨厌吧。
乡下的就不一样了。
小时候,我回乡下姥姥家时最常去的就是姥姥家对面的“老赵家小铺”。青石明瓦的墙面,敞亮!冲进店门,扑面而来的,先是店里那缕缕不绝的油、烟、酒、糖、茶、花椒、大料、瓜子、火腿—赶上饭时,还有店主家饭桌子上热气氤氲的饭包、大葱鸡蛋酱等,经长期的混合发酵所腌出的味道,这派人间烟火的图景,可太“纸醉金迷”了!再看店里那些商品呀,啧—直面过去,架子中间是一整队“军队”似的酱油、陈醋、二锅头,下面是一排小文具,抬头挺胸、不卑不亢;“军队”一侧呢,挂着些花花绿绿的香烟盒子,什么555啊、利群啊等,不过这些香烟跟隔壁“军队”一比,总显得不甚光彩;“军队”另一侧—天哪!大板巧克力和麦丽素在颔首微笑,“不老林”携手“健力宝”在手舞足蹈,摇头摆尾的“小浣熊”和“汾煌”雪梅在热泪盈眶地拥抱……“买啥呀?”店主老赵的一句笑眯眯的问候往往会及时把我们拽回现实,现实就是—囊中羞涩。不过不要紧,看看也很满足。再说,前面的橱窗里面躺着的小家伙可都是我们这些小孩儿分分钟豪爽地将之纳入麾下的橙甜玲珑的“小淘气”啦,用小勺抿着让人倍感高贵的酸甜粉啦,进嘴噼里啪啦的跳跳糖啦……我和我的小伙伴如龇牙咧嘴的饕餮,總能引来老赵或者老赵妻子并无恶意的逗弄—“叫我啥呀?答对了给你好吃的。”我们这些小聪明当然是知道“叔叔或者阿姨”这个答案了,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这样一来,“豪掷”几毛、囊内虚空的我们经常会额外得到一两块“小淘气”,或者一两袋酸甜粉,挺开心。
后来,因一些琐事,三舅跟老赵生了龃龉,还动了手,老赵夫妻俩见了我和我的小伙伴终于变得讪讪起来,连带着我们这些小孩儿也跟着愧赧了。再后来,我们便照大人的嘱咐,去了远一些的“古记”小卖部,可真是店如其名,店里的一切都古旧极了—没有橱窗,只有不知从哪辈子传下来的几列铁质货架。物品摆放也不按套路—田字格旁边放个手电筒,咪咪条附近堆卷卫生纸,二锅头一侧摞着打火机……不过,东西倒是货真价实的,店主对我们也是和善得很,便也罢了。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如今,人们已惯见于盘踞在繁华地带的商超的喜庆富态,它们迎来送往,它们纳宝招财。商超里更是明净阔气,一进门,琳琅满目的水果冷鲜、粮油调味、进口特供、电器数码……瞬间压得人眼花缭乱、晕头转向,简直忘了自己此行的初心。跟财大气粗的商超相对的,是小区里开的那些小超市,它们确实没有它们的前辈那么逼仄,但也确实比不上大商超的气吞山河,更别说打什么“价格战”了。不上不下的,倒也尴尬。
而乡下的那些,则靠着周边的老邻老户的支持,苟延着,支撑着……更多的,则是随着店主的乔迁改行、远走他乡,永远地沉默了。去年,我和母亲回姥姥家旧宅整理姥姥的遗物。到姥姥家时,屋内已是永无姥姥姥爷慈爱的呼唤与欢颜了,屋外的“老赵家小铺”也是人去屋空,早先的青石明瓦早已不复存在,唯有那剥落了墙皮的墙身伛偻而立。苍凉萧瑟的天空下,尘土不时与疾驰而过的车辆飞扬相应,间或一两声老鸹的嘶哑;不远处,是不甘示弱地林立巍耸的如职场新贵般的高楼,它们漫不经心地、年轻气盛地俯瞰着我与“老赵家小铺”的相对无言。湮芜的掩映下,“老赵家小铺”似欲向我痛陈它原本熠熠生辉的招牌、如今的灰污,它那荒草丛生的屋顶上矗着的缄默的烟囱也欲言又止地提醒我这里曾经的烟火从容。不想,门前那把锈迹斑斑的大锁,旋即无情地封锁了它们的倾诉,封锁了屋里贮存过往鲜活的琐碎,也封锁了目之所及的不合时宜。时移世易,落花流水,天上人间—一切,终是回不去了。
可回不去的,又岂是那区区“不合时宜”的小卖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