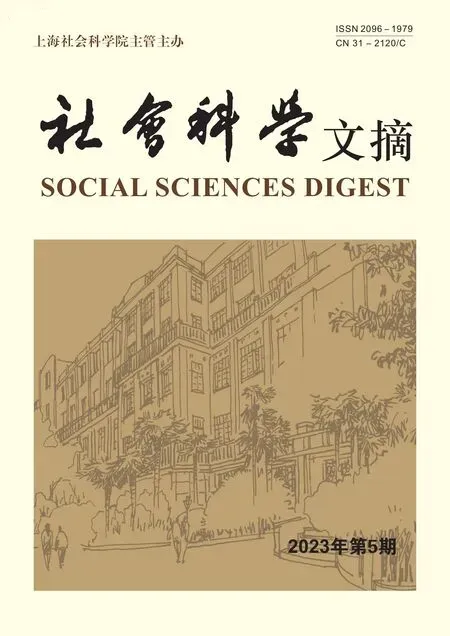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的机理、特征与实施方式
文/刘金全 郭惠萍
早在202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提出“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的重要思想,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成为我国经济政策理论、宏观调控理论的重大认识和理念突破。为此,本文对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的机理、特征和实施方式进行理论思考和全面解读。
宏观调控、跨周期的研究综述和主要观点
(一)国外政府经济政策干预的起因和效果
虽然西方国家推崇市场经济的放任自由,但是在应对经济萧条和危机过程中,设计和实施过多种经济振兴措施。西方国家经济政策干预的主要思潮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1.20世纪20年代末的大萧条,引发经济学家对于市场放任自由观念的反思,需求管理政策和凯恩斯经济学开始流行;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石油危机并导致经济滞胀,对总供给管理政策带来巨大打击;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持续萧条,催发了“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开始从“流动性陷阱”、贸易摩擦等角度提出了一系列旨在脱离“流动性陷阱”和促使经济复苏的政策主张。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不确定性冲击影响下,这些政策主张并未起到预期效果而受到质疑,引发了对宏观经济分析框架重构的思考。
2.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期,西方国家出现了“大缓和”。在“大缓和”时期,出现了低经济增长、低通货膨胀和低失业率等“三低”趋势,这被认为是发展效率高和管理成本低的时期。虽然经济运行中的“大缓和”态势被后来的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冲击所打破,但是较低经济波动环境下经济增长的显著福利提升也是熨平经济周期波动、实施逆周期和跨周期调控的重要经验依据。
3.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出现了“无增长发展”和“无效率增长”的新现象。经济学家霍尔称之为“现代衰退”。为了解释金融危机的原因,相继产生了三代金融危机模型: Krugman(1979)认为政府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与稳定的汇率政策之间的矛盾是货币危机产生的原因;Obstfeld(1996)认为,投机者与中央银行之间的博弈导致投机冲击的多重均衡,进而产生经济不确定性甚至危机;Corsetti等(2009)认为,当借款者违约、资本流动逆转以及货币贬值时,资产负债表效应将会引起银行清偿能力恶化从而导致破产。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衰退给出了解释,但无法从根本上救治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
(二)我国宏观调控和宏观经济治理的实践与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了大量宏观调控探索和实践,宏观经济管理绩效显著提升。关于宏观调控的主要认识和观点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1.我国经济增长过程出现经济长波的基本态势,实现了经济增长过程的“绝对收敛”“条件收敛”和“集团收敛”。经济增长收敛必然出现稳态的平滑迁移,进而导致收入阶段的迁移。Barro(2016)认为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能够为我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提供动力,中国有望在未来15年进入高收入水平国家行列。我们需要在长期限结构内,利用宏观调控和宏观经济治理将短期经济波动和长期经济增长结合,使宏观调控的研究视野进一步扩大,经济周期的长度进一步延伸。
2.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必须遏制经济的趋势性下滑和严防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科学稳健把握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和节奏,在“稳字当头”前提下,采取与经济周期波动态势和经济发展阶段相匹配的宏观调控模式。经济政策工具要具备刺激经济增长和“对冲”经济风险的新功能,这就要求宏观经济调控和宏观经济治理具备长期性、持续性和稳定性。
3.我国宏观调控在经济总量平衡上取得了重大进展并积累了宝贵经验。我国新发展格局的典型特征是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公平性和包容性,在创新驱动、环境保护和共同富裕等要求下,宏观调控目标将向长期调控、方向调控、平衡调控方向转化,形成政策引导高质量供给和推动需求结构升级。宏观调控模式的设计必须考虑长期变化和经济总量的协调平衡,需要强调宏观调控和宏观经济治理的期限结构问题。
我国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的机理和典型特征
跨周期调控的“奥妙”在于跨周期的“跨”字,对于“跨”字的理解和认识成为研究跨周期调控设计的关键,跨周期的“跨”字主要有三个基本含义。
“跨”的第一个含义是指经济政策制定和执行期在接续的两个经济周期上的延伸和跨越。而在跨越时需要考虑“跨”的时点、条件,以及方式等多种制约因素。宏观调控跨越的不仅仅是两个不同的经济周期,很可能也是两个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这种“跨”具有鲜明的动态属性,可能在跨越周期的同时,经济发展态势、结构特征、周期阶段都发生突变和转折。当两个经济周期衔接较平稳时,跨周期调控相对容易;反之,跨周期操作就极为困难。
“跨”的第二个含义是必然面对和经历两个经济周期之间的交叠,必然跨越经济周期收缩期和扩张期的分界,甚至面对经济周期形态的重要转变。这种“跨”是一种兼顾两个以上周期的宏观调控的动态过程:跨周期的宏观调控要兼顾经济增长的快和慢、经济增速的绝对水平和波动率、经济总量和微观个量的综合平衡、总需求管理和总供给管理的政策安排,同时要实现宏观经济“稳增长”和金融系统“防风险”的动态平衡。如果“跨”之前是刺激经济复苏,“跨”之后则是稳固经济复苏。
“跨”的第三个含义是“跨”必然要经过经济周期的分界,这就意味着跨周期期间也有“骑在”经济周期分水岭上的“静态时刻”。经济周期的分界点往往是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点,或者是经济总量关系实现再平衡的时点。这要求跨周期调控的经济政策工具具有前瞻和后顾两种属性。如果我们在“十四五”规划起始时期讨论跨周期调控,正是跨周期处于经济周期分界点上,此时跨周期调控设计更具现实意义。
我们认为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实施主要具有如下基本属性和典型特征:
(一)宏观调控跨周期调控是在逆周期调控基础上的改进和升级,是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要内涵和主要构成
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实践已经能够采取顺周期或逆周期调控模式。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阶段,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下移,经济周期处于长收缩期,在该阶段主要采取积极财政政策来促进经济恢复,宏观调控逆周期特点明显。我们发现逆周期时间要比预期时间长,将要延续和跨越到下一个经济周期,因此在逆周期的基础上形成了跨周期的思想。如今的逆周期和跨周期调控体现了在国家发展规划引导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跨周期和逆周期调控需要符合国家发展战略为导向的宏观调控主导思想,是实现国家中长期经济发展规划的主要抓手
国家发展规划是有关国家发展的长远总体计划安排,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宏观经济治理必须以国家发展战略为导向。通过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有效调动各类资源,推动落实国家重大战略。需要利用不同经济周期的特点,综合考虑经济增长的综合成本与收益,通过跨周期的长期战略部署来实现新发展格局下的高质量发展。
(三)跨周期和逆周期调控仍然要以财政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兼顾与其他经济政策形式的协调配合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控主要侧重于短期调节,避免经济增速滑出合理增长区间,而跨周期调控则注重中长期目标,进行趋势性和中长期调控。现阶段国内经济面临“三重压力”,实际利率接近“低边界”状态,此时货币政策的短期效应比较微弱,应侧重财政政策的跨周期调控。货币政策要保证资金的合理流动和发挥实际效应,财政政策则要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节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缺口并推进新发展格局下的循环畅通。
(四)跨周期和逆周期调控的具体目标出现了新变化和新要求,宏观调控方式由“点调控”向“区间调控”甚至“方向调控”转化
以往宏观调控通常将最优调控目标落实到具体的数值上,即寻求“点目标”的实现。当面对当前“三重压力”,单一最优目标无法体现宏观调控整体意图。宏观调控若是仅追求局部和短期最优很可能面临着长期内更大的困境。例如“四万亿”刺激计划使我国迅速摆脱了“次贷危机”的泥淖,但也引致后续的“三期叠加”困境。逆周期与跨周期调控的组合意味着二者不再是追求各自的最优“点目标”,而是在统一框架下寻找长期内的加权最优解。
(五)跨周期和逆周期调控将更加注重经济政策、经济政策工具的规则性和稳定性
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是指,开始设计的最优宏观调控政策,随着时间推移,仍然能够保证初始的最优性。我国宏观调控初期的目标、工具和模式,都带有明显的相机选择性,没有考虑整体效率和时间一致最优性。随着宏观调控经验的积累,我国实施时间一致性政策的能力得到了显著提高。为了实现跨周期调控的长期目标和全局目标,则必须加强宏观调控政策的规则性、持续性和稳健性。
我国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实施方式
(一)跨周期和逆周期调控要采取多种政策工具的复合方式,并创行新的经济政策工具和操作模式加以支持和辅佐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稳增长”“防通胀”“调杠杆”“防风险”等目标之间出现“多元悖论”,单一经济政策工具的宏观经济调控效果不尽人意,针对短期应急、中期区间掌控和长期跨周期目标等具体要求,采取多种政策工具组合来实施跨周期调控。十九届五中全会中明确提出“2+6”的经济政策形式,这些经济政策可以“两两组合”或者多维组合,以实现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和“双碳”目标等跨周期的经济发展要求。
(二)加强经济政策调控的目标管理、预期管理,适当采取各种名义变量和实际变量“盯住”的方式,保证跨周期调控的平稳实施
虽然我国没有给出明确的“盯住”目标和“盯住”机制,但是每年周期性的政策引导和中长期发展规划还是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有助于跨周期调控的设计和实施。在对经济重点目标“盯住”或者采取重要目标预期管理时,我们要对实际目标和名义目标、存量目标和总量目标、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等进行区分。经济政策目标“盯住”、有效预期管理和经济风险监测,都是与跨周期调控密切相关的重要措施。
(三)跨周期调控将由旧“二元目标”向新“二元目标”看齐,甚至多元目标,宏观审慎政策和具有“风险对冲”功能的政策工具成为必然选择
传统二元调控目标是:稳增长、防通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出现下移,新的“二元目标”转化为稳增长、防风险。随着结构的矛盾开始显现,宏观调控开始考虑刺激实体经济增长、稳定杠杆率、实现双碳目标等多重宏观调控目的。需要注重开发具有风险对冲功能的经济政策工具和经济政策形式。目前宏观审慎政策、绿色金融、绿色创新、区域协同发展战略和发展数字经济等都具有兼顾多元目标、统筹发展理念和控制金融风险的功能。
(四)有效精准跨周期调控设计的条件是对经济周期及其子类经济周期进行实时监测及预测,掌握经济指标周期性变化信息
跨周期调控是更高层次的宏观调控方式,对经济周期测度和监控提出了高要求,这就需要对经济周期子类进行拓展。目前子类经济周期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波长类经济周期”“并行类经济周期”与“经济政策类周期”。在全面监测上述各种子类经济周期时,还要提出宏观调控周期和经济风险周期,这两种新型的子类经济周期测度和监控可以为跨周期宏观调控提供直接参照,并给出“跨”的时空对比,以更好地测度跨周期调控进程及取得的绩效。
(五)要积极为跨周期调控提供必要条件,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平抑跨周期调控波动,降低跨周期调控政策成本
跨周期调控的重点是持续和稳定。当经济运行处于收缩或下行阶段,宏观调控模式改变将带来显著的社会福利损失。因此为了降低跨周期调控面对的波动,既要在经济周期收缩阶段保持积极政策,又要利用跨周期调控来对经济收缩和扩张阶段进行有机衔接;既要保持逆周期调控中的经济稳定增长,又要利用跨周期调控来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平稳度过本轮经济周期的收缩期。
(六)关注经济发展新格局的特征,充分发挥经济新形态的引领作用和“溢出效应”,让经济增长要素的作用实现“跨周期”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网络和数字在新经济发展格局中的重要作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都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引擎。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接续的单独经济周期已经衔接成了我国增长型的经济长周期,现在正处于经济长波中后阶段,经济增长动力出现转变,应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第四类要素”,促使这些新要素的作用“跨周期”,也是当前跨周期调控的重要导向。
跨周期调控不仅是实施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抓手和主要方式,也是连接宏观调控和宏观经济治理之间的桥梁,还是应对目前经济下行压力和经济不确定性影响的创新性举措。正是宏观调控模式中提出了跨周期设计的思路和设想,才促成了宏观调控向宏观经济治理的提升和转变,使得跨周期调控成为宏观经济治理中最为重要的创新性内容,应继续深入研究跨周期调控的主要模式和具体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