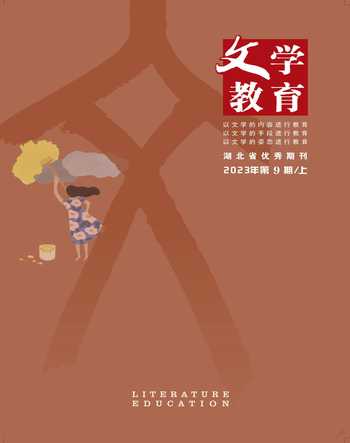论阿特伍德对尼采的变奏与共振
王梦潇
内容摘要:阿特伍德描绘了监视与操控下的同质化图景,为福柯的权力话语和尼采的价值论提供了对话的文学空间。随着时间推移,三部曲分别以不同的方法和标准试图撕破这张同质化规训的大网,阿特伍德也依次实现了其与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不同对话。《羚羊与秧鸡》看似是用尼采的“超人哲学”重估价值的文学实践,实则扭曲、背离了尼采的思想;《洪水之年》反叛了尼采对于“弱者”的定性,看到了被尼采否定的重估方式的价值;而《疯癫亚当》则试图以尼采的酒神精神打破同质化,但又走向了新的同质化。不过,在小说的结尾,艺术帮助这些秧鸡人们找到了同质化的突破口,“后启示录三部曲”与尼采思想也在这一层面实现了共振。
关键词: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后启示录三部曲 尼采 重估一切价值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后启示录三部曲”以近未来世界为背景,深入探讨了科技发展、环境灾难、基因改造等议题,对环境、科技和社会的发展进行了幻想性揭示。她对科技发展到极致后的同质化空间展开了想象,又以不同群体的视角,书写了对这种同质化状态的多形式突破。在这一维度上,阿特伍德“后启示录三部曲”与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思想内核有着共通之处:二者都呼吁人们重新审视那些确定性的道德准则,并强调个体的自主性和独立思考的重要性。因此,以“价值重估”的为切入点比较二者,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尼采和阿特伍德的思想。
而阿特伍德的三部小说分别出版于2004年、2015年和2016年,在这个过程中,她的思想也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可以说,阿特伍德的“三部曲”分别展现了她对价值重估的三种想象,那么,这种转变与尼采“价值重估”的标准究竟是逐渐趋近还是走向背离呢?二者看似契合的观念背后是否隐藏着异质的部分?在“重估价值”的标准上二者又有何种异同?
一.監视与操控下的同质化——尼采与福柯的对话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后启示录三部曲”被设定在这样的背景下:书中的世界被分隔成大院内和墙外废市。大院内戒备森严,看起来生活无忧的精英们实际上却受到“公司警”的监视和操控,失去了自由与个性。他们必须按照所谓集体的价值观念各司其职,否则就会突然死于非命。而大院外的世界科技化程度没有那么高,这里就像是贫民窟一般——杂乱无章、充满了暴力。大院内的人会将科技废品倾倒在大院外的废市之中,在这个不平等交流的过程中,大院外也深受大院内的集体价值观的影响。这共同影响大院内外的,其实就科学精神和理性主义被推到极致的一种价值观。
尼采认为,科学走向极限,可能会成为目的本身,人们会因此成为获取知识和发展科技的工具,成为技术发展大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丧失对人的本体性的关注[1],成为 “末人”的一种。他认为,科学和知识本身是不能成为最终的目的的,它只是人实现自身价值的一种手段,如果将这种手段和目的颠倒了,那么人们则不可避免地会丧失价值感和意义感,从而堕入虚无。在“后启示录三部曲”的开头,阿特伍德恰恰将尼采的这种担心落到了文本之中,展示了尼采预想的图景被推到极致的一种可能性。
大院内外,科学精神和理性主义被推到了极致,社会地位唯一的参考标准则是技术与理性知识掌握的多少。这个世界就像尼采所担忧的那样,人们把科学当作目的本身,不断追求对物的支配,最终丧失了人生本真的意义。在这里,人体不再是情感和意义的诠释,而是科学、技术和资本的从属品,它为技术服务,成为了科学与技术的奴隶。人的本能和个性在这一过程中受到了压抑,他们在精神上变得平庸而衰弱,逐渐趋于同质化。
在这种语境之下,技术和理性被看作了真理。而在尼采看来,根本不存在真理,世界的意义是需要人来置入[2]。尼采的“超人”学说和“永恒轮回”学说打碎了凝固的本质与自我,也击破了同质的时间与空间,期待让人类的生命恢复自身独特的创造性,以进入到具有差异性和丰富性的状态。巴塔耶继承了尼采对理性的批判,并提出了“异质”的概念。同质意味着主体在社会秩序的控制下,遵循统一的规范,服务于社会机器。而异质则代表着一种对社会秩序的挑战,代表着向不确定敞开。沿着巴塔耶的思想,福柯关注着监闭所、监狱、精神病院等空间。
大院内外两个空间则符合福柯所说的“权力空间化”[3]。福科认为,规训是需要封闭的空间的,玛格丽特笔下戒备森严、被公司警监控的大院内的世界正符合这样一个设定。在这样一个空间下,技术精英们在监视与操控之下按照统治者所引导他们的方式思考、生存,走向同质化的境地。如果有未被规训成功的个例,便会被公司警关注并处死。
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提出,权力是不断衍生的,它会一点点蔓延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的。阿特伍德和他的权力观一致,在三部曲中,技术和权力相互勾结形成了集权,并将同质化的技术至上的思想逐渐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技术至上的思想也从大院内逐渐渗透到大院外。
于是,在这种技术与权力共谋的规训下,科学严格分工,个人被编织到集体的技术成果演进之中,也被剥夺了自主潜能,丧失了自我的个性与生命力。而这种规训带来的同质化恰恰与尼采所提倡的酒神精神所背离。尼采高度重视的生命本能和个人独特性也在福柯所说的权力规训之下被抹杀。“后启示录三部曲”中所描述的“监视与操控下的同质化”在某种意义上为福柯与尼采的对话提供了一个文学空间。
在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后启示录三部曲”中,对这种趋于同质化的价值规训的反叛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无论是秧鸡、园丁会还是作者在作品中创造的世界,本质上都是想要撕破这张社会秩序的大网,对现有价值体系进行一种反叛与重估。而早在19世纪,哲学家尼采就曾大声地向世界呼喊过“重估一切价值”的宣言,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作品中的一些反转价值体系的方式似乎也与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的方式有相似之处。然而,这种相似真的是趋近吗?这也是我们后文要探讨的问题。
二.《羚羊与秧鸡》的价值重估——扭曲了的“超人”哲学
在第一部《羚羊与秧鸡》中,秧鸡首先发起了“价值重估”,他采用了极端的方式,试图打碎现存的价值体系。在他看来,那些被技术异化的人已经沦为了一种工具性的人,自己没有办法改变这些人固有的价值观。而只有清除这些“混沌”,制造出空白与虚空,再把世界交给自己创造的秧鸡人,人类才有希望。为了完成自己的构想,秧鸡用伪装成延长青春的药传播全球性瘟疫“红死病”,以此消除“混沌”,并在天堂制造出了全新的人类——秧鸡人。
乍一看,秧鸡的身上着实有许多尼采“超人”的气质:他有着蓬勃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他想要摧毁一切旧道德,建立全新的价值观念,他试图主宰世界上的平庸之辈,创造全新的世界。秧鸡似乎将尼采个人心灵上的价值粉碎外化于行动之中了,可事实真是如此吗?
在尼采的话语之中,超人最重要的本质是不斷超越自我,并利用人的未定型性,自由地发展自身。而秧鸡却否定了人的超越性,将人规定为确定性。他对他人和自身都彻底失去了重塑与改善的信心,将现存的人类凝固为现存价值体系的附属物。他在否定这一凝固体的同时,也否定了人超越的可能性,这是和“超人”精神完全相悖的。
此外,秧鸡将自身也看作技术异化的产物,并从一开始就做好了赴死的准备,让吉米成为唯一幸存者。在他看来,为了达成目的,同样失去希望的自己也可以被毁灭——因为肉体的陨落仅仅是作为个体的人死亡,创造出的新的版本的人才是真正的希望。殃鸡的想法实际将人物化了,他把人看作达成目标的过程而不是目的本身,这就否认了人性的独特价值。而尼采是将人看作最终价值的,二者在这一观点上构成了背反。
可见,看似“超人”的秧鸡实际上背离了尼采的超人哲学,他用科技反叛科技,用理性反叛理性,最终却丧失了个体的意义。又或许,他并未想成为“超人”,他想成为的是制造“超人”的人。尼采提出,超人是人自身创造的高于人的种类。他认为所有的生命体都能够发展出高于自身的生命,人也理应如此。现存的人是介于猿猴和超人之间的,是走向超人的中间环节。从这个角度来看,秧鸡人就像是秧鸡想要创造出来的那种高于人的生命,是秧鸡人眼中的“超人”。
尼采在《查拉图斯如是说》中描述了超人产生的过程,即“精神的三种变形”[4]。骆驼受到传统宗教束缚,轻蔑肉体,是禁欲的;狮子背离一切价值,摧毁旧世界,让精神世界变得干净。而由于狮子摧毁了一切价值,因此,孩子可以不带任何前提和条件地开始,从而拥有一个没有外界干涉的、完全由自己决定的开端。秧鸡人看起来就像是尼采精神三段论中的“孩子”阶段,他们是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长大的,因此没有受到过外界道德观念的影响,可以重新定义善与恶。
从芸芸众生到秧鸡再到秧鸡人,也像是精神三段论外化的过程。这就像是把尼采精神系谱的三个阶段外化到实体之上的一场实验。秧鸡认为现代人都已经被道德观念或是现代性荼毒得太深,处于骆驼阶段,且没有改造与超越的可能性,因此想创造出全新的“孩子”。可他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从盲从的“骆驼”阶段走到了摧毁一切的“狮子”阶段。他坚决地否定了自身的超越性,不相信自己能够在内在精神的层面摧毁旧有价值观念,再创造出独立的精神世界,从而进入孩子阶段。因此,他将这种对于精神世界的期待寄托到了自己所创造出来的全新的物种身上,并将这种新物种秧鸡人视为“新人”。
从表面上看起来,秧鸡人和尼采所说的“超人”有相似之处,是“猿人-人-超人”中比人更高级的一环。然而,尼采精神三段论中的超人经历了摧毁和重建:在“骆驼”阶段,他对现有的知识结构和价值体系都是盲从的;在狮子阶段,他产生了自主意识,对先前被动接受的知识和价值都予以批驳,重新审视并摧毁自己旧有的观念;而到了“孩子”的阶段,他则拥有了自己独立的精神世界。这是一个精神变迁的过程,也是超人不断超越自身的过程。但秧鸡人却脱离了个人精神成长的语境,他们是被秧鸡直接置于世间并进入第三个阶段的。此外,他们与人类之间的关系也是断裂的:对于人类而言,他们是无中生有的一种生命,是人类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而不是人在自我超越之后自然发展出的生命,这就与尼采的“超人哲学”产生了根本性的背离。
此外,在秧鸡的设计下,秧鸡人纯真、善良、性情温和,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头脑简单,缺乏创造力。这是否意味着,他创造出了反创造的力量呢?秧鸡将自己的价值赋予了秧鸡人,却抹杀了秧鸡人这些行为主体的个性,他想反叛同质化,但却在无意中走向了更深刻的同质化。超人是人类自我克服的崇高理想,探索人的存在中的高度和深度,是尼采创造的测试人的尺度。要成为超人,就要变得更有人性和有超越性,而殃鸡人却仿佛远离了人性。在超人哲学语境下,这是否意味着一种回归与倒退呢?
三.《洪水之年》的价值重估——从“弱者”到“强者”
《洪水之年》的故事围绕着大院外的园丁会展开,创始人亚当一号看到了极端理性的恶果以及随之而来的虚无感,于是站在了技术主导的现有价值体系的对立面,对之进行了重估与反叛,而他所建立的新的价值观念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保观念。然而,他却将环保与宗教联系在了一起,他借鉴了基督教的罪感,以约束园丁会成员的欲望。尼采认为这种罪感会压抑人的本性,导致生命力的衰弱,他肯定人的现世生活和自然的生命本能,反感基督教禁欲主义对本能欲望的拒斥,并认为禁欲的价值判断让人无法意识到本性的价值究竟何在。
不过,园丁会为人们设定这种罪感,是出于对环境的保护和延续人类生存的家园的目的。在园丁会看来,人的原罪出于追求过多的知识和权力,而人的堕落则源于从食素到食肉、从本能到理性到技术、从简单的纯粹到对昨日和未来的焦虑。他们本质上是伪装成宗教的环保组织,想要利用宗教来改变人的价值观念。因此,他们的禁欲是是生态意义上、现实意义上的。此外,尼采认为,人类为了生存给万物价值,万物才有存在的价值,这包含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这种思想也是为园丁会反对的。可见,对于园丁会的书写从生态学的角度反驳了尼采。
然而,园丁会虽然在现实世界中积极地翻转价值、改造社会,但他们其实还是相信在现实的世界之外有一个所谓“真正的世界”,他们希望通过信服存在的整体性来克服过度理性带来的虚无感。而这些相信彼岸世界的话语在尼采看来都是对现实世界的逃避与否定,暗含着无知意志。
和基督教相似,园丁会的人也对苦苦挣扎在社会底层的人民怀有同情与怜悯,并会伸出援助之手,因为他们坚信,所有的生命都有存在的理由。托比就是被园丁会救助的对象。但尼采认为,怜悯是虚无意志和反动力的联合。在他看来,这种慈悲和怜悯让人们远离了蓬勃的生命力,因为当一个人同情的时候,他就会由于痛苦的蔓延而失去力量。他还认为,正是由于有这些对他人心生怜悯的人,那些接受援助的人也失去了自主创造的力量:因为这让他们愈发渴求外部的力量,变得更加弱小。
在尼采看来,正是怜悯让那些原本因为软弱无力的东西继续存在,并指出“怜悯阻碍了淘汰律,它保存行将灭亡的东西”[5],可是,尼采将这种将弱软无力的人视为应该被淘汰的人,并将之定性为永恒的“弱者”,岂不是也犯了和“秧鸡”一样否定了人的超越性的错误?
园丁会的书写则在这一层面上反驳了尼采对同情弱者的否定,并提出“弱者”在受到怜悯者的援助后,也有可能会成长为富有生命力的“强者”。在园丁会收留的人中,虽然也有依附于强者而愈发弱小的存在,但大多数受救者即便没有从宗教中获得力量,也在这些心怀慈悲的人身上看到了希望。这在《洪水之年》中主要表现为两个女性的成长。她们最初都处于社会底层,是尼采所说的随波逐流的“弱者”,但在园丁会的救助之下,她们的价值观受到了洗礼,有了批判的能力,并一点点充盈自己的内心,从“弱者”走向了“强者”。
园丁会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教派,用以翻转价值,但环保式的宗教非但没有让他们变得软弱,反而让他们在抵抗社会中的强势者的同时,自身也居于了强者。而在这些“强者”的影响下,包括托比在内的“弱者”也逐渐成长为了“强者”。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对于园丁会的书写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尼采哲学中关于宗教与怜悯内容的反叛。
四.《疯癫亚当》的价值重估——酒神精神下新的同质化与突破
正如前文所言,在秧鸡把瘟疫带到人间之前,这个世界有两个空间:一个是大院内的高度理性化、科技化的空间,另一个是大院外混乱却有生命力的空间。而这大院外的空间就暗含着一种酒神精神,身处大院内的吉米对大院外世界的向往则显示着他对强生命力的追求。
在小说中,吉米和秧鸡这两个主人公有着明显对立的特质。秧鸡逻辑性强,心智成熟,“活在概念的世界中”[6],是理性的代表;而吉米“缺乏精确的头脑”,感情用事,理想主义,容易沉浸在感官刺激之中,是非理性的代表。他从不掩饰自己对肉体的欲望,认为肉体也有其文化形式。[7]吉米的这些特质让他在这将理性推到极致的生活中触到了价值的虚无感,而他唯一热爱的东西是艺术,并认为人类的意义就是用艺术作为注脚的。因此,在这个人文极度衰弱的时空里,吉米始终坚持把被世人看作无用的艺术当作目标来追寻。
由此可见,酒神精神在第一部吉米和秧鸡的对比之中已经初见端倪。把吉米和秧鸡人留在一起,也就意味着将人类的希望放在了艺术和酒神精神之中。然而,狂欢、迷醉、非理性、生命力、本能的放纵等等这些酒神精神的特质在秧鸡人被放出“天塘”后才得到了真正的释放,对这些新新人类酒神精神的书写在《疯癫亚当》中被推到了极致。
首先,对秧鸡人而言,本能的放纵对他们而言非但不是非道德的,反而是自然生命力的彰显。在秧鸡人中,性行为不再是需要私下进行的活动,反倒更像是轻松的体育游戏。即便他们对着一丝不挂的裸体,也不会感到扭害羞。尼采曾提出肉体才是生命的最真实的显现,只是被传统理性思维所掩盖,因此,肉体在反抗理性上起到重要作用。秧雞人毫不掩饰地彰显肉体便构成了对人类道德理性的反叛。
此外,秧鸡人们喜欢用音乐表达自己,用唱歌的方式去消解、稀释痛苦。在歌唱的过程中,秧鸡人们将个体的生命融入到了整体的生命之中,克服了恐惧和痛苦的情绪。他们用一种狂欢化的、非理性的、热烈迷醉的方式感受着狄俄尼索斯式的狂喜,在原始的快乐和狂喜中通向永恒。而这恰恰就是尼采的“酒神精神”最主要的特质之一。
然而,在这种酒神精神之下,身为反叛同质化产物的秧鸡人却仿佛走向了一种新的同质化——他们在用歌声消解一切的过程中,个性好似也被消解掉了。秧鸡人构成了一个平和理想的世界:他们是素食者,也是和平主义者,因此他们与自然万物均能和谐相处。可与此同时,秧鸡为了让他们保持在孩子的阶段,也试图抹除它们身上的想象、情感、需求、理性和创造力,而这些正是人之为人的真正特质。
不过,在故事的结尾,当秧鸡人脱离了秧鸡的设定时,这种同质化又发生了新的转机。这些秧鸡人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进行了自我的启蒙,他们试图突破这新的同质化,成为树立全新价值的“孩子”。当秧鸡人开始对幸存者告诉他们的事情产生质疑之时,也就是秧鸡人展开价值重估之时。就这样,秧鸡人开始构建属于他们自身的新的价值体系而这摧毁重建的能力与他们“听故事”这一行为不无关系。
在秧鸡的设定中,秧鸡人没有宗教观念,也不需要读书写字。然而,这些秧鸡人非常喜欢听故事,在托比给“秧鸡人”讲故事的过程中,秧鸡人甚至产生了宗教崇拜般的心态。后来,他们学会了写字,进而学会了自己去记录、创造故事。秧鸡人黑胡子接下了托比记录写作的重任,开始书写属于秧鸡人的故事。
尼采曾高度肯定虚构与创造,并指出创造性的“本能比一切价值感更强大。”[8]因为艺术有益于人的感受力的提升,能够张扬人的生命意志。这些秧鸡人便是通过创造成为了真正的“人”。它们开启了艺术之门,试图将自身充沛的能量转化创造力,以创造出永不枯竭的歌声与故事。可见,在小说的最后,玛格丽特也将希望留给了隽永的艺术。她期待着秧鸡人用审美与艺术重新张扬蓬勃的生命力,与同质化悲剧抗争。
总之,实现价值的翻转是“后启示录三部曲”的主线之一,也是尼采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在“重估一切价值”的问题上形成了对话与冲突。“三部曲”在为尼采哲学提供文学实践样本的表象之下,实则处处暗含着对尼采的反叛和挑战;尼采与同质化抗争的方式在玛格丽特笔下也成为了消解个性、走向新的同质化的助推剂。看似契合的文学文本和哲学话语实际上却走向了对立面,这构成了二者之间独特的张力。不过,在变奏之余,于艺术的创造性上他们的确实现了同频共振,阿特伍德和尼采共同将希望留给了那片能不断唤起更多生命意识的艺术天地。
参考文献
[1](德)尼采著;杨恒达译.尼采全集(第2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458.
[2](德)尼采著;维茨巴赫编;林笳译. 重估一切价值(上、下)[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764
[3](法)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215.
[4](德)尼采著;孙周兴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22.
[5](德)尼采(FriedrichNietzsche)著;梁锡江译.道德的谱系[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79.
[6](加)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著;韦清琦,袁霞译.羚羊与秧鸡[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158.
[7]同[8],第97页。
[8]同[2],第7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