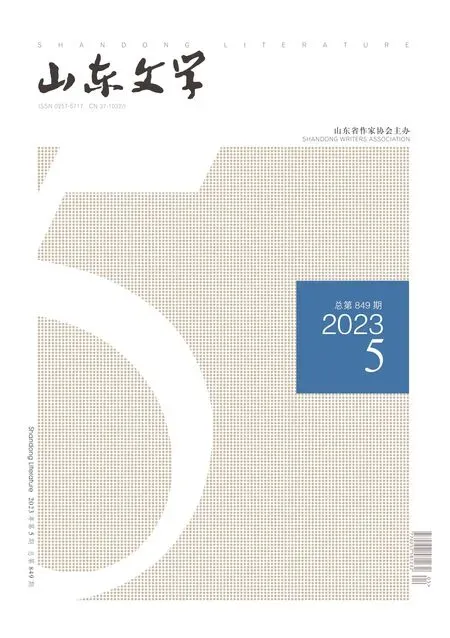随笔二题
陈 光
盐工情
盐,人类每天必须食用的东西,官称食盐,俗称咸盐,民族地区叫盐巴。所谓盐工,当然就是生产食盐的工人。许多地方把盐场里的人统称为盐民。
在我的老家寿光县羊口镇,镇上的人一直看不起盐场的人,他们把制盐叫“晒滩”,把盐工叫“滩汉”,把我们这些盐工的孩子叫“滩汉料子”。我的父亲是老盐工,我自然就是“小滩汉料子”了。在羊口镇上学的时候,我和同学走在路上,时常会看到人们投来鄙视的目光,经常会听到有人指着我们叫“滩汉料子”。我们不做声,也不生气,我们并没有觉得做盐工不好,也没有觉得镇上的人比我们高多少。
如果说水是生命之源,那么盐就是文明之泉,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盐,凭借其独特的美味,吸引着人类聚集在一起,形成了最早的城邑。多少部族、城邦和国家,因盐而战,因盐而兴,也因盐而亡。在中国古代社会许多朝代,食盐成为盐民的生计、商人的钱袋、官府的金库。食盐营销的管理,自然是历朝政府的重要政务之所在。盐粒虽小,盐法很大。细碎的盐粒,严峻的法律,曾经有人因为从盐场私带了一粒盐而被盐官杖杀,古代盐法之严峻,远不是现代人所能想象。
山东省寿光县是齐鲁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制盐历史悠久。寿光北部的渤海边上有四个大盐场,面积上千平方公里,是全国最大的海盐和井盐生产基地。从12 岁起,我就生活生长在这里。从14岁开始,我学做盐工。五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当年的生活场景,仍然历历在目。那是刻在我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记忆,是痛苦的回忆,也是幸福的回忆。
往事并不如烟。父亲从上世纪60 年代就在盐场工作,是老盐工了。母亲带着我们三兄妹长期生活在农村,我是在60 年代末跟随父亲到了盐场。父亲工作的单位是卫东盐场老八队。卫东盐场五十年代建场时叫寿光县合作盐场,是县属大集体企业,后改名叫卫东盐场。
盐场在羊口镇周边,北面是小清河,东面是大海,自东向西共十个大队,绵延30公里。之所以叫老八队,是因为地处老场区,后来场里又建了新场区,不再称队,叫工区。老八队规模很小,孤零零的两排砖瓦房躺在盐碱滩上,周边十几里荒无人烟,除了职工宿舍和一间食堂,其他什么都没有,买一根针一轴线也要跑十几里路。
盐工几乎全部是“单身”,家属都在农村,是农民。队里只有一户“双职工”,就是夫妻都是盐工。男的姓周,他家女人做炊事员,儿子叫周义,与我一般大。父亲和十几个工友住一间大宿舍,每人一张单人床。在父亲的床边塞了一张小床,就是我的住处了。没有桌椅,也没有橱子,我和父亲有点杂七杂八的东西,都堆在床底下。
白天,父亲和工友们下滩干活,我和周义结伴去场里的职工子弟学校上学。学校在场部,步行要一个多小时。我们每天早起吃饭,6 点出发。书包里放一个窝头、一块咸菜,中午在教室里凉着啃,这就是午饭。下午放学回来,趴在床上完成作业,然后与大人们一起吃晚饭。
叔叔们用废旧材料制作的小饭桌摆在宿舍中间,每人一个小板凳或者小马扎,有的干脆在地上蹲着。饭菜极简单,食堂做什么吃什么,一样的馒头或窝头,一样的咸菜,一样的粥,没有任何选择。偶尔有人回家探亲捎回来一点家乡特产,或者有人去场部办事买回来一包点心、一瓶酒,大家一起分享,这就是全屋最高兴的时候了。
宿舍里没有电话,没有报纸,没有书籍,没有收音机,没有电视。晚饭之后,各人在自己的床上抽烟、想心事,很少有人说话,然后就是静静地休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盐场的夜很长。清晨四五点钟醒来,躺在被窝儿里不动,望着渐渐发白的窗户发呆。我不知道别人家的孩子是不是也这样生活,更不知道外边的世界是不是很精彩。老八队,让我学会了保持沉默、不怕孤独、忍受寂寞。
盐场的星期天不休息。盐工每人每月四天假,攒起来一起休,为的是便于盐工回乡探亲。也可以把自己的假期借给或者送给别人。谁家里有了大事,可以借用别人的假期。盐工们都很团结,也很义气,这种事经常发生。每到周末,我便顶替父亲下滩干活,换下父亲洗洗衣裳,稍作休息。周义则是替他母亲。这是盐场不成文的规矩,允许孩子星期天替大人干活,相当于一种福利。我那时年纪还小,个子很矮,力气不足,充其量算个半劳力,叔叔们便让我干轻活。我很过意不去,觉得这是占了别人的便宜,便早出晚归,尽力去干,多做些打水扫地的事,而且认真学习手艺,很快掌握了许多盐业生产必需的技术。
让海水或井水变成盐,是最神奇的过程。最早的制盐方法是煮盐,早在神农氏时代,寿光北部的夙沙氏部落首领,用陶钵装满海水,放到火上煮。海水煮干后,钵壁上出现的白色粉末,就是最早的食盐,煮食物时加入,感觉微咸,使人兴奋,让人浑身充满力量。夙沙氏“煮海为盐”,开创了华夏制盐历史之先河,被称为盐业之鼻祖,史称盐宗,备受推崇。到清朝乾隆年间,制盐方式演变成了“晒盐”,这种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
所谓“晒盐”,就是选择大片平坦的沿海滩涂建设盐场,也称盐田。即在海边用挖土筑堰的方式,建设一大片盐池子,盐池分成两部分:蒸发池和结晶池。蒸发池很大很深,每个面积几千平方,蓄水上千立方米。结晶池稍小,也比较浅。池堰和池底用厚厚的红泥抹平,确保海水不漏。
生产过程是先将海水引入蒸发池,通过日晒蒸发水分,让海水的含盐量不断增加,变成“卤水”。衡量卤水浓度的标准是“波美度”,测量浓度的工具是“重表”。卤水浓度达到25 度,就成为饱和卤,继续蒸发,盐就会从水中析出。生产过程中,把即将饱和的卤水放入结晶池,继续日晒,不用几天,食盐就会在水底迅速结晶,迎着阳光,闪闪发亮,那就是盐粒。先是薄薄的一层,眼看着一天天变厚,会达到十几厘米。这时候,用特制工具将其捞出,得到的就是原盐了。
国有企业羊口盐场用的就是这种工艺,年产量达到数百万吨。卫东盐场、岔河盐场、菜央子盐场用的则是井水制盐。就是先在盐碱滩上打井,然后用风车和水车把水提到地面,后面的工艺则完全相同。相比而言,地下卤水浓度更高,生产的原盐也更洁净。
盐场每年的生产分为“春晒”和“秋晒”两季。每年三到五月前后是“春晒”,是盐业生产的黄金季节。这三四个月,风和日丽,阳光充足,气温升高,而且少雨,最适合盐业生产。如果到五月底完不成全年生产任务,这一年的生产计划要想顺利完成,就很困难了。因为“秋晒”只有九、十两个月,温度原因,产量很低。因此,对于春天的生产旺季,场里高度重视,抓得很紧。层层召开动员大会,人人都要发言表态,一切行动听指挥,苦干巧干拼命干,不休假,不歇班,多为国家做贡献。全场上下,到处红旗招展,标语口号一片,广播喇叭反复播放厂长的动员讲话和职工代表的发言,一片大干快上的局面。
每天凌晨三到五点,是盐工最紧张最忙碌的时间。因为一天24 小时,只有这个时段没有太阳,气温最低,卤水不蒸发,就选准这个时间收盐。第一道工序是“起盐”,就是用特制的大耙子,把水底的原盐搂起来。一耙子盐足足二三百斤重,双手紧紧抓住耙柄,用尽全力拽着耙子往后挪,把盐搂成一道道岭。我的力气不足,只靠两手拉不动,就在耙子上拴一条绳子,挂在肩上,用全身的力气拽。
第二道工序是“推盐”,用木锨把盐装上盐场特有的独轮小推车,送到几百米远的滩头空地上。刚从水里捞出来装上车的盐,水还在哗哗地流,人在水中干,车在水中行。推车上池堰的时候,要弯下腰,用力推,否则上不去。过水沟的时候,车要通过不到一尺宽的“独板桥”,一不小心就会人仰车翻。
第三道工序是“赶浑”,就是把起盐之后的池子里的浑水赶出去,把清水留下,这是盐工最拿手的绝活儿,我干得很漂亮。清理后池子里留下来的水叫老卤,再放上一部分新的卤水,五点多钟太阳出来,马上开始蒸发,进入一个新的生产流程。这个安排的确很科学,一点儿也不浪费时间和空间。
第四道工序是“打坨”,就是把收上来的盐堆成一个个圆圆的盐坨,每个坨子五六米高,大致有二三十吨。盐坨要用草苫子盖起来,避免淋雨化掉。几天后,县盐务局会来收购拉走。说实话,这盐工的活儿,既需要力气,也需要技术,一般人还真的干不来。
晒盐旺季最怕老天下雨,因为雨水落入盐池,卤水就会稀释,已经结晶的盐粒也会化掉,前面几十天的努力就会前功尽弃,池堰和上下水沟渠被淡水浸泡也会坍塌。场部有人专门负责天气预报,一有情况,大喇叭立即广播。每到这时候,盐工们会毫不犹豫,一跃而起,冲进盐滩,不分白天黑夜“连轴转”,那叫“抢盐”。不难理解,辛辛苦苦大半年,不就是为了这点盐吗?在盐工眼里,盐场是他们的家,盐就是他们的命。
一连三四个月,盐工们每天都是这样干。没有人请假,没有人叫苦,没有人喊累,没有人抱怨,大家都认为这样干是天经地义。没有加班费,没有奖金,没有补贴,没有会餐,谁也不知道场里有这种福利待遇。每到饭时,仍然是馒头、窝头、咸菜、稀饭,静静地吃完,倒头便睡。只有他们包括我自己,知道身上有多累。
我不知道人们在吃到咸盐的时候,知不知道每一个盐粒都来之不易。我只知道,盐工,是天下最苦最累的工种。盐工,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是世上最高尚的人。人这一生,只要做过盐工,就没有吃不了的苦,就没有受不了的累,就没有干不好的事儿,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一条公路穿过老八队,一头连着镇上,一头蜿蜒伸向远方,听说能到县城。我哪儿也没有去过,除了小时候生活过的农村,再熟悉的就是盐场,就是这老八队了。我经常向着公路眺望,经常看着偶尔驶过的汽车遐想,我什么时候能够走出这老八队呢?
14 岁那年,我走出了老八队,到镇上读高中。父亲调到场部工作,周末也不用再替父亲干活。但是,就从这时起,我成了地地道道的“准盐工”。每到学校放假,我和同学们一天也不耽搁,立马到场里新建的工区“打零工”。住的是二十多人一间的大通铺,铺盖卷儿要自己背着去,吃的仍然是窝头和咸菜,干的活比“抢盐”还要重。在老盐工的带领下,我们每天早出晚归,要干十几个小时的活,很苦,很累,但是我打心眼儿里高兴,因为我终于可以用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了!第一年的工资是每天一块四毛八,第二年涨到一块七毛六,偶尔得到包工活,一天可以赚三四块钱。这样一年下来,靠假期打零工就可以赚到二百多元钱,我自己一年的吃穿基本就够用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对此坚信不疑。能够从十几岁开始就为父母、为家庭做点贡献,是我一生的自豪。
盐场的景色是美丽的。所有的盐场,总是与大海相伴。站在高处放眼望去,一边是湛蓝的大海,烟波浩渺,一望无际。一边是无边的盐田,波光粼粼,银光闪烁。海水、盐田、天空合为一体,分不清是水还是天。清晨,旭日从海面喷薄而出,将碧波荡漾的海水和盐田染得金碧辉煌,清爽的潮湿的带着淡淡腥味的风,吹拂着人的头发、面颊和身体的每一处,让人心旷神怡。傍晚,金色晚霞映照在大海和盐田上,让人立即想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这样精美的诗句。盐、盐田、盐场、盐工,拥有的是一种精神、一种生命,沟通了大海与人世,串联起古往与今来。面向大海和盐田,就像人的心灵面向着无限辽远。
后来,终于,我走出了盐场。沿着老八队门前的那条公路,我走进了县城,走进了省城,走到了很远。但是,我永远铭记寿光北部渤海湾畔那抚育我成长的盐场和盐工,不管多么繁忙,每年必须回去看看。斗转星移,盐场已经今非昔比,早已机械化电气化了,老八队的大屋早已不见,盐工们已经住上了楼房,生产生活条件大为改善。
我爱大海,爱它那波涛汹涌的气势;我爱盐场,爱它那无边无际的胸怀;我爱盐工,爱他们永不停息的劳作。是那些淳朴的盐工,给了我第一份工作,教会了我怎样对待生命,怎样对待生活,怎样对待艰难和困苦。教会了我怎样做人,怎样干事,怎样为官。生命里有幸做几年盐工,是一生的幸运。
有付出就会得到拥有,有执着就会收获喜悦,有奉献就会拥有力量,有真情就会找到相濡以沫,有梦想就会有不倦的追求。
杏村情
时光如水,岁月如歌。回首一生中经历的风风雨雨,总有一些特殊的片段令人难以忘怀。记忆的闸门在夜阑人静时不经意地打开,那些生命中难忘的时刻,便如彩蝶翩翩而至,而最清晰绚烂的旋律和画面,便是四十五年前那葱茏的知青岁月。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各地一千多万名城镇青年,响应国家号召,远离父母亲人,经历了十年之久的上山下乡运动。他们栉风沐雨,把汗水洒在了广袤的田野上,甚至把生命留在了那片苍茫的土地上。他们的名字叫知识青年。“知青”这个名词,对于当今年轻人或许仅仅是一段朦胧的历史,但对于亲身经历者来说,却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山东省寿光市有个纪台乡,乡里有个村叫杏村,向北30 里到县城,向东3 里到乡驻地。村西有条河叫弥河,是寿光市的母亲河,发源于临朐,途经青州,从杏村这里进入寿光,经过县城一路向北最后注入渤海。弥河从杏村的西面和北面绕过,河边有一块二百多亩的杏树林,每年阳春三月,河水潺潺流淌,满园杏花盛开,正是“一陂春水绕花身,花影妖娆各占春”“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景色极美,杏村因此而得名。
1974 年春天我高中毕业,便响应号召,主动报名下乡当了一名知青,来到了杏村。
杏村知青组共15 人,因为曾在一个学校上学,彼此并不陌生。村里非常重视,把大队部院里的几间房子腾出来当知青宿舍,每间住三人,条件很不错。另有一间做伙房,盘了一个大锅台,放了几张小地桌,每人一个小板凳,村妇女主任桂香大姐暂时给我们做饭。
没有客套,“开拳就打”,进村第二天就下地干活。正值“三夏”大忙,我们和村里的青壮劳力一起下地割麦。生产队长亲自示范,我们认真学习,很快也就上手,只是速度慢一些。割麦需要保持一个姿势:90 度弯腰,干了一会儿腰就疼得受不了。我只得左腿蹲着,右腿跪在地上,一边挥镰收割,一边拖着腿往前挪。生产队长告诉我们:“必须经过这个过程,三天以后就不疼了。”我们信以为真,不过三天以后真的好多了。
麦收是一年中最紧张的季节。辛辛苦苦8 个月长成的小麦,如果不能在一周内抢收到手,一旦来了大雨或冰雹,就会前功尽弃。所以,全村上下齐动员,男女老少齐上阵,田地里人影流动,所有人来去匆匆,连续十几天连轴转, 累得头昏脑涨、腰酸背痛,手心磨出了水泡,脸上晒得爆了皮,但是我们咬着牙坚持下来。
好戏开台,一幕一幕拉开。麦收之后就是秋季作物管理,一连几天给玉米追肥。两人一组,一人用镢头顺着玉米根部刨沟,一人用筐子装着土杂肥撒到沟里,再用脚踩踩把土埋上。生产队长自豪地说:“浇上水,过半月刨开看看,这玉米根会长的和蓑衣一样,不想高产都不行。”我们听了觉得很长知识。
这是简单劳动,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用力气不是很多,但那个天热得实在让人受不了。七月的大地像蒸笼,空中没有一丝风,火辣辣的太阳硬是要将人晒晕才肯罢休。玉米长得比人高,有风也刮不进去。不出20分钟,浑身上下衣服湿得呱呱透,脱下来能拧出水。只能光着膀子干,不一会儿,胳膊让玉米叶子划出一道道小口,被和着粪土的汗水一浸,生疼生疼,着实难受。
进入九月,三秋生产开始,最考验人的是推车送肥。玉米收获之后接着种植冬小麦。为了保证来年小麦丰产丰收,每亩要施足40车土杂肥作基肥。土杂肥先用牛拉大板车运到地头,再靠人力用小推车运进田里,均匀撒开,然后耕翻,确保9 月底小麦播种完毕。小推车运肥一个来回平均一里地,个人自己装卸,每人每天的定额是50 车,必须完成。推小车是技术活,要保持平衡,一不小心就侧翻。刚收获的农田土很软,第一车要两人合伙,一人用绳子在前面用力拉,一人在后面使劲推,先压出一道沟来,再后面就可以一个人推着小车顺着这道沟往前拱。这活儿着实不轻,村里的年轻人都叫苦。
清晨,知青组的男青年一人一辆小推车,顶着满天星星上工。白露已过,一阵凉风吹来,让人禁不住打个寒战。田野的黎明静悄悄,偶尔听见鸡鸣、狗吠和老牛的吼声。到了地头,挽起袖子就干,装满车、推进田,目测好距离,均匀排列。整整一天,就这样马不停蹄地干。早上和中午两顿饭在地头上吃,大饼咸菜绿豆汤,吃着吃着就不自觉地躺在地上,一闭眼就睡过去了,劳动强度很大,确实太累。傍晚,披着星光回家,浑身就像散了架,吃完饭赶紧上床睡觉,第二天还得早起。
“三秋”生产时间长,活很多。抢收玉米、运送肥料、耕翻土地、按时播种小麦,还要割豆子、刨花生、收地瓜、晒瓜干。为了保证白天干集体的活儿,队里都是每天傍黑分地瓜,不管早晚都要当晚切成片,摊在地上晒瓜干。碰上天好,三天可以晒干。如果这中间被雨淋了,就会发霉变绿,吃起来很苦。有一天凌晨两点突然下雨,我们立即起床,顾不上穿雨衣,冲到地里抢收尚未晒干的地瓜干。等到把瓜干装进麻袋运回家,人人都成了“落汤鸡”。我们一点儿也不觉得辛苦,因为这是自己的口粮。一连40 多天,每天都是这样连轴转。的确很累,好在一天三顿能吃饱饭,加上年轻力壮,一觉醒来,又是一条好汉!
“三秋”生产告一段落,农田基本建设接着上马,任务是参加公社组织的挖河工程。大队长亲自带队,男知青全部参加,扎了两个帐篷,用麦草打成地铺,在帐篷外面支锅做饭,吃住在工地。活儿是三人一组一辆推车,先把河底的泥土装上车,然后一人推,两人拉,运到河坝上。刚开始比较好干,因为河道还浅。往后越挖越深,而且见水,泥土变成了淤泥,就比较麻烦。十月下旬,天气已经很冷。我们上身穿着棉袄,腰里扎着麻绳,下身穿着裤衩,站在泥水里干活。河水冰冷刺骨,淤泥又滑又软,站也站不稳,一不小心滑倒,立即变成个泥人。没有工程机械,劳动效率很低,但想不出别的办法,只能这样拼命。
村支书来工地慰问,带来一头杀好的猪,一连两天猪肉炖白菜,大家像过年一样高兴。工地上白天红旗招展,晚上灯火一片,公社指挥部的大喇叭里不停地播放工程进度和好人好事,声音很大,七八里路外都能听见,倒是满热闹。半个月后,工程顺利完工,我们“打道回府”。
劳动锻炼是知青生活不变的主题,值得回忆的场景太多。一个矮小瘦弱的身子,干过了农村一年四季几乎所有的活儿,时间一长,还真把人给煅炼出来了。大活小活能伸出手,牛栏猪圈能下去脚,田边地头能睡着觉,粪坑厕所旁能吃下饭,往日的知青已经成了地道的农民。辛勤的汗水和泪水,让我们这些刚走出校门的青年,亲近了大地母亲,接触了农村农民,感悟了生活真谛,磨砺了身心意志,增长了智慧才干,收获了欢欣喜悦。一段苦乐年华,绘就了知识青年艰苦创业的青春底色。入冬之后,队里让知青们分开干些杂活儿。有人去油坊帮工,有人到牛棚铡草,我和大部分知青去果园帮着剪枝、除草、追肥。这些活儿相对轻松,收工也比较早。傍晚,站在弥河岸边,看看脚下的土地,望望身后的村庄,看着那袅袅升起的炊烟,望着落日缓缓西下,心中升起一种莫名的惆怅。我的一生真的就要在这个小村庄度过,没有别的选择、没有别的机会吗?遥望远方,想起了家,一年没回家看看了,父亲母亲身体好吗?弟弟妹妹学习怎么样?不知不觉间,心中一酸,眼中竟然流下两行泪。
知青组的生活是清苦的,但是充满欢乐。下乡第一年,我们每人分到六百斤玉米和地瓜干、一百斤小麦,这样每人每月的口粮就有60 斤。女知青饭量小,男女通算,保证能够吃饱,这在当时已经很不容易。须知我们上高中时每月只有27 斤粮食定量,每天都得掐着肚子,真吃不饱。现在,玉米面窝头儿管够,有时还能改善生活吃白面馒头,已经很幸福了!
过中秋节的时候,我们下决心好好改善一次生活,买了5 斤猪肉,炖了一大锅白菜,还去供销社用地瓜干换了5 斤白酒,请来党支部书记、大队会计和带班人吕爷爷一起过节。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喝酒,那一天,我们全组的人都醉了。
在生产队的账上,知青组是一个户。真实生活中,我们是15 人组成的一个大家庭,非常团结和睦。生活上互帮互助,亲如兄弟姊妹。劳动中,男知青尽量干重活、多干点,让女知青干轻活,少受累。下雨天,我们一起“剥玉米”,或者组织集体学习。劳动之余,也一起谈谈人生、未来和理想。高兴时就聚在一起吹笛子、拉二胡、吹口琴,扯着破锣嗓子吼吼歌,那声音虽然很不着调,但至今时常在我的耳边回响,挥之不去,历久弥新。有一次,我在干活时被机器伤了脚,大家七手八脚把我抬上小推车,送到公社医院,包扎好了又推回来,第二天又用自行车把我驮到县医院做手术。女知青吴秋敏因为干活淋雨得了感冒,后来发展成白血病,住在益都县医院,我们全组知青一个不少坐着火车去给她献血。纯洁简单的友情薪火,温暖了知青生活的点点滴滴、日日夜夜,伴随我们走过那段难忘的岁月。
村里给知青组派了“带班人”,是党支部委员吕凡俊,老人六十岁了,我们都喊他“爷爷”。爷爷每天从早到晚蹲在知青组,啥都和我们一起干。爷爷是农业的“老把式”,像“扶耧播种”这样的技术活,没有他亲手示范还真学不会。爷爷协调村里给知青组划了一亩菜地,天天蹲在那里教我们种菜。秋天,爷爷帮我们买来大缸,一次腌了满满4 大缸咸菜,他笑眯眯地说:“这下好了,够吃一年了!”爷爷还帮我们抓来几只猪崽,让我们自己养着,长大了杀猪吃肉,改善生活。爷爷是我们知青组最最亲爱的人,45 年过去,我至今清清楚楚地记得他那慈善的面容。
最难忘的是杏村那淳朴的百姓。刚来时,他们用异样的目光看我们,好像我们是来抢他们的粮食一样。斗转星移,时光流逝,短短一年时间,我们用实际行动让他们刮目相看。我们和村里的青年一起劳动,不管力气活还是技术活,一点儿也不落后,这一点最让他们服气。
我们也是一年四季吃窝头,啃咸菜,没有一点特殊待遇。夏天我们男知青也光膀子、剃光头,这样利索!我们也穿打了补丁的衣服,不是装穷,而是的确没钱买新的。下乡时母亲给我带了两条裤子,很快都磨破了。我便把一条剪了,选好点的布剪下来,补到另一条裤子上去,这条裤子上就先后补了14个补丁,有的地方补了三层,我穿着一点也不觉得难为情。我们和团支部的青年一起出黑板报,晚上也会和村里的青年一起跑七八里路去邻村看电影。谁家盖房子,我们就去搭把手。谁家娶媳妇,我们也去闹洞房。村里的人也经常到知青组去说话拉呱,我们会给老乡们写生画像、教他们打拳。
我的脚受伤时,几个邻居大妈听到消息,赶紧跑到野外采来“艾草”,用这种中药煮水煮鸡蛋,给我送来20 多个,看着我吃下去,她们说吃了这鸡蛋,伤口保证不会感染,感动得我直掉泪,因为我打小也没一次吃过这么多鸡蛋。在和乡亲们近距离的相处中,我们深刻地了解了农民。农民的苦自不必说,那纯朴自然、忠厚老实、待人热情、吃苦耐劳的精神特别令人钦佩。他们祖祖辈辈在黄土地上耕耘劳作,默默无闻,无怨无悔。看着这些朝夕相处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我曾多次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我是谁?我家祖祖辈辈也是农民,只是到了父母亲这一辈因为上了学才当了工人,我才成了知青。一代又一代的农村青年安心在这黄土地上终生劳作,我为什么不能在这杏村当一辈子农民?
转眼间,下乡后的第一个春节到了,生产队搞年终决算。我们知青组的人全部评了最高工分。村里这一年丰收,每个工日值三毛二分钱。除了分到手的700 斤粮食,我分了107 块钱,这就是我劳动一年的全部报酬。春节回家,我把钱交给了母亲。母亲收下100 块钱,把零头儿给了我。7 块钱,是我新一年的零花钱。冬去春来,又是一年杏花开。知青组的人全部到大队科技队干活。科技队有40亩地,有自己的机井和排灌设备,各种基础设施和农机具比较齐全。在乡农机站的指导和老科技队员的带领下,我们边学习,边实践,搞了“泰山系列”小麦良种繁育和“掖单系列”玉米密植高产实验,取得了丰硕成果。杏村人过去种玉米,每亩就是3000 棵、单产600 斤,这是当时传统的种植模式,我们依据“掖单系列”玉米上冲型的特点,试验每亩种植5000 株,单产超过了1000 斤,在当地引起了轰动。
这一年,第二批知青又来到了杏村。在他们面前,我们成了老知青。知青大院已经建成,新房子很宽敞,生活条件大为改善。这一年,根据国家政策,老知青陆续离开农村。有的上了技工学校,有的被招工进了工厂、学校、医院、商店。我没有走,决心扎根农村60 年,是真心实意的。又是一个春天,杏花依然绽放,我最后一个离开杏村知青组。本来是不想走的,很想和新知青这些弟弟妹妹做个伴。但领导反复动员,村里的乡亲也好言相劝,坚持几个月,最后还是离开。我走了,弟弟来了,他是第三批下乡知青。住的还是我那间屋,睡的还是我那张床。人都是有感情的。离开杏村,恋恋不舍。广阔天地上的阳光和风雨,让我从一个青涩的学生娃变成了结结实实的农村青年。杏村给了我一生最难忘、也是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淬火和锤炼,就是凤凰涅槃。
时光荏苒,往事如烟。历史,对记录者来说只是叙述和文字,而对于亲历者而言,却是刻骨铭心的体验和记忆。